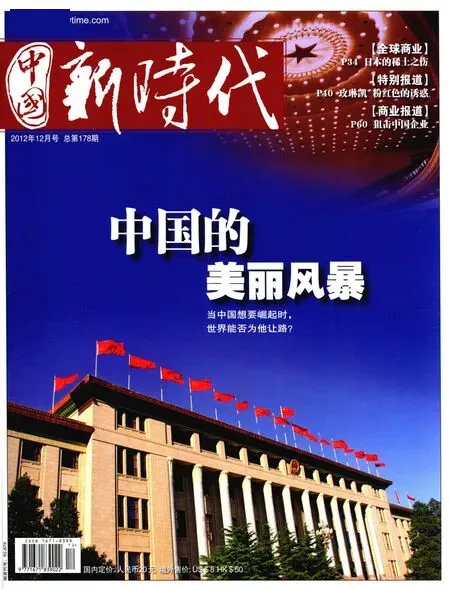學術研究屬于“說”和“想”的范疇——經濟學家左大培講述治學心得
開放社會學術研究的敵人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整齊劃一、非此即彼的排他與專斷
追求經典 不做“亞流”
我是1982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1988年博士畢業。當時我,還有樊綱,都是朱紹文老師的學生。朱老師為人治學都是我們的榜樣。
朱老師為人耿直,講真話,不貪錢,也不巴結、諂媚官員。我記得他說過這樣一件事情,建國后他到國家機關去,看到以前都是西裝革履的人改穿中山裝了,他很不以為然,覺得沒有必要從這個方面顯示自己的進步。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和他愛講真話有關。和現在的有些導師不同,朱老師從來不讓學生替他“打工”,或者是侵占學生的研究成果。我和樊綱早期的一些文章經朱老師推薦發表,但是他從來不署名。
朱老師治學非常嚴謹。他的名言是“追求經典,不做‘亞流’”,要求做出高水平的研究來,而不是隨便做出一些“次品”就拿去發表。他對學生的要求就是畢業論文一定要做好,在校期間發不發文章無所謂,但是發了不好的文章就要挨罵。我碩士期間發表過兩篇文章,是關于系統論的。朱老師看了以后,狠狠地訓了我一通。他問我發表的是什么東西,訓誡我以后不要再做這種華而不實、不是正道的研究,而是要專心致志地夯實學術功底。在這一點上,朱老師其實是很典型的中國文人,追求精深專一的學問。朱老師那時經常說,在中國出名很容易,發表三五篇文章就可以了。然而,只有做出真正讓人信服的一流成果,才能在學界長久立足。朱老師的眼界很高,真正能夠入他法眼的學術研究成果并不多。
由于朱老師要求嚴格,他帶的好幾個研究生都因為耽誤了寫論文而被他取消了學籍。有一個同學在畢業當年論文答辯期間,學校因為他犯了錯誤而不讓他答辯,朱老師卻力主讓他答辯,雖然后來沒能成功。1992年,學校不管這個事情了,這位同學找到朱老師要求論文答辯,這時朱老師卻又不同意了。他說,當年同意是怕這個錯誤對這位同學造成太大影響,現在不同意是因為這位同學的論文確實沒有達到要求。
朱老師本人的學術功底非常深厚,我說兩件事情。朱老師1945年回國后,一直在上海的大學任教。1950年夏來到北京,就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專門委員。朱老師能進入人民銀行,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他精通馬克思的貨幣理論。貨幣理論是《資本論》當中比較難懂的部分,真正爛熟于胸的人很少。我們當時要搞計劃經濟,需要這方面的專門人才,朱老師就成了不二人選。1979年,“文革”結束后先后任經濟所所長和社科院副院長的許滌新把朱老師調到經濟所工作。許滌新本人是著名經濟學家,在經濟思想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詣。以前看過他的一本書,批評十幾個經濟學派,其中有幾個恐怕其他人都沒聽過。但是,許滌新卻很佩服朱老師的學問,力主把朱老師調到經濟所,增強所里的研究力量,朱老師的學術造詣就可想而知了。
我就適合分工到做學問上來
我這些年來一直做學問,潛心治學,我覺得這是由我的性格和氣質決定的。現在回頭想,自己似乎從來就是只能當學者。我從小就喜歡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可以說是哲學性的問題吧。我也喜歡和人辯論,非得把自己的想法說明白,讓別人理解了。我從來都說得多,想得多,做得少,屬于“只想事,不干事”的類型。
學術研究屬于“說”和“想”的范疇。我所說的“做事”是做一些具體的、實際的工作和事情。舉個例子,“文革”的時候我似乎也是“造反派”,但是一直停留在口頭和思想上,而沒有付諸行動。我沒有參加過武斗,沒有打過人,覺得這些事情不是我應該做的,或者說我的性格決定我不會去做這些事情。我認為自己的性格最適合做學問,而且早就定好了人生目標。其實我一直都很有雄心壯志,想在經濟學研究上做一些大的成就。
當然,總得有人做實際的事情,得有人經商,也得有人從政,大家性格不同、偏好不同,社會分工也就不同,我就適合分工到做學問上來。我覺得自己的一些優點適合用在做學問上,比如對許多事情有正確的預見,喜歡聽有經歷的人講事情,有愛好研究的習慣等。我現在幾乎全部的時間都用在學術研究上,不去參加那些實際問題的爭論。
兩次論戰我都是迫不得已
在我迄今為止的學術生涯中,有兩件事把我卷入了對實際問題的爭論之中,即社會上流傳的“左氏風波”和“郎咸平事件”。不過關于這兩件事情,我要強調兩點。第一,進行這兩次論戰我都是迫不得已,可以說是被外界干擾拉下水的,自己本質上都不是非常愿意干,而且我對自己參加這兩次論戰的作用評價不是很高。第二,人總是有立場的,搞經濟研究更不可能沒有觀點和立場。同時,這又和自身的利益有關系,和你關心的人、喜歡的人的利益有關系,和社會利益有關系。是專心做純學術的研究,還是參加社會上對政策的爭論,我在這方面有時候也很矛盾,因為總會有利益糾纏在里面。
1993年到1994年大家討論經濟是否過熱,有一百個經濟學家說經濟并不過熱。當然也有人出來反對。但是,有些人講得不行,有些人講不出像樣的道理來,有些人沒有像我想的那樣去講。總之,問題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弄清楚,要讓大家都弄明白,我很著急,最后只好自己站出來講。當時也有很多經濟學家支持我,也就有了“左式風波”這個說法。
10年后,也就是2004年的“郎咸平事件”大家了解得比較多。因為當時互聯網已經非常發達,這個爭論在網上獲得了廣泛開展。其實在郎咸平之前已經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比如秦暉先生。可是主流經濟學家不理這個問題,甚至可以說是集體封殺你。“郎咸平事件”剛開始,主流經濟學家也沒有回應,以至于被媒體稱為經濟學家集體失語。因為自己一貫的觀點和郎咸平的主張比較一致,我覺得自己不講不行,最后就和楊帆、韓德強幾個人一起支持郎咸平。
經過這兩次爭論,關于“新左派經濟學”,或者說“非主流經濟學”的主要觀點和主張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總結。
第一,“非主流經濟學”強調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反對主流經濟學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的傾向。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以“講效率”為借口,極力鼓吹對老的國有企業實施斬盡殺絕的政策,以便最終推行“悄悄私有化”的政策,打著“國企改制”的旗號將國有企業的產權最終轉移到少數私人手中。
這些主流經濟學家之所以對國有企業抱這種態度,是因為他們對國有企業職工的生活境遇漠不關心,甚至可以說是懷有敵意。有些人很武斷地把國有企業職工都看成是“工人貴族”,認為他們是傳統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反對任何緩解國有企業困境、改善國有企業職工生活和福利的政策措施。但是基本的事實是,大多數國有企業職工的處境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不是很好。他們所鼓吹的“競爭政策”,不是要將全中國的勞動者和廣大農民都提高到國有企業職工原來的福利水準,而是要將國有企業的普通職工都降低到貧困農民的生活境遇。他們主張的“企業改制”和“民營化”,是要快速地制造財富上的兩極化,讓少數人成為企業全部資產的所有者,而剝奪國有企業大多數職工的工作崗位和一切社會福利待遇。
第二,“非主流經濟學”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國際壟斷資本與中國人民有著長遠的利益上的重大突出,要求以國家政策的手段和外國企業損害中國長遠利益的做法相斗爭。在這方面,“非主流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分歧集中在兩點上。其一,反對主流經濟學的自由貿易政策主張,要求堅決地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特別是技術密集度比較高的產業;其二,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可能帶來重大危害,因而堅決反對讓外國企業奪取中國投資機會的政策。
第三,“非主流經濟學”重視經濟生活中的各種結構因素,特別是強調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性。經濟增長的源泉是技術進步,這意味著必須通過產業不斷升級來實現經濟發展,意味著落后國家必須使自己的支柱產業不斷向技術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轉移。因此,盡快完成這樣的產業升級,是高速發展經濟的關鍵所在。
我覺得自己的學術研究才剛剛開始
我從事學術研究20多年,一直研究西方主流經濟學。我對經濟思想史和當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有一定的了解,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我覺得自己的學術研究才剛剛開始,還有許多事情等著我去做。最近,我正在進行兩個方面的研究,準備在未來幾年中完成。第一個研究是企業理論方面的,第二個可以算是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研究。
企業理論方面的研究準備出一本專著,書名都定好了,叫《突破企業理論的前沿》。這項研究準備討論兩個問題:為什么會有企業以及為什么資本雇傭勞動。現代企業理論對這兩個問題都有回答,但是沒有給出清晰的定論,我從自己的視角給出了獨特的解釋。我的這項研究以博弈論為主要工具,中間有很多數學模型。我認為自己的研究會為理解現實中的企業提供更好的框架。在研究過程中我閱讀了大量西方企業理論方面的文獻,獲益良多,但是也發現了這些文獻的不足,有些甚至有數學推導錯誤。比如霍姆斯特姆在1982發表的一篇論文,我初讀的時候就覺得后面的數學附錄有問題,后來和我自己的博士生進行了詳細的推導,發現果然有錯誤。
另外一項研究關注不確定性條件下企業的價格和產量決定,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一般非均衡分析。我們知道,在經典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價格決定需要一個假設的瓦爾拉斯拍賣人,這當然和現實不符,現實經濟生活中沒有這樣一個拍賣人。現實的企業行為大致是這樣的:企業預計或確定自己產品的售價時,其實并不能確切預言每一價格上產品的需求是多少,而只能大致知道自己產品的最低和最高賣量。我的數量分析可以證明,企業在自己確定的產品價格銷售上,一般按照最大可能的銷售量供給產品,然后根據真正實現的銷售量進行調整,確定其每一期的產量。每一期實現的銷售量不同,使企業期末產品存貨發生變化,形成一個非均衡的過程。我想以這個思路做一個模型,刻畫企業的價格和產量決定行為。因為模型設計不確定性,企業根據貝葉斯規則進行決策。有了這樣一個基本模型,很多宏觀經濟現象都可以得到解釋。因為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非均衡是常態,所以我認為非均衡模式會更有解釋力。這種非均衡模型所給出的解釋是通過一個個案例實現的,當然,理論基礎都是這個基本模型,但是在具體的案例中要靈活運用,要看研究者的“臨場發揮”。
除了這兩項研究,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也是我長期關注的領域。我在2002年出版的《混亂的經濟學》中有所涉及,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現在的一些研究和我的觀點比較接近,也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提出質疑。這些研究的最大特點是有大量數據支持。我當時的研究沒有做到這一點,是一個缺憾。這個方向研究的核心在發展和貿易的關系上,這涉及保護主義的作用,更廣泛的,也涉及政府政策如何在改變比較優勢方面發揮作用。這項研究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搞清楚,我很早以前就想進行一個更系統的研究。可是一直沒有時間。也許等到前面說的兩個研究項目完成以后,我會再轉到這方面的研究上來。
在學術研究上,左派經濟學家不僅可以學問深厚,而且在學術上也可以是最嚴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