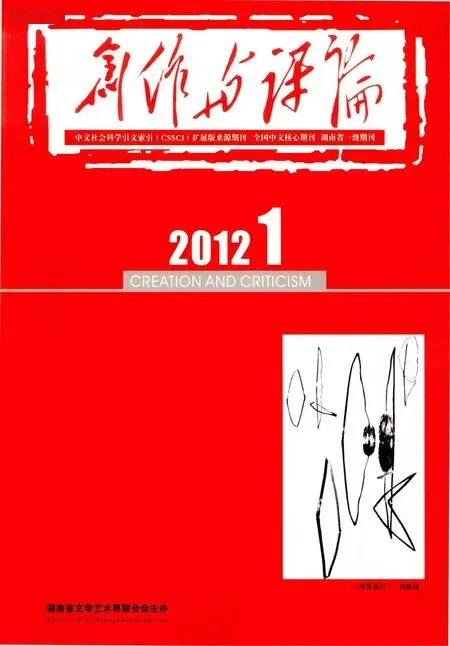林懷民的“文脈”及“東方肢體美學”
■陶琳
一
在大陸的舞者看來,林懷民顯然不是一個可以稱作“科班出身”的“專業”舞者。但是,正是這個并非從小就歷經了“殘酷舞蹈磨礪”的臺灣舞者,卻可以率領著他的舞團走向世界各地、成為聞名海內外的“世界級華人舞團”。時下,當林懷民的舞作以DVD為載體,出版傳播于全國各地,大多數的舞者或觀眾可能并不知道這位叱咤世界舞壇的林懷民作為“文化舞者”的一面。這本2002年11月由上海文匯出版社推出的林懷民舞蹈專著《云門舞集與我》,不但記錄了林懷民和他的云門舞集“揚帆舞海”的人生場景,更能使舞者或觀眾從一個較為全面、理性的角度,認識到從文學家轉身為舞蹈家的林懷民,是怎樣根基中華文脈,使其“舞蹈思維”及“舞動形態”,煥發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第42章)的能量。
“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是1973年代云門舞集創立時的一個“口號”。于是,一群具有民族認同感的青年舞者,緊緊圍繞在當時年僅26周歲的林懷民身邊,開始追求“嶄新的舞蹈藝術”的創作與演出。最初的云門舞集在舞蹈題材的選擇和動作語言的提煉、創造上,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陸歌舞院團有著大致相同的審美取向,無論前者是怎樣融合美國瑪莎·葛蘭姆“現代舞語匯”和后者是怎樣對前蘇聯“古典芭蕾程式”的引進與效仿,在對中國傳統戲曲挖掘后所交融、產生的“戲曲舞蹈形態”,成為了各自“中國式”的、最具特色的動作語言。林懷民與他的云門舞集最初幾年的創作實踐,應該說是糾葛在瑪莎·葛蘭姆的現代舞技術與中國戲曲舞蹈“中西合璧”后,可能產生的種種新的動作語言的“創造”中。盡管在創作方法或某種表現形式上,云門舞集超越了大陸在特殊時期被“模式化”了的創作樣式,并可自由地選擇更能適合舞蹈藝術“本體”發揮、發展的藝術方法或藝術手法,但是,直視云門舞集的《白蛇傳》抑或大陸的《雷峰塔》(中央歌劇舞劇院創作演出),無論前者是怎樣“應用了瑪莎·葛蘭姆以腹部伸縮為主的肢體語言……再度回到‘動物’的本質”(《云門舞集與我》第4頁)、蘇式古典芭蕾的結構樣式與形式特點,創作的“被舞蹈化”了的白素貞、許仙、青蛇、法海,臺灣與大陸的舞者,完成的僅僅是一種從戲曲到舞蹈,從現代舞或古典芭蕾到“中國舞劇”的初級階段的“形式實驗”。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致力“編舞”的林懷民進入“文化自覺”的境界。“思考臺灣本土文化的定位”(《云門舞集與我》第4頁),使林懷民與云門舞集在“貼近生活”中,創作、演出了聞名于海內外的大型舞作《薪傳》。今天看來,林懷民的《薪傳》,向觀眾展示的不僅僅是一部三百年前中國人揚帆劈浪移民臺灣、尋求生機的壯烈史詩。《薪傳》,如同一種宿命,牽引著林懷民和他的云門舞集從此注定要航行在浩瀚博大的中華文脈的海洋,不斷地升帆降帆,做一個逐日的夸父。《水月》、《行草》,是林懷民求索“東方肢體美學”,最具代表性的兩個作品。“動與靜”、“虛與實”、“呼與吸”、“勁與氣”,林懷民的舞者們在水月澄懷的境界中,身如行草般流暢自如且氣韻生動。這是一種吸納中華傳統文化精髓而呼出的精氣,也是一種自覺中華文化傳統精神的再度“薪傳”,更是一種為形塑、書寫“東方肢體美學”的新的章節,又一次地揚帆踐行。“不二法門”的里程,精神的“禪宗”、肉體的“自性”,林懷民與他的云門舞集在重歸東方的行程中,為我們燃亮起“東方肢體美學”的航標燈。這是林懷民和他的云門舞集的一種文化的宿命,也是一種歷史的宿命。
二
信步舞海的無極,恬淡的孤獨從此結伴而行……閱讀《云門舞集與我》的過程,是一種很能使人產生舞海無涯,時空飛度、人物風云且“剪不斷,理更亂”的別樣心情,這種在閱讀中所滋生情感,總是縈繞于胸懷、思緒。林懷民“很孤獨”,但林懷民的“孤獨”是一種中國文人般的“孤獨”。而“恬淡”,是一種境界,如同林懷民靜觀、靜思、靜坐在印度菩提迦耶的神態。
將舞蹈“娛樂化”,舞蹈便成為了“快樂的舞蹈”,其實這種“快樂的舞蹈”是無需載重太多的“文化內涵”的。有了文化的分量,“快樂的舞蹈”便很難快樂得起來,因此我們不必再三去強調綠地上舞著綢扇的老太太們舞出一種“舞蹈文化”。問題是,我們有太多太多的“專業舞者”雖肩負著“文化的使命”,但卻始終“文化”不起來,從而使本該具有文化品格的舞蹈藝術作品抑或舞蹈創作、表演、教育教學理論的表述,總是滯待在“沒文化”的這個公共認同之中。林懷民作為“文化舞者”,他所帶來的一種思考是,云門舞集的舞作作為“劇場藝術”或一種“藝術形態”,其成功的先決條件并非將“舞動”作為一種單純的“審美愉悅”或“娛人娛己”,而是賦予其舞作某種文化符號的品質與意義,并力圖將“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肢體舞動形態的思考與研究,置入“東方肢體美學”的境界。在《云門舞集與我》的專著中,回歸“中國傳統文化”原點,探尋“東方肢體美學”濫觴,構成林懷民與云門舞集不懈的藝術行為與主要的理論表述。“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林懷民和他的“東方肢體美學”,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的文脈,而絕非任由“他者文化”的浸漫或同化。在林懷民創造的“舞動形態”的運化中,“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成為他的“東方肢體美學”所呈現出的最高審美境界。“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為和”(《老子》第42章),“陰陽二氣”的交通和合在“動靜無始,變化無端,虛虛實實,道法自然”(中華武術“自然門”的武道宗旨)的“舞動”中,浩然抵達形而上的審美層面。
在對林懷民的“文脈”考量時,筆者發現,林懷民與中國新舞蹈藝術開拓者、踐行者吳曉邦先生,有著大致相同的“歷經之路”。前者是“盜來”現代舞之“薪火”,燎原起中國新舞蹈藝術的蓬勃生機;而后者是將現代舞之革新精神,注入“東方肢體美學”和“舞動形態”的創造之中,而二者的終極追求是,力圖創新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舞蹈藝術,而這種“新舞蹈藝術”或“嶄新的舞蹈藝術”的“根基”,最終歸屬、貫通于中華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的文脈之中。如果說吳曉邦先生提倡、構建的“中國新舞蹈藝術”,業已成為中國當代舞蹈“宏大敘事”中的一種最為貼近生活、貼近大眾的舞蹈種類,那么,林懷民與他的云門舞集所力求的“嶄新的舞蹈藝術”,不但使我們在云門舞集的“舞動”中,真正感受到作為中國舞蹈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東方肢體美學”的確立,亦為“中國舞蹈美學”的理論建構,提供了一種具有范疇性、命題性意義的研究途徑。
三
《云門舞集與我》以較大的篇幅介紹了世界范圍內、一批舞蹈革新家們所取得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藝術成就”上。在這種類似如“外國舞蹈史”的書寫中,對舞蹈革新家們藝術觀的理論闡述,成為林懷民“敘事”的重點。在這里,無論是伊莎多拉·鄧肯、露絲·圣·丹尼斯、瑪莎·葛蘭姆、多麗絲·韓芙莉、莫斯·坎林漢;抑或是狄亞基列夫、尼金斯基、喬治·巴蘭欽、米哈伊·福金,等等現代舞、后現代舞者和芭蕾舞者的精英們,在林懷民充滿文學色彩的敘說中,圍繞著“革新”與“貢獻”兩組“關鍵詞”,舞動在跨越時空的悠悠歲月中。將“共享性”的“文獻資料”轉化為極富個性色彩和文學意味的語言表達,從而使讀者在閱讀中進入一種能激發情感沖動的閱讀狀態,這是《云門舞集與我》給予讀者的另種饋贈,“理論的”而不枯燥、晦澀;“知識的”而不單調、炫耀。在這里,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化合為林懷民與云門舞集的濫觴,鼓動著林懷民與他的云門舞集在對“他者”的革新和對“自我”的確定中,實現著他們“嶄新的舞蹈藝術”的夢想。
針對大陸舞者而言,林懷民的《云門舞集與我》亦可提供我們這樣一種反思,即:當“文學的”、“戲劇的”、“美術的”……“藝術理論”在我們尋求“本體論”的過程中,以期求得“門類”的“獨立性”而一度遭遇排斥,我們是否忽視了舞蹈在“本體論”的構建過程中,由于自身特殊的歷史原因與所謂門類特點作用下所造成的較為明顯的學知局限?“排它”首先是要“知它”,一味“排它”的結果使我們的“本體論”并未像預想中的博大、深厚,舞蹈理論層面的狹窄、單薄,早已顯現于我們極度推崇的所謂“舞蹈思維”上的營養不良和思維堵塞。一方面,對歐美文化藝術理論的“嫁接”或生硬的“對應”,往往忽略了民族文化背景作用下“肢體表達”的差異性、以及由這種“差異性”所導引出的理論闡述和創新;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對中華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的“學而時習之”,致使當下舞蹈理論、特別是美學理論,仍然處在由“他者”文化觀左右、并總是處在“落后于實踐”的“爭鳴”中,從而使舞者們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籠統的“印象”與“感性”之中。在此,林懷民的舞蹈專著《云門舞集與我》進一步凸現的意義是:其一,集身于“編舞者”、“導舞者”、“說舞者”、“寫舞者”的林懷民,其實正是中國舞蹈人才培養的一種范式,換言之,作為舞蹈藝術門類的從業者,能否“可持續性發展”,借用那句曾在“藝術圈”廣泛傳誦的言說,“拼到最后拼的還是文化”。這是一種層次,抵達了這個層次,舞者,方可稱其為“職業的”、“專業的”的舞者。其二,云門舞集的實踐證明,一個可稱其為優秀的舞蹈團體,必須在藝術探索的全過程中,逐步確立起具有“個性化”意義的藝術方向并形成具有理論價值的“科學發展觀”,而其訓練體系形成、代表性劇目和代表性人物的成就,構成其作為優秀職業性舞團存在的基本標準。顯然,這必將牽涉到中國舞蹈教育機制的創新,舞蹈院團體制改革等一系列的問題,但是,只有在“文化自覺”、“理論自覺”的真正“自覺”下,中國舞蹈藝術才能獲得藝術品格的進一步提升。不然,我們將繼續被“頭腦簡單,四肢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