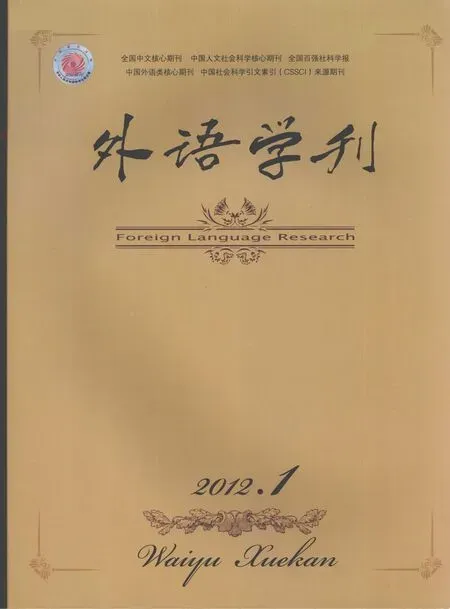語言之象與語言之相
——語言批判及其在語言學領域中的運用
陳 杰
(上海大學,上海200444)
1 引言
如何處理語言學理論與語言事實之間的關系問題,外語界有過討論(陳平1987,徐烈炯1997,許余龍2000,伍雅清2004,司富珍2006),而在漢語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似乎要熱烈得多。外語界往往以技術性問題為導向(徐烈炯1997,許余龍2000),條分縷析而又連篇累牘,幾至偏題的地步;漢語界在強調語言學理論與語言事實這“兩張皮”能夠互補統一的同時,仍然堅持以語言事實為重(陸儉明 郭銳1998;陸儉明2005,2007;沈家煊 2007a,2007b;陸儉明2010)。本文以康德先驗哲學為進路,重新審視語言學理論與語言事實的關系。
2 知性與理性
康德認為,人類的一切知識始于感性,進入知性,止于理性。知性以感性雜多(manifold)為質料,以感性直觀(intuition)為形式,將雜多聯結起來,在一個認識中加以把握,從而生成知識。因此,知性是一種規則的能力,處理的是經驗之內的認識。而理性是一種原則的能力,這種原則不是指可以作為一條原則來運用的知識(如數學公理),而是指從原則而來的知識是人們通過概念在普遍中認識特殊的知識,不包含任何經驗或來自經驗的概念。三段論就是這樣一種從原則推導出的知識的形式。“在三段論中,我首先通過知性思考一條規則(大前提),然后通過判斷將某一認識歸于該規則條件之下(小前提),最后通過該規則的謂詞,因而是先天地通過理性來規定認識(結論)”。(Kant 1929:304)
所以,知性是借助規則聯結許多表象的能力,而理性是借助原則聯結知性規則的能力。理性無法直接應用于直觀或經驗對象,即使針對對象,也必須且只有與知性及其判斷發生關聯,由知性及其判斷指向感性直觀,將直觀雜多納入概念之中進行聯結,通過使知性達到與自身徹底一致的方式來規定自己的對象。理性的自發性居于知性的自發性之上,后者從自身的活動出發生成概念,對原則和概念進行經驗而非先驗的運用;前者則能超越感性提供給它的一切,對其產生的原則進行先驗而不是經驗的運用。
相應地,就知性的經驗運用而言,凡是出現在時空中,由范疇聯結起來形成一定關系的東西,都是現象(ap-pearances);而如果通過先驗的知性概念或范疇對現象進行綜合,以便生成更為清晰的說明,那么這種作為思考對象的現象就是現相(phenomena)。人們雖然不直觀后者,后者也不屬于感覺的對象,但它卻是人們通過知性進行思維的對象,用來理性地認識和把握本體。這樣,“對象就有了‘現相’和‘本體’之分”。(Kant 1929:266)而既然本體就人們直觀它的方式來說是非感性的,那就必定還有一種特殊的直觀方式,一種脫離人的一切能力,對于人來說是不可能的,但并非對任何存在者都是不可能的智性直觀(intellectual intuition)。“通過它,對象以自身所是的那樣得到表象,而在知性的經驗運用中,對象則以自身所表象的那樣獲得認識。”(Kant 1929:267)
3 語言之象
語言屬于直觀,可分為語言感性直觀和語言智性直觀。前者是人類的感性接受表象的能力,后者意味著一種雖然人類不具備但超驗的領域的存在者(比如靈魂、上帝)可能具備的直觀。盡管就感性而言,語言智性直觀并無存在的可能,然而另一方面,人們也同樣無法確定語言感性直觀是直觀的唯一存在方式。語言感性直觀使知性將經驗的雜多聯結起來,生成先天必然的知識;而語言智性直觀則使人們無須借助感官經驗而直接通達本體——盡管這只是一種想象或推理。所以,鑒于語言智性直觀不是經驗上的而是邏輯推理上的存有,具有通達理性的可能,筆者將語言智性直觀叫做“自在之語”(language-beyond-itself)。
自在之語是一種本源的、具有能動性和創造性的直觀,比如“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思’是一種邏輯機能”,“能夠自發地聯結語言直觀的雜多”;借助“思”,“我把我向我自己既不像我所是的那樣,也不像我對我自己顯現的那樣”(Kant 1929:381),而是像我之“我在”的那樣表象出來。因此,我沒有關于我自己在的知識,而只有關于我對“我在”向我自己顯現的知識。思維一個對象,語言感性直觀無須在場,所以“我在”作為表象,就是一個思維;作為思考的對象,就是一個現相。另一方面,如果我要對作為思維著的自己進行自覺(conscious),由于我不是在語言感性直觀中想到我自己,而需要語言智性直觀發揮作用,所以,“我自己對于‘我思’的‘我’來說就是表象,而對于‘我思’來說就不僅僅是表象,而是在純粹思維的自覺中的存在本身”(Kant 1929:382)。這個意義上的我已經近乎上帝,無需任何經驗語言的雜多,不用局限于語言的感性直觀,只要有自在之語就能夠自發地創造對象。正如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光就被直觀地給予出來。因此,自在之語存在于對象以及整個世界之前,作為本源的直觀(original intuition),它永遠超越人類能力之外,以此為基礎,理性就能夠獲得最大運用。在這個意義上,本體就成了自在之語的產物,這種產物刺激人類的感官,生成語言感性直觀,人類通過語言感性直觀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由此,語言感性直觀就成了派生的直觀(derivative intuition)。鑒于語言感性直觀相對于自在之語來說具備其表象的意味,筆者將語言感性直觀稱為“語言之象”(language representation)。
作為語言之象,語言感性直觀也可演化出自身的表象,其表象的方式在經驗的視域中往往虛實夾雜,亂象紛呈。例如:
①John is easy to please.
②John is easy to please.
我們通過語言感性直觀所得到的表象是同一的,即John is easy to please.但是如果我們借助知性概念對這個表象進行判斷,那么就能夠認識到句子①具有以下深層結構:

其中的嵌入式從句(embedded clause)屬于非限定性從句,其主語為空格,因此無法與根從句(root clause)下的[SPEC,AgrsP]進行匹配。又,根據 Burzio’s Generalisation,如果V/please沒有為[SPEC,VP]指派論元,那么V/please就不對其賓語進行格標記。因此,作為V/please的補詞,DP/John可以提升至[SPEC,AgrsP],以獲得主格標記。但是,如果 DP/John的提升受阻,則必須通過在[SPEC,AgrsP]的位置上插入附加語it,以確保根從句滿足格的需求。所以,句子①可以轉述為It is easy for others to please John.而句子②的深層結構是:

其中,DP/John生成于[SPEC,VP],因為其所在的嵌入式從句屬于非限定性從句,所以DP/John無法獲取與[SPEC,AgrsP]的格匹配。為了滿足格的需求,DP/John提升至[SPEC,AgrsP],從而獲得由AgrsP分配的主格。這樣,格驅動的 DP提升排除了生成 It is easy John to please”這類句子的可能,因為DP/John無法在[SPEC,T1P]這個位置獲得格標記。所以,句子②可以轉述為It is easy for John to please others.
作為語言感性直觀的表象,句子①和②的存在方式相同,但這僅僅是語言感性直觀進行表象時所生成的偶然的同一。假如違逆人類的自然傾向,在語言感性直觀進行表象的過程中,DP/John的提升不是由格來進行驅動,而是由EPP(Extended Projection Principle)進行驅動,便可以產生亂象,以致無法濾除It is easy John to please.這類句子的可能。但是,即便如此,這種表象也絕沒有過錯,因為語言感性直觀是被動的,不論知性作出何種判斷,表象或亂象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在經驗世界中真實現存的。所以,既然語言感性直觀本身已然是一種象,那么它演化出來的表象就是“象之象”;雖然語言學家喜歡稱其為“語言事實”,但我們卻非常樂意向人們揭示出它的本來面目:“語言重象”(ghost representation of language)。
4 語言之相
就語言直觀而言,自在之語派生出語言之象,語言之象衍化為語言重象,語言重象在全然而徹底地進入“虛無”前,再一次被拋回到人們(包括說者)的經驗視域之內,即語言之象之內,與感官發生接觸,形成“語言現象”(language appearance)。在這個意義上,自在之語是語言現象之外的本來面目,前者是后者作為經驗而形成的基礎和原因,也是后者在被動的感性能力的范圍內所無法把握的存在。自在之語呈現給我們的不是其自身,而是聽者感覺到的通過說者的聲門,由其口腔和鼻腔內沖出的那股氣流所引起的空氣粒子的振動以及由此導致的聽者的鼓膜的振動;此外,它不會有任何其他的呈現。
然而,如果換一個角度考察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一旦通過先驗的知性概念或范疇對語言現象進行綜合,進而生成系統、一致的、抽象的說明,那么這種被納入思維范疇進行統一處理的語言現象就過渡到知性意義上的“語言之相①”(linguistic illumination),即語言學意義上的“語言的知識”,而對這種知識進行的系統、全面的表述,就是語言學家所謂的“語言學理論”。人們無法感覺語言之相,只能在意識中生成并把握這種思維的對象,并通過自在之語,在理性的層面上認識純粹的、絕對的、超驗的本體。這種自覺的語言之相可以分為“語言真相”(linguistic truth)和“語言幻相”(linguistic illusion),兩者不在語言重象/現象之中,而在通過知性的范疇對語言重象/現象的判斷之中。所以,雖然人們認為語言重象/現象不犯錯誤是對的,但這絕不意味著它們始終在正確地作著判斷,而是它們根本就不作判斷。
進一步說,既然通達本體所需要借助的自在之語和語言之相與語言相關,那么這個本體必然是關于語言的,我們稱其為“語言之體”(linguistic noumena)。雖然就人而言,其靈受制于知性,其肉受縛于感性,囿于智而乏于力,認識語言之體終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這種超驗的認識在邏輯上并非沒有存在的可能,它終究是人類在其自然傾向的引導下所思考的對象;或者,另一種可能,通過自在之語對語言之相的綜合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形式,而沒有任何內容。總之,語言之體的概念構成人類對世界的一種最基本的理解,作為無法從語言各象推導出的、無法證實的一條信念,支撐著整個語言學大廈。
5 語言批判在語言學領域中的運用
在完成對語言范疇的考察之后,嘗試從語言學視角論證和演繹以上相關概念,并以科學史為參照,衍生出對語言學理論與語言事實的關系的討論和判斷。
5.1 語言事實不證明②語言學理論
語言工作者認為語言事實真實可靠,因此僅僅對語言事實及其描寫感興趣,只有有了語言事實的支撐,語言學理論才能完善自身。這種說法固然沒有錯,但這僅僅是由于對語言事實根本就不作判斷,當然也就無所謂判斷的正確或錯誤了。真相也好,謬誤也罷,幻相也行,都只可能存在于語言學理論之中。如果知性和感性按照各自的規律各司其職,那么在合理設定的范疇中進行必然的概念推導而生成的語言學理論本身就沒有錯誤;而由感官表象衍生出的不包含判斷的語言現象本身,也不會有錯誤。前者是因為其判斷結果與自身規律必然一致,這種一致是真相之其為所是的形式基礎;后者是因為感官只有被動的接受性,不具備能動判斷的能力。所以,既然錯誤不可能來源于語言學理論(語言之相),也不可能來源于語言事實(語言現象),那就只能來源于語言事實對語言學理論的不可避免的干擾。因此,1)當語言事實納入語言學理論,作為其解釋對象而獲得適當的限制的時候,語言事實就有幸成為真相的來源: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只對語言事實感興趣的人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只有以可感可測的語言事實為媒介,才能對語言產生正確的認識,構筑精致而又宏大的語言學理論;2)如果語言之體與自在之語發生交融,遮蔽了自身,以至于偏離了各自原來的功能,那么當語言事實納入語言學理論時,前者的感性運作就會對后者的知性活動產生影響,甚至干擾和逾越其自身的判斷:在這個意義上,語言事實就是當之無愧的錯誤的來源。
司富珍(2006)從積極的角度論述過語言事實和語言學理論的關系,以牛頓和蘋果落地的故事為例,引證理論對事實具有指導性作用。我們從消極角度補充這一問題。
假設根據牛頓的力學理論(N),人們發現一顆行星(P),但是P偏離理論軌道。科學家絕不會因為這個事實與理論不符而否定N,而會假設有一顆不為人知的小行星P′干擾了P的軌道。于是,他建造一架更大的望遠鏡去觀察。如果觀察到P′,它就會被當作牛頓力學的新勝利而受到歡呼。如果沒有觀察到P′,科學家也不會因此否定N,他會提出有一團宇宙塵埃(D)擋住了P′,P′其實是存在的。于是,他計算出這團塵埃的位置,發射衛星檢驗。如果衛星探測到D,它就會被當作牛頓力學的新勝利而受到歡呼。但是,沒有探測到D.這時,他仍會說D(當然還有P′)是存在的,只是衛星上的儀器不夠靈敏,D無法在上面成像。于是,他又發射了一顆新的衛星……Lakatos(1968:169-170)這個思想實驗再現了科學史上理論的實際遭遇,即對事實的挖掘當然可以不停地進行下去,但事實永遠也無法構成對科學理論的證實或證偽,更鮮有對理論進行的無謂的干擾,而只是適時地被理論所建構與證明。相應地,作為語言的事實絕不可能證實或證偽語言學理論:語言事實沒有對錯之分,它甚至無關對錯真假:它沒有假象,作為感官各象,它已然存在,存在本身無所謂真假;它不涉及知性,無法能動地判斷,因此它無關對錯。只有具備了對錯的資質,才能具備在同一個基礎上與同樣屬于知性的判斷比較,構成可能的矛盾沖突或者尋求融合的可能。
5.2 語言事實不是語言學理論的充分條件
司富珍(2006)針對孟德爾豌豆實驗與遺傳學理論關系的說明可能由于轉述而有所不確。事實上,作為現代遺傳學的奠基人,孟德爾在對豌豆進行雜交試驗前,已經意識到遺傳的一些規律,比如分離律(law of segregation)和自由組合律(law of independent assortment),因此試驗對象的確是他有意選取的。盡管試驗數據與理論值一致,但一切又都過于完美。Fisher(1936)在運用統計學方法分析后指出,“……證據顯示,孟德爾的試驗數據,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大部分都作了篡改,以達到與其期望的高度一致”(Fisher 1936:132)。更要命的是,孟德爾的理論如果不是全部錯誤的話,至少也不全部正確,因為“……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幾乎無法解釋的矛盾:有一組數據……與孟德爾的期望值嚴重不符,而他的理論本可以經過修正后預測這組為數不多的測試后代”(Fisher 1936:132)。雖然最近人們試圖從遺傳學的角度(Novitski 2004)或統計學的角度(Pires&Branco 2010)了結這段科學史上的公案,但他們還是不得不坦言,即使孟德爾沒有篡改數據,出現這種理想數據也相當偶然。
可見,1)孟德爾的遺傳學理論出現在前,豌豆試驗在后,根本不存在由試驗數據推導出理論的可能;2)豌豆試驗中的數據或誤差過大,或過于理想,但這種現象絲毫沒有對理論本身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此既然作為科學的遺傳學的理論發展與實踐路徑如此,我們看不出作為科學的語言學就可以不必訴諸如此的科學理念及方法。相應地,就語言學理論而言,它具備真假對錯之分,因為它是能動的知性判斷:將語言現象作為質料納入知性范疇中進行綜合,就有語言之相(真相、幻相或假相);將語言現象濾除,而憑借知性自身的能力進行概念推導,語言之相就是一種純粹的思維運作:在這個意義上,它又無關真假對錯——孟德爾的遺傳學理論原型(prototype)便是如此。
5.3 真理的版本沒有優先程序
許余龍認為,“不同的語言學理論側重于解釋語言事實的某一個方面”,若以時間為軸,后一種語言學理論必定優于前一種,而“最后一種”必定是最“適用”的(許余龍2000:8)。例如光理論,人們在經歷了“微粒說”、“波動說”、“波粒兩象性”等等之后,對光才有了較為全面和深刻的認識。此其一。所以,其二,我們可以“將互補原理推廣和運用到語言學研究中去”,將許多語言學理論(比如形式語法、功能語法)統一起來,因為“這似乎又是語言學的發展方向”(許余龍2000:9)。
這種說法問題有三。其一,它意味著功能語法出現在形式語法之后,所以必定優于形式語法。至于“優”在何處,許文沒有論及,我們自然也無從評述;其二,許文引述的人們對光的認識一直在變,但這些認識實際上多以量子力學的發展為基礎,具備共同的理論內核,因而并未對量子場理論(quantum field theory)本身構成反動。正如對反身代詞“自己”的認識,既有“約束”到“最簡”的轉變,又有GPSG和HPSG的模型,但在形式語法框架內實現的對諸如“自己”認識的任何變化都不可能揚棄形式語法本身,抑或導致語言理論的更迭。其三,作為對量子場理論的反動,目前物理學界(Hawking&Mlodinow 2010)對弦理論(string theory)作了延伸,提出M理論(M-theory)。既然能夠將形式語法和功能語法統一起來的“互補原理”指的大概就是自然科學領域中的通常作法,那么似乎也存在將M理論和量子場理論統一起來的可能。或者,如果這兩個理論孰是孰非,當下尚無定論,加之術語艱澀,難免走入迷局,而不得不以能夠抽身事外的為例,那么是否就可能存在將譬如“日心說”和“地心說”統一起來的可能,因為這似乎就可以想當然地成為現代天文學的發展方向了——這是許文必須回答的第三個問題。
所以,作為語言學理論的存在方式之一,語言真理必須具有兩個層面上的含義。第一,相對的語言真理。當語言現象作為質料被納入知性范疇綜合后,就會有語言真理/相。但是,如果語言現象沒有接受知性的恰當限制,甚至干擾知性的運作,語言真理/相就不復存在:因為這種語言真理畢竟與經驗世界有關,當它們運用于經驗時,至少還有衡量它們正確性的標準。所以,這種語言真理是可錯的(falsifiable),它們的出現雖有時間先后之分,但除此以外也就沒有其他任何的不同了。第二,絕對的語言真理。如果語言之相作為質料被納入概念或范疇進行思考,那么它們作為知性的對象就需要自在之語的參與,否則便無法進入語言之體:因為人類并不擁有自在之語,因此永遠也無法通達語言真理的絕對彼岸。所以,盡管在時間維度上可以出現不同的真理版本,但由于真理本身在時間維度之外,真正的語言真理實際上是不可接近的(unapproachable),即對語言學理論的統一是不可能的。
6 結束語
本文以康德對知性和理性的區分為框架,提出語言直觀分為“語言感性直觀”和“語言智性直觀”的觀點;以此為切入點,建立“語言之象”、“語言重象”、“語言現象”等一系列概念,以語言學的視角演繹“語言之象”和“語言之相”,證明語言學理論和語言事實的關系,批駁中國語言學界重考據、輕理據的研究傳統。
語言學是一門經驗科學,但這絕不應該成為中國語言學人的一種借口,放棄對一種更為宏大的目標進行關照的精神;更不能閉目塞聽,自我戕害,終日皓首窮經,搜羅證據,實則卻偏離理性的約束,進行著癲狂的運作。本文作為康德哲學和語言學相結合研究的嘗試,是正本清源還是謬種流傳,筆者引頸而望,以此求教于方家。
注釋
①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中只有對真相/真理(truth)、幻相(illusion)的論述,而沒有一個直接對應于“相”的術語,筆者暫且將之處理為illumination:因為“相”是相對于知性(知道、認識、啟發、照亮)而言的,作為動詞原形的illuminate正好有“在……其上照亮”(in— [upon] +lumin—[light])的意思。同時,筆者將“語言之相”中的“語言”處理為linguistic,以示與關于感性的“語言(language)之象”有所區別。
②此處,證明既指先天必然的證明,又指經驗的證實和/或證否。
陳 平.描寫與解釋:論西方現代語言學研究的目的與方法[J].外語教學與研究,1987(1).
陸儉明郭銳.漢語語法研究所面臨的挑戰[J].世界漢語教學,1998(4).
陸儉明.漢語語法研究的必由之路[J].語言文字應用,2005(3).
陸儉明.談語言事實的發掘與理論方法的更新——在南開大學語言研究所成立儀式上的講話[J].南開語言學刊,2007(2).
陸儉明.漢語語法研究中理論方法的更新與發展[J].漢語學習,2010(1).
沈家煊.關于外語界做研究的幾點想法[J].中國外語,2007a(1).
沈家煊.對當前語言研究的三點體會——在南開語言研究所成立儀式上的致辭[J].南開語言學刊,2007b(1).
司富珍.語言學研究中的科學方法[J].外國語,2006(4).
徐烈炯.語言學理論與語言事實[J].現代外語,1997(3).
許余龍.也談語言學理論與語言事實[J].外國語,2000(3).
伍雅清.語言實證的必要性,還是語言觀念的必要性[J].外語學刊,2004(2).
Fisher,R.A.Has Mendel’s Wrk been Rdiscovered[J]?Annals of Science,1936.(1).
Hawking,Stephen W.,Leonard Mlodinow.The Grand Design[M].NY:Bantam Books,2010.
Kant,Immanuel.Critique of Pure Reason[M].London:Macmillan,1929.
Lakatos,Imre.Criticism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J].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1968(69).
Novitski.E.On Fisher’s Criticism of Mendel’s Results With the Garden Pea[J].Genetics,2004(3).
Pires,Ana M.,Jo?o A.Branco.A Statistical Model to Explain the Mendel-Fisher Controversy[J].Statistical Science,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