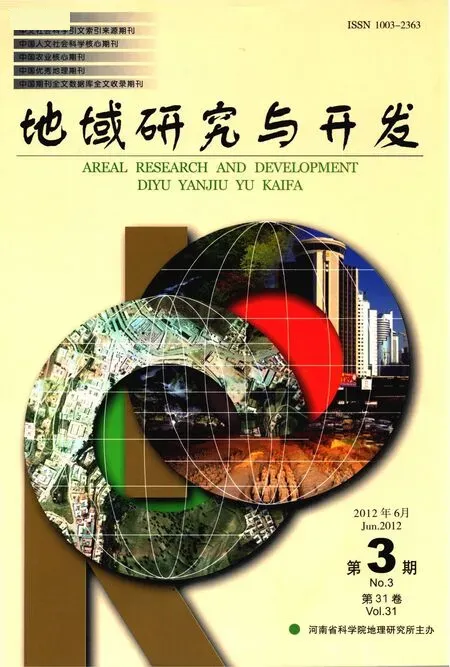1999—2009年新疆能源消費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實證研究
顧成軍,龔新蜀
(石河子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0 引言
2003年,英國政府公布了《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白皮書,使得“低碳經濟”第一次見諸于政府文件。自此,各國政府紛紛致力于對推動本國“低碳經濟”的發展進行研究;同時,關于“低碳經濟”相關的研究迅速也在國內外學術界成為研究的熱點。2009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5次會議(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召開,中國承諾延緩二氧化碳的排放,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1]。現在,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頭號排放國,碳排放量占世界碳排放總量的約21%。新疆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省區卻面對著二難選擇:一方面是快速發展經濟的內在需求,這將推動新疆的碳排放量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是碳排放減排的外在約束,這將使新疆面臨減少碳排放量的壓力。破解此二難選擇的方法便是轉變新疆經濟發展方式。基于此,本研究利用LMDI分解方法對1999—2009年新疆能源消費碳排放進行了實證研究。通過對能源結構因素、能源強度因素、產業規模因素和人口規模因素對新疆人均碳排放的拉動和抑制效應進行分析,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1 模型構建
1.1 碳排放驅動因素分解模型
國內對碳排放進行因素分解研究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是徐國泉等,他們的創新之處在于通過數學等式變換的方法構建用于實證分析的模型,其優點在于等式變換有目的的將被解釋變量分解出多個解釋變量[2]。遵循已有文獻(徐國泉等,2006)[2]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將被解釋變量碳排放量分解為4個主要影響因素,即,產業能源結構因素、產業能源強度因素、產業規模因素和人口規模因素。于是,可以構建新疆能源消費碳排放因素分解實證研究的模型(1)如下:

模型(1)中:C為被解釋變量,也就是新疆能源消費的碳排放量;Ci為新疆第i種能源產生的碳排放量;Ei為新疆第i種能源消費的量;E為新疆消費的能源總量;G為新疆國內生產總值;Pi為第i種能源消費對應的年末人口數;P為新疆年末總人口數;用i區分不同的能源類型(i=1,2,3),分別表示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需要說明的是,模型(1)等式右側括號中各個相乘的因子實際上就是解釋變量,并且為了分析的簡便,文中按照已有文獻(徐國泉等,2006)[2]的慣常處理方法求取人均碳排放量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模型并加以簡化,簡化后的人均碳排放量影響因素分析模型為模型(2):

為了對新疆能源消費碳排放的各個因素的影響效應進行實證分析,還需要依據模型(2)測算新疆能源消費碳排放的各個影響因素的貢獻值和貢獻率,由此,基于模型(2)可以得到模型(3)和模型(4):

在模型(3)和模型(4)中:設定第T期人均碳排放量為AT,基期人均碳排放量為A0,則第T期相對于基期的人均碳排放量的貢獻值ΔA為各個分解因素貢獻值之和,并且貢獻率D為各個分解因素貢獻率之積。具體來說,ΔAc,ΔAs,ΔAq,ΔAm和ΔAp表示各個分解因素變動對人均碳排放變動的貢獻值(t/人);Dc,Ds,Dq,Dm和Dp為各個分解因素變動對人均碳排放變動的貢獻率,無單位;并且ΔAc和Dc均為碳排放系數因素,可看作分解余量;ΔAs和Ds均為能源結構因素;ΔAq和Dq均為能源強度因素;ΔAm和Dm均為產業規模因素;ΔAp和Dp均為人口規模因素。
1.2 對數平均Divisia指數分解法
LMDI指數分解法是指Ang(2004)的對數平均Divisia指數分解法[4]。設基期人均各能源消費碳排放量為A0i,第T期總量為AT i,函數F(x,y)=(x-y)/(lnxlny),分解因素變動對人均碳排放變動的貢獻值和貢獻率的測算公式為:

從而,ΔA1,ΔA2,…,ΔA5和D1,D2,…,D5依次表示ΔAc,ΔAs,…,ΔAp和Dc,Ds,…,Dp。由于各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在實際應用中一般取常量,因此在進行因素分解分析時ΔAc的數值始終等于0,從而D的數值為e0,即Dc≡1[5]。由此可知ΔA和D的進一步簡化公式:D=Ds×Dq×Dm×Dp,ΔA=+ΔAs+ΔAq+ΔAm+ΔAp。
2 實證研究
2.1 數據收集與處理
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新疆統計年鑒。其中,國內生產總值為當年價統計數據(億元),人口數為年末人口數(萬人),價格指數為1995年不變價居民消費價格指數E為總能源消費量(萬t標準煤)(表1)。鑒于統計數據口徑的一致性和可獲得性,選取新疆1995,1999—2009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其中,2008,2009年部分數據來源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2008年[6],2009年[7]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表1 新疆1995,1999—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人口數以及總能源消費量Tab.1 GDP,population and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of Xinjiang in 1995 and 1999—2009
由于新疆歷年消費的各種能源產生的碳排放量難以獲得,所以本研究利用各類能源的碳排放系數等相關變量加以估算[8]。具體的估算公式為,E表示新疆能源消費總量;si表示第i類能源所占消費的能源總量的比重;ci表示各類能源的碳排放系數(表2)。另外,為了消除物價變動造成的影響,本研究對新疆歷年國內生產總值數據進行了“平減處理”(表3)。
根據表1和表2中的相關數據,估算得到新疆歷年國內生產總值(G)、人均總能源消費碳排放量(A)、人均煤炭消費碳排放量(A1)、人均石油消費碳排放量(A2)、人均天然氣消費碳排放量(A3)的數據(表3)。

表2 各類能源的碳排放系數[8]Tab.2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s of various energy

表3 新疆國內生產總值處理和人均總能源消費碳排放量等數據估算結果Tab.3 Processed GDP and estimated data of carbon emission quantity of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apita etc.
2.2 因素分解分析
利用表1和表3中的相關數據和各分解因素對人均碳排放變動的貢獻值和貢獻率的具體測算公式可以得到相應的結果。其中,各分解因素對人均碳排放的貢獻值的測算結果如表4所示,各分解因素對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的測算結果如表5所示。

表4 各分解因素對人均碳排放的貢獻值測算結果Tab.4 Calculated outcomes of carbon emission contribution value per capita from the decomposition factors
表3顯示,1999—2009年間新疆總能源消費人均碳排放量表現出逐年增長的趨勢。表4和圖1表明,新疆總能源消費碳排放分解為能源結構、能源強度、產業規模和人口規模四個因素后,能源結構和能源強度與新疆人均碳排放增長反方向變動,表現為負效應;產業規模和人口規模與新疆人均碳排放增長同方向變動,表現為正效應。1999—2009年,新疆能源結構對人均碳排放年平均貢獻值為-0.042 58 t/人,能源結構效應為-7.798%;能源強度對人均碳排放年平均貢獻值為-0.371 68 t/人,能源強度效應為-65.168%;產業規模對人均碳排放年平均貢獻值為0.938 05 t/人,產業規模效應為134.150%;人口規模對人均碳排放年平均貢獻值為0.236 43 t/人,人口規模效應為38.815%。

表5 各分解因素對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測算結果Tab.5 Calculated outcomes of carbon emission contribution rate per capita from the decomposition factors


產業規模是新疆人均碳排放快速增長的主導因素,人口規模對新疆人均碳排放快速增長的推動作用弱于產業規模的推動作用。按1995年不變價核算,新疆國內生產總值從1999年的814.85億元至2009年的4 273.57億元,以年均14.953%的增長率擴張了約5.244 61倍。同期,新疆總能源消費量以年均9.609%的增長率擴張了約2.919 37倍。從圖1可以看出,產業規模因素對新疆人均碳排放貢獻值曲線始終處于新疆人均碳排放總貢獻值曲線的上方,并表現出近似指數增長的趨勢。人口規模因素對新疆人均碳排放快速增長也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但沒有表現出近似指數增長的特點,其原因可能在于新疆1999年至2009年的能源消費量快速增長,而新疆年末人口的年均自然增長率處于相對穩定的水平,為11.21‰。在產業規模因素和人口規模因素的共同推動下,新疆碳排放表現出較快增長的特征,但是也間接反映出了新疆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
能源強度對新疆人均碳排放增長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能源結構對新疆人均碳排放增長的抑制效應相對微弱。實測數據顯示,新疆能源強度從1999年的3.091 31 t標準煤/萬元以年均-2.077%的增長率逐漸下降到2009年的2.462 94 t標準煤/萬元。換就話說,隨著新疆利用能源的技術進步或者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新疆能源強度表現出了一定的抑制效應。能源結構對新疆人均碳排放增長的抑制效應相對微弱。雖然抑制效應不太顯著,但這反映了新疆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已經初見成效。1999—2009年,新疆能源結構(si)表現出由于能源結構優化調整而不斷波動的特點。雖然煤炭消費所占的比重(s1)有明顯下降的趨勢,但是煤炭消費所占的比重(s1)仍較高,仍高于55%,另外兩種能源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增長或下降的特點,所占比重均低于25%。
為了強化因素的可比性和便于進一步分析,對新疆人均碳排放起抑制效應的能源強度和能源結構兩個因素的貢獻率(均小于1)取倒數(圖2)。取倒數后,新疆能源強度從1999年的1.019 68緩慢增加到2009年的1.042 75,能源結構從1999年的1.084 89緩慢增加到2009年的1.359 01。這與圖2中能源強度和能源結構曲線的扁平型“U”型結構左側的特征相符。1999—2009年期間,新疆能源強度因素和能源結構因素都表現出了較弱的抑制效應,但是新疆產業規模因素表現出了非常顯著的拉動效應,從而拉動效應大于抑制效應。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產生抑制和拉動兩種效應。能源結構和能源強度對新疆人均碳排放增長起抑制效應,且能源強度的抑制效應大于能源結構的抑制效應;產業規模和人口規模對新疆人均碳排放增長起拉動效應,且產業規模的拉動效應大于人口規模的拉動效應。
能源強度和能源結構的抑制效應難以抵消由產業規模因素和人口規模因素拉動的新疆人均碳排放量的增長。新疆人均碳排放的拉動效應主要來源于產業規模因素,人口規模因素的拉動效應相對弱一些。能源結構因素對新疆人均碳排放增長的抑制效應不太顯著,但反映了新疆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已經初見成效。能源強度因素對新疆人均碳排放增長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由于新疆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和能源利用技術水平的相對穩定,從而能源強度和能源結構的抑制效應難以抵消由產業規模因素和人口規模因素拉動的新疆人均碳排放量的增長。
3.2 建議
轉變新疆經濟增長方式和居民生活消費方式。一方面,新疆發展相對落后,有著迫切的發展社會經濟的訴求。但是,從全國甚至全球的角度看,低碳經濟日益受到推崇。新疆面對如此兩難抉擇,最佳的選擇便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另一方面,雖然新疆地處西北邊陲,和發達地區市場相距甚遠,但由于少數民族消費傳統的影響,居民總體生活消費水平很高。所以,新疆的碳減排事關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乃致社會穩定,需要通盤考慮以實現碳減排與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的共贏。
調整能源消費結構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一方面,近10余年來,新疆能源消費比重中煤炭在55%以上,對煤炭依賴程度較高。為了節能減排的推進和低碳經濟的發展,調整新疆能源消費結構勢在必行。例如,可以大力發展以新疆達坂城為代表的風能。另一方面,由于新疆地處高緯度地區,寒冷季節較長,每年需供暖5~6個月,并且較長時間氣溫在-30℃以下,從而需要大量能源。當前,新疆供暖能源仍以煤炭為主,積極開發新技術、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對于碳減排有重要意義。
[1]馮相昭,王雪臣,陳紅楓.1971—2005年中國CO2排放影響因素分析[J].氣候變化研究進展,2008,4(1):42-47.
[2]徐國泉,劉則淵,姜照華.中國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實證分析:1995—2004[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6,16(6):158-161.
[3]朱勤,彭希哲,陸志明,等.中國能源消費碳排放變化的因素分解及實證分析[J].資源科學,2009,31(12):2072-2079.
[4]李國璋,王雙.中國能源強度變動的區域因素分解分析——基于LMDI分解方法[J].財經研究,2008,34(8):52-62.
[5]王鋒,吳麗華,楊超.中國經濟發展中碳排放增長的驅動因素研究[J].經濟研究,2010(2):123-136.
[6]阿不拉·玉素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10-11-27)[2011-08-03].http://www.xjtj.gov.cn/stats_info/tjgb/101127130331651.html.
[7]阿不拉·玉素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10-11-27)[2011-08-03].http://www.xjtj.gov.cn/stats_info/tjgb/101127125599191.html.
[8]韓文科.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R].北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