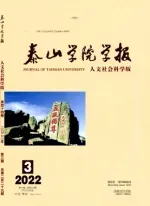魯迅早期書信中革命話語的內涵演變
趙 強
(泰山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山東泰安 271021)
“革命”一詞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流行的關鍵詞之一,正如李歐梵所說:“從晚清到現在,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和文學都籠罩在這個革命的‘話語霸權’之下”。[1](P2)可見,每一個身處其中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都不可能忽略對革命話語的使用,并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可能會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這一話語。而且關于革命話語并不是相當然地就是一個含義,其具體內涵也是歷史變化的,而使用他的主體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取舍與偏重。因此,考察現代思想家、文學家魯迅對于革命話語的使用及其內涵演變就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必須要厘清的。當然,魯迅在其小說和雜文等多種文本中對此都有所涉及,前人對此也有比較充分的研究,但是作為最為私密性文本的書信,魯迅在對友人和親人的交流中是如何對革命話語進行認識和使用的,卻沒有比較系統的研究。本文擬從魯迅早期(1905-1927)書信中對革命話語的涉及,結合革命話語演變研究,分析魯迅早期對革命話語的態度及內涵界定。
“‘革命’一詞本來是個本土詞匯,但它在本世紀初的復活,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日語的翻譯,也即受了某種西化的洗禮,遂構成如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說的‘革命之謎’——在本世紀最初二十年里激進主義的形成。”[2](P2)陳建華對革命話語的詞源演變及內涵演變都做了詳細的考證和分析。中國古語里“革命”一詞是早就存在的,只不過最初在《易經》里的基本含義是改朝換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對舊皇族的殺戮。但是這里面臨的問題是革命合法性從何而來?是武裝背叛還是正義革命,其關鍵在于是否順應天道民心。因此革命的正義性、合法性多少年來聚訟紛爭沒有統一的標準,最后就成了“勝者王侯敗者寇”的強權邏輯,而世界范圍內英法革命的爆發,又提供了暴力革命之外的新的元素。正如陳建華所指出的:“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領域里產生新的含義,衍生出和平漸進和激烈顛覆這兩種政治革命模式。霍布斯鮑姆提出的英法‘雙輪革命’說即基于此”[3](P7),那么問題的關鍵是這種和平漸進的改革元素是如何進入中國的革命話語的,這就必須要借助日本這個東西方文化的傳播媒介,以及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學者是在何種意義上理解革命的。最早把日本含義的革命話語引入中國的就是梁啟超,梁啟超經過數年的對于革命話語的實踐和思考,最終對于這一與現代中國命運密切相關的詞語作了一個相對科學的界定。他從廣義和狹義的角度解決了革命話語中不同要素的體現。“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者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是也。”[4]可見梁氏對于革命話語所包含的諸多要素都進行了必要的涵蓋。其中的最廣義所說的有形與無形,范圍相當廣泛,既包括了制度層面也包括了思想和文化層面,且沒有運用暴力的要素完成這種變革,這與魯迅一直致力于的國民劣根性的改造不謀而合。而第二種含義則更多地體現在政治制度的變革,其手段則和平與暴力皆可。其狹義則是專指暴力革命,正如毛澤東對革命的說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5](P17)
但對于中國的革命歷史進程而言,卻并不是簡單的擇其一而否定其它的。仔細考察應該是三種涵義都有。正如費正清所說的:“在西方世界,革命一般發生在誕生它們的文化中。一般說來,革命首先是政治變革,是一種政治制度的改變,這種變革有時候也使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改變成為可能。我非常懷疑,當人們講到中國的‘革命’時,是否忽視了一個根本點,就是中國不僅進行了政治、經濟和社會革命,而且確實在進行整個文化的轉變……這些疑問就使我想到,中國發生的事情,是不是用‘轉變’這個字來概括,更精確一些?然而,我能看出,‘轉變’這個詞,除了用在宗教方面之外,不像‘革命’——我用這個詞來概括中國整個現代歷史過程——那么激動人心。”[6](P49-50)因此很多敘述中使用革命一詞更多地可能是因為這樣的話語更具有煽動性和表述的激動性。但具體到不同的個體在使用革命話語的過程中卻具有相當復雜的特質。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之中誕生的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對于革命問題自然會有他自己的思考,而這種對革命話語的獨特理解和使用通過對其早期書信中所涉及此類問題的分析,應該能夠了解魯迅思想深處對革命話語的真正態度及認識程度。
《魯迅全集》所收魯迅早期書信(1905-1927)共有269 封。其中給友人以及同鄉官員的大約200封,給許廣平60封(因為魯迅寫給許廣平的書信,作者本人于1934年將其中大多數作了增刪修改,編入《兩地書》出版。但是《兩地書》所收書信與原信差異較大,因為考慮到公開出版所以功用不同內容也差別較大,為準確了解魯迅當時的真實思想,本文所引用書信均為未經刪改的原信。)在這些書信中明確提及革命的次數并不多,但其變相提及革命和變革問題之處也不少,這些言論體現了魯迅早期的革命觀。
當辛亥革命剛剛發生時,魯迅以其知識分子的特有立場提出了自己的革命觀。1911年11月寫給辛亥革命后紹興縣議會議長張琴孫的信中明確提出了教育在共和大業中的重要作用。“比者華土光復,共和之治可致,地方自治,為之首涂。……側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則以公民程度為差。故國民教育,實其本柢。上論學術,未可求全于凡眾。今之所急,惟在能造成人民,為國柱石,即小學及通俗之教育是也。顧教育一端,甚關國民前途。故區區之事,亦未可緩。”[7](P350)魯迅在信中指出國民教育實在是地方民眾能否自治的關鍵,而地方自治則又關系共和之事是否可成。因此教育一端就成為甚關國民前途的大事。由此可見,魯迅對于國家改革大業的認識,從一開始就是遠離暴力而關注國民素質改變的,這也是梁啟超對革命所作定義中的最廣義的解釋。直到1920年5月4日寫給他的學生宋崇義的信中還談到“中國學共和不像,談者多以為共和于中國不宜;其實以前之專制,何嘗相宜?專制之時,亦無重臣,亦非強國也。仆以為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現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惜此又非今之學者所樂聞也。”[8](P383)魯迅在這封信中對于學生運動影響到學界其實是頗有看法的。他認為:“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于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贊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然由仆觀之,則于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9](P383)他在此信中明確指出學生的運動則于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既不能過譽,也不能過毀,但是如果沒有學問做底蘊,愛國之類,都是空談。由此也可見魯迅對當時的五四學生運動的態度,這也反映出他一直堅持的教育才是改變國家民族的主要舉措的觀念。但是1925年3月18日寫給許廣平的信中再談到教育以及中國的情況及將來時,則表示出他的悲觀和懷疑。他說“現在的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哪一國,其實都不過是制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罷了,要適如其分,發展各各的個性,這時候還未到來,也料不定將來究竟可有這樣的時候。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里,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里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么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對于現在這一個題目,都交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其中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的就是。”[10](P466)對于現在的中國卻是誰都沒有辦法的,將來也是虛幻的,而教育也不過如此而已。這表現出魯迅的悲觀、迷茫,因為現在的中國像一只黑色的染缸,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沒有別的出路了,可見魯迅實在是開不出改革的藥方了。至于他最初所堅持的教育救國論,自然也受到了質疑和否定。
魯迅在對教育的推崇產生質疑后,又明確地把改造國民性與中國的改革聯系起來(魯迅所使用的國民性改造話語其內涵就是今天的改革,之所以有人用革命,只不過是敘述更加引人注目而已。)1925年3月31日致許廣平的信中正面談到革命和改革問題:“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不是新添的壞,乃是涂飾的新漆剝落已盡,于是舊相又顯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最后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但說到這類的改革,便是真叫做無從措手。不但此也,現在雖想將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難。在中國活動的現有兩種“主義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們的精神,還是舊貨,所以我現在無所屬,但希望他們自己覺悟,自動的改良而已。”[11](P470)魯迅在對辛亥革命以來的革命過程進行了總結之后,認識到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專制共和那種制度的改變只是換個招牌而已。但同時他也清醒地認識到這類改革的艱難,不但無從下手,而且困難重重,對于當時活躍的兩種主義魯迅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他們的外新內舊。間接地表明了魯迅對當時的政治主義的疏離和批判,對改革國民性問題的思考和重視。在后面的一封信中魯迅對這個問題又進行了進一步的闡發,并更加明確了自己的態度。在1925年4月8日致許廣平的信中指出:“大同的世界,怕一時未必到來,即使到來,像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開起軍官學校來,惜已太晚。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不是因為顧家,他們也未嘗為家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的。”[12](P476)這段話首先指出了中國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為像中國現在似的民族,即使到了將來的大同世界,也是會被排斥在大門以外的。其次,魯迅認為孫中山的失敗在于對武力控制的乏力,并認為軍官學校的開辦已為時已晚,這反映了魯迅思想中的矛盾,也說明魯迅在對革命內涵的理解中,暴力革命和武力掌控的因素也是存在的。當然盡管他自己沒有主張武力的革命,但他對孫中山革命徒勞的評價和分析,也表現了這點。但很快又回到了國民性墮落的分析上來,并且認為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且伴隨著卑怯和貪婪。而且是比較頑固的劣根。在同一信中魯迅還談到了自己的反抗方式:“關起門來長吁短嘆,自然是太氣悶了,現在我想先對于思想習慣加以明白的攻擊,先前我只攻擊舊黨,現在我還要攻擊青年。但政府似乎已在張起壓制言論的網來,那么,又需準備鉆網的法子,這是各國鼓吹改革的人照例要遇到的。我現在還在尋有反抗和攻擊的筆的人們,再多幾個,就來試試,但那效果,仍然還在不可知之數,恐怕也不過聊以自慰而已。”[13](P476)自己想辦法起來進行攻擊的依然是“思想習慣”,這表明了魯迅一貫的思想革命和國民性改造的立場和態度。但是在另一封給許廣平的信中又反映出魯迅思想上對革命內涵的復雜態度,比如在1925年7月29日致許廣平的信中對革命黨的革命時的不夠暴力進行了批評。“我常想:治中國應該有兩種方法,對新的用新法,對舊的用舊法。例如‘遺老’有罪,即該用清朝的法律:打屁股。因為這是他所佩服的。民國革命時,對于任何人都寬容——那時稱為‘文明’——但等到第二次革命失敗,許多舊黨對于革命黨卻不文明了:殺。假使那時的新黨不文明,許多東西早已滅亡,那里會再來發揮他們的老手段。現在已他媽的罵背著祖宗的木主自傲的人,夫豈太過也歟哉!”[14](P513)在這段話里魯迅明確指出民國革命時不應該如此寬容和文明,應該學習舊黨的手段——殺,并且認為如果當時更堅決的使用暴力,則許多東西早已滅亡了。而在早些時候的另一封信中,也表現出魯迅的這種糾結。在1925年4月14日的信中談到宣傳對于革命的作用時指出:“我有時以為‘宣傳’是無效的,但細想起來,也不盡然。革命之前,第一個犧牲者我記得是史堅如,現在人們都不大知道了,在廣東一定是記得的人較多罷,此后接連的有好幾人,而爆發卻在湖北,還是宣傳的功勞。當時和袁世凱妥協,種下病根,其實還是黨人實力沒有充實之故。所以鑒于前車,則此后的第一要圖,還在充足實力,此外各種言動,只能稍作輔佐而已。”[15](P480)宣傳其實是非暴力的革命要素,但是魯迅既覺得好像是無效的,可是又覺得有點作用,并且舉例肯定了宣傳的功勞。可后面的話中很快就提到宣傳只能稍作輔佐而已,最根本的還在充足實力,此處的實力雖沒有明確是軍事政治實力,但肯定不是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實力。由此也可以看出魯迅對此的猶疑和矛盾。果不其然,魯迅在另一封給許廣平的信中就對自己的反抗和犧牲進行了質疑。在1925年5月18日致許廣平的信中談到:“我現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他們即使怎樣無理,事實上卻是著著得勝。然而,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么?我還要反抗,試他一試。”雖然還要堅持試一試,但是對于說話和弄筆墨這種反抗方式,也即國民性批判和改造的方式發生了懷疑和否定。“我那時曾在《晨報副刊》上做過一則雜感,意思是犧牲為群眾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眾就分了他的肉,散胙。”[16](P491)借用雜感中的言論再次表明自己犧牲的無意義。這不僅是對自己反抗方式的質疑,而且是對自己反抗價值和意義的懷疑。這恐怕是更可怕的一種認識和想法。從堅定不移地認識到改造國民性并積極投身到國民性改革的事業中,到后期對這種改革的意義和方式發生懷疑和否定,反映了魯迅思想隨時代發展的復雜變化,及對社會變革和革命的復雜性認識。
政治革命的局外人意識越來越強烈而明確。在1925年6月13日致許廣平的信中,魯迅對上海的學生運動表現了他一貫的理性冷漠。他說:“上海的風潮,也出于意料之外。可是今年學生的動作,據我看來是比前幾回進步了。不過這些表示,真所謂‘就是這么一會事’。試想:北京全體學生而不能去一章士釘,女師大大多數學生而不能去一楊蔭榆,何況英國和日本。但在學生方面,也只能這么做,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意外飛來的公理。”[17](P496)對于學生運動效果的質疑一如既往。而且還有淡淡的嘲諷。對于當時中國社會中影響最大的政治事件——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事件,魯迅表示了適度的關注。在1926年10月15日致許廣平的信中對北伐軍的勝利消息表示了謹慎的歡迎。“今天本地報上的消息很好,但自然不知道可確的。一,武昌已攻下;二,九江已取得;三,陳儀(孫之師長)等通電主張和平;四,樊鐘秀已取得開封,吳逃保定。但總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總是真的。”[18](P575)雖然其勝利的真實性并不確定,但這表明了魯迅對此的關注和肯定的態度。并且在1926年10月20日致許廣平的信中明確批評了那種只做學問不問政治立場的學者。“現在我最恨什么‘學者只講學問,不問派別’這些話,假如研究造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為之造嗎?”[19](P581)盡管魯迅激烈地批評這種沒有政治立場的學問,但對于自己他并沒有特別強調應該有鮮明的政治立場,這依然是他者的批評立場,并沒有把自己放在這個大的歷史漩渦中。在此后給許廣平的幾封信中,魯迅最關心的問題是自己到底應該選擇創作還是選擇教書的個人未來,而對于北伐戰爭只是偶爾從報上看點不知真假的消息,也很少提及。并且因為廣州當局對顧頡剛的邀請,而對當局的看人和用人眼光頗不以為然。而他自己的最大野心就是到廣州后給研究系也就是顧頡剛之流進行打擊,這是他的首要目標,其次才是同創造社聯絡,向舊社會進攻。第一個目標實為個人恩怨,而向舊社會進攻才是魯迅從事思想革命的正業。可見魯迅關注的重心所在,顯然并非當時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當然,我們不是要求魯迅沒有私心,畢竟顧頡剛之流對他的打擊和傷害讓他耿耿于懷。但這至少表明了他對當時北伐的關注和態度。在1926年11月26日給許廣平的書信中對廈大的國民黨進行了委婉的批評:“今天本地報紙上的消息很好,泉州已得,浙陳儀又獨立,商震反戈攻張家口,國民一軍將至潼關,此地報紙大概是國民黨色彩,消息或傾于宣傳,但我想,至少泉州攻下總是確的。本校學生民黨不過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開會,我覺得他們都不經訓練,不深沉,甚至于連暗暗取得學生會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開一回會,徒令當局者注意,那夜反民黨的職員卻在門外竊聽。”[20](P633)先是對北伐的進程表示了一定的關注,繼而批評本校民黨的幼稚,不經訓練,不深沉,表達了他的無奈,依然是一種置身事外的態度。在提到廈大風潮時,也對許廣平表明與己無關的態度和對此的不以為然。1927年1月5日給許廣平的信中提到:“校內似乎要有風潮,現在正在醞釀,兩三日內怕要爆發,但已由挽留運動轉為改革廈大運動,與我不相干。不過我早走,則學生們少一刺激,或者不再舉動,現在是不行了。但我卻又成為放火者,然而也只能聽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罷。”[21](P12)在1月8日給韋素園的信中則認為這種學生的改良運動,未必能改良也未必能改壞。保持了魯迅對于學生運動的一貫的態度。“與我不相干”這恐怕正是魯迅所要表達的真實想法。
在1927年“四一二”之后,魯迅的第一封信是寫給李霽野的,在信中簡單描述了廣州的情況,依然是旁觀者的立場。1927年4月20日在給李霽野的信中說:“這里現在大討其赤,中大學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別處我不知道,報上亦不大記載。其實這里本來一點不赤,商人之勢力頗大,或者遠在北京之上。被捕者蓋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這幾天放了幾個。”[22](P30)對于辭職的理由,也沒有說是因為要營救被捕學生未果而為,他的解釋是:“我在此的教務,功課,已經夠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閑氣。所以我決計于二三日內辭去一切職務,離開中大。”[23](P30)所以魯迅對于廣州的清黨事件參與極少,此后5月15日給章廷謙的信中所說“廣東也沒有什么事,先前戒嚴,常聽到捕人等事。現在似乎解嚴了。我不大出門,所以不知其詳。”[24](P33)“不知其詳”也表明了魯迅的局外人身份。而此后對顧頡剛之流對他辭職流言的解釋,更加說明了魯迅對這次政治事件的態度。1927年5月30日給章廷謙的信中說:“不過事太湊巧,當紅鼻到粵時,正清黨發生之際,所以也許有人疑我之滾,和政治有關,實則我之‘鼻來我走’之宣言,遠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顧傅為攻擊我起見,當有說我關于政治而走之宣傳,聞香港《工商報》,即曾說我因‘親共’而逃避云云,兄所聞之流言,或亦此類也歟。然而‘管他媽的’可也。”[25](P35)對所謂的“親共”傳聞,一概斥之為流言,并且表明他的離開與政治沒有關系。魯迅在撇清自己與政治的關系之后,又多次談到自己的打算,在給章廷謙的信中,他曾經說自己現在相信“剎那主義”,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顯得比較消極。到上海后,則抱怨除了應酬之外,無法看點書,或譯作文章,并明確表示遠離政界、學界。1927年9月19日給翟永坤信中表明了這種態度:“我先到上海,無非想尋一點飯,但政,教兩界,我想不涉足,因為實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許翻譯一點東西賣賣罷。”[26](P67)在自己的好友章廷謙無端受連累,傳言與共產黨有關而被捕的事件時。魯迅重申了自己的無奈和得過且過的態度。1927年12月9日給章廷謙信中說:“池魚故事,已略有所聞。其實在天下做人,本來大抵就如此。此刻此地,大家正相互斥為城門,真令我輩為魚者,莫名其妙,只能用紹興先哲老話:‘得過且過’而已。”[27](P96)而在 1927 年 12 月 19 日給邵文熔信中明確表示了這種局外人態度:“時事紛紜,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近兩月來,凡關涉政治者一概不做。昨由大學院函聘為特約撰述員,已應之矣。”[28](P98)至此魯迅對于政治革命的疏離從思想到行為都比較明確而自覺地得以完成。
總之,從魯迅早期的書信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魯迅對革命話語的不同理解和自己的參與態度。早期是積極主張教育改革,認為這是關系國家存亡的大事,到后來對此產生質疑和否定。但同時又積極投入國民性改革和批判中,這其中出現了很多矛盾的因素,對于暴力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魯迅有時是處于矛盾和猶疑之中的,再加上個人的很多恩怨,魯迅對自己所從事的國民性改革也發生了懷疑,雖沒有徹底否定,但卻表現出勉力為之的悲壯和底氣不足。而后中國政局頗多變動,魯迅值此多事之秋,更多地表現出他對政治革命的遠離態度,表明了他政治革命的局外人立場,頗多避之為恐不及之感。因此,從魯迅的書信中我們能認識到魯迅對于革命話語的復雜認識和自己立場的變化。對于全面了解魯迅的革命思想的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
[1]李歐梵.革命的現代性·序[A].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3]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梁啟超.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A].新民叢報[N].第46-48合號,1904年2月.
[5]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A].毛澤東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6]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魯迅.魯迅全集[C](11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1][22][23][24][25][26][27][28]魯迅.魯迅全集[C](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