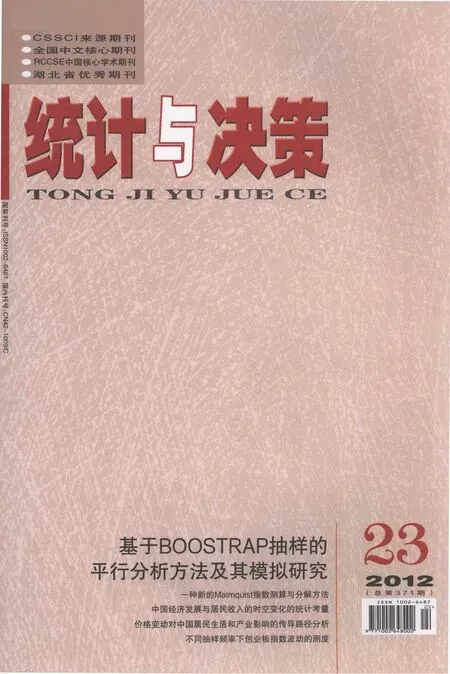基于區域合作治理視角的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考量
鄭永蘭,丁曉虎
0 引言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產業工人主體,其政治參與是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組成部分。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針對性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是我國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學術界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尚無定論。最早提出“新生代農民工”概念的是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王春光研究員,后來學者多采用年齡劃分來界定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新生代農民工一般是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1]。依據我國憲法規定,未滿18周歲的公民不能行使選舉權等政治權利,為方便研究,本文將新生代農民工界定為年齡在18~35周歲,具有農村戶籍而主要從事非農就業的人群。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是指新生代農民工關心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或其它公共管理活動,并試圖影響政治或公共管理體系構成、運行方式、運行規則和政策過程的行為。
1 調研數據材料的整理與分析
為了解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情況,課題組選取江蘇省鹽城市、南通市、無錫市、南京市4地作為調研區域,采用調查問卷與半結構訪談的方式,對隨機選取的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調研。筆者依據調研數據材料,通過構建Logit二元選擇模型探討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因素對其政治參與的影響,并分析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現狀。
1.1 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因素對其政治參與影響的Logit模型分析
為合理地分析新生代農民工自身若干因素對其政治
參與的影響,本文根據調研數據,構建Logit二元選擇模型,模型如下:

其中,participation是新生代農民工是否選擇政治參與的選擇變量,取值為1時表示選擇政治參與,為0時表示不選擇政治參與;gender是性別虛擬變量,取值為1表示為男性,為0時則為女性;age是年齡變量;married是結婚與否的虛擬變量,取值為1時表示已婚,取0表示未婚;education為受教育的年度變量;children為家庭子女數變量;wage為工資水平變量;polity為政治面貌虛擬變量,分為黨員(包括預備黨員)與非黨員兩個類別,政治面貌是黨員(包括預備黨員)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運用Stata12.0版本對該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新生代農民工自身若干因素對其政治參與影響的估計結果
表1給出了新生代農民工自身若干因素對其政治參與影響的估計結果,從準似然比檢驗結果Pseudo R2可以看出該模型整體擬合效果較佳。對于該二元選擇模型,系數估計值不能被解釋為對因變量的邊際影響,但系數的符號可以作為我們判斷的依據:如果為正值,表明解釋變量越大,因變量取1的概率越大;反之,如果系數為負,表明相應的概率將越小。
從表1中可以看出,家庭子女數變量的估計系數為負,其余均為正。其中,性別、結婚與否虛擬變量以及年齡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教育程度變量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工資變量與政治面貌虛擬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也就是說,對于性別、結婚與否、政治面貌虛擬變量和工資變量而言,性別為男性的新生代農民工和政治面貌為黨員(包括預備黨員)的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概率更大,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較未婚的概率更大。對于年齡、工資和教育程度變量而言,隨著年齡、工資和教育程度的提升,其政治參與的概率更大。表中,家庭子女數變量的估計系數為負值,但是家庭子女數變量不顯著,也就是說,家庭子女數對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概率無直接影響。
1.2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現狀分析
1.2.1 受教育程度提升,參與意識增強
與傳統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顯提高。在640份以新生代農民工為調查對象的有效問卷中,僅有102位是小學文化程度,僅占樣本15.9%,本次調查對象中未見傳統意義上的文盲。文化水平的提升在客觀上使得新生代農民工開始有能力關注時政,逐步形成參與意識。通常來說,公民文化水平越高,參與意識也就越強。調查顯示:有高達85.3%的調查對象經常或偶爾收看、收聽時事新聞;有83.1%的調查對象經常或偶爾與家人朋友談論國家大事;經常和偶爾關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新生代農民工占71.7%,參見表2。筆者在訪談中得知,他們是關注黨政方針政策的,只是他們的關注選擇性很強,他們更關心與自身或家人工作、生活有密切聯系的政策方針。當被問到“自己是否應該有選舉、被選舉等政治參與的權利?”時,筆者得到的是一致肯定的回答。

表2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關注情況調查統計表
1.2.2 參與愿望強烈,參與渠道受阻
問卷調查中當被問及“是否希望加入黨團組織?”時,78%的調查對象選擇了希望或非常希望加入;高達83.3%的新生代農民工希望或非常希望參加居住地社區的選舉與管理活動;而代表新生代農民工權益組織的缺位直接體現為高達81.7%的調查對象“希望加入屬于農民工自己的組織”,參見表3。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新生代農民工有著較為強烈的政治參與愿望。可是,當被問到是否參加了最近一次家鄉村委會選舉和務工地社區選舉時,結果有些令人失望,參加的比例較低,分別是16.4%和5.0%,“政治邊緣人”的現狀再次顯現。訪談中筆者了解到新生代農民工大多與家鄉的聯系日漸淡漠,回鄉參與選舉的動力不足,而且回鄉又需要付出一定的經濟、時間等成本,這就導致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寧愿放棄回鄉參加選舉的政治權利;另外,繁瑣的程序和相關制度的限制又導致他們不能或不愿參加務工地城市的選舉,久而久之導致了他們政治權利的“虛置”。[2]

表3 新生代農民工參與意愿調查情況表
參與行為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參與渠道不暢而導致的。理論上,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我國公民,能通過人大、政府、政協或媒體等多元渠道表達利益訴求,然而在現實中,這些渠道作用有限,而且并不暢通,甚至流于形式。隨著新生代農民工參與意愿的增強,更加凸顯參與渠道的不暢,而且還會在一定程度上使新生代農民工的參與意愿蒙受打擊,形成惡性循環。
1.3 理性參與為主,非理性參與潛在
新生代農民工的理性化參與程度比較高,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關于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目的的調查顯示,高達75%的調查對象政治參與的目標是謀求農民工群體的利益,46.3%的人選擇謀求自身的權益,比例遠高于那些在道德層面處于更高層次的“出于自身社會責任感”等目標,見表4;第二,體現為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制度化的參與方式。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82.5%)傾向于選擇法律途徑、求助媒體、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反映等方式來處理自身遇到的侵權行為;當其他工友遭遇侵權要找有關部門反映時,他們也大多選擇支持。這種制度化傾向的路徑選擇無疑體現了當前新生代農民工更為理性的參與態度。當然,我們不能忽視主流趨勢外的個體,在與新生代農民工的交流中,筆者發現一部分調查對象把極端(罷工、鬧事、自殺威脅等)維權行為作為“走投無路的最后選擇”,贊同此舉的新生代農民工占調查總數的25.6%。這種潛在的抗爭意識讓人擔憂:如果抗爭取得成功,他們實現了維權的勝利,這無疑會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將會有更多的人傾向于選擇此類極端途徑進行抗爭,這勢必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如果抗爭以失敗告終,付出的可能會是血的沉痛代價。

表4 新生代農民工參政的目的(多選)
2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困境與區域合作治理的釋解
基于調研材料分析和已有相關研究成果梳理,可以將當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困境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的限制;參與渠道的不暢通;組織和參與型政治文化的缺失;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素質的限制等。不難發現,這些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因素都與政府管理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如圖1。戶籍制度最初的功能是人口信息的統計,時至今日,戶籍功能已嚴重超載,它承載了諸如身份界定和權利分配等社會管理功能,而且這些異化的社會管理功能甚至有喧賓奪主的趨勢。依附于戶籍制度的政治權利繼而呈現出城鄉的顯性不平等,使得具有農村戶籍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權利弱化;參與渠道不暢通一方面由于制度化參與渠道成本較高,另一方面是制度化參與的“門檻”過高,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連“入門”的資格都沒有;新生代農民工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這與政府的民間組織發展與管理政策有直接的關系:繁瑣的行政“主管單位”掛靠制度和嚴格的組織審查制度使得民間組織的建立絕非易事,發展舉步維艱;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形成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當前我國以政府為主導的治理環境下,相關制度從設計到實踐仍需政府來組織和協調,這使得政府對于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培養擁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因素的限制主要體現在文化素質和參政技能上,義務教育的推廣與深化和農村基礎教育設施的完善與師資隊伍的提升是消解此種困境的重要路徑之一,而在當前政治生態環境下,這些工作都需要政府來主導實施。

圖1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困境與政府的關系
(實線代表直接關系,虛線代表間接關系)
針對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面臨的諸多困境,學者們提出了若干建設性的對策。然而這些分散的對策建議終歸不是一套系統的解決方案,其忽略了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是一個跨越行政邊界的區域公共問題,故而無法從根本上突破制約治理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瓶頸。筆者認為,區域合作治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釋解這些困境。首先,區域合作治理機制的建立使得區域內各地區在實質上突破了戶籍限制,“區域內流入地與流出地實行統一的雙重管理”,[3]使得戶籍導致的制度性“鴻溝”得以弱化甚至修復,這是區域合作治理帶來的優勢,它將逐步掃除制約合作主體共同利益實現的障礙;其次,區域合作治理建立的專職化協調性組織,能夠在疏通常規參與渠道的同時開拓新的特色化參與渠道,從而大大降低參與“門檻”,壓縮參與成本;再次,區域合作治理機制將充分挖掘和利用社會力量。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給予的政策扶持,提供民間組織建立與發展的寬松空間,逐步組建起代表新生代農民工利益的非政府組織。新生代農民工民間組織實現從無到有的突破將是新生代農民工權益保護史上的里程碑,它的出現將會使新生代農民工的弱勢地位得以階段性的扭轉;最后,區域合作組織在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之前開展全方位的宣傳,提供免費參與技能培訓。政治參與期間的針對性宣傳與指導,輔之非參與期間參與知識的普及,多管齊下有助于逐步形成成熟的參與型政治文化,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參與的積極性和參政技能的提升。
3 結語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過渡性群體,其弱勢的社會地位與其對社會、經濟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是不相稱的。政治參與權利的保障不僅是其社會地位得以提升的重要基礎,也是我國民主政治進程不斷推進的內在要求。如何消解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困境,進一步保障他們的政治權益?筆者認為區域合作治理是一種可嘗試的創新型機制,它是西方社會所倡導的治理理論在區域公共管理活動中的具體運用,是解決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權利保障問題的新思維。當前,需要借助科學、規范的研究工具,從制度設計,配套支持和推進模式等多角度逐步構建系統的區域合作治理機制,從而為實踐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豐富的理論支持。
[1] 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N].工人日報,2010,(6).
[2] 趙排風.城市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有序政治參與問題研究[J].河南社會科學,2008,(4).
[3] 臧乃康.多中心理論與長三角區域公共治理合作機制[J].中國行政管理,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