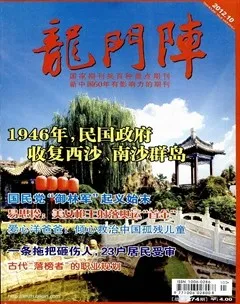“文革”中,我參加“三支兩軍”
熙成
一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四川當兵。當時,解放軍的主要任務就是“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和軍管、軍訓。隨著全國陷入大規模武斗局面,內戰一觸即發,我們的任務又由“三支兩軍”演變成了“制止武斗”。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是全國有名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參與人數之多,損失之重,全國無地能比。“文革”初期,紅衛兵派系很多,他們在全國各地串聯,到北京的人數最多。后來經過分裂重組,基本形成兩大派別,在重慶及川東地區是“反到底派”和“八一五派”,在成都則是“八二六派”和“紅成”派。兩派都標榜自己是正宗左派。人民解放軍支左到底支持哪一派,我們也不清楚,成都軍區領導要求我們保持自身穩定,靜觀其變,隨時執行命令,服從指揮。這樣,我們就成天待在軍營里待命,無所事事。后來,兩派武斗開始了,我軍才陸續由縣城開進成都、重慶等大城市,并在那里住了下來。接著又是靜觀待變,哪里有武斗就到哪里制止。四川兩大派別的武斗不斷升級,開始在城市里斗,后來到農村發展組織,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
有一次,兩派群眾組織在城里組織大批紅衛兵乘汽車浩浩蕩蕩向郊區開去,與農村兩派群眾會合,各自占領山頭,處于嚴重對峙狀態,隨時有發生大規模武斗的可能。部隊奉命到郊區去制止這場即將發生的武斗,我和另外兩名同志當時在成都軍區總醫院擔任軍管任務,也要求隨大軍一起到郊區。當我們部隊趕到郊區時,只見兩邊山頭上人山人海,黑壓壓的一大片。我們部隊就站在兩派之間開始喊話,要求他們各自回去抓革命促生產,堅守自己的崗位,不要鬧分裂,要團結。可是他們哪里肯聽。兩派人員距離遠的有幾百米,最近的只有幾十米。他們開始用石頭、土塊你打過來我打過去,石頭、土塊在我們戰士頭上飛來飛去,呼呼作響。兩派群眾均有被石頭、土塊打中受傷的,解放軍戰士也有被砸傷的。我們軍管會的一名副營長叫匡順生,被飛來的石塊砸傷頭部,頓時血流滿面。我看到他用手去捂傷口,血就順著他的手往外冒。經過簡單包扎,我們把他送回醫院休息。幾天后,他還在喊頭痛。我們軍管會有3個人,都住在一間房子里,我與匡副營長的床是頭對頭,每天晚上都聽到他胡言亂語說夢話。我估計他是被石頭砸傷后留下后遺癥了。再后來他轉業了,聽說不到60歲就去世了。
那次兩派群眾的武斗,直到天黑,人們才陸續散開,由城里去支援的造反派們也撤了回來。
部隊在群眾組織撤退完后開始返回。途中,又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差一點要了我的命。那天天黑后,我們軍管會的同志隨大部隊一起往回撤,我因一點小事落在了行軍部隊的后面,但距離并不遠。突然,有十來名造反派從我軍行進的反方向走過來。他們走到我跟前時,突然有兩個紅衛兵把我拉住,我還沒有來得及呼救,前面的隊伍已經走遠了,戰友們也沒有發現。造反派抓住我不放,邊推邊搡,硬說我是劉少奇的黑兵,要把我送到他們總部審問,任我怎么解釋,他們都不聽。有兩個人還說要把我的帽徽、領章摘下來,一邊說就一邊動手來扯我的領章,摘我的帽徽。我心想,如果沒有了領章、帽徽,那就真成了“劉少奇的黑兵”,那個年代這樣的人不知被打死了多少,而且不會有人來過問。就在這個危急關頭,后面來了一隊在另一個地方制止武斗的解放軍。他們見狀,立即把我從造反派手里搶過來,我才得以脫身。這件事發生后,我更加小心,無論到哪里,都不敢脫離大部隊,不敢單獨行動。
二
“支農”是我軍“三支兩軍”的重要任務之一。1968年農業大豐產,但大豐產不等于大豐收。由于很多地方都在鬧革命、搞武斗,農作物無人去收,成熟的稻子倒伏在田里,紅薯爛在土里,花生沒人挖,高粱無人收。有關部門發現這些問題后,要求軍隊到農村開展“支農”工作,幫助農民把地里的糧食搶收回來。
就在那年秋天,由我擔任組長,一名參謀擔任副組長,帶領一個排30多人,來到成都郊區一個公社開展支農工作。我們背著背包來到公社,直接去了生產隊。30多人在一個生產隊住下來后,第二天就開始工作,白天分別到田邊地頭搞宣傳,同群眾談心,了解情況;晚上回來交流各自的所見所聞。通過一段時間的工作,我們逐步取得了群眾的信任,群眾到我們工作隊反映情況的越來越多。我們對地里莊稼無人收割的情況進行分析,發現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勞力不足,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不在隊里搞生產,而是到外面搞武斗去了;二是領導不力,公社的領導班子基本處于癱瘓狀態,多數干部回家去了,留下來的人不愿意下到基層抓生產;第三是人心不穩。我們針對這些問題分別展開工作。首先動員群眾將出去搞武斗的人勸回來,就地抓革命促生產;同時,組織老人和婦女下地勞動,把爛在地里的農作物收回來。我們組織公社領導開會學習,要求他們務必深入基層抓革命促生產,保證農業不受損失。我們還在群眾中廣泛宣傳黨的政策,以穩定人心。經過一段時間扎實細致的工作,外出武斗人員回來了不少,下地勞動的人也多起來了。
不久,我接到團部通知,說部隊有更重要的任務,支農人員要歸建。我們工作隊向公社相關領導作了一些交代后,就撤回來了,重新回到團部。
三
1967年下半年,我與另外兩人組成軍管會,奉命對成都軍區總醫院實行軍事管制。另外兩人,一位是團政治處副主任張本初,一位是副營長匡順生。從人數上看,我們這個軍管會勢單力薄,不過我們是奉軍區命令,所以底氣很足,膽子也很大。我們剛到醫院時還挺有權威,不僅院領導全力支持我們,造反派也十分歡迎我們,醫院的傷病員都對我們軍管會抱有很大期望,希望醫院不要亂,外面的造反派不要進來。
我們一到醫院就馬不停蹄地展開工作,召開會議,進行政策宣傳,提出相關要求。醫院秩序迅速恢復,軍管會的工作也受到各方好評。但不久,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接連發生。造反派召開批判會,不請示不報告,直接把院領導揪上臺,讓他們低頭彎腰,有人還動手打他們的耳光,用腳踢他們腰部。我們軍管會對這樣的行為進行了堅決制止,但效果不太理想。到后來,軍管會的工作受到更大挑戰,做的指示、貼的布告都不起作用了。有一次,造反派竟然召開全院群眾大會,要求軍管會派人參加,面對面地回答他們的問題。軍管會主任沒有到場,便叫我去參加大會。我去的時候,參加會議的人已全部到齊,把大禮堂擠得滿滿的。我一走進會場,“熱烈歡迎”、“打倒軍管會”、“打倒賀××”的口號聲就不絕于耳。我一看陣勢不對,但又不能退出來,只好硬著頭皮參會。他們讓我站在臺上,一個接一個地向我提問。對付造反派我還是有些經驗的,那就是要有耐心,任何時候都不能對他們發脾氣,如果不小心,把他們惹火了,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二是回答他們的問題時,不能太具體太明確,更不能隨便答應他們的要求,對一些根本不能辦的事情,絕不能隨便許愿;三是無論回答什么問題,都要有針對性地念一段毛主席語錄,然后才說我們軍管會如果不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你們隨時可以提出意見。他們見我態度還可以,提問時火藥味也就不是太濃。首先發問的是一個造反派小頭目,他原是醫院的辦公室主任,他的問題是,你們軍管會為什么不讓批判走資派,還要保護他們?我回答說,走資派可以批判,但只能文斗不能動手動腳搞武斗,你們院領導大多是老紅軍、老干部,他們為了革命,曾經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個個身上都留有多處傷痕,他們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了,你們讓他們在臺上站幾個小時,還讓他們低著頭彎著腰,有的還挨你們的耳光,腰部被踢打,你們如此作為究竟為什么?主持會議的是一位年齡較輕的女造反派頭目,聽我這么一說,可能覺得心里有些不安,就叫大家安靜些,說:“對軍管會同志講的話要好好聽。”提問的人很多,對能夠回答的問題,我都一一作了答復,不好回答的,就老實說要回去研究一下再作答復。會議開了兩個多小時,最終不歡而散。當我回到軍管會時,其他兩位成員都有點驚訝,他們擔心我發生什么意外,正準備向軍區打電話匯報呢。他們見我沒什么事,才安下心來休息。
我們軍管會在總醫院工作了半年多,經歷了許多事情,其中有些事至今仍難以忘懷。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醫院有位副政委,很年輕,是個大學生,抓了很多造反派頭頭,不僅在醫院抓,還派人到郊區去抓,抓來后把他們都關起來。可不久翻案了,造反派重新當權,這位副政委就倒了大霉,在批斗中被打得遍體鱗傷。我們軍管會卻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造反派打人。
1971年林彪墜機事件后不久,我們“三支兩軍”人員陸續撤回部隊。到1973年,我們“三支兩軍”辦公室工作人員都重新作了安排,有的留在軍區政治部機關,有的回到了原來的單位,而我則被調到了軍高炮團政治處工作。
(責編: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