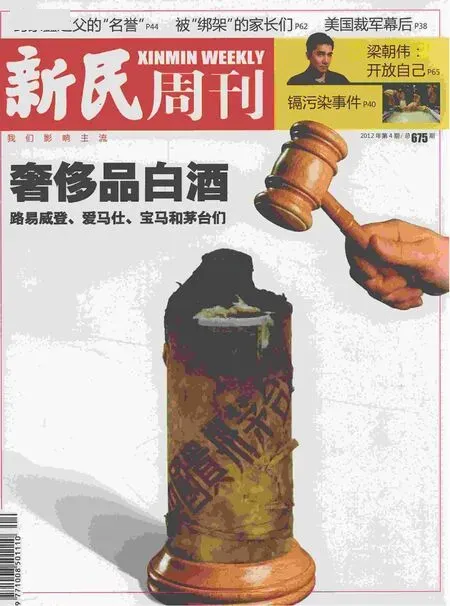普通話說得不錯
林奕華
不少人問我我的普通話為何講得尚算流暢——流暢者,該是在講普通話時不會被母語廣東話那九聲造成的復雜性牽牽絆絆——我第一時間總有“一言難盡”之感。皆因始末有三個,卻不易選擇誰先誰后:(一)曾在臺灣當過半個學期的初中學生;(二)更早之前,在香港已慣性隨大人上電影院看國語片;(三)或比更早還要再早之前,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已是南和北兩種文化的熔爐。有這么一個說法,香港島是南來的大陸新移民較多——北角便有“小上海”之稱;九龍、新界則是原居民的大本營。我的童年,本來就是一半一半。父親的家庭,即我的姑姑們住在羅便臣道;母親的家庭,包括外婆和阿姨舅父,住在西洋菜街。往來雖不頻繁的他們,碰巧又都是鐵桿電影迷,于是,港九兩地的戲院,成了給我提供廣東與外省文化的教室。
姑姑們看的是西片和國語片——粵語片她們不是完全不看,只是口味上與外婆不同,戲院更是重要考慮:香港島的戲院印象中就是較少放映地道的粵語片,不是沒有,是更多坐落在銅鑼灣與西環。姑姑們帶我去的卻多是中環一帶,看國語片就是“娛樂”,看西片就是“皇后”。當年的中環可以說是內地今日的CBD的原型,商廈林立,即便當時尚未被冠上大都會光環,可是洋氣的感覺肯定不會少。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是邵氏,便是國泰出品的國語片,確實由于洋氣十足連帶讓觀眾也自覺時髦起來。若用今日的語匯,就是國語片雖不及西片“型”,但是它仍然穩坐“潮”的交椅,不似粵語片,“土產”的“土”之余,也是“老土”的“土”。是題材決定面貌嗎?是,也不是。因為,外婆(那些年她不過四五十歲)作為老一輩觀眾會挑古裝宮闈大鑼大鼓的戲才買票入場,不代表粵語片就沒有年輕觀眾,其實它也一樣五花八門。愛情類型片中,謝霆鋒爸爸謝賢,與后來變身著名邵氏導演的楚原的太太南紅,便是經典的銀幕情侶。謝賢南紅的《黑玫瑰》(1965,楚原導演),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史密斯夫婦》。只是這些“土法炮制”的“流行物種”在身價上到底較難取得國語片的優勢和觀眾認同。
在電影院學普通話,大抵是我這輩子最早趕的潮流。之后,當電視扮演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時,它教給我的則是另一種時髦——美式英語:可笑的我曾立下長大后要當操美式英語的新聞主播的宏愿——影與視,誰說不是現代人避無可避的Vanity Fair(名利場)?
然而,我并未因為愛上國語片而“忘本”。粵語片市場沒落是在60年代末期,因過去曾是票房支柱的紅伶嫁的嫁、息影的息影而迅速式微(“七日鮮”式制作的粗制濫造也是原因之一)。但自小與蕭芳芳陳寶珠培養了“血濃于水”的感情——小學二年級的我曾在教室中參與“搞分化”的明星政治活動:每個同學必須為支持芳芳抑或寶珠表態——以及粵語片獨有的世故又天真的氣韻,使我至今仍無比關注香港一個名叫“粵語片研究會”的組織,重新發掘這些后來因賤賣給兩家電視臺而被謔稱“殘片”的深層價值。
身為舞臺劇導演,自2006年的《包法利夫人們》開始,我的劇目基于演員的選擇而在語言上有所取舍,致使“你的普通話說得不錯”的背后,隱隱還有另一個問號:“是為了迎合更廣大的內地市場,你才拋棄你所熟悉的廣東話?”這問號又隨著香港人與內地人日漸趨向激烈的“本位論述”而愈來愈敏感。觀此現象,似是再次印證了歷史依然有被記憶冷待的時候——香港人跟普通話的淵源當然還有很長的故事可講(70年代初的香港娛樂事業,大部分靠臺灣輸入),只是利害關系當前,有誰還有耐心從頭聽起?
雖然,語言只是表面,語境才是內蘊;語言只是手段,語境才是目的——正如《包法利夫人們》在大陸港臺的53場演出可以證明它是三地共通的文化現象——我們經常只把語言當作工具,是否因過于把“我講,你聽”視為理所當然,卻不是追求互相明白和自我聆聽所致?在這前提下,我由衷覺得自己的普通話程度與廣東話仍有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