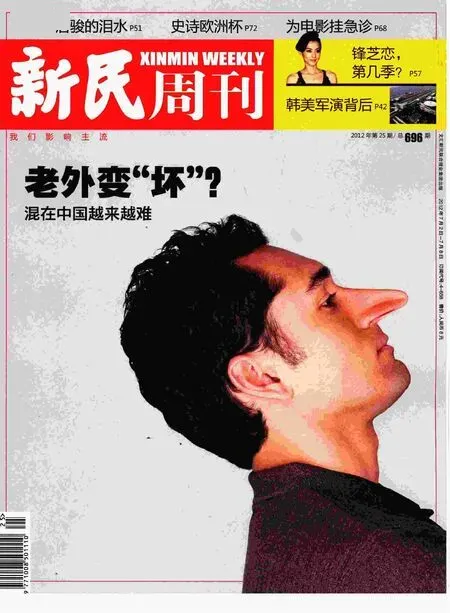混在中國的日子
黃祺


20年前,只要生一張一目了然的洋面孔,普通話帶點兒化音,一個老外很容易在中國如魚得水甚至一舉成名。但如今,混中國越來越難。且看愛思考的老外,怎樣解讀自己身邊的變化。
老外的黃金時代
普通中國人“認識”的第一個老外,是電視熒屏上的大山。這個加拿大留學生,1990年代初露面中央電視臺元旦晚會,在一檔小品節目扮演名為“大山”的外國青年。大山一夜成名,此后多年,每逢中國佳節,大山都會出現在央視的節目中,表演相聲、小品或者擔當主持人。大山成為整個1990年代中國最有名的老外,也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認識并喜愛的唯一一個老外。
今天看來,當時中國觀眾喜愛大山的原因,與其說是被他流利的普通話折服,還不如說是被他愿意效仿中國文化的態度折服。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大眾的心態十分糾結,大家一方面對自身經濟和物質的落后感到自卑,對“外面的世界”心存向往,另一方面,強大的民族自尊心,又期待著得到“別人”的認可。從大山身上,國人的復雜心態得到安慰:你看,老外也來學咱們了。
在大山之前,對于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的年輕人來說,到中國去不是一個“正常”的選擇,只有那種極其另類的角色,才會有勇氣去封閉、貧窮的中國。但大山的成功,給外國人以啟發,因此,除了公司委派、政府機構派駐等原因來到中國,很多年輕人開始通過留學、當志愿者等途徑,試圖到中國混出個模樣。
盡管會遭遇被圍觀、被指指點點的困惑,但總的來說,整個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最初幾年,是老外混中國的黃金時代。法國人戴亮2000年來到上海,對那時候外國人“如魚得水”的境遇,他體會深刻。
“那個時候,老外很‘寶貴。什么叫‘寶貴,我慢慢跟你說。”戴亮的普通話絕對不比大山差,不過,他不靠這個吃飯,他那愛思考的腦子,比流利的嘴皮子更有價值。戴亮在中國生活近10年,現在是一名用中文創作和演唱的歌手。
到上海留學第三天,22歲的戴亮接到留學生宿舍管理老師的通知,下午有一家演藝經紀公司來招聘外國人做兼職。戴亮非常愛好文藝,接到通知就參加了經紀公司的面試。戴亮輕松過關,招聘的條件很簡單,洋人面孔、會說普通話、長得“稍微帥一點”。
出身普通家庭,從未當過演員的戴亮,在到中國的第三天就接到了一次演出。第一次拍戲的地點是上海百樂門酒店,他扮演舊時代某國領事館官員。從此以后,戴亮片約不斷,生活也變得異常忙碌。“上午上課,下午拍戲。”
這樣的兼職收入不菲。“跑龍套8小時400元,加班1小時加100元,如果有角色,2000-5000元不等。”22歲的戴亮,生活驟然發生了改變。戴亮在老家也曾勤工儉學賣手機,這算是輕松的工作,但跟在中國當演員相比,賣手機來錢實在太慢了。
當時的中國演藝界,四處發掘洋人。“我背著吉他在路上走,會有騎摩托車的人停下來遞名片給我,問我是否愿意跟他去演出。”這樣的遭遇,戴亮碰到不止一次。有才藝的外國人會被叫去上電視,沒有才藝的,則被聘用為兼職“副經理”,為各種公司充門面。戴亮的不少留學生同學,就被叫去當“副經理”,從廣義上講,也是一種表演。
處處受優待,處處被照顧,還能賺不少的外快,生活向戴亮展現出誘人的一面。戴亮說,曾有一段時間,自己真的有些迷惑,生活變得“太簡單了”。
如今30出頭的戴亮回憶起那一段經歷,慶幸自己沒有迷失。因為他受到的教育,因為他的宗教信仰,因為母親時常提醒,戴亮開始理解這一切都不太正常。讓戴亮記憶猶新的一幕,是他在上海繁華的靜安寺街頭,看見自己做模特的廣告,一家香港服裝公司找他代言,讓他登上20多米的巨幅廣告墻。戴亮自認外形不錯,但絕沒有達到做服裝模特的標準, “那一刻,我覺得很可笑。”
既是貴賓又是道具
從普通大學生到明星般的待遇,戴亮為期一年的中國留學生活就像夢境。幸好,戴亮一年后回到法國老家,遠離五光十色的中國“夢境”,他有機會靜下來好好想想。戴亮在法國用兩年時間研讀關于中國社會的各種資料,這讓他對自己在中國的經歷有了更多的理解,也讓他在重返中國并定居后,對自己的道路有著清晰的規劃。
戴亮再次回到中國,從事自己喜歡的音樂工作。跟之前一樣,2003年的中國演藝圈,依舊很喜歡老外,他常常受邀參加電視節目。在參加節目時,中國導演總是要求戴亮演唱中國歌曲,比如《月亮代表我的心》,最好還能說一段繞口令。戴亮明白,中國觀眾需要這個,老外唱中國歌,能讓中國人的自尊心得到極大的滿足。不過,戴亮不喜歡這種“道具式”的表演,他用中文創作歌曲,帶點搖滾風,他希望唱自己的歌,但這樣的要求往往讓導演不滿。最后,戴亮只好妥協,唱一首中國歌,再唱一首自己的歌。
在很長的時間里,老外在中國既是“貴賓”,又是“道具”,越來越多的老外意識到這一點。
同樣活躍在上海演藝圈的老外華波,名片上印著“多語主持人”的頭銜,目前正在上海戲劇學院攻讀播音主持專業的碩士學位,畢業后,他將是中國播音主持專業唯一的外國籍碩士。
伊朗帥哥華波有著語言天賦,到中國僅6年時間,就滿口成語、俗語、唐詩,他的普通話測試成績是“二甲”,這個水平,大多數中國人都難以達到。華波參加過電視漢語大賽,其中的遭遇讓他倍感屈辱。華波的漢語水平恐怕沒幾個老外比得過,但他還是很早就被淘汰。“最后進入前五名的一個老外,漢語特爛,只不過長得像足球明星。”比賽結束后,導演還要他們身著各國民族服裝上臺,以達到“各國人民齊聚中國”的舞臺效果。
在這樣的節目中,中國人對老外文化、宗教缺乏尊重,也讓華波很無奈。漢語大賽中有一個評委向華波提問:“酒是誰發明的?”伊朗是一個絕大多數人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信徒穆斯林禁酒。華波回答:“我不知道,我們不喝酒。”
作為“貴賓”,老外享受了高于國人的待遇;作為“道具”,老外們常常感到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這種復雜的感受,常常讓外國人困惑。戴亮理解,那個時候,中國急于得到國際認可,所以電視節目里需要一個洋面孔來宣揚中國文化。
中國人的新態度
不過,戴亮發現,一切正在改變。
戴亮說,2005年左右開始,老外變得不像他剛來時那么“寶貴”,再沒有人找他當模特,因為更多專業的外國模特進入中國。“中國人開始區分,這個老外是唱歌的,不是當模特的。”
這時候再上電視節目,當戴亮提出唱自己原創的中文歌曲,節目導演會說:“這個人有想法,唱唱看。”
到2010年以后,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讓更多的中國人見識了更多的老外。記者采訪2010上海世博會時發現,許多外國國家館的工作人員都是中國通,這些人不僅漢語流利,還深諳中國交際之道。幾千萬中國游客,在世博會上與各色老外“抬頭不見低頭見”,對于出國機會不多的內地人來說,是難得的體驗。
最近一兩年,戴亮感到,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發生了進一步改變。“中國人發現,原來老外里也有好人、壞人。”特別是西方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蕭條,讓中國人自信心膨脹,老外在一些人眼中,從“貴賓”淪落為淘金者。
這樣的評價,讓老外們原本享有的優待,變得越來越少。與10年前相比,戴亮的人生變得“正常”,這種生活讓他感到踏實。他要為自己的演出奔波,要通過演出贏得更多人的喜愛,他必須努力才能獲得成功。
“現在,一個老外來中國,如果他沒什么本事,他就什么都不是。”戴亮慶幸自己來得比較早,比后來者更了解中國,而且有自己的特長。
如今的中國,越來越難混。
戴亮在上海管理一個非營利機構,他舉了一個例子。“如果我現在需要招聘一名職員,我打算付給這個人每月5000元的工資。一個中國人和一個法國人來應聘,我很可能要中國人。中國人更了解中國,他們外語水平很高,這個工資水平對他來說也還可以,而且中國人很勤奮。我為什么要招這個法國人呢?除了可以跟他用法語聊聊老家,他沒有更多的優勢。”
事實也的確如此,戴亮接納過一個法國女孩做實習生,沒多久,她就回國了。對于這個女孩來說,她在中國沒什么優勢,還不如回國過得自在。
華波同樣知道,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會說繞口令就能成名的時代,他打算在碩士畢業后攻讀博士學位。他的目標不是與老外們競爭,而是與中國人競爭。
現在,中國人更能接受老外們的評價。七八年前,戴亮在電視上被問得最多的問題是“你喜歡中國嗎”、“你怎么學中文的”,現在,他常被問“這個事情如果發生在法國,你們怎么看?”
日本人吉井忍,在中國媒體上撰寫專欄,內容涉及在中國的生活,也偶有對中國社會現象的評價甚至批評。如果回到20年前,中國讀者恐怕很難接受一個老外的“指手畫腳”,更別說是一個日本人。
因《尋路中國》而被中國讀者熟悉的美國人何偉,1990年代以志愿者身份到內地小城涪陵當老師,他描寫中國生活的第一本書是《江城》,之前在臺灣出版。《尋路中國》在中國內地風行以后,何偉發現,中國內地讀者已經不再那么“脆弱”,他們不再回避他筆下的“社會陰暗面”,甚至對何偉挖掘的社會細節十分喜歡。《江城》簡化字版終于在今年與內地讀者見面,事實證明,并沒有多少人反感這個老外對中國的的嬉笑怒罵。
正如戴亮所說,外國人在中國的境遇,與中國人的態度有很大關系,而中國人如何看待老外,取決于他們怎么看待自己。看起來,老外們的“貴賓”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是,排斥與鄙視,同樣是一種“畸形”。
采訪結束,戴亮跨上白色助動車,融入上海淮海路涌動的人潮中,隨著中國社會的開放,老外注定越來越“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