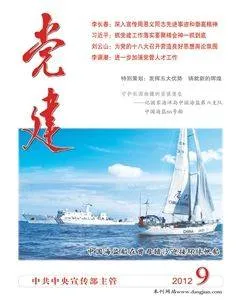美國中東戰略:一廂情愿的選擇
“9?11事件”后,美國中東戰略日趨轉向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霸權戰略,最典型的體現就是發動兩場反恐戰爭和進行“中東民主改造”。
美國本想更牢固地掌握中東地區主導權,卻使該地區力量對比嚴重失衡,并導致了美國最大死敵——伊朗作為地區霸權國的崛起。
事實表明,美國策動的民主改革僅僅是攪動起中東地區長久積郁的內部矛盾,使中東未來走向更加不確定。
奧巴馬政府縱然有心全力收縮,緩解與伊斯蘭世界關系,但其“中東新政”調整有限。這種因路線錯誤導致的“外交后遺癥”,不是奧巴馬短期的“靈巧外交”所能挽救的。
目前,敘利亞政府軍和反對派武裝戰事處于膠著狀態,美國正在主導制訂“禁飛區”行動方案,以期待實現大中東戰略。其實,過去相當長時期,美國在中東一直奉行現實主義政策。“9?11事件”后,美國中東戰略日趨轉向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霸權戰略,最典型的體現就是發動兩場反恐戰爭和進行“中東民主改造”。但十年過后,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非但未持續上升,反而日漸衰減,最終不得不重新進行戰略調整。這種戰略調整能否達到預期目的仍很難料定。
戰略嬗變:從維持現狀到顛覆秩序
以“9?11”事件為分水嶺,美國中東戰略可分為清晰可辨的兩大發展階段:自二戰結束到“9?11”事件發生前的近60年內,美國基本奉行的是維持現狀的均勢戰略;“9?11”事件后,美國轉而奉行全面改造的霸權戰略,這實際也是從經典現實主義向進攻性理想主義的轉型。
1.維持現狀的均勢戰略:“9?11”之前的美國中東戰略。在中東,美國長期奉行的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實用政策。石油供應和防范蘇聯是兩大核心內容,而石油利益又是美國在該地區最具體的利益。美國在中東的總體戰略就是促進和維護該地區穩定:
首先,在國家層面,采取“代理人政策”,避免干涉中東內部事務。1945年2月,沙特國王與羅斯福達成“石油換安全”的歷史性交易。從此,沙特提供石油,美國提供安全就成為美國與沙特,乃至美國與海灣國家合作的基本模式。因此,盡管這些國家在人權、民主方面不盡如人意,但美國基本都是睜一眼閉一眼。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因深陷越戰泥潭,因此在中東更加依賴扶植“代理人”來確保美國對中東的控制。總體來說,美國對中東事務的介入相當有限,所用手段也謹慎而節制(尤其是忌諱使用武力),這就使美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戰略自主性。其次,在地區層面,推行相互制衡的均勢政策,防止出現威脅美國霸權的地區性大國。美國的中東政策主要由阿以政策和海灣政策兩大部分構成。在阿以乃至大中東范圍內,美國通過扶植以色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國家來抑制阿拉伯民族主義;在海灣地區,美國通過支持沙特、科威特等溫和阿拉伯國家來平衡伊拉克等激進阿拉伯國家,同時又通過伊拉克來制衡伊朗。
在阿以關系問題上,美國不遺余力地支持以色列,正是因為以色列能夠成為美國平衡阿拉伯力量的戰略籌碼。美國的海灣政策同樣如此。海灣地區作為世界上石油貯量最豐富的地區,伊朗和伊拉克均有可能稱霸海灣,因此美國基于利益考慮,在海灣地區的基本政策就是防止任何一方過于強大,避免海灣油田被任何一國控制。因此,當1980~1988年的兩伊戰爭爆發后,美國在伊拉克節節勝利時,美國就暗中支持伊朗,而當伊朗轉守為攻后,美國又開始偏袒伊拉克。總體看,美國的目的就是要使兩伊兩敗俱傷。1990年,當薩達姆入侵科威特,并可能稱霸海灣時,美國對伊拉克的態度驟然轉變。美國在1991年發動海灣戰爭的基本目的就是恢復地區均勢,防止中東石油為少數國家控制,這就決定了它是一場點到為止的有限戰爭。
總的來看,這種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中東戰略,較為有效地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并保持了戰略靈活性,應該說得大于失。
2.顛覆秩序的霸權戰略:“9?11”后的美國中東新戰略。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國家實力的膨脹使美國再次滋生出全面稱霸的帝國野心。在很長時期內,美國對怎樣塑造世界和中東一直舉棋不定。而“9?11事件”的爆發使美國最終將恐怖主義鎖定為最大威脅,將中東作為反恐主戰場。在美國看來,要想根除恐怖主義,就必須對中東進行全面改造。
首先,通過發動戰爭建立親美政權,進而實現地區霸權。蘇聯解體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極大地刺激了美國控制中亞、南亞和西南亞的地緣政治興趣。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五角大樓就開始準備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也就是“9?11事件”發生多半年前,就表示要改變巴格達政權。伊拉克戰爭就是美國在實力膨脹后武力稱霸世界的戰例。
其次,推行民主改造,將影響范圍從外交延伸到內政領域。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哲學深受新保守主義熏陶。在他看來,其他國家所能做的就是效仿美國模式,而美國也負有某種“天定命運”去救助和推動落后國家向這一方向前進,在必要時甚至可以采取干涉和高壓的方式輸出民主理想。“9?11事件”發生后,小布什提出“新十字軍東征”口號,要用美國價值觀來“改造”伊斯蘭世界,因此,美國必須采取“一種新政策,一個推動中東自由的戰略”。他這種“新政策”的最明顯體現就是美國在2004年2月推出全面改造中東的“大中東計劃”。
陷入困境:美國中東戰略的轉型
美國中東戰略轉型并未給其帶來相應戰略收益,反而日趨被中東問題所困,這與美國新時期霸權戰略本身存在的缺陷直接相關。
1.黷武主義本身存在缺陷。二戰結束后,美國先后在朝鮮和越南發動兩場局部戰爭,結果都是被戰爭所困。因此里根時期的國防部長溫伯格與其助手鮑威爾主張如果不是與美國的重大利益有關,美國不應該隨便動用武力。但小布什政府對前輩的這些告誡不屑一顧,而決意通過“反恐戰爭”來實現霸權目的,并在短短兩年時間里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了兩場戰爭。阿富汗戰爭使美國的霸權觸角首次延伸到中亞這一權力真空地帶,并在俄羅斯、中國與伊朗三個潛在或現實對手之間打入楔子;伊拉克戰爭則使美國首次在阿拉伯世界心臟地帶獲得戰略立足點,并使美國有可能通過控制伊拉克和中東石油,達到控制其他大國的目的。
但這種戰略收益極其有限,離美國的政策目標相距太遠。首先,發動戰爭使美國深陷戰爭泥潭。美國本想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根除恐怖,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權,但反恐戰爭使伊拉克陷入前所未有的動蕩,美國在伊拉克陷入了“輸不起、打不贏、走不了”的戰略窘境。同時,美國推動的“民主化”使伊拉克各派分離意識不斷增強,這使美國塑造的“中東民主樣板”面臨全面失范危險。其次,戰爭破壞了中東脆弱的力量平衡,導致了美國最大死敵——伊朗作為地區霸權國的崛起。
長期以來,伊拉克一直是制約伊朗崛起的最主要因素。對美國來說,兩伊關系的長期敵對,使美國長期坐收漁翁之利,以低廉成本維護著海灣利益。但小布什的反恐戰爭就像公牛闖進瓷器店,把中東本就脆弱的地區平衡完全搞砸了:一方面,兩場反恐戰爭為伊朗崛起提供了重要機遇。阿富汗戰爭幫助伊朗鏟除了塔利班政權,伊拉克戰爭又幫伊朗剪除了薩達姆政權。在不存在地區力量制衡的條件下,伊朗自動成為影響中東地區命運的決定性力量。另一方面,美國“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使伊朗生存危機感陡增,并由此激發了伊朗盡早崛起的危機意識。伊朗決策者認為,伊朗作為美國眼中的“邪惡軸心”和“暴政前哨”,隨時可能成為下一個打擊對象,對美國服軟不會有什么好處,這也是伊朗近些年在核政策上日益強硬的根本原因。目前,伊朗通過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正迅速填補因缺乏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地區核心國家留下的空白,并由此直接威脅美國在中東的霸權地位。這與美國一再強調的“防止地區霸權國家崛起”的中東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對伊朗怎么辦”已成困擾美國的頭號難題。
2.“民主改造戰略”存在重大缺陷。美國要對深受伊斯蘭傳統思想熏陶的中東進行全面改造,某種程度確有“改造伊斯蘭文明”的嫌疑,這種外交思路不僅缺乏“政治正確性”,而且完全不切實際。
中東地區矛盾錯綜復雜,其社會發展程度與美國所期待的自由民主標準相去甚遠。以伊拉克為例,它是1920年由英國把奧斯曼帝國中的巴格達、巴士拉、摩蘇爾三省合并而成,這三部分始終沒有完整地整合到一起。薩達姆之所以能在該國長期統治,是因為“他們具有在地區所有三個政治傳統(部族政治、極權主義和民族主義)中來回活動的出色能力。他們一直在和這個世界下三維象棋,而美國人似乎只知道如何走跳棋——每次只有緩慢的一步。”
事實表明,美國策動的民主改革僅僅是攪動起該地區長久積郁的內部矛盾,使中東未來走向更加不確定。近兩年來,美國盡管為推行“大中東計劃”不惜巨額投入,但“民主改造”結果,一方面是損害了與中東傳統盟友沙特、埃及等國的關系,使這些國家離心傾向增加;另一方面是使伊斯蘭極端勢力借機崛起(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伊朗等均出現類似問題),尤其是2006年1月激進組織哈馬斯的上臺,令美國極為被動。而且,哈馬斯還與伊朗、敘利亞等反美勢力出現了相互聯手的跡象,從而對美國的中東利益構成直接威脅。
從長遠看,由于伊斯蘭勢力是中東唯一有影響力的反對派,而且中東地區反美主義情緒高漲,因此,政治改革要么可能出現“伊斯蘭民主化”,要么使醞釀于“草根階層”的反美情緒上升為現實政治力量,出現“反美的民主化”,無論哪種結果都有悖美國的國家利益。播下龍種,卻收獲跳蚤。由此使美國“民主改造”陷入欲罷不能但又難以維系的困境。
戰略收縮:美國中東戰略的再調整
美國霸權周期歷來是“強大—擴張—衰落—收縮”。自二戰以來,美國對外政策共經歷了兩次大的收縮:一次在20世紀70年代的尼克松時期。冷戰結束后,美國憑借一超地位,在中東全面擴張,結果無疑導致國力透支,深陷戰爭泥潭,加之國內金融危機加劇,既定政策難以為繼,被迫開始新一輪戰略收縮。這種收縮從布什后期就已開始。
而2009年上臺的奧巴馬進一步加快了這種戰略收縮步伐。奧巴馬繼承的中東外交遺產,與當初克林頓從老布什繼承下來的完全不同,中東現實要求其對地區秩序進行重組。在美國實力不濟、四面受困的背景下,奧巴馬明確放棄小布什時期“文明沖突”的話語體系,盡可能緩解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關系,依靠“巧實力”維護自身利益。奧巴馬上任后,大幅推行“中東新政”:與反美國家接觸,如對伊朗發出和談信號、對敘利亞選派新大使等;加大扶植親美國家,用地區盟友和相互制衡來取代美國直接統治;降低反恐調門,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盡快從伊拉克撤軍,將反恐戰場轉移到巴阿地區。其“中東新政”的核心目標就是緩解伊斯蘭世界反美情緒和“東向”傾向。
奧巴馬意圖通過戰略收縮化被動為主動,重新掌握中東主導權。但奧巴馬很難超越中東已有的現實:從傳統安全看,中東的戰略重要性決定了美國不會真正退出。美國不可能承受“失去中東”代價,尤其不可能容忍敵對的伊朗填補權力空白。從非傳統安全看,中東活躍的恐怖活動決定了美國無法輕易離開。目前,伊拉克已成為恐怖主義的策源地;阿富汗塔利班也已卷土重來;2011年中東劇變更使“基地”等極端恐怖組織得以恢復、壯大力量。恐怖主義不絕,美國就不可能從中東從容脫身。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政府縱然有心全力收縮,緩解與伊斯蘭世界關系,但其“中東新政”調整有限。有學者認為,奧巴馬中東政策與布什并無本質不同,而只是前者的副本,這種政策必然失敗。這種因路線錯誤導致的“外交后遺癥”,不是奧巴馬短期的“靈巧外交”所能挽救的。(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馮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