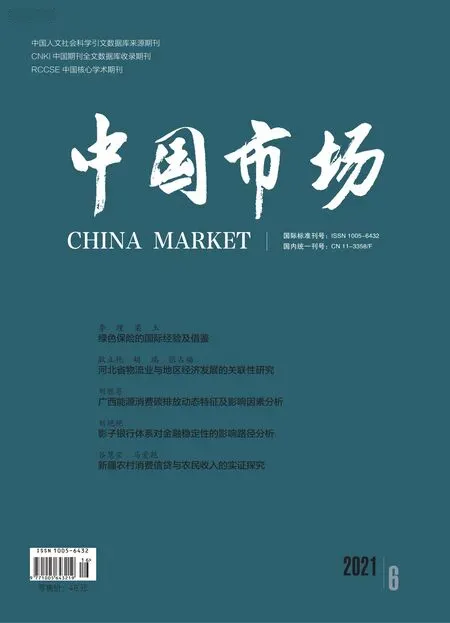環境規制分權與治理成本在政府間分擔的分析
張文彬 張良剛



摘要:本文探討了混合治理結構下我國現有的環境治理成本在各層級政府之間的分擔方式,分析中央政府分擔支出的必要性,指出地方財力與環境職能之間的不匹配性以及地方環保部門的獨立性問題,指出我國環境執行成本在分擔方式上改革的方向。
關鍵詞:環境規制分權;執行成本分擔;轉移支付
中圖分類號:F205
在實踐中,非對稱跨界污染的廣泛存在以及在我國分權治理結構下難以避免的以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地方政府經濟競爭,產生中央政府干預的必要性,環境治理結構表現為集權、分權混合結構。滿足環境標準的過程是有成本的,在混合治理結構下,我們面臨環境治理成本在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分配問題。而目前的文獻主要關注不同政府層級之間環境規制職能的分工問題,卻很少涉及環境標準執行成本的分擔問題(Segerson et al.,1997)。
環境標準執行成本在政府層級之間的分擔問題之間關系著環境標準設定是否有效率、環境標準執行成本是否有效率,地方財力與環境職能之間的匹配性以及環境執行機構的獨立性等問題,這些都直接影響環境規制的有效性。在以前分析中,我們只是簡單的假定由地方政府完全承擔環境標準的執行成本,而且中央政府在其決策中考慮到地方政府的執行成本。那么,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擔執行成本、而中央政府在其決策中卻不考慮這種成本支出的方式是否合理,如何形成合理的環境標準執行成本的政府層級分擔方案是本文的研究內容。
一、雙重道德風險與過度規制
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雙重道德風險可能會惡化環境規制的效率。Segerson et al.(1997)在跨界污染情形下由中央政府設定最低標準、地方政府負責執行(設定至少高于最低標準的具體標準)的制度安排中,分析了執行成本分擔問題的重要性。由于跨界外部性的存在,為了避免地方政府設定偏離最優的過松的標準,需要中央政府設定標準(最低標準)。如果中央振幅完全不承擔成本,機會主義動機使其選擇過度規制,制定過高的標準;如果中央政府完全承擔成本,地方政府則將失去創新和成本最小化的正確激勵,這便是因為成本分擔問題引致的不同政府層級之間的雙重道德風險問題。Segerson et al.(1997)考慮到跨界外部性和雙重道德風險,構建一個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環境政策形成過程中的互動行為的博弈模型,表明完全由中央支付和完全由地方支付兩種規則分別會導致中央和地方的道德風險,均會形成過度規制的無效率,而當且僅當跨界外部性足夠大時,中央完全支付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率的標準設定。
比如在美國,在1995年無資助命令改革法案(Unfunded Mandate Reform Act)出臺之前,美國國會在1986年到1994年之間通過了多達72項無中央資助的中央命令(Segerson et al.,1997),地方政府認為這種命令極大加重了地方財政支出的負擔,地方財政缺乏足夠的能力去承擔這種日益增長的執行成本。比如俄亥俄州的Columbus市政府估算其2000年執行聯邦政府的環境政策的支出占其城市預算的1/4以上(Segerson et al.,1997)。在我國,地方政府對本轄區的環境問題負責,因此,地方政府承擔了大部分環境標準的執行成本,2008年,我國財政支出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支出為1451.36億元(決算數),其中中央財政支出僅為66.21億元,僅占4.56%。在這一分擔方式下,如果中央政府并不考慮地方政府的執行成本,勢必造成環境標準過緊問題,從而導致地方政府缺乏激勵執行標準。在實踐中,如果中央政府并不承擔相應成本,很難保證其決策能夠完全考慮到地方的執行成本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尋找一種合適的執行成本分擔方式來破解這種雙重道德風險所導致的效率損失問題。
二、地方財力與環境職能之間的匹配性
在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地方政府是本轄區環境治理的主體,承擔絕大多數環境治理的執行成本,2008年地方環境保護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95.44%,地方財力與環境職能之間的匹配問題尤為重要,如果地方財力與其需要履行的職能并不匹配,地方政府自然難以完成其執行任務。所以,不同成本分擔方式通過這一途徑影響環境規制的效率。我們從地方總體財力、地方財政支出結構以及地方不同政府層級財力結構角度出發討論這一問題。
從中央和地方的財力分配來看,根據圖1,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我國地方財政收入占國家總收入的比重從1993年的78%下降到1994年的44%,中央政府對財政收入的控制力明顯上升而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明顯下降。但是,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并沒有在1994年出現明顯的拐點,且總體上呈增長的趨勢,到2009年接近80%。因此,從支出角度來看,地方政府依然居于完全主導地位,分稅制改革并沒有改變這一點。就環境保護支出而言,該項指標地方財政支出比重超過整體比重近16%,而剔除掉中央政府在國防、外交上的支出之后,只超過整體比重10%,而且,中央政府在環境標準建設、環境科技等方面的投入并沒有計入該項指標。所以,考慮到我國較高的財政支出分權結構的現實,在地方政府對環境問題負主要責任的情形下,地方政府試圖要求中央政府承擔更高的環境治理成本的份額的空間盡管有,但并不是很大。
實際上,地方財力與環境職能之間匹配性的問題在于地方財政支出中分配給環境保護部分的支出和其履行環境職能之間的匹配性。在中國式分權結構下,財政收入激勵和政績考核需要,為增長而競爭導致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結構偏向于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而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公共服務的支出(傅勇、張晏,2007)。顯然前者的投入可以直接產生GDP并能在短期內促進更多新的GDP以及財政收入的產生;后者在短期內表現為財政支出的擴張以及在短暫任期內難以轉化為GDP,因此,政府競爭會加劇財政分權對地方公共支出結構的扭曲。我國財政年鑒從2007年開始單獨報告地方財政支出中的環境保護支出項目,從表1可見,2007和2008年我國地方政府環境保護支出分別為961.23億元和1385.15億元,僅占地方本級財政支出的2.51%和2.81%,僅高于主要依賴于中央財政的外交、國防、科學技術以及文化體育與傳媒四個項目的支出,因此,環境保護在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偏低。根據陳斌等(2006),地方經費總體缺口達40%,其中人員經費,公用經費、監督執法經費、儀器設備購置經費、基礎設施經費缺口率分別為12 .9%、30%、50.8%,104.5%和146.2%,基礎設施經費和儀器設備購置經費的缺口最大。所以,我國地方環保部門預算明顯偏低,難以與其環境保護職能相適應。
以上基于加總數據的分析可能忽視了省份之間的差異。從分省地方政府支出來看,根據表2,江蘇省地方財政支出中的環境保護支出數額最高,其次為內蒙、四川,最低的分別西藏、海南、天津,因此,環境保護的財政支出數額并不和地區的發展水平相關,沒有呈現明顯的東、中、西的差異。而從人均環境保護支出來看,則西部地區,尤其是西北地區的數值明顯高于其他地區。最后,從各省份環保支出占其本級財政支出的比重來看,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比重明顯高于東部地區,內蒙、寧夏、青海最高,在5%以上,上海最低,不到1%,但是與上文提及的美國城市環境保護支出占其財政預算收入的10%~25%有明顯的差距。上述現象可能和環境保護支出統計中包含了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有關,這兩項地方財政支出在2008年分別達到301.33億元和19.29億元,總計占地方財政環保支出的23.15%。退耕還林工程涉及除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6個東部省份之外的其余25個大陸省份,其中長江上游地區、黃河上中游地區、京津風沙源區①以及重要湖庫集水區、紅水河流域、黑河流域、塔里木河流域等地區作為重點區域,而這些重點區域主要分布于我國西部地區。限于數據缺失,我們不妨假設在這兩項支出90%、80%、70%、60%屬于西部地區的情形下,如果剔除這一支出項目,西部的環境保護支出、人均環境保護支出以及環境保護支出占本級財政支出的比重發生了明顯的變動。根據表3,即使有90%的地方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支出屬于西部地區,剔除之后的西部地區人均環境支出和比重的優勢雖然明顯下降,但是兩項指標仍高于廣東、福建等東部省份,另外,占本級支出的比重還超過天津、上海。我們再從2008年各省份環境治理投資占GDP的比重來看,根據表2,最高的是寧夏,但僅為2.81%,其次是為浙江,省份環境治理投資占GDP的比重偏低,且與經濟發展程度也基本上沒有正向關系。不過,從環境監測經費來看,江蘇最高,廣東次之,東部地區基本上高于中西部地區,人均環境監測經費則是內蒙最高,東部地區仍有明顯優勢。因此,省份在環保支出內部結構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可能因為東部地區的環境治理水平相對較高,并將重點轉向環境監測。
為了進一步討論省份環保投入差異的原因,我們選擇人均GDP、人均本級地方財政支出、單位GDP能耗、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單位工業增加值SO2排放和單位工業增加值COD排放6個省份特征與上述環保資金投入的相對值做相關性分析。簡單的相關系數表明,表征省份經濟發達程度的人均GDP和地方財政環保人均支出、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不相關,而與環保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呈顯著的負相關,但與人均環境監測經費呈顯著正相關,因此經濟發達程度與環保投入的重要性并沒有相關性。表征省份財力的人均本級地方財政支出則只與地方財政環保人均支出和人均環境監測經費正相關,因此地方可支配財力仍是地方環保支出的重要保障。表征省份能耗強度、污染排放強度的指標與地方財政環保人均支出、環保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和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基本上呈顯著的正相關,這意味著環境、能耗問題相對嚴重、環保壓力大的省,其環保資金投入的相對值也較大,但是這些地區可能仍處于環保治理的初級階段,在環境監測方面的投入相對較低,環保投入的資金需要壓力較大。
因此,從省份差異來看,地區經濟的發達程度與地區人均環境保護財政支出和支出占本級支出比重并不呈正相關,即發達地區的支出結構并不優于欠發達地區,甚至不及欠發達地區。這和傅勇、張晏(2007)發現地方財政支出結構的扭曲并不會伴隨經濟增長而自動糾正的結論是一致的。如果不對當前政府治理結構加以調整,通過經濟增長并不能解決環境保護支出比重偏低的狀況。同時,我們也發現,重大生態環境工程項目的開展也會深刻影響一個地區環境保護支出。上文提及的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工程對于加大西部地區環保支出和提高環保支出比重發揮重要的作用,上述工程的實施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央轉移支付的支持。但是,目前轉移支付在地方環境支出方面的誘導作用仍主要體現在少數工程上,沒有形成全面、系統化的誘導機制。最后,地方可支配財力決定其環保資金投入,而節能減排壓力大的省份在這方面投入的相對值也較大,同時這些省份往往也是欠發達省份,因此,這些地區的環保投入資金的增長空間的拓寬難度較高。
這種不匹配性在地方政府的不同層級之間亦表現為明顯的差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本轄區的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因此,省、市、縣三級政府都是本轄區環境保護治理主體,而且縣級政府是環境治理最基層的政府機構。根據國家環監局和美國環保協會基于我國8個省(山西、遼寧、吉林、江蘇、湖北、湖南、廣東、海南)、4個直轄市和4個其他城市(武漢、西安、鄭州、馬鞍山)為單位的調研表明,2004年省、市、縣三級環境執法機構的財政預算資金平均為183.8萬元、236.5萬元和64.8萬元,與2003年比較而言,省、市增長較快,而縣級僅增長1.5%;而就各級環境執法機構實際支配資金(包括專項資金、預算外資金)來看,省、市、縣三級平均分別達到220.7萬元、466.1萬元、185.1萬元,省市兩級的預算外資金大幅增長而縣級預算外資金明顯下降。因此,在實行《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關于環保部門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后經費安排的實施辦法》之后,相對于省市兩級,縣級機構的經費壓縮較多,且沒有及時通過財政預算補充,資金缺乏保障。縣級機構資金的缺乏直接導致縣級環保執行機構人員素質結構偏低,中專以上(不含中專)比例僅為63.1%,本科以上比例不到10%;執法設備落后,縣級設備估值平均僅為44.86萬元,不到市級的25%,人均車輛數為0.08輛,達到三級以上標準的僅為59.3%(陸新元等,2006)。而在《國家環境監管能力建設“十一五”規劃》執行以來,中期評估也表明縣級環境監管能力建設總體仍較慢,達到建設標準的縣級環境監測機構不到17%;全國區縣級環境監測機構平均16人,低于《全國環境監測站建設標準》的三級標準,環境監測的專業人才比例偏低;監測執法經費不足問題仍未有效緩解(吳舜澤等,2009)。基層環保部門的經費現狀與其作為“處于環保‘戰場的最前沿,是環保事業的根基和命脈”的地位極不匹配。
所以,因為政府治理結構中的激勵扭曲和中央轉移支付的誘導作用有待完善,地方財政支出中分配給環境保護部分的支出偏低,和其履行環境職能之間的不匹配性較高。而且,這種不匹配性在縣級環境執法機構呈現更為突出的矛盾。目前環境標準執行成本的分擔模式直接導致地方執行能力欠缺,執行效率低。
三、成本分擔方式與環境執行機構的獨立性
成本分擔方式會影響環境執行機構的獨立性,進而影響地方環境標準的執行能力。執行成本在不同政府層級之間的分配決定著各級地方政府執行經費的來源構成。在我國,在環境保護的政府支出中,地方政府居于絕對主導地位,而且,地方環境保護行政部門的資金來源明顯依賴于預算外資金,包括排污費、行政收費和專項資金等,在2003年,排污費收入占地方環保經費來源的51.3%②。地方環保部門對排污費的依賴產導致環保部門對企業征收排污費采取策略性行為,甚至故意放縱企業排污,從而獲得收入,那么,環保部門由監督保護環境轉變成傾向于放縱污染 (裴敬偉,2009)。為了治理“亂收費”、預算外資金膨脹等問題以及排污費收入與部門經費掛鉤導致的諸多不利影響,我國在2003年頒布《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關于環保部門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后經費安排的實施辦法》,規定排污費必須納入財政預算,列入環境保護專項資金進行管理,大多數用于治污項目補助,取消了排污費20% 提留作機構自身能力建設的制度安排,并要求東部地區一步到位、中西部地區分三年完成。
環保機構收支兩條線的改革之后,地方環境保護行政部門的經費來源將基本上依靠地方財政預算。而就目前我國地方預算編制情況來看,并沒有對環境保護方面有明確的規定,因此,地方環境保護行政部門在財力支配上對地方政府獨立性基本喪失。這意味著地方環境保護行政部門的執行能力及其效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意愿。如前文所述,在當前政府治理結構下,地方政府預算在不同支出項目上的安排具有一定程度的彈性,環境支出等公共服務的比重受到生產性服務支出的擠壓,直接導致地方環境部門經費的緊張。而且,由于在經費上完全依賴于地方政府,經費獨立性的喪失也導致地方環境機構執法獨立性的喪失,甚至還要為地方“創收”服務,因此,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面臨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短期矛盾,地方政府,尤其是欠發達的地方政府可能出于經濟增長的目的而直接干預環保機構的執法。比如在陸新元等(2006)的調研中發現,在認為環保執法機構處罰不合理的情形下,企業的最先選擇是,與執法機構所述“環保部門協商”和與“政府協調”,而不是法定的“行政復議”、“行政訴訟”,這與法定的執法程序不相符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國環境執法彈性較大,企業傾向通過與地方政府及其行政結構的協商這種非正規渠道來“擺平”處罰的可行性大,環保的執法受到地方政府不合理的干預。而且,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環保部門還需要承擔招商引資工作,被視為企業落戶絆腳石的“環評在先”和“三同時”③ 制度無法等以保障;環保部門要處罰一些重大違法行為必須要經過地方有關領導同意,甚至連日常到企業履行正常的環境檢查義務也要經過相關部門批準④。因此,如何提高地方環保機構在經費上的相對獨立性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四、結論及改革方向
本文探討了混合治理結構下,我國現有的環境標準執行成本在各層級政府之間的分擔模式與我國環境治理存在的問題。首先,在地方政府完全承擔或者承擔絕大部分環境標準執行時,除非環境地理外溢效應足夠大,否則可能會出現中央政府的道德風險問題,即過度規制。因而在地理外溢效應并不明顯的污染物治理方面,如果有中央政府設定標準的話,可以考慮中央政府也承擔部分成本來避免過度規制問題。其次,地方財力與環境職能之間并不匹配,這和政府治理結構中的激勵扭曲導致的環境支出在地方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偏低有關,也和當前的財政體制有關。盡管地方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比重提高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相當一部分地方財政支出實際上來自于中央的轉移支付,這種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在環境支出方面的誘導作用有待加強。地方財力與職能的不匹配性在縣級層面表現的最為突出,而這一層級也是環境治理職能的主要實施者,從而導致基層環境標準的執行能力的欠缺。最后,無論是2003年以前的地方環境行政部門的經費主要來自于排污費和行政收費還是以后來自于地方財政預算,都無法擺脫地方環境行政部門對地方政府的依賴性,因此也難以保證地方環境行政部門的獨立性。上述問題都要求我國環境執行成本在分擔方式上有所改革。
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環境治理成本分擔方式的改革方向:
首先,在中央政府設定標準、地方政府負責執行的環境治理結構中,完全由中央政府和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擔環境治理成本都不是最優的,可能會因為雙重道德風險問題導致低效率。因此,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擔環境治理成本。例如,中央可以采取配套資金的方式,根據地方政府的投入多少給予相應比例的配套。這樣一來,一是可以避免中央政府完全不承擔成本下可能產生的過度規制問題;二是能夠減輕地方財政壓力;三是能提高地方治理的積極性,提高環保支出在地方財政支出中的比重。
其次,針對不同類型的污染實施不同的資金配套方案。對于影響全國生態環境安全的全局性環境問題,治理費用主要由中央財政承擔;對于局部對稱污染,則應當由主要由相關地方政府分擔,對于財力較弱的地區,中央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給予專向補貼;對于非對稱跨界污染治理,考慮到我國東富西貧、南富北貧,通常上游地區或者上風向地區是欠發達地區,下游和下風向地區是發達地區,中央政府可以在生態職能區劃分的基礎上,確定利益相關方,建立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將受益方(發達地區)的上交的轉移支付轉移給欠發達地區(上游或者上風地區),作為跨界污染治理的專項資金。如果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在環保方面有支援,可以扣減這部分的轉移支付。結合我們實證部分提出的環境治理邊際成本遞增的現象,欠發達地區(上游或者上風地區)的環境治理成本低于發達地區(下游或者下風地區)治理上游跨界污染轉移的成本,因而這種轉移支付是有效率的。
第三,中央政府的環境配套資金撥付應該考慮地區財政收入能力的差異。我們的研究發現我國省際政府環境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人均環境方面的財政支出并不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財政能力相關,而是與其因為產業結構導致的節能減排壓力有關。由于中西部地區污染密集型、能源密集型產業的比重較高,因此其用于環保方面的財政支出比重較高。因而這些地區環境財政支出比重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有限,而且其財力也難以保障,因而需要中央政府在配套資金方面給予這些地區照顧。
第四,中央政府在環境治理專項資金配套過程中,要關注基層環境行政部門財力與職能的不匹配性。縣級環境行政部門是政府環境治理最基礎的部門,也是經費、專業人員需求缺口最大的政府層級,極大制約了其環境行政能力。基層財政緊張的問題與當前的分稅制密切相關,因此,從長期來看,這個問題有賴于財政體制的改革。但是,在近期內,需要中央政府考慮設立針對基層的環境治理配套專項基金,以專款專用的方式直接撥付給基層環境行政部門用以添置環保監察工作設備,配備專業人才,提高行政能力。
第五,建議中央政府規定地方財政支出中環境支出應該達到的最低比重,從而使得環境行政經費得以保障以及獲取具有相對獨立性,避免因為經費問題限制了地方環境部門在行政、執法過程中的獨立性。
最后,建議開征環境稅。將目前的企業排污費等收費項目規范化,由費改稅;計稅對象為超過一定污染強度(污染排放占其總產出的比重)的企業,從而促進企業采取更為清潔的生產工藝;環境稅稅收收入歸地方政府,主要用于轄區內的環境保護支出。
注釋:
① 顯然,內蒙、河北、山西在環保支出及其比重方面遠高于北京、天津的原因與其為京津風沙源區密切相關。
② 根據陳斌(2006)的數據計算而得。
③ 建設項目中的環境保護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制度。
④ 詳見郭遠明等:《地方環保局長“夾縫執法”》,《瞭望(新聞周刊)》,2006年9月;郄建榮:《基層環保薄弱狀況尚未根本扭轉 一線環保執法現狀透析》,法制網,2009年9月2日。
參考文獻:
[1] Segerson,K.,et al.,1997,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in Federal System: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Unfunded Mandates”,In: Braden,J. B. and Proost,S. (ed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a Federal System,Edward Elgar Publisher,Cheltenham,UK,1997,43-65.
[2] 陸新元,Daniel J. Dudek,秦虎等.中國環境行政執法能力建設現狀調查與問題分析[J].環境科學研究.2006,(19).
[3]傅勇,張晏.中國式分權與財政支出結構偏向:為增長而競爭的代價[J] .管理世界.2007,(3).
[4] Hutchinson,E. and Kennedy,P. W.,State Enforcement of Federal Standards: Implications for Interstate Pollution”,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8,30(3):316-344.
[5] 吳舜澤,逯元堂,周勁松等.國家環境監管能力建設“十一五”規劃中期評估[J].環境保護.2009,(5).
[6] 裴敬偉.中國環境行政的困境與突破[N].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9).
(編輯:王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