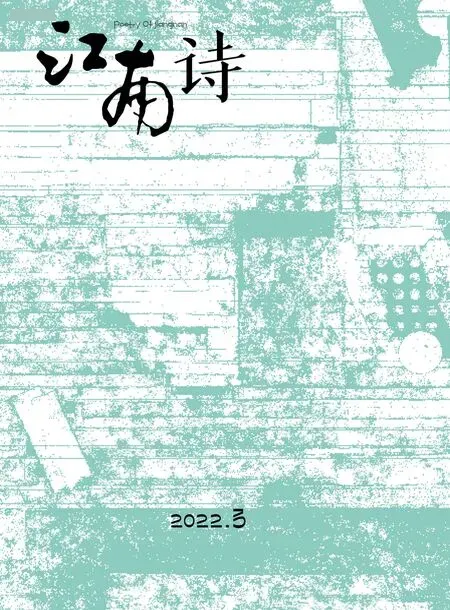盧布的皮夾
張樂朋
盧波是我們的老大哥,他背后大家一律喊他盧布。他是唯一有權坐上工棚里那張露餡的紅皮革椅子的人,因為他是工長,破紅椅子是他的待遇。
于是,紅皮革成了他的威權和背景,他經常坐在椅子上,給青工們講他如何在半月之內把讀師大的姑娘盤在腳下,和足球一樣,帶到床上,“直接破門。”然后狂笑,擦擦嘴角,再補充兩聲“嘿嘿”。
盧布有沒有這本事,說不清楚,大家就知道,他沒什么工作能力,他是連車床卡盤都拆不下來的維修工長,實際的頂梁柱是老許,老許是個干巴猴。
老許是維修工段唯一敢當面呼叫盧波盧布的人,因為他可以憑技術撂翻,盧布深明大義,對老許另眼相待,一來是年齡相仿,二來是他技不如人,三個是籠絡人心,他要求青工們多向老許學技術。然后,一有什么故障,就派老許帶著青工去處理,他只配合,或者背抄著手,在附近轉來轉去,如果車間主任過來探看,他就蹲下來抓起一塊油棉紗,裝成身先士卒,拿著扳手緊幾下螺絲。更多的時候,車間主任在辦公室里算計工人,他就冒充領導,指指點點,負責現場監督。
由于盧布考慮到副工長也拿獎金系數,所以堅持維修工段不設副手。這樣一來,老許除了干活,在工段里就連個名分都沒有。老許只好說他不在乎,像盧布那樣占著茅坑不拉屎,而且還是托關系,讓他老婆的單位領導替他使勁兒。
大伙的理解,他老婆的單位領導替他使勁兒,就是替他給車間這邊的頭頭打招呼,總之,這年頭,有這么一個人,就能頂大事。
時間一久,大家就認可,盧布這也算有本事,沒有靠山,想這么連年鬼混,在車間里恐怕連一天都站不住腳。
盧布的歷史,車間人都知道了,但盧布還是要講,邊講邊用眼角余光瞟在場的女工……
維修工段的女工比較少,也比較老,這幾個不吃虧女工,從頭到腳都透著尖酸的氣味。
可盧布干嗎一眼一眼瞟她們,眼神還那么黏糊。
估計盧布對他們也沒什么想法,那年過三八,車間給女工放半天假,他趁那幾個女人不在,公開評頭論足,邪惡地告訴大伙,這些老幫菜,底下流出來的都是姜汁兒。
大伙聽罷,眼都花了,盧布說得太具體了,而太具體了就太惡心了,大伙都往地下啐了一口,然后才笑。
老許逮住話頭,陰陰地問:“盧布,你不會是嘗過誰的吧?”
老許這一問,問題更具體了:老姜?老柴?斑馬?惡心呀天呀,左猜右猜,不外乎她們三個。
盧布愣了一下,然后笑而不答,他的那個笑,淫淫地,故意不置可否,故意高深莫測,故意含著姜汁兒,惡心大家。
根據盧布的表情和話里流露出來的東西,大伙心里認定是老姜,以后就注意盧布和老姜,在盧布給人講風流史的時候,悄悄觀察老姜的反應,老姜的丈夫是一個部隊轉業的物業經理,她當過多年的曠婦,割過子宮肌瘤,會不會在那些年,在那些十五的月亮照在邊關的時候,把盧布當作不時之需?
有人想找到蛛絲馬跡,老許則說決不可能。老許問題問得深入,看事看得透徹,他說兔子不吃窩邊草,何況,倆人就他媽在一個窩里頭。老許指的是臟污的工棚。老許接著說,中國人歷來的講究是遠嫖近賭,盧布再傻也不會真那么干。有個技校畢業生嘰嘰歪歪地討教,那他干么說是姜汁兒?老許失笑,這孩子,他說啥你就信啥?他要說馬尿,那你說就是斑馬了?老許把技校生引入迷津,最后才深入淺出:“盧布是南方人,他那姜汁兒打比,那是他愛好的口味。”
按照老許的分析,再看老姜,平時正眼都不搭盧布,盧布說他的風話,她氣定神閑織著毛活,鄙夷不屑地嗔責盧布:“講你娘有一千遍了,沒得一些咸濕。”
真的看不出老姜受到了邪言的入侵,大伙不好意思齷齪地推想,老姜會分泌姜汁兒。
除了老許,盧波不容許本工段的伙計喊他“盧布”,但喊“工長”可以。李曉跟著老柴實習時,老柴告他:“盧波心里蝎著呢,他不容許手下冒犯。”
李曉是西交大畢業的,他進了工棚的第二三天,就聽說了盧波的風流史,盧波自個兒講的。看來柴師傅所言不虛:半月以內把球帶進門里,證明他的家伙和心都是黑的。
不過聽說那師大姑娘成了他現在的老婆,李曉就不以為然,這不算本事,很可能是老婆故意漏球呢,如果這樣,更加可疑。
盧布連著讓李曉給他跑腿買早點,有一次,一早上跑了兩趟,第二趟買來,盧布拎著出了工棚,送到機鉗工段的一個青年女工手里。那個女工一腦門粉刺,看見李曉跟過去,把盧布推拒不要的一塊錢直接給到李曉手里。
盧布這才看見李曉在他后邊,而李曉也看見盧布臉上那種愚蠢的慌亂,和故作鎮定的愚蠢。
他沒有聽盧布解釋,拿了錢,扭頭離開。
李曉讀過書,讀過書的人更容易對人產生極度厭惡的情緒,這件事情究竟怎么刺激到李曉,李曉沒給任何人說起。
大伙事事讓著盧布,也讓李曉覺得郁悶和可氣。有一天,他來早了,坐在那個紅皮革椅子上看書,盧布和那個滿腦門粉刺女鉗工說笑著進門,盧布進門就讓李曉去買早點,李曉抬頭問給誰。盧布給女工這邊是笑臉,掉過來就是一張霸道的黑臉,蠻橫地說,讓你去你就去,問那么多干啥?李曉說不去,然后低頭繼續看書。
盧布的臉馬上放下來,滿腦門粉刺的女鉗工趕緊說算了算了,我自己去。
粉刺走了,盧布沒走,他盯著李曉,李曉抬頭朝他一笑,絲毫沒有承讓之意。
其他人陸續到了,看著李曉挑戰盧布,都不言語。只有老柴擔心盧布上來脾氣,打這個孩子。
盧布沒有動粗,他也動了腦子,出門轉了五六分鐘,又轉回來,客客氣氣地給他派活兒:“帶上錘子鏨子,跟叉車司機去設備庫拉五百米鋼絲繩。”
李曉那天也是成心造反,他不會干活兒,但更會動腦子(三年后他轉回這個車間擔任主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攆走盧布)。李曉問盧布我跟誰去。盧布說你自己去,跟上司機。李曉說這也不對,我在維修工段實習,為啥要干準備工段的工作?盧布終于扔開他的調虎離山計,厲聲說我讓你去你就得去?然后指著椅子說,讓雞巴開。李曉顧左右而大笑,說:“你是不是想坐這個破椅,才讓我跑腿買飯、去干臟活兒?”鋼絲繩上的黃油很厚,鋼絲繩又那么不屈不撓,怎么干都要弄一身黃油。盧布見李曉說破原委,臉上實在掛不住了,只好狠聲說是要咋的?李曉往坦然里坐了坐,說:“看來我得告訴你,盧師傅,你是工長,不是土皇帝。我再告訴你,第一我不去,第二我不讓。說完真的一動不動,坐視盧布的反應。
平時盧布才那樣坐著給人布置營生,輪到他站在當地,他都快不會做人了。他惱羞成怒,比畫起來,要動手,老許等人趕緊兩邊擋住。老柴生氣地說李曉:“你非得坐他那破椅子啊。”李曉站起來,說:“你想打架,我勸你最好不要動手。下了班,咱們到球場馬路都行,隨便你挑,我奉陪。”李曉說出這幾句有爆發力的話時,大伙才發現這孩子肩膊上鼓鼓的肌肉。李曉抬腳狠跺椅子,靠背上的皮革面應聲豁開一個大口子,李曉接著說,至于這把破椅,就不應該擺在這里。
盧布已經被人擋在門外,眼見李曉發威毀壞他的專座,他跳著腳罵道:“小B崽子,你看我到主任那里告你破壞公共財物。”李曉笑道:“你應該去告廠長,問問他該不該給你留這個公共財物。”
盧布后來沒有約戰李曉,上年紀、有家口,都不能再打光棍兒架。再一個是,李曉在大學校隊踢前鋒,后來在廠隊里踢,是個生猛的家伙,盧布看過李曉踢球,覺得免戰是老年人智慧圓熟的表現。
李曉在維修工段實習了不到三個月,調到另外的車間實習,盧布的威脅就隨之解除。有一天,大伙聊天說起李曉,老許預言李曉說話占理,很有前途。盧布倚在紅椅子上哼哼冷笑:“這輩子他別想,主任給他填實習鑒定時,征求過我的意見。”
盧布還是老樣子,胡說八道,只要是看見青工欽佩、女工羞澀,他就特別滿足,表情十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