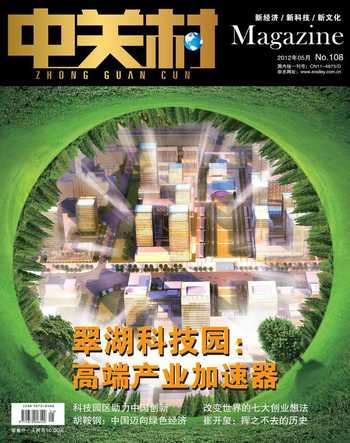崔開璽揮之不去的歷史
張越



從一個普通的士兵蛻變成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崔開璽走過了一條漫長而崎嶇的道路,但他卻樂在其中。
打開崔開璽的畫冊,仿佛打開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長篇畫卷。他的筆觸從歷史的縫隙中揮灑而出,時而追溯到血雨腥風的戰場,時而捕捉到日本戰俘的噩夢,時而描繪戰后和平環境中在清風曉日下散步的牛羊……
這個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老人,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回憶幾乎就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文化大革命的回憶。這不禁讓人思考人生的命運和老一輩藝術家成長的過程。從一個普通的士兵蛻變成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崔開璽走了一條漫長而崎嶇的道路。
彩虹
1959年,崔開璽的處女作《演習之后》在全軍第二屆美展中引起轟動。這幅畫不僅是崔開璽軍旅生涯的經典回憶,也是他藝術生涯的精彩開篇。
那個年代,中國的油畫創作深深地受到俄國繪畫藝術的影響,尤其是對俄國乃至世界繪畫藝術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巡回畫派”。這些畫家提倡面對現實,主張藝術要有思想性,通過繪畫參加改造現實生活的斗爭,這些思想在崔開璽的作品中樣樣都尋得到。他的作品就像歷史的一面鏡子,表現出了當時老百姓苦難的生活,并創造出了一批為爭取新生活而斗爭的革命者形象。
與生俱來的天賦,加之源自對美術的熱愛而勤奮地努力,讓崔開璽從一個普通的士兵成漸漸為了一名小有名氣的畫家。
然而,正當此時,一個驟然而至的災難卻讓中國的藝術突然之間沉沒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在那段日子里,很多畫家都無心創作,即便一些人依舊有創作的熱情,但卻沒有了畫畫的機會。大家整天開會鬧革命,人們參加不同的組織,然后與不同的派別斗,最嚴重的時候還要打。
但相對而言,崔開璽又算是幸運的。因為他在部隊里,部隊經常會為犧牲的戰士搞展覽會,宣傳英雄模范人物,所以畫畫的機會還相對多一些。文革發展到中期的時候,崔開璽還畫過一些“紅光亮”的作品,“雖然我并不情愿”,但還是出現了諸如《千年荒灘運糧船》等優秀的作品。最讓崔開璽難忘的是,1975年,在文革的后期,他與幾位畫家一起沿著紅軍長征路遠游寫生,創作出了他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的《長征路上的寫生》。
在崔開璽的家中,我看到了這幅曾被無數人臨摹過的油畫,尤為令人難忘的就是整幅暗色調畫面中的那道色彩艷麗的彩虹。
想起那段旅程,崔開璽津津樂道:“那次遠游寫生主要圍繞四川一帶紅軍長征走過的路。成都軍區為我們準備了一輛吉普車,我們驅車前往了雪山、草地、金沙江、大渡河和彝族大小梁山等紅軍長征中最精彩的那一段路。1975年的四川還都是砂石路,經常塌方。一次我們從大渡河沿岸的石棉縣前往瀘定橋,剛走不遠,就發現前面路段出現了嚴重的塌方,車都堵住了。于是我們干脆掉頭往回走,可還沒等汽車啟動,后面路段又塌方了。直到天黑路才修通。”講到此處,崔開璽緊張的神情突然放松下來,繼續說道:“當汽車緩緩啟動時,天色已經很暗了,整個山只剩下一個模糊的輪廓,前方的大渡河像絲帶一樣繞在山前,那美麗的景致令我至今難忘。”
那次寫生整整走了四個月,在那四個月里,崔開璽與妻子和孩子都斷了聯系。最后因為出了車禍,人傷了,錢也花完了,連糧票也都用完了,“直到山窮水盡了才回來”。
我想,是那道彩虹讓崔開璽堅定地走過那段災難的歲月,也是那道彩虹預示著新的時代即將來臨……
觸動心靈的畫面
也許是軍人所獨有的情懷,即便今天的中國早已遠離戰場,但崔開璽的畫布上總有揮之不去的歷史。無論是對腥風血雨的戰場的刻畫,還是定格混戰年代難得的溫馨畫面,崔開璽的畫筆直指備受爭議的戰爭,其歸宿與目的都是和平。
1984年,崔開璽創作了代表作《長征途中的賀龍與任弼時》。這幅畫別具匠心,作者沒有描繪兩位將軍高坐馬背指揮千軍萬馬的壯觀景象,反而選取了賀龍和任弼時在長征中短暫休息的瞬間,抓住了釣魚這個頗有意義的細節,著意刻畫了賀龍和任弼時兩位將軍“后有敵軍緊追,我自穩坐釣魚臺”的非凡氣度。這種寓動于靜、小中見大的手法,是軍事題材上一個突破性的嘗試。
1987年,崔開璽又創作了《士兵之家》、《噩夢》和《北京保衛戰》等幾幅影響較大的作品。
《噩夢》描繪的是日本戰敗后,戰俘聚集到一起,他們神情絕望,猶如剛剛做了一場噩夢。崔開璽通過這幅畫,站在文化、歷史和人道主義的高度來批判戰爭,向人們揭示了八年鏖戰的受害者不僅僅是中國人,作為侵略者工具的日本士兵同樣深受迫害。這樣凝重而意味深遠的畫面,牽動著每一個人的神經,讓無論經歷過還是沒有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們震撼。
在崔開璽筆下,觸動心靈的畫面不勝枚舉,在《上甘嶺最后的屹立者》中,倒下的戰士與“屹立者”的對比,告誡人們“雖然我們打贏了這場仗,但也是傷痕累累”;在《紅軍攻占了臘子口》中,作者通過還原險關臘子口的原貌,告訴人們勝利來之不易;在《木蘭秋獵》中,飛騎上的將軍對準逃命的小鹿曲弓射箭,但畫面卻在箭離弦的瞬間定格,至于中與不中,成了一個懸念……
崔開璽的每一幅畫都是一篇寓意深遠的哲文,隨著閱歷的增長,修養的充盈,他將更多的發現用智慧的手段抒寫成一幅幅撼人心魄的藝術精品。
“走上畫畫這條路,能不能創作一些精神上的東西是至關重要的。”崔開璽說,“藝術是偉大的,就像偉大的導演,可以把一個故事通過演員、影片制作等變成一部有血有肉,能觸及人靈魂的藝術作品。一部好的藝術作品甚至能改變一個人一生的觀念。一本好的小說可以調動文字,讓語言入目三分,它把一段事情,攢綴得成為一段歷史,或是人生,因此說這種人才是藝術家。而我充其量也只是把一些自然或者歷史轉變成一個個形象的畫面,用一點塑造的能力,把景物變著法子再現出來,如果這種再現能愉悅一下人們的眼睛,抑或觸動人們的心靈,我也就倍感安慰了!”
樂在其中
與前期相比,近年來崔開璽的作品中硝煙味淡了許多,而充盈著清波碧草的原野和霧靄彌漫的遠山,以及悠然自得的牛羊的畫面逐漸增多。這似乎是一個從形式到內在的轉變,也是一個更加貼近于自然,并在自然中充分感受生活的開端。
在崔開璽筆下,那些愜意的景致并非信手拈來,大多意象都源自先生出外寫真時捕捉的物象,所以,在崔開璽抒寫的畫面中你總能找到藝術家在自然中獲得的激情。
近年來,許多藝術家已經不再背著畫具去寫生了,而被相機取而代之。但崔開璽卻對寫生情有獨鐘,“時間長了不出去寫生就手癢難耐,雖然在畫室內同樣在作畫,那總不如在野外來的瀟灑。”
崔開璽每年都會背上畫具行囊到大自然中去畫兩筆散散心,雖然起早貪黑、風吹日曬是尋常事,但也總少不了鮮為人知的寫生趣聞。
“記得2005年春季,應我一個學生的邀請到他的家鄉內蒙古呼和浩特周邊去寫生,畫草原畫牛羊是我所好,在廣闊的草原上可以看到藍天白云,可以感受到天之高、地之闊,可以忘卻城市的喧囂,于是乎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再去體驗那參與的快樂。”
“到了目的地,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畫的畫也日有所曾。某日轉到一個新點無旅店可住,就在鄉政府的籬下借住了數日,我們依然是黎明即起勤懇作畫,但想不到的事來了。一日清晨,當我們興沖沖地穿戴完畢背起畫箱準備出門的時候,卻發現鄉政府的大門被那個‘將軍不下馬鐵鎖鎖得死死的,四處找不到值班的人來開門,只有那‘將軍還在‘馬上。大院的圍墻足有兩米高,看來這鄉政府的安全意識很好,壞人確實不易進的,但也苦了我們,這清晨的時光正可以搶一幅畫,卻被它這道墻攔住了。跳墻吧,他們幾個四五十歲的‘小伙子還問題不大,而我這個年近古稀之人再去跳墻似乎有點可樂了。唉!時不待我,跳吧!于是乎在前扶后擁之下翻墻而過,總算繞過了那個不下馬的‘將軍,搶時間畫了一張畫回來。事后畫友們揶揄地說:‘把你當時翻墻的鏡頭拍一張照片就有意思了。我說:‘那這張照片就變成一個老賊的旁證材料了。”回憶起這段趣事,崔開璽再也忍俊不禁。
“到了我們這個年齡,畫畫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種純粹的興趣,已經沒有了任何目的。一筆一筆地涂抹可以消磨時光,如果偶爾能畫幾幅滿意的畫那也是一種刺激、一種興奮。這種興奮的延續就逐漸成了一種奢好,最后的結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參與了這個寫生的過程。就像那幫愛釣魚的釣友們每天起早貪黑地背著漁具出去,折騰一天下來土頭土臉地回到家里,有時一無所獲也無所謂,第二天日依然如舊,關鍵是他們體驗了那種參與中的快樂。”
身為外行人士,我無法得知崔開璽窮盡一生到底為中國藝術的發展帶來了什么影響,但我卻知道藝術深深地影響了崔開璽,使他從一個普通的小士兵蛻變成偉大的藝術家,最為關鍵的是,崔開璽參與并享受這個蛻變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