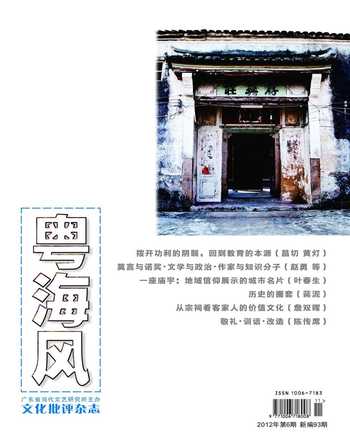“劇本荒”與網絡改編熱
康建兵
當代戲劇特別是近十余年來的戲劇一直遭遇戲劇危機的嚴重困擾。從1980年代初起圍繞黃佐臨先生的《漫談“戲劇觀”》一文展開的對“戲劇觀”的爭鳴以及對戲劇危機的探討,及至本世紀初由劇作家魏明倫在岳麓書院關于當代戲劇之命運的演講再度引發的討論,戲劇界也一直在為當代戲劇把脈,最后綜合各家之言發現,當下戲劇從里到外都有病,其中最要命的病根是“劇本荒”。當下的戲劇危機首先危在缺乏劇本,不是數量上缺乏,而是缺乏原創性的好劇本。黃佐臨在半個世紀前談到的他心目中那種“最理想的劇本”在當下寥寥可數。
當下戲劇遭遇著劇本質量上的“無米之炊”,這種情況不獨是戲劇的窘境,也是電影和電視劇面臨的大難題。在以往對戲劇命運的討論中,大家常常將三者擱到一塊兒談,將電影特別是電視的發達視為造成戲劇危機的禍首之一。而就在中國互聯網在新千年剛開始便勢頭猛進時,魏明倫則看到網絡對戲劇的影響,認為我們進入“電視電腦的時代,就是居室文娛,斗室文娛的時代”。[1]然而,對戲劇與網絡關系的探討卻一直未得到應有重視。應當說,造成今天居室斗室文娛現象的出現,網絡“功不可沒”。互聯網時代的戲劇與影視不再是冤家,而是在快速推進的媒體融合進程中被整合進新媒體,其間關系也從競爭走向競合。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隔離了人與人在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交流,反之網絡又促成斗室中的人與人在網絡上實現集群虛擬交流,網絡自身這一悖謬特性也與戲劇發生關系,其表現之一就是一些流行網絡文學對當下戲劇影視帶來的誘惑和影響。
戲劇遭遇“劇本荒”,戲劇自身也在百思其變,比如奉行“拿來主義”。這里說的“拿來”,既指從一批優秀小說或者傳統經典劇作那里取經,以共享藝術精華,展現多重魅力。比如近年來舞臺上常見的還是那批常排常演的經典劇目,或者改編當代著名小說入戲,或者邀請小說家操刀劇本。于是,莫言的戲劇《我們的荊軻》、陳忠實的小說《白鹿原》和余華的小說《活著》等都被搬上舞臺,這確實為當代戲劇注入一劑強心針,也是我們應當大力提倡的。正如莫言所說:“小說家寫話劇,應該是本色行當。”但在不斷“拿來”中也出現了戲劇搭順風車現象,不僅搭影視劇的順風車,也搭網絡文學的順風車,省心省時省事。特別是由于影視“劇本荒”之荒謬和荒蕪程度不亞于戲劇,因而也紛紛向網絡文學要奶喝,戲劇影視三者歸一,殊途同歸,都在網絡文學中挖劇本。當代美國戲劇學者羅伯特·科恩曾說:“從舞臺實踐的角度而不是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戲劇是一種相當保守的事物。”[2](P288)如果將科恩的判斷置于網絡時代的中國當代戲劇場域,可以發現戲劇與網絡文學發生關系后,其舞臺實踐不是相當保守,而是十分活躍。
回首過去十余年,當代戲劇不僅向網絡文學要素材,而且有時候還同影視賽跑,往往一部網絡文學的影視版還沒殺青,戲劇版反倒捷足先登。一時間,話劇《杜拉拉》、《步步驚心》,越劇《第一次親密接觸》和粵劇《夢驚西游》等紛紛登臺亮相,轟動一時,戲劇也因對影視劇的間接改編或對網絡文學直接改編而淪為二度乃至三度改編戶。但即便如今茅盾文學獎和魯迅文學獎等都對網絡文學“網開一面”,終歸網絡文學還是被視為下里巴人,不為陽春白雪的精英文學真正接納。改編自網絡文學的戲劇版也常常脫不了“趕潮”或者“要市場不要藝術”等非議。進而,即便戲劇與網絡文學發生關系十余年,卻未能觸動學界去思考網絡改編劇以及戲劇與網絡文學的關系,這也應了布萊希特一句話:“大眾戲劇通常被認為是幼稚的,乎庸的,學院式的美學要么不理睬它,要么貶低它。”[3](P137)
我們不妨先來梳理一下當代戲劇與網絡文學親密接觸的過程。戲劇與網絡發生關系可以追溯到互聯網在中國的起興初期。從1990年10月中國開始參與國際互聯網活動到1994年4月被國際正式承認為有互聯網的國家,國內互聯網這一新興媒介在快步發展的同時,順勢催生了一批與網絡有關的新生事物,其中網絡文學發展迅猛,并在1998年至2001年迎來黃金時期。1998年3月22日到5月29日,臺灣的蔡智恒在網上電子公告欄發表長達34篇連載的網絡小說《第一次親密接觸》,在臺灣和大陸文學界掀起網絡文學熱潮。此后,一大批網絡小說陸續面世,有的以驚人的閱讀量和下載量異軍突起,引人關注。而戲劇與網絡文學發生關系正是從開網絡文學先河的《第一次親密接觸》開始的。2000年12月1日晚,北京“70”劇社將《第一次親密接觸》改編為同名話劇,在清華大學藝術中心首演。2001年3月20日,同樣改編自這部網絡小說的同名話劇被北京人藝搬上人藝小劇場,成為當時國內影響最大的網絡題材話劇,北京人藝也由此成為國內主流劇院開戲劇改編網絡文學之先河。此后,不少成名于互聯網并被出版成書或被改編為影視劇的著名網絡文學都出現了戲劇版。比如,李唯的《跟我的前妻談戀愛》、張小花的《史上第一混亂》、六六的《雙面膠》、三十的《下班抓緊談戀愛》、鮑鯨鯨的《失戀33天》等都被改編為同名話劇。有的被改編為戲劇后劇名稍有改動,如唐浚的《爸爸,我懷了你的孩子》被改編為話劇《戀人》,李可的《杜拉拉升職記》被改編為話劇《杜拉拉》。慕容雪村的“青春殘酷系列”《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天堂——打左燈向右拐》和《多數人死于貪婪》均被搬上舞臺。不僅話劇界出現網絡文學改編熱,連戲曲也躍躍欲試,而且戲曲觸網也是從痞子蔡的《第一次親密接觸》開始的。比如,上海越劇院于2003年將其改編為同名越劇上演,開戲曲改編網絡文學先河。廣東粵劇院在2004年將今何在的《悟空傳》改編成青春粵劇《夢驚西游》。2008年,廣州紅豆粵劇團又將慕容雪村的《天堂向左,深圳向右》改編為粵劇《廣州淘金人》上演。2012年,上海越劇院再度出擊,購得流瀲紫的網絡小說《甄嬛傳》的越劇改編權。
對于當下戲劇出現的網絡文學改編熱,我們通常將其歸為兩個主要原因,其一即戲劇“劇本荒”,其二是劇院出于票房考慮,故搬演之。就前者來看,如前所述,“劇本荒”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問題在于,假設戲劇沒有出現“劇本荒”,是否同樣會出現對網絡文學的改編呢?戲劇與其他文學樣態之間常常互為主客,從古至今相互改編是戲劇的一個傳統,不足為奇。而要從網絡文學改編戲劇,必然得有互聯網新媒介的出現以及網絡文學發達的時代才有可能。以互聯網為主要支撐的新媒體對當今的文學藝術產生的影響非常明顯。作為藝術載體和傳播媒介的網絡不僅對戲劇的傳播起著媒介作用,載體本身所衍生的新文學藝術樣態也會對戲劇產生影響。那些發端于互聯網并且已經從網上到網下都發生了轟動效應的網絡文學不可能不為戲劇所關注和改編。戲劇自身特有的觀照時代和求新變異的藝術特質也會使其注意到網絡文學的出現、存在和影響。人類戲劇特別是20世紀戲劇從來不曾拒絕過任何新興藝術或新媒介的融入,為我所用,并衍生出一些新的戲劇類型和戲劇形態。早在1990年代末國內就有研究者喊出“網絡戲劇——未來的戲劇”[4]口號,當下又出現了手機戲劇、博客戲劇等說法,這些命名是否得當還有待商榷,但其客觀存在卻是事實。近年來學者鄒華斌提出“大戲劇”觀念,認為“不管何種載體、何種形態的戲劇,都有它發生、發展、演變甚至消亡的歷史過程,都值得研究”,“用‘大戲劇的觀念來觀照戲劇,其形態和內涵多姿多彩。”[5](P2)學者王廷信也指出:“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會以不同的手段創造戲劇……那么會不會出現‘網絡戲劇?我想也是有可能的。”[5](P9)關于網絡戲劇的說法,是應該側重從網絡的媒介載體功能著手考慮,還是應該更多以網絡文學提供的題材或者關于網絡自身的故事題材考慮,不一而足,但戲劇改編網絡文學熱卻預示了網絡對戲劇的影響走向多元以及網絡戲劇出現的一些征兆。因此,將當代戲劇置于這一大時代來考慮,足見戲劇與網絡文學發生關系是必然趨勢,“劇本荒”只是佐證戲劇對網絡文學改編熱的必然,但它卻未必全然是禍首。
就后者來看,有人指責改編網絡文學是“要票房不要藝術”。如果說從網絡文學改編的戲劇幾乎都有極高的上座率和票房成績,倒也是事實。北京人藝的《第一次親密接觸》首演起在人藝小劇場創下了連演57場且場場爆滿的奇跡。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戀人》首輪14場演出也是場場爆滿。其他網絡文學的戲劇版演出也是如此,常常是戲還沒上演,前幾輪的票早已告罄,一票難求。有的改編劇先在小劇場演,但周末為滿足觀眾需要就得加座或臨時改到大劇場演,這種情形似乎在1980年代戲劇的短暫春天時才易出現。北京的戲逍堂在2010年以百萬天價購得《鬼吹燈》的話劇改編版權,可以管窺網絡文學給戲劇制作方拋出多大的票房暢想。而一部改編劇打出名堂后,地方劇團很快移植排演,同樣反響不錯。北京人藝在2011年還隆重重排《第一次親密接觸》,以紀念該劇演出十周年。網絡文學改編劇也讓一些年輕導演嶄露頭角,如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80后導演何念就經常選擇熱門網絡小說予以改編,《跟我前妻談戀愛》、《雙面膠》和《杜拉拉》等均由其執導,何念還監制了一批其他網絡小說改編劇,同樣獲得成功。
但僅僅將劇院的票房考慮視為戲劇網絡文學改編熱的出發點也有失偏頗。一些網絡文學之所以走紅,原因很多,有情節吸人眼球的,有團隊精心策劃的,有不少是炒作的,但往往流行作品都比較關注當下現實生活特別是一些熱點問題如情感、婚戀、倫理和職場等,這些容易引起年輕群體的興趣。當然,隨之而來的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甚至庸俗化的套式泛濫。另外,一部網絡文學被改編為戲劇時,多由名導執導或明星參演,戲劇也借了網絡文學的人氣,但還得在舞臺表現藝術上下一番功夫。網絡文學大都長篇累牘,動輒幾十萬字,改編為電視劇后也是長劇,而要將其時間、地點濃縮在方寸舞臺上的有限時間里更不容易。從這個角度來說,改編網絡文學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戲劇可以借著網絡文學的東風,省去宣傳環節,有一定的源自網絡文學和影視版的觀眾群的保障,往往戲未上演就賺足人氣,在改編上也有影視版參照;另一方面,戲劇既要為搭順風車而頂著各方面壓力,還得頂著戲劇帶給自身的壓力。演砸了不僅得罪觀眾尤其是得罪難得進劇場的年輕觀眾,更容易在他們心目中敗壞了本已是冷清藝術的戲劇的口碑。或許正因為如此,當下戲劇的網絡文學改編雖然出現了一定熱度,但幾乎就是北京和上海的“雙城記”,如再算上廣州,頂多就是“北上廣”三足鼎立。北京和上海的戲劇活動最活躍,劇團眾多,思潮涌進,更有北京人藝和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等牽頭,出現網絡文學改編熱自不待言。廣州地處開放前沿,敢于嘗鮮,包容性強,粵劇又以“善變”著稱,因而出現網絡文學粵劇版也屬正常。實力派劇院參與網絡文學改編,無論在題材把握還是藝術創新上都會有一定保證。
魏明倫曾說:“當代戲劇的特征是觀眾稀少。不是沒好戲,而是戲再好,也少有觀眾上門。”[6]好戲自然是有的,魏明倫就寫了很多好戲,但像魏明倫、李龍云、劉錦云、過士行、陳亞先、郭啟宏和鄭懷興等能寫出好戲的當代劇作家卻不多。從網絡文學改編的戲多半不是魏明倫認為的“好戲”,卻能讓一部分觀眾心甘情愿掏錢買票進劇院,值得我們思考。有人說這些觀眾中有的只是網絡文學迷或網絡文學影戲改編版的迷,他們追的不是戲劇,而是網絡文學的效應,甚至有的觀眾直言他們之所以看《和空姐同居的日子》只是沖著劇名去的。但不管如何,這總比那種“臺上振興,臺下冷清”的局面好,也比那些拿到“工程獎”后便被束之高閣的陽春白雪好。就像曲潤海先生所說:“有的戲真的是陽春白雪,但獲獎后便束之高閣,再無人問津,甚至壽終正寢了,陽春白雪又能怎么樣呢!而下里巴人,雅俗共賞的戲卻沒有真正受到提倡和支持。”[7]南京軍區前線文工團在2008年根據湯顯祖的《牡丹亭》創演的一部優秀同名舞劇摘得中國舞蹈“荷花獎”在內無數大獎,并于2011年1月登上紐約林肯藝術中心這一世界藝術圣殿。這部備受贊譽的好戲雖然也在國內一些城市巡演,但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幾乎是既看不到也看不起,甚至劇團所在地南京的觀眾也很難一睹風采。該劇編導呂玲老師去年還向筆者坦言,雖然他們也想在南京公開售票演出,以饗家鄉觀眾,但又擔心有票房壓力,于是作罷。而網絡文學改編劇至少能讓一部分觀眾特別是越來越稀缺的年輕觀眾走出網絡,走進劇院,去感受劇院的神圣,感受劇場戲劇藝術的真正魅力,感受人與人之間活生生的現場交流,這也算是一個功績。
當然,那些走紅的被戲劇人看中的網絡文學自身的質量也良莠不齊,像《甄嬛傳》等引起不小爭議的作品更需要戲劇人在改編時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雖然向網絡文學改編劇既要票房又要藝術有不小的難度,但若能起到一些借他山之石來攻戲劇這塊玉的效果未嘗不可。對于網絡改編劇的走向,我們不妨本著“不排斥、不提倡、不棒喝”的態度,將其交給觀眾去裁奪。良好的戲劇生態需要百舸爭流以激活世界大舞臺,也要承認和允許分流現象的存在。北京人藝在2011年不僅重排《第一次親密接觸》,也將莫言的戲劇《我們的荊軻》搬上舞臺。如今,將兩者相提并論似乎更不太恰當,但這不正說明人藝的革新姿態和包容精神嗎?!這種“巴人”和“白雪”同臺表演的景況難道不應是良性發展的戲劇生態理應秉持之道?!當然,終歸我們不僅需要飽含思想深度、人性關懷和“藝才”豐呈的好戲,也要讓觀眾尤其是普通老百姓能夠看得到、看得起這些好戲。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
[1][6]魏明倫.當代戲劇之命運——在岳麓書院演講的要點[J].中國戲劇.2002.12
[2]羅伯特·科恩.戲劇(第6版)[M].費春放主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3]貝·布萊希特.布萊希特論戲劇[M].丁揚忠、張黎等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4]孫文輝、浩歌.未來的戲劇——網絡戲劇[J].東方藝術.1997.6
[5]鄒華斌、李興國.大戲劇論壇(第2輯)[C].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
[7]曲潤海.從臺上臺后看中國當代戲劇之艱難[J].中國戲劇.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