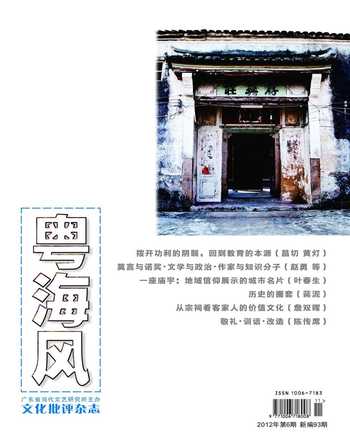撥開功利的陰翳,回到教育的本源
昌切、黃燈
一、“去行政化”只是一個偽命題
改革的核心不就是把政教分開嗎?政教分立,辦不到。辦不到的事,你提它作甚!所以,教育部門的“去行政化”,如果不與政治體制改革聯動,是不可能的。
黃燈(以下簡稱黃):昌切老師,歷年的“兩會”,教育都是一個熱門話題,例如,高校“去行政化”的呼聲就很高,但對此的分歧也很大,贊成的人多,其中熊丙奇的呼聲就很響,但也有一些憂慮的聲音,認為去行政化很難,人大校長紀保成和中山大學前校長黃達人可為代表。您對此有何看法?
昌切(以下簡稱昌):實際上,“去行政化”應該叫“去集權化”,行政化是集權化的表現形式。教育部的規劃草案里沒有這樣提,或者說提得比較模糊。教育是社會的一個特殊部門,由于集權,教育的一些特性被忽略甚至被抹去,形成了用行政管理方式來管理教育的模式。教育管理部門成了政府的機構,完全按行政的一套運作。
黃: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如果不觸及政治體制改革,“去行政化”幾乎沒有可能?
昌:是的。行政肯定是要的,世界上沒有一所大學沒有行政。“去行政化”的意思,我想是尊重教育規律,去掉無視和抹去教育特性的那些管理方式。
黃:那您說的教育規律具體指什么?
昌:這個涉及面太大。首先要看高等教育是干什么的,在社會中處于什么位置。我把高校看成人類知識的集散地。人類知識在高校集成、集中并傳播、發散出去。人類社會越來越復雜,人類知識越來越豐富,高等教育也就越來越專精。
黃:也就是專業化越來越明顯,專業設置越來越細。
昌:越來越專門化。既然大學是人類知識的集散地,那么它必然會以傳承知識和創造知識為己任。要完成這兩個方面的任務,一個必備的前提是:自由!在中國,就不同的學科而言,情況是不一樣的。理工科沒有問題,但人文和社科領域的問題非常大。你看得到的,中國建國后的知識生產,是由政府部門主導的。上面下達政策,下面按照它的政策去落實。就拿我熟悉的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學科來說吧。1950年政務院教育部搞了一個高校文法兩院的課程草案,規定高校要講授現代文學。現代文學被確認為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內容是新文學、白話文學,而不包括文言文學和用白話寫的俗文學,如鴛蝴派的作品。隨后王瑤、丁易、蔡儀和劉綬松的講稿接連問世,于是有了中國現代文學這門學科。最初還有些搖擺的地方,經批判和調整,可指責的東西少了。到了唐弢本,就定型了。80年代以來不知出了多少現代文學史,大都是從一個模子里敲出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不過是中共黨史的一個分支。現在的知識生產也是如此,只是采取了課題規劃和學科評估的變通方式。這兩個東西都是行政按國家的意志在搞。
黃:上世紀80年代采用課題的方式像現在一樣嗎?
昌:也有,沒有這么多,覆蓋面沒有這么大,也沒有這么熱。
黃:我們還是回到集權那個問題。
昌:集權可分為縱向集權和橫向集權。一個權力中心,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這是縱向集權。把社會各部門的權力統統集中到一個權力部門,這是橫向集權。50年代的院系調整,便是橫向集權的好例。你看我們國家教育的性質,與文藝是不是一樣的?有區別嗎?我看沒有。以前都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現在都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集權的必然結果。這種情況下的“去行政化”實際上分權。辦得到嗎?不可能。教育部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相對獨立的權力機構,它必須服從權力中心的指令,它的基本任務是在教育領域傳達和貫徹權力中心的旨意。
黃:因此,也可以說,教育行政化是與生俱來的,這個問題并不是今天才存在,只是由于在當下處境下,行政體制改革的要求越來越強烈,教育行政化的弊端才凸顯出來。
昌:比較一下很有意思。國外的大學,像德國的大學,基本上都是公立的,教職員工的薪水來自各個州府。雖為公立大學,但辦學基本上獨立的,州府干預不了。常見的是它出錢,你罵娘,政府是掏錢買罵。大學的行政攤子很小,如歌德大學,也就是法蘭克福大學,一個校長,兩個副校長,真正管事的是總務長,底下只有人事、學生等幾個具體辦事的部門,工作人員少得驚人。院系和研究機構的行政攤子更小,像系主任,就一個,換得勤,由教授輪流做莊。這個大學設有一個立法機構即議會,議會里面有四個專業委員會,大概由九十多人構成,其中人數最多的是教授,其次是學生,第三是教輔人員、助理研究人員,第四才是行政干部和輔助人員。議會的職責是決策和監管。行政部門按議會的決策行事,受議會制約。
黃:顯而易見,歌德大學的行政管理是從下往上的,是完全服務型的,整個運作完全以服務為中心,但我們的大學,好像完全倒過來了,指令不是來自教育的主體——教師和學生,而是來自上一級的教育部門,行政成為執行上面命令的力量,根本不會顧忌到教師和學生的感受。
昌:對。學校主要是教授和學生的學校,教授和學生是學校當仁不讓的主體。行政部門只有執行權,而且受議會監督,預算多少,經費怎么走,都不是它能決定的,搞行政純粹是服務。再看看我們這里,行政部門之多、之大,都到了什么地步?不是有“處長一走廊,科長一操場的”說法嗎?有個重點大學,一個百把人的學院,居然有一正八副九個院級干部,如果加上黨的系統和相當于院級的干部,那是個什么數字?關鍵在于政教一體,行政是最大的學術資源,誰擁有行政權力,誰就能獲取相應的學術資源。你的行政級別越高,意味著你越容易成為大學者,事實就是這樣。
黃:在我們的行政化里面,還有一個很重要、很微妙的問題,就是黨政關系的問題。企業里面,可以很明確提出廠長負責制,但大學里面,提的始終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一個大學,到底是校長為主導,還是書記為主導,在表述的時候,始終很含糊,很多時候,這兩者的力量對比,完全取決于個人狀況。比如說,有些書記強勢一點,可能很多決策就由書記說了算,有些校長強勢一點,可能校長的地位就會高些。這種狀況帶來的一個直接問題,就是導致了兩套行政機構。
昌:黨也有一套機構。還有群團組織。黨團機構的工作與行政機構有些是重疊的。這源于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黨領導一切,這個是不能動的。所有成績都歸功于黨。“去行政化”是個有限的宛轉的提法,只能是一個偽命題。一直在說教育改革,卻一直沒有大的動靜。變化不大,完全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反而是行政的權力越改越大。改革的核心不就是把政教分開嗎?政教分立,辦不到。辦不到的事,你提它作甚!所以,教育部門的“去行政化”,如果不與政治體制改革聯動,是不可能的。
黃:“行政化”的根源確實和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去行政化”的真正實現也有賴于政治體制的改革。但在我們當下的教育中,所有問題的出現,也總是被情緒化簡單地歸結到教育體制改革的滯后。我所關心的是,在行政體制改革還不能立即實行的情況下,我們的教育是否可以在局部進行一些調整,或者進行一些突破,甚至是大膽的嘗試,是否可以更多的回歸到教育的本質。
二、回到教育的本源
把學生培養成為一個成功的人?還是把學生培養成為一個獨立、具有創造性、人格完善健康、具有基本的社會公德的人?現在的教育在這方面好像沒有任何猶疑,都是很明確地選擇了第一個方面。
昌:教育的要義是很清楚的。它要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這是對教育的基本要求。社會需要交通、航海、采礦方面的人才,那我們就培養這些方面的人才。社會的需求很多,所以大學里面的專業設置也就與之相應。
黃:從社會需求的層面而言,教育確實如此,所以很多高校都將就業率的高低一個學校的辦學水平聯系起來,很多高校甚至直接用就業率來決定一個專的前途,是辦還是不辦,是讓它發展,還是讓它萎縮。除了社會的需求外,教育本身還涉及到人自身的培養,涉及到一個人的精神成長和人格培養。
昌:這是我想談論的第二個方面。教育還有一些虛玄的東西,人文素養的東西,不干實用的東西,人本身的提高的問題,目前在這方面遇到的問題最大。
黃:把學生培養成為一個成功的人?還是把學生培養成為一個獨立、具有創造性、人格完善健康、具有基本的社會公德的人?現在的教育在這方面好像沒有任何猶疑,都是很明確地選擇了第一個方面。什么是成功的人呢?諸如考試成績好啊,能夠找到一個好工作呀,能夠出人頭地啊,與此相關的,諸如競爭啊,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啊,升學率啊,就業率啊,高考獨木橋啊,都是成功的標準已經深入人心的體現。我們中國父母的心態就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我昨天和一個師兄聊天,他女兒在一個省屬重點小學讀書,很多高干子弟集中的地方。學生們私下攀比的就是誰家官大,誰家更有錢。這個學期她本來可以評到三好學生,但最后沒有評上,家長都替她難過,她反過來安慰父母,說是沒關系的,無所謂,他爸的官大,三好學生給別人是很正常的,幾歲的小孩就認定了這個,心理沒有受挫感了。當然,也從小在活生生的現實中,接受了一套“潛規則”的價值規范。這些潛移默化的東西比什么灌輸都有效得多,一旦認定,就是深入骨髓的。
昌:是的,是這樣的。社會流行的東西已經滲透到學校里頭去了。這是一種教育,這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從小學、初中、高中、甚至大學,無不如此。功利性的原則已經滲透到方方面面。大學里盛行功利原則,它的衡量標準,對學生的評價就會出問題,比如要求學生怎樣怎樣,就不斷宣傳,誰誰進了美國的什么名校,誰誰進了什么大公司,誰誰當了什么大官,誰誰進了外交部,誰誰做了某要人的翻譯。
黃:我們的教育好像缺乏一種共識,盡管表面上說什么四有新人。但現實是,對人的評價,基本上就是看你是否成功,一個人有沒有價值,就看他是否成功,而不會從別的層面來評價,所有媒體廣告也無不如此,成功人士的形象和物質需求結合到一起,共同塑造了一種價值追求。
昌:這是單質化。一個孩子從小到大,家長、親友、老師和同學,還有輿論宣傳,告訴你的都是功利化的東西。只有一條道,你別無選擇。學生求學,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學習成績好不好。城里的孩子學習成績不好,老師和家長就會說,“你看你,你將來就配掃大街。”掃大街是低賤的,這種壞觀念就是這樣來的。這種教育不是殺人嗎?這是人性的喪失。
黃:其實教育和被教育本身是令人愉快和充滿快樂的一個過程。一個蒙昧無知的個體通過教育,獲得了基本的素養和生存本領,這和小動物在大自然的環境中獲得個體的成長,沒有本質的差別。一個農村的孩子可能從小會覺得家鄉很美,會覺得在農村生活一輩子其實也挺幸福的,但通過教育,他對自己的身份可能會帶上一種恥辱感,尤其是走到外面以后,這種來自身份上的恥辱感會更加強烈,他慢慢知道,當一個農民其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勞動也不是一件光榮的事,種田更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換言之,我們的教育一開始就被一種“目的性”特別強的東西所控制,所以“被教育者”一開始就有一種“被教育”的感覺,而這種感覺給他帶來的是被迫感,是屈辱感,是表里不一樣的分裂感,從個體的角度而言,他對這種教育是抵制的,是不情愿的。教育者也越來越難以感受到教育的樂趣,在一種功利化的環境下,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創造性的樂趣也越來越少。教育的目的不是讓一些孩子成功,而應該讓所有的孩子都能夠獲得充分的發展,都能夠凸顯個體的價值。
昌:人的潛能是多方面的,好的教育是開發人的多方面潛能。但現在基本上只開發讀死書這一種潛能。誰知道這種教育扼殺了多少天才。一個人可能在某一方面很有才能,但沒被開發出來。這是教育的失敗。教育有相關的兩面,不管是哪個教育學家,他談教育都不可能離開這兩面。一面是人,一面是社會,兩面都要求教育多元化。不是所有人都適合讀書的。如果一個人不適合讀書,不會考試,即便他在其他方面有非常大的潛能,他也可能被學校悶死。這是功利化教育最失敗的地方。
黃:我昨天在電視上看到一個觸目驚心的新聞,現在很多中小學的老師要求家長帶孩子去醫院做智商測試,為什么呢?因為這些孩子的學習成績不好。如果醫院測出的結果低于70,學生的成績可以不計入班級的平均成績。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好的教育將弱智教育成正常人,但我們的教育卻已經走上了將正常孩子逼成弱智的境地。我們的教育已經無知、短視、功利、冷漠到了如此程度!
昌:事實上,我們并不是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也知道學生發展的多種可能性,所以在應試教育中也提素質教育。不過提歸提,提也是白提,應考才是硬道理,所以素質教育到現在并沒有一個好結果。功利化的標準非常實在,大都是實用性的,符合王國維所說的中國人現世的和樂感的品格。現在大學生選專業,一般都是實用性的,人文學科一直很冷。我們這里的歷史系十多年前就很難招到第一志愿的考生。文學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參加了好幾次校園開放日活動,家長和考生經常問的問題是多少分才能進文學院。回答很簡單:只要達到武大的錄取分數線。
黃:這也使我想到目前的“國考”,公務員考試。一些熱門的部門是幾千個人競爭一個職位,這種現象像一面鏡子,最能照出社會的本相和我們教育迷失到了什么程度。一方面說明行政的力量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和實際的利益掛鉤,另外一方面,我們的教育也已經徹底將一種實用的東西,根植到了學生的內心深處,使學生能自然地判斷,什么是對自己未來的生存最有用的。我總認為,這種瘋狂的背后其實恰恰隱藏某種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他們需要找到一種可以真正依靠的東西,但現在,作為弱勢群體的大學生,顯然已經沒有任何可以依賴的東西,他們的大學生身份在大學并軌以后,已經不能給他們帶來任何恒定的東西。當然,表面上看,學生的選擇更自由了,但學生的焦慮感也更強了,尤其是農村來的孩子,這種天生的焦慮意識會多很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公務員考試能夠獲得成功,他們的這種拼搏顯然是能夠給他們帶來保障的。“國考”的盛況,其興盛的真正原因也許和這個有關吧。但不管怎么說,整個大學,整個教育界,無論教育機構,教育者,還是被教育者,彌漫著一種和人的發自內心的探索世界的沖動無關的實用實利原則,這種無孔不入的功利化的原則已經滲透到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已經滲透到了我們的骨髓中。
昌:這種商業的實用原則,正好跟大學的信條是違背的。公認的現代大學之父是德國的洪堡大學,也就是柏林大學。洪堡大學的辦學理念被歸結為“洪堡五原則”,其中學術自由、學術非功利化和學術無權威的信條尤其值得我們重視。有一所大學很特別,它就是有名的巴黎高師。它每年從全球招一千多本科畢業生。它是不授學位的。它這樣做是要告訴你,來這里是求知、求真理的,不是來謀取什么的,要拿文憑請到別的學校去,它要滿足的是你好奇和求知的本能。尊重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這正是從洪堡那里來的。我看過一個電視片,記者問巴黎高師的一個副校長:薩特為什么不去領諾貝爾獎?校長的回答很輕松:這是我們的傳統。搞學問不是為了獲獎。再舉個學術無權威的例子。數學的最高獎是菲爾茲獎,相當于諾貝爾獎。法國的獲獎者大都出自巴黎高師。它還出過總統和一些非常有名的思想家、作家,如司湯達等等。可是這所學校沒有任何偉人的掛像和塑像。按理說,這些偉人不是學校的榮譽嗎?巴黎高師的解釋是:他們不能成為學生的榜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探求真理,必須超越權威。當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學,他搞的兼容并包就是從洪堡那里來的。所以陳獨秀可以和辜鴻銘攪在一起。可是現在,我們的大學已經喪失這種最重要的原則了,行政主導,評價已經壞了,評價系統可以說一塌糊涂。
三、功利的評價導致底線的喪失
至于評價,也就是所謂級別,什么權威、核心之類,也是集權的產物。一個衙門化,一個商業化,兩結合便把大學變成了官方市場。沒有底線了。
黃:從這個層面來看,行政主導才是導致功利化辦學的關鍵。但作為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一個群體,這種幾乎全軍覆沒的狀況背后是否頗能說明一些什么問題呢?上次西安交大造假案,弄得沸沸揚揚,其實現在學界關于造假的新聞早就不是新聞了。而且我還注意到,現在造假的已經不是一些默默無聞的年輕人,一些手頭掌握了很多資源的、職位很高的人,也敢公開造假,這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群體現象,造假已經和誠信沒有任何關系,也和一個知識分子、或者說一個學者的學術良知和學術堅守沒有任何關系了。盡管很多人會從人性弱點的層面來為這些造假的人辯護,但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知,他們良知的喪失是否意味著我們的社會早已經跨出了最后的底線呢?或者說,我們的社會已經沒有任何底線呢?那些敢于反抗的、那些殘存學術良知的人,那些敢于在現有的體制下說出真相的人,現在真的越來越少,其處境也越來越艱難了。
昌:那些敢于說出真相的人,大都是體制外的,不是退休了,就是身居國外。方舟子在美國,揭露浙大造假案的那個人在荷蘭,要是在中國早被按在水里憋死了。西安交大的造假案是由幾個退休教授捅出來的。肇事者表面看是那個長江學者,實際上是作為一個整體的西安交大,因為他的榮譽也就是學校的榮譽,所以他的事情也就是學校的事情,把他推上去也就是把學校推上去。為了息事寧人,出面的不是西安交大的學術委員會嗎?它代表組織。教育部搞了百來個人文社科基地,經常要組織檢查,什么硬件軟件啦,煩瑣得很。要達到要求還真難。不過不要緊,總會有人幫你做的。誰?學校。缺什么補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一應俱全,再蓋上大紅章子,不容你不信。你不是你,你代表學校,你獲得或失去什么,關系到學校的聲價。行政的指標多如牛毛,而且還在增加,什么多少基地、一級學科點,幾個院士、學科評議組成員之類,搞學科建設就成了爭這爭那。好多學校報院士,一給就是好幾十萬上百萬的公關費。行政啦行政,多少罪惡假汝而行。
黃:在這種情況下,教師沒有任何尊嚴感。他的日常工作受到各級行政力量的監督,一個教務處可以管一個教授在課堂的表現,可以像管理一個小學教師一樣地檢查他的教案,可以在班上安插信息員,其實就是相當于特務里面的臥底,目的就是為了監督老師的上課情況,這種管理上面的俯視姿態,已經毫不顧忌到一個教師的尊嚴。更為關鍵的是,一個教師的價值,很多時候是處于一種行政的評比中的,他必須評職稱,不評職稱,可能最后飯碗都保不住,但只要走向評職稱這條路,實際上,他就不得不接受種種的評價標準,諸如論文的數量呀,論文發表的級別呀,是否出版專著呀,是否獲得課題呀,而這些論文、課題、獲獎總是和級別聯系在一起的。什么權威、核心、國家級、省級、廳級之類的。從來沒有任何一條標準說,就看你成果本身的價值怎么樣。這些條件像一張無形的網,將一些鮮活的生命,一些本來很有學術抱負,本來很有學術潛力的人網住,在這部網中掙扎幾年以后,可能也就慢慢習慣了網中的生活了,可能也就喜歡在網中的生活了,不知不覺中,就被異化掉了,有沒有尊嚴感對一個教師而言,他們可能自己也不在乎了。所以每次看到武大的半山廬,每次從中大陳寅恪故居前經過,我就感到恍如隔世。一種真正的精神的光芒的消失不是從某個地方消失了,而是消失在某種具體的制度下面。不是我們當下的人比不上前人的智慧,而是我們當下的人難以呼吸到那種自由的空氣了。當我們大學教授的地位已經比不上一個行政的科長的時候,當我們的大學教授不得不看別人臉色行事的時候,當我們的大學教授敢于拿自己的信譽打賭,去從事學術造假的時候,當我們的大學教授已經不可能從內心感到一種崇高的榮譽感,他們的身份只和某些具體的利益相關的時候,我們的教育已經走向怎樣的歧途,每一個人心里都知道。
昌:是的,高校的老師一點權力也沒有。每年的教學獎,大都被領導拿走了。一天到晚在那教書,帶那么多學生,一點用也沒有,因為你如果不去活動,和教學本身有關的獎最后都會被弄行政的拿走。有所重點大學,去年獲得國家教學獎的,主持人都是學校的高官。行政資源真是太重要了,有沒有是大不一樣的。誰管你什么真知不真知,快樂不快樂。
黃:在這種情況下,虛假之風必然興盛。很多造假者心安理得,就算查出來,也不怕,也不覺得羞辱。造假的不是我一個,造假的也不是我一個學校!很多國家重點大學,很多211大學都這樣,我怕什么?
昌:前兩年的教學評估,鬧了不少笑話,評估大員們得了不少實惠。吃得進去就吐不出來。有什么可怕的?我代表的是組織嘛。你作為一位大學教師,你敢揭發誰呢?你知道的再多也不會說的。不信你試試,看是個什么結果。較真是很痛苦的,較真的不是傻子就是呆子。有些人習慣了,玩起假的東西來如魚得水。
黃:與此密切相關的就是,與評價體系相對應,現在很多雜志,尤其是人文雜志,已經變得差不多了。
昌:變成了賣場。
黃:就是直接拿來賣,不看文章質量,只要有版面費,直接可以發表。
昌:一個愿打,一個愿挨。你發了文章可以晉升得利,幫你發文章的可以撐起腰包。雜志社來錢靠版面,跟大學的文憑一個樣。大學只有一個東西值錢,那就是文憑。想想看,拿文憑做買賣,個人做得到嗎?需要一個行政的聯動機制。想要文憑的人很多,但不是那么容易,但對于官員和老總來說,實在是太簡單了。主要還是行政的問題,交換是外在的表現形式。至于評價,也就是所謂級別,什么權威、核心之類,也是集權的產物。一個衙門化,一個商業化,兩結合便把大學變成了官方市場。沒有底線了。
黃:沒有底線了,什么都能做!
昌:是的,你看那個交換,都是什么人在做?有些學校,每年擠出一些正式的招生指標去做交易。相對來說,研究生以上的好做,名大利也大,做起來方便。另立標準,別擇“權才”。標準是雙重的,甚至是多重的,因人而異。
黃:現在很多學校都以培養官僚為榮,一到校慶,就說從我們這里出去的部級干部多少、廳級干部多少,沒有說培養多少一流的科學家、學者、培養多少作家、思想家之類的。
昌:建國前,僅人文領域,就出了好多大師,后來有誰?大家彼此彼此,都差不多。這也是錢學森提出的問題。失去特性的教育只能產生無個性的學人,想要頂尖的人,做夢去吧。就此而言,50年代初的院系調整,可謂“功不可沒”。政教合一,蘇化了。
黃:上世紀末的那股高校合并風,可以說是登峰造極的表現。表面上看是整合資源,優化辦學,實際上還是行政的力量在干預,還是那些當權的在進行利益博弈。
昌:蘇化之外,后來又襲得美國的一些皮毛,如五年一晉職等,實質并無變化。美國晉職有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三個內容。學校初評,通過后把被評者的代表作送兩位同行專家匿名評審。兩位都肯定,通過;都否定,pass;一位肯定,一位否定,送第三位專家,他肯定則通過,否定則pass。我們是這樣嗎?不是。做不到的。我們也試過匿名評審,但很快就變味了,有的論文還沒到同行專家手里,電話就打過去了。中國是人情國度,不足為奇。最后還是得靠由行政部門主導的由一大堆各類專家組成的職稱評審委員會來評,還是得依靠一套死板的評審標準。
黃:伴隨而來的是大量的學術垃圾,是成果原創性的嚴重匱乏。科研成果很多時候僅僅成為獲得一些利益的條件。沒有了敬畏,沒有了創造的激情和樂趣。
昌:以前我常說評職稱是最簡單的事情,搞一幫小學生,認得字,會做算術,就行了,要專家干什么!專家是沒有用的,只是豪華的擺設,用魯迅的話說,是“做戲的虛無黨”。再回到雜志審稿上來。國際知名的刊物,像英國的《自然》、美國的《科學》,像《分子細胞學》之類,人家的審稿專家是全球一流的,稿子經匿名評審發表出來,一般是可信的。我們這里的人文社科雜志沒這套程序,有決定權的是編輯。編輯的能力和喜好,編輯的交際圈,決定了雜志的質量和品位。這個搞法不對,等于把學術評價的權力交給了編輯。
黃:我們現在發表文章,幾乎不管專家不專家,大部分看關系。一些重點大學的博導啊、教授啊,最好是什么學部委員,他們手頭擁有大量的公共資源,他們可以拿這些資源去交換。諸如,發表文章、撈取課題、安排學生就業等等。實際上已經存在明顯的團伙化傾向。在這種情況下,雜志的發表機制和作者的投稿行為已經構成了一種可怕的惡性循環。什么都可以交換,什么都能夠交換已經成為一種潛規則,現在的很多學術會議,打著會議的牌子,實際上就是提供了一種交換的場所。當然也不排除一些真正的知識分子,但整個的學術風氣已經非常壞了。
四、堅守自由和寧靜的內心
做學問不是出自興趣,出于好奇,你會快樂嗎?我們實在是太勢利了,內心充滿功利。
昌:剛才講過,大學是人類知識的集散地,主要有兩個功能,一個是傳承知識,一個是創造知識。一個國家的知識水平取決于它最好的大學。我們國家的知識水平不高,北大、清華有責任,但主責不在兩校,而在教育的被集權。創辦一流大學,照現在這個樣子搞下去,沒戲。教育作為一個整體沒有特性,教師作為個體沒有個性,同質化,一個模子,怎么弄出大師來?前不久講中國現代學術史,講到魯迅、王國維,就覺得被郭沫若稱為“雙璧”的《中國小說史略》和《宋元戲曲考》是不可復制的。而我們現在的文學史,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的,都基本是一個面相。問學生看教材記不記得住作者,回答是記不住。作者不重要,教材上印不印有他或他們的名字無關緊要。署了名等于沒署,我把這叫匿名寫作。這樣的教材是集權制的產物,是根據行政化的知識生產規則生產出來的,雷同化,同質化,既無個性也無創造性。在這樣的體制下做這樣的學問,我越來越覺得毫無生趣。我認識一位德國學者,他搞中國研究,純粹出于興趣和好奇。他原是學地球物理的,偶然接觸到一本介紹禪宗的小冊子,感到神秘,就有探究的興趣,于是改學漢學。我們還有好奇心嗎?太生疏了。做學問不是出自興趣,出于好奇,你會快樂嗎?我們實在是太勢利了,內心充滿功利。
黃:我們受到的干擾太多了!不管是內心還是外在。一個教授,在教書做學問之余,可能一天到晚還要填無數的表格,生活的完整性就被這些無趣的表格破壞掉了,這只是一些表象,更為重要的是,內心的完整性、內心對某種價值的確認也被破壞掉了。整天處在一種毫無理由的評價體系中,天長日久,這些形式化的東西會改變一些非形式的東西。慢慢的,習以為常了,能接受了。我感興趣的是,為什么很多人不滿意這種生活,但少有人公開地背叛這種生活,可怕的惰性和慣性,有時真的已經像一個泥潭一樣將我們困住。
昌:這個跟中國知識人的傳統有關。古代的知識人是士子,西文譯成officer-scholar,是很確切的。經學是官學,不是私學。這是我們的傳統,知識只是進階的依據。
黃:也就是“學而優則仕”。
昌:對!它就是你謀生的一個手段。亦官亦學,官學一體。
黃:這樣看,教育體制改革的難度和我們的傳統的價值觀念的桎梏有關。
昌:肯定跟文化有關。中國古代的家族制本身就是集權制。傳統的東西不容易消失。因襲的負擔太重了。換湯不換藥,有些表面的東西迷惑了我們。官本位的根源在集權制。它不是重智的,智是依附性的。古代未仕的落魄文人,如蒲松齡、吳敬梓等,只配搞點小說。
黃:像屈原,屈原還是覺得自己失敗。他的這種挫敗感來自于沒有實現的政治抱負。他的那么多作品,其悲憫的情懷到現在都令我們動容,他內心高潔、也高傲,他沒有從一個文化人的角度來認識自己的價值。屈原這么一個冰清玉潔的人,最后都掙不過復雜骯臟的現實,最后還是只能以死明志,是否也恰恰證明了中國知識分子無法逃脫的“人事”的宿命呢?
昌:在中國高校,“人事”太重要了。我們提創辦一流大學,不突破集權制下的人事網絡,必將是一句空話。創辦一流大學,不是做不到的。美國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并不悠久,很快就成了一流大學。歌德大學復校后不久就產生了至今名滿全球的法蘭克福學派。香港科技大學,90年代初創校,現在亞洲已名列前茅。道理似乎并不復雜:一個是投資,創造一個好的硬環境;一個是體制,創造一個好的軟環境,好的軟硬環境可以吸引全球一流的學者來投,所謂筑巢引鳳是也。全球聘人,如今國內的機制辦得到嗎?形式上辦得到,實質上辦不到。迄今為止,我們已經引進了不少海外人才,但還沒有形成一個一流的學科。原因恐怕在于限制太多,軟硬環境不理想,來了很快就會被悶死。像英超的曼聯和切爾西,西甲的巴薩和皇馬,軟硬環境都不錯,拿大錢全球聘一流和超一流的球員,就能保持一流水平。可是你做不到。這不是說說就能辦到的。自生產是生產不出一個一流大學來的。流動是必須的。我非常喜歡孩子般的好奇,對這個世界,孩子總是充滿求知渴望。屈原《天問》里的問題就是孩子的問題,老子的也是,什么混沌、陰陽啦,都是孩子的問題。孩子的問題原是世界原初的問題。現在世界上的問題再多、再復雜,都可以追溯到其起點。起點永遠是簡單的。
黃:回到原初的問題,就是要恢復我們內心的寧靜,要恢復內心的自由。我記得陳平原說過這樣的話,一個好的學者,他需要的不是金錢,也不是權力,而是時間。他的意思是,對一個真正有創造力的人而言,給他創造的時間和空間,就是給他生命。說到底,我們當下的教育體制對教育最大的傷害,就是不但使教育者喪失了創造的樂趣和自由,也使被教育者失去了生命的激情和活力。
(作者單位:昌切,武漢大學黃燈,廣東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