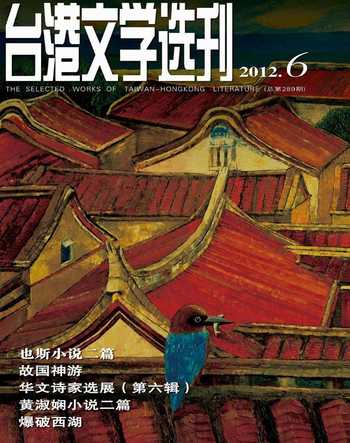黃淑嫻小說(shuō)二篇
黃淑嫻(香港)
我們的時(shí)代
爸爸的年代
路易莎有一個(gè)很古怪的童年, 但她并不知道。 她們一家三口,住在優(yōu)雅的市中心地段,四周是膨脹中的購(gòu)物商店。從外面看,她們住的那條小路被人潮重重包圍著,但如果你不慎在購(gòu)物大街迷路誤走進(jìn)去,你會(huì)為這兒寧?kù)o的氣氛感到措手不及。這里偶然會(huì)有巴士經(jīng)過(guò),為這片寧?kù)o補(bǔ)充一點(diǎn)大城市的節(jié)奏。路易莎家里養(yǎng)了一只貓,它喜歡低頭望著巴士經(jīng)過(guò)的一刻。貓年輕的時(shí)候經(jīng)常在下午走出花架曬太陽(yáng),但每次當(dāng)小貓懶洋洋地躺在花架旁邊的時(shí)候,路易莎總會(huì)使力把它扯回屋里,她害怕小玩伴會(huì)失足從五樓滑下去而死掉。每次當(dāng)她成功地把小貓拉回來(lái)后,她會(huì)嚴(yán)厲地教訓(xùn)小貓一頓,然后探頭望出窗外,從小貓剛才睡覺(jué)的角度俯視樓下的風(fēng)景。對(duì)面街上的粥面鋪噴出一陣陣強(qiáng)勁的白煙,樓下速食店傳來(lái)炸雞腿的味道,還有斜對(duì)面的那所神秘的杭州菜館,白天好像是一間空置的店鋪,晚上變身成衣香鬢影的場(chǎng)所,一排排名貴的房車(chē)擠滿了這條小小的街道。路易莎不明白當(dāng)中的原因,她只是不自覺(jué)地把這些影像一格一格印在腦海中。但這些眼前的風(fēng)景都不是路易莎最關(guān)心的,她把身體攀前,嘗試望向街角最右邊的一系列時(shí)裝店櫥窗。今天的模特兒公仔穿什么衣服呢?她喜歡那件日本深黑色的短褸,她認(rèn)為這是一件相當(dāng)入時(shí)的服裝。但媽媽在花架種的那盆可惡的蘭花一天一天地長(zhǎng)高,把她的視線擋住了,她只好把身子再攀前一點(diǎn)。
路易莎的學(xué)校就在她家的對(duì)面,這是她生活的中心。不知不覺(jué)間,她在這里過(guò)了十三年,在傷感時(shí)她走遍學(xué)校里每一個(gè)神秘的角落,在炎夏中她感受到大理石建筑的清涼,但路易莎對(duì)這以外的事物一無(wú)所知。長(zhǎng)大后朋友之間有時(shí)互相談到過(guò)去讀書(shū)的生涯,路易莎會(huì)皺著眉頭說(shuō):“香港有這樣的一所中學(xué)嗎?”朋友總以為她恥笑他們,但他們內(nèi)心的不快,路易莎并不知道。路易莎有幾位好同學(xué),每逢假日都來(lái)她的家,或者與她一起到海邊無(wú)無(wú)聊聊地游蕩逛街。這樣一個(gè)星期的七天其實(shí)她都沒(méi)有離開(kāi)過(guò)那優(yōu)雅的市中心地段,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十多年。她并未感到有什么特別,因?yàn)檫@里有她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或者是這里不知不覺(jué)改變了她的生活。她有不少同學(xué)都是住在附近的,形成了一個(gè)小小的生活圈。如果她想借功課,她會(huì)走到對(duì)面的電器鋪,那是她一位同學(xué)的爸爸開(kāi)的店鋪,她常常跟這位同學(xué)在店里溫習(xí)功課,坐在電飯煲和冷氣機(jī)之間思考算術(shù)難題。路易莎喜歡音樂(lè),她家里長(zhǎng)期放著一把木吉他,她會(huì)坐在窗邊自彈自唱,小貓是她的聽(tīng)眾。但吉他不是她的,是她住在海邊的一位不懂日語(yǔ)的日籍同學(xué)的。不知過(guò)了多久后的一天,這位日籍同學(xué)突然取回吉他,之后她便回到日本去了。路易莎有一個(gè)葡萄牙籍的同學(xué),從她家的窗口可以看到她的睡房。每次上中文課的時(shí)候,這位葡萄牙籍的同學(xué)總會(huì)帶著書(shū)本離開(kāi)課室,過(guò)了幾個(gè)月后路易莎從班長(zhǎng)那里打聽(tīng)得出原來(lái)她到另一個(gè)班上法文課去了。路易莎覺(jué)得這個(gè)同學(xué)很神秘,很想跟她成為朋友。有一次路易莎很高興到她家里玩,她從木柜中拿出一件薄薄的、圓圓的,直徑大概五寸長(zhǎng)的小金屬片。“這是什么?路易莎瞪大眼睛問(wèn)她。”“這是CD! 它比黑膠唱片好得多了,它不會(huì)容易弄花。你看!”話還未說(shuō)畢,她把所謂的CD用力擲到地上來(lái)證明自己的話。十五年后,CD在大街小巷普及起來(lái),路易莎走到音樂(lè)店鋪里,被數(shù)萬(wàn)張CD包圍著,但她記起的是掉在地上的那一只圓圓的物體,未來(lái)好像預(yù)先墮落在她面前。
路易莎有一個(gè)好爸爸和好媽媽。他們的分別是:爸爸喜歡揮霍,媽媽喜歡節(jié)儉。路易莎不明了他們的分別,但路易莎喜歡爸爸。大概用現(xiàn)在的社會(huì)角度看,路易莎的爸爸是一個(gè)購(gòu)物狂。他最喜歡購(gòu)買(mǎi)各式各樣潮流的東西。在路易莎小時(shí)候家里有一套高級(jí)Hi—Fi,無(wú)論是擴(kuò)音器、唱盤(pán)、收音機(jī)、錄音機(jī)和揚(yáng)聲器都是爸爸精挑細(xì)選的。路易莎不知道爸爸何來(lái)這樣的知識(shí)。這一家三口的另外兩個(gè)房間還有兩部當(dāng)時(shí)還未流行的微型音響組合。值得一提的是,爸爸是不喜歡聽(tīng)音樂(lè)的,好像連收音機(jī)也不聽(tīng);媽媽又只愛(ài)看電影,所以使用這些器材的重大責(zé)任便落在路易莎一個(gè)人身上。音響器材的熱潮過(guò)后,爸爸便向冰箱和電視機(jī)埋手。有一個(gè)時(shí)候,他們一家三口有兩個(gè)不同型號(hào)的大冰箱和兩部新款的大電視。媽媽用盡全力才能夠把其中一個(gè)冰箱轉(zhuǎn)讓給親戚。爸爸沒(méi)有氣餒,因?yàn)樗€有很多東西可以買(mǎi)呢。他鼓勵(lì)路易莎學(xué)習(xí)不同的東西。路易莎想成為女童軍,他便說(shuō):“真好! 我會(huì)送你一套童軍制服。”路易莎早上告訴他想學(xué)鋼琴,下午他便帶她到琴行買(mǎi)下一座黑色的高身鋼琴,很有氣派。爸爸去世的那一天,路易莎從醫(yī)院回來(lái),一個(gè)人在暗黑的房間聽(tīng)音樂(lè),那座Hi-Fi還是穩(wěn)固地站在這里,唱片不停地轉(zhuǎn)動(dòng),路易莎流著眼淚。
媽媽的年代
爸爸死了以后,路易莎再?zèng)]有學(xué)鋼琴了,節(jié)儉的媽媽把鋼琴轉(zhuǎn)讓給了親戚,換來(lái)了六千元。考入大學(xué)后,路易莎亦再?zèng)]有時(shí)間聽(tīng)音樂(lè)了,整天忙著跟同學(xué)一起。路易莎在不知不覺(jué)間走出了那優(yōu)雅的市中心地段,走遍大街小巷,但她還是喜歡每晚回到那熟悉的環(huán)境。路易莎離開(kāi)香港到外國(guó)進(jìn)修之前,把Hi-Fi搬到她的好朋友家里,她希望Hi-Fi能夠繼續(xù)奏出音樂(lè)。當(dāng)她把音響器材一件一件地搬上朋友唐樓的住所時(shí),她感到這些笨重的東西好像真的有點(diǎn)過(guò)時(shí)了。三年后路易莎回港,擴(kuò)音器已經(jīng)發(fā)不出聲音了,她把這兩大座的擴(kuò)音器抬到修理鋪去。“小姐,這個(gè)型號(hào)太舊了,我們修理不來(lái)的。”路易莎不懂得如何回應(yīng):“是這樣的嗎?”路易莎已經(jīng)記不起這套Hi-Fi的下落了。
回港后的路易莎感到一陣失落,她的貓已經(jīng)過(guò)世了,她的媽媽已經(jīng)老了,但流動(dòng)的城市仍然在路易莎眼前,她帶著興奮的心情踏入社會(huì)。她很快找到一份洋行工作。她和一個(gè)大學(xué)女同學(xué)搬了出來(lái),在海邊的一幢舊樓開(kāi)始新的生活。買(mǎi)家具、買(mǎi)電視、買(mǎi)家庭用品把路易莎忙了好幾個(gè)星期。她用最低的價(jià)錢(qián)購(gòu)買(mǎi)這些東西,好讓她不會(huì)花掉太多薪金。終于在一個(gè)天色灰暗的下午她們搬進(jìn)新居。路易莎滿懷希望地在自己的房間把一切東西安放好,然后走出客廳,探頭欣賞窗外的海景。但海面上的一層灰讓她感到不舒服,這個(gè)顏色好像是一襲白色婚紗浸在污水中。她記起那優(yōu)雅的市中心地段有很多婚紗店,那種白色是明亮的,好像包涵著無(wú)數(shù)的色彩在內(nèi)。路易莎不想再看下去,她轉(zhuǎn)過(guò)頭來(lái)逃避窗外的灰色,可惜屋內(nèi)的家具沒(méi)有放過(guò)她。她購(gòu)買(mǎi)的東西此刻讓她感覺(jué)更難受,她看到那沒(méi)有牌子的電視、沒(méi)有質(zhì)感的木桌椅和劣質(zhì)的窗簾布,她感到自己活在一個(gè)錯(cuò)誤的世界中。然而,這些東西老老實(shí)實(shí)地站在她面前,好像想跟她握一握手。
路易莎自此喜歡走回那優(yōu)雅的市中心地段。每逢假日的下午她喜歡與朋友在市中心的傳統(tǒng)酒店喝茶,閣樓的樂(lè)隊(duì)奏出輕快的華爾滋,一切還是歌舞升平。有一天的下午,路易莎在酒店遇上她的舊中學(xué)同學(xué)瑪格蘭。瑪格蘭在路易莎的成長(zhǎng)中扮演一個(gè)很重要的角色,一個(gè)反面的人物。在路易莎的記憶中,瑪格蘭每一天都是異常清潔的。她有兩條長(zhǎng)長(zhǎng)而帖服的辮子,以她當(dāng)時(shí)的年紀(jì)是不可能梳理得如此整齊的,她的家人每天一定花了很多時(shí)間幫她梳理。她身上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都是完美的,而且絕對(duì)符合校規(guī)的要求:藍(lán)色晶瑩的發(fā)夾、雪白通花的白襪、光亮有質(zhì)感的黑色皮鞋。她是一個(gè)活生生的小公主,永遠(yuǎn)帶著一個(gè)令人舒服的微笑。路易莎希望自己永遠(yuǎn)不會(huì)變成瑪格蘭。路易莎望著此刻的小公主已經(jīng)是媽媽了,她的兩個(gè)小朋友靜靜地坐著,旁邊還有一個(gè)傭人。路易莎沒(méi)有上前打招呼便離開(kāi)了,好一段時(shí)間她沒(méi)有再和朋友到酒店了。
媽媽過(guò)世的那一天,她接到醫(yī)院的電話便立刻乘坐的士趕到醫(yī)院。她的心情隨著車(chē)輪奔馳,眼前什么也看不到。“司機(jī),請(qǐng)你再開(kāi)快一點(diǎn)!”但車(chē)輪的轉(zhuǎn)速突然變慢。“司機(jī),是什么事情?”路易莎望見(jiàn)前方有一輛車(chē)和另一輛車(chē)相撞,兩名司機(jī)正在吵起來(lái)。“司機(jī),可以走另一條路嗎?”司機(jī)沒(méi)有回答她,因?yàn)樗腥硕伎梢钥吹竭@條小路只有一個(gè)方向。路易莎想馬上離開(kāi)車(chē)廂,她整個(gè)人好像在極度吵鬧和混亂的搖擺音樂(lè)會(huì)中,但突然她的眼睛接觸到她窗外的現(xiàn)實(shí)世界,她感到有點(diǎn)熟悉。那不是杭州菜館?她回頭望向上方,那不是我的舊居?一切好像回到默片時(shí)代,的士的車(chē)輪在優(yōu)雅的市中心地段慢慢前行,一種完全不真實(shí)的節(jié)奏。路易莎從來(lái)沒(méi)有從這個(gè)角度看自己的家,她很久沒(méi)有回來(lái)了,很多店鋪都變了,這段小路再談不上優(yōu)雅了。不知過(guò)了多少時(shí)間,前方的意外似乎得到緩解,兩個(gè)司機(jī)很滿意地各自走上自己的車(chē)。下一秒鐘,的士的車(chē)輪又以全速轉(zhuǎn)動(dòng),離開(kāi)了這條小路。路易莎回頭望向那優(yōu)雅的市中心地段,那漸漸變小的杭州菜館,她惟一認(rèn)識(shí)的店鋪。
我們的時(shí)代
我的名字是史提夫,我是一間偏遠(yuǎn)小學(xué)院的社工。一個(gè)月前我轉(zhuǎn)到這里工作,我喜歡這里,因?yàn)楣ぷ鞑⒉环敝亍W(xué)生有時(shí)會(huì)走來(lái)跟我談話,但總不是什么大問(wèn)題,我的責(zé)任是跟這群缺乏家庭照顧的青年人聊天。老實(shí)說(shuō),如果真的有有問(wèn)題的學(xué)生來(lái)找我,我又能夠幫到他們什么呢?我大部分時(shí)間其實(shí)是在處理文件、寫(xiě)報(bào)告,這個(gè)部門(mén)有很多文件要寫(xiě),什么事情都要報(bào)告,但不知給誰(shuí)看。
我的第一個(gè)“個(gè)案”是關(guān)于本校的一位英語(yǔ)教師,她就是路易莎。其實(shí)這不是一個(gè)什么個(gè)案,只是在上任的頭一天,一名很出鬼的學(xué)生走進(jìn)我的辦公室,他說(shuō)有一位老師責(zé)備他穿“人字拖”上課,他不明白為什么老師要這樣對(duì)他。他的家就在學(xué)院的對(duì)面,他到樓下茶餐廳與朋友見(jiàn)面或到對(duì)面報(bào)紙檔做兼職,他都是穿“人字拖”的,他認(rèn)為穿“人字拖”上課沒(méi)有問(wèn)題。我認(rèn)為這是小事,不需要小事化大。我隨即向他解釋老師只是希望你多注重外表,好讓往后找工作比較容易之類(lèi)的話。學(xué)生似乎對(duì)于我的解釋很滿意。他臨離開(kāi)辦公室前,我不經(jīng)意望向他很自豪的“人字拖”,當(dāng)中露出十只圍滿黑邊的腳趾。學(xué)生稚氣地?fù)]手跟我說(shuō)再見(jiàn),我看見(jiàn)他的手掌也染上一片黑色。我好像在“人字拖”與路易莎之間明白了一點(diǎn)事情。
我第一次碰到路易莎是她離開(kāi)學(xué)院的那天,幾位英語(yǔ)老師在辦公室為她搞了一個(gè)簡(jiǎn)單的歡送會(huì),我也有份參加。很奇怪,路易莎的面容有一種戰(zhàn)敗國(guó)人民的愁緒。她的衣服很簡(jiǎn)單,很樸素,你以為她是一個(gè)衣著隨隨便便的人嗎?看真一點(diǎn),她衣服的剪裁很特別,有點(diǎn)含蓄的怪異,質(zhì)料不是平時(shí)常見(jiàn)的。我直覺(jué)地認(rèn)為她不屬于這里。我一個(gè)人站在窗前,這里大部分人我都不認(rèn)識(shí),我看見(jiàn)他們談得很高興,說(shuō)到有什么好工請(qǐng)介紹之類(lèi)的話。路易莎似乎要到另一所學(xué)院教英文了。吃了一些三明治后我便獨(dú)個(gè)兒離開(kāi),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工作。
五時(shí)半下班的時(shí)候,我發(fā)現(xiàn)自己遺失了一張音樂(lè)會(huì)門(mén)票,這是一件很?chē)?yán)重的事情,因?yàn)檫@是一隊(duì)我很喜歡的樂(lè)隊(duì),很難得來(lái)香港表演。我找了很多地方也找不到,一個(gè)人很沮喪地在陌生的學(xué)院的角落四處尋找。我走過(guò)英語(yǔ)教師的辦公室,駭然發(fā)現(xiàn)門(mén)票很隨意地貼在辦公室門(mén)口,下面是粗大的黑字,寫(xiě)道:Who has left his precious ticket at my offce?Louisa。 我高興得手舞足蹈,馬上推門(mén)想說(shuō)多謝,而竟然忘記了敲門(mén)。門(mén)內(nèi)的路易莎與我對(duì)望,露出不高興的樣子,我隨即向她解釋事情,她聽(tīng)后笑了起來(lái)。這樣我和路易莎便認(rèn)識(shí)了。
幾個(gè)月后的一個(gè)下午,天氣突然轉(zhuǎn)冷,放學(xué)的時(shí)候我看到路易莎拖著一個(gè)很笨重的暖爐。她原來(lái)還是住在學(xué)院附近,我?guī)退雅癄t搬上她的家,然后把電源插上,暖意開(kāi)始一絲一絲地包圍著我們。她的家很講究,很整潔。我想象她是住在市中心的女性,但其實(shí)她就住在“人字拖”的對(duì)面。路易莎很客氣地為我準(zhǔn)備茶點(diǎn),小小的蛋糕很精致,白色的杯碟是名貴的骨瓷。屋外的陽(yáng)光慢慢消失,我們?cè)谌岷偷臒艄庀抡勗挕B芬咨f(shuō)她很喜歡“人字拖”這個(gè)學(xué)生,性格真誠(chéng),但她希望他明白生活的細(xì)節(jié)是很重要的。我告訴她“人字拖”在報(bào)紙檔兼職的事情,她走到窗邊張望,好像要尋找現(xiàn)實(shí)的全部。她坐下來(lái),說(shuō)起最初在學(xué)院教書(shū)的感受。她記得那一天走進(jìn)一個(gè)不像教室的教室,樓梯傳來(lái)學(xué)生大聲叫囂的聲音,她感到不知所措;以前自己學(xué)校上課的氣氛簡(jiǎn)直是蒼蠅飛過(guò)都聽(tīng)得到,她不懂得如何處理叫囂,這從來(lái)不是她所理解的。她緊緊地拿著課本,低頭想著:課室門(mén)口就在面前,要踏進(jìn)去,還是走回頭?路易莎這樣在學(xué)院教了兩年。路易莎把她自己的事情說(shuō)得很平淡,但我還是感受到她內(nèi)里的激動(dòng)。我覺(jué)得路易莎是一個(gè)很有趣的個(gè)案,第二天回到辦公室后,我把她的資料寫(xiě)在筆記簿上:“獨(dú)生女、講求生活細(xì)節(jié)、性格孤僻、教學(xué)問(wèn)題”。
第二次探訪路易莎是圣誕節(jié)的時(shí)候,那一天天氣變得溫暖,路易莎調(diào)了一杯果汁特飲給我,說(shuō)是什么酒店的招牌飲料。她向我講到她父母的事情。她總愛(ài)把沉重的事情變得輕松化。聽(tīng)完后,我想把氣氛變得真的輕松一點(diǎn):“你現(xiàn)有聽(tīng)什么音樂(lè)? ” 路易莎停了片刻沒(méi)有回答,“聽(tīng)的”。“那你喜歡聽(tīng)什么音樂(lè)? ”“我以前很喜歡聽(tīng)搖滾樂(lè)。”我馬上跟她說(shuō)了我對(duì)音樂(lè)的看法,又比較現(xiàn)在的音樂(lè)與八九十年代的分別。大概我說(shuō)得太興奮了,感染了路易莎,她開(kāi)始告訴我以前聽(tīng)音樂(lè)的事情。我們的關(guān)系有突破性的進(jìn)展。可是我不知為何說(shuō)了以下的一句話:“那你應(yīng)該買(mǎi)這個(gè)牌子的擴(kuò)音機(jī),我認(rèn)識(shí)一間在銅鑼灣的店鋪,店主比較老實(shí)。”我在紙上寫(xiě)了一個(gè)名字給路易莎,她可能以為我是推銷(xiāo)員,但我真的覺(jué)得這個(gè)牌子是好的。路易莎望著紙上的名字若有所思。回到家里,我繼續(xù)寫(xiě)有關(guān)路易莎的報(bào)告:“喜歡貓、音樂(lè)、爸爸是個(gè)購(gòu)物狂。”
過(guò)了幾個(gè)月,我接到路易莎的電話,她說(shuō)自己有一些儲(chǔ)蓄,希望可以買(mǎi)一部Hi-Fi。我和她到了銅鑼灣的店鋪,她選了一個(gè)很好的牌子,我非常滿意她的選擇,但我發(fā)現(xiàn)她是完全不懂得買(mǎi)東西的,她的表現(xiàn)太真誠(chéng)了,她應(yīng)該扮作漫不經(jīng)心,令他們感到焦急,然后要求一個(gè)折扣。路易莎付錢(qián)后,我在商店的門(mén)外用責(zé)備的眼神望著她,但可惜她仍然不明白,她還很高興地說(shuō)要請(qǐng)我喝咖啡,我拿她沒(méi)有辦法,只好直接跟她說(shuō)出我對(duì)她購(gòu)物態(tài)度的意見(jiàn):“現(xiàn)在所有東西都可以減價(jià)發(fā)售,你這樣購(gòu)物是很愚蠢的,很快便會(huì)把儲(chǔ)蓄花光。”路易莎說(shuō)她明白,但她每次扮演這個(gè)角色總是不成功,最后還是店主戰(zhàn)勝,她不想因購(gòu)物而產(chǎn)生挫敗感。自此,我和路易莎經(jīng)常一起購(gòu)物,她帶我到各式各樣的店鋪,我實(shí)地訓(xùn)練她成為一個(gè)稱(chēng)職的消費(fèi)者。我們喜歡在大減價(jià)的時(shí)候買(mǎi)質(zhì)料好的衣服、顏色特別的皮鞋和耐用的家具。在這不講求品質(zhì)和細(xì)節(jié)的年代,路易莎有不一樣的追求。不知不覺(jué)間,寫(xiě)報(bào)告一事已經(jīng)忘記了。
很多年后,我和路易莎在城市中心的酒店喝下午茶,我突然想到那一張貼在門(mén)口的音樂(lè)會(huì)門(mén)票。“路易莎,其實(shí)你不應(yīng)該把門(mén)票隨便貼在門(mén)上,萬(wàn)一有頑皮學(xué)生經(jīng)過(guò),那就不堪設(shè)想……”路易莎望著我笑一笑,不知道她明白還是不明白,但她的精神是如此放松,我感到很高興,這是她成長(zhǎng)的環(huán)境,她從這里離開(kāi),最后還是回到這兒,哪怕這個(gè)年代變成怎樣。
(選自《香港文學(xué)》2010年1月號(hào),題為本刊所易)
“贊”:一件日常生活瑣事
張清平以一身輕便的服裝走進(jìn)新近發(fā)展的東京國(guó)際羽田機(jī)場(chǎng)。一切很簡(jiǎn)單和直接,沒(méi)有擁擠人群,他把護(hù)照和機(jī)票遞給柜臺(tái)后的女服務(wù)員,一分鐘后他的登機(jī)手續(xù)已經(jīng)辦妥。接過(guò)登機(jī)證,張清平準(zhǔn)備到商務(wù)客位的候機(jī)室。他今天很愉快,他身上那件別致的Comme des Garcons T恤,令他在東京濕冷的空氣中也有快活的感覺(jué)。“希望您有一個(gè)愉快的旅程!”女服務(wù)員望著他身上五彩繽紛的格子布說(shuō)出有禮貌的話。
偌大的玻璃窗比電影的銀幕還要真實(shí),二十八歲的張清平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份差事,現(xiàn)在正把手腳放松,坐在候機(jī)室的巨型玻璃前自我感覺(jué)良好。候機(jī)室很寧?kù)o,電視機(jī)有時(shí)傳來(lái)幾陣笑聲,但很快便給沉默的空氣吞噬。張清平雖然精通日語(yǔ),但他對(duì)日本文化是不了解的。他暫時(shí)沒(méi)有興趣思考為何這個(gè)候機(jī)室會(huì)鴉雀無(wú)聲,現(xiàn)在他只想任由自己漫無(wú)目的望向窗外飛機(jī)的升降。這是一個(gè)視覺(jué)的享受,但他并不知道這種享受是因?yàn)樗恍枰鎸?duì)視覺(jué)帶來(lái)的噪音。這里一切是震撼的,同時(shí)又是靜默的。
其實(shí)張清平內(nèi)心的某一處清楚知道自己根本不是精通日語(yǔ),至少不是個(gè)及格的翻譯者,一切都是他姑丈的誤會(huì),或者是親戚們希望他能夠有一種謀生的才能而夸大其詞。張清平跟著姑丈來(lái)到東京與當(dāng)?shù)匾患曳b公司談中國(guó)大陸生意,他當(dāng)了半天的翻譯,把他在大學(xué)三年的日語(yǔ)知識(shí)全拿了出來(lái),算是盡了他最大的力量吧,所以他感到很快樂(lè),很滿意。大概這次工作的滿足感可以讓他一年內(nèi)不用再工作了。距離登機(jī)還有個(gè)把小時(shí),張清平開(kāi)始對(duì)眼前的升降影像生厭。他左手拿著啤酒呷一口,右手從軟牛皮的黑色背囊里取出電腦,開(kāi)始上Facebook。離開(kāi)香港數(shù)天,好像沒(méi)有什么改變,但他照例也會(huì)對(duì)不同事情表示“贊”的態(tài)度,他不是那種喜歡長(zhǎng)篇大論的人,沒(méi)有什么特別的感想,他覺(jué)得“贊”最適合他的個(gè)性。
還有很多時(shí)間,張清平無(wú)無(wú)聊聊地打開(kāi)他不常看的電郵,喝了兩罐啤酒后,他差點(diǎn)兒連密碼也忘記了,“123abc”,打開(kāi)了。電郵畫(huà)面是密密麻麻的文字,他最怕的,其實(shí)當(dāng)中大部分都是宣傳廣告。他逐一打開(kāi)看看有什么適合自己的。看了差不多十分鐘,到了最近的三天,他發(fā)現(xiàn)有一個(gè)人每天都傳給他一封電郵,三封都是以“盜竊”為主旨,他好奇地打開(kāi)第一封,馬上嚇壞了,他很少看到這么長(zhǎng)的中文電郵,署名是一個(gè)名為沈大志的人。
這個(gè)沈大志是張清平的大學(xué)同學(xué),沈大志念的是中文系,張清平是商科學(xué)生,他們從來(lái)沒(méi)有在同一課堂上過(guò)課,他們互相認(rèn)識(shí)是因?yàn)閮扇送瑯悠珢?ài)大學(xué)某大樓某某層的洗手間,見(jiàn)面多了便開(kāi)始交談起來(lái)。他們?cè)?jīng)通過(guò)一兩次電郵,交換一下音樂(lè)會(huì)的情報(bào),但只是這樣而已。如果世界上有一些朋友只會(huì)在洗手間碰上才會(huì)談話,他們大概就是這類(lèi)型的朋友了。酒精讓張清平處于無(wú)重量的狀態(tài),他喜歡這樣,他也經(jīng)常是這樣,這種熟悉的感覺(jué)像他老朋友一般。“啊!沈大志,三樓廁所。”他弄了一杯咖啡好讓自己清醒一點(diǎn),他終于想起來(lái)了。身體上某種動(dòng)力叫他急忙走回電腦前,好像小孩子發(fā)現(xiàn)了新玩藝似的。在這樣單調(diào)的氣氛下,他終于尋找到刺激。他開(kāi)始閱讀第一封“盜竊”電郵。
清平:
你還記得我吧?三樓廁所。上次跟你在音樂(lè)會(huì)相遇后,已經(jīng)有五年沒(méi)有見(jiàn)面了。不知你近況如何?我想告訴你,我昨天被人偷了兩百元,為何是我?為何是我?為何是我?我在這所惡劣的中學(xué)教書(shū)多年,我比任何一個(gè)老師都要用心。昨天,你知道嗎?坐在后邊的林老師在科主任面前撒嬌,她的工作便轉(zhuǎn)到我的身上,我都欣然接受。你還知道嗎?我從來(lái)不會(huì)罵學(xué)生,處處保護(hù)他們,就算他們抄功課,我都會(huì)為他們解釋?zhuān)o他們機(jī)會(huì)改過(guò);但這班沒(méi)有良心的學(xué)生,還是擁戴那個(gè)沒(méi)有文化的體育老師,說(shuō)他有型、有個(gè)性。我做錯(cuò)了什么?為什么他們不放過(guò)我?為什么他們還要偷我的錢(qián)?我很害怕,我很害怕,莫非我得罪了什么人,他們要向我報(bào)復(fù)?
沈大志
張清平把電郵讀完,四周的環(huán)境仍然是寂靜無(wú)聲,不少穿著西裝的中年男子正在休息,張清平這時(shí)的心臟好像跳得快了一點(diǎn),與這里的節(jié)奏開(kāi)始不協(xié)調(diào)。他為何這樣緊張,只是兩百元而已,為何這樣大驚小怪呢?工作不愉快,可以告假休息,例如找個(gè)假期到瑞士滑雪。張清平近年愛(ài)上滑雪,每逢冬天便跟一幫網(wǎng)上認(rèn)識(shí)的朋友一起到歐洲滑雪,這些是他的滑雪朋友,只有在雪山上才會(huì)見(jiàn)面。沈大志應(yīng)該跟他到瑞士,這樣他便會(huì)忘記學(xué)校的煩惱,就是這樣容易。他沒(méi)有馬上回應(yīng)沈大志的電郵,他選擇繼續(xù)閱讀第二封。
清平:
今天我又被人偷去一百元了,為何在這學(xué)校只有我才遇到這樣的事情?我告訴你,我現(xiàn)在知道是誰(shuí)干的。昨天我跟同組的陳老師吃中午飯,希望多了解一點(diǎn)學(xué)校的事情。我在他面前說(shuō)科主任的不是,因?yàn)槲抑浪麄儾缓停R上興高采烈地回應(yīng),一頓飯說(shuō)個(gè)不停。回到教員室以后,我到洗手間刷牙,隱約聽(tīng)到兩個(gè)人在門(mén)外細(xì)聲說(shuō)話,我輕步走到門(mén)后,把耳朵緊貼在木門(mén)上,我肯定這是陳老師與科主任的聲音,沒(méi)錯(cuò)。我不敢推開(kāi)門(mén),而聲音好像愈走愈遠(yuǎn),我全身顫抖,只好繼續(xù)刷牙,直至臉盆一滴一滴的血絲提醒我是上課的時(shí)間了。我現(xiàn)在知道了,是他們一伙人合干的,他們要讓我感到不安,逼我走上絕路……
張清平開(kāi)始懷疑這個(gè)人為何要告訴他這件事情,他從來(lái)沒(méi)有他的電話號(hào)碼;說(shuō)真的,如果他在這里出現(xiàn),他也未必能夠認(rèn)出他來(lái)。然而,這個(gè)電郵令張清平感到不安,他覺(jué)得事情不是這樣簡(jiǎn)單。雖然他一般拒絕參與太復(fù)雜的事情,但這件事有一定程度的娛樂(lè)性吸引著他。究竟誰(shuí)偷了沈大志的錢(qián)呢?他愈想愈緊張,迫不及待地打開(kāi)第三封電郵。
很高興告訴你,清平,我們學(xué)校今天又發(fā)生偷竊案了,但主角不再是我了。我可以安心回到自己的座位批改功課了。
張清平很失望,這樣便完結(jié)了?太缺乏情節(jié)吧!他走向酒柜,選了一種當(dāng)?shù)爻霎a(chǎn)的清酒,味道較苦澀,但在這種環(huán)境下有這樣的沖擊也不錯(cuò)。張清平又回到那片偌大的窗前,呆呆地望著機(jī)場(chǎng)跑道上的飛機(jī),消磨他上機(jī)前最后的半小時(shí)。不知為何,他腦海中浮現(xiàn)了臉盆上那一滴一滴的血絲,不斷地從沈大志的口中流出來(lái)。他內(nèi)心有一種從輕松中產(chǎn)生的激動(dòng),他大聲推開(kāi)了椅子,發(fā)出尖銳的聲音,然后跑到電腦前,按下回復(fù)鍵,給沈大志寫(xiě)下他最熟悉的一個(gè)字:
“贊!”
(選自 《香港文學(xué)》 2011年1月號(hào))
·本輯責(zé)編馬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