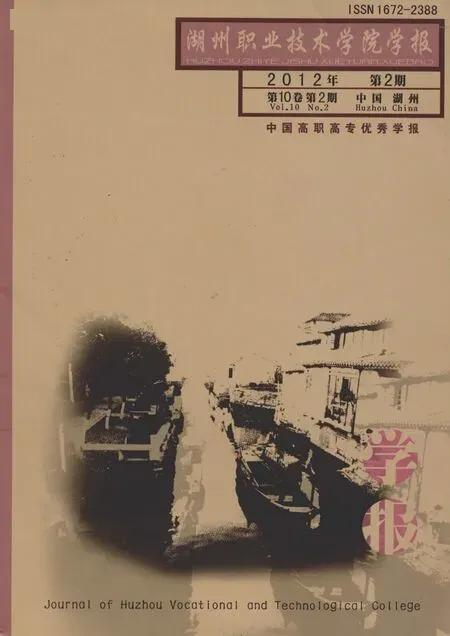湖州古代商業起源探析*
周 向 陽
(湖州師范學院 社會發展學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長期以來,人們形成了一種觀念,即我國商業起源只始于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至于江南地區的商業在中國商業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則少有人注意。但實際上,江南商業的發展并不晚于中原地區。從考古發掘材料和古代文獻資料記載來看,作為中國人類歷史發源地之一的浙江湖州地區,商業發展非常早。本文擬就此展開探究。
一、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個別的、偶然的物物交換的出現
湖州是人類歷史的發源地之一,歷史十分悠久。在距今10萬多年前,古人類就已經在西苕溪流域這塊土地上生活棲息。雖然,“邃古之民,生活鄙陋,穴居野處,飲血茹毛,食草之食,衣禽獸之皮,不獨經商服賈,茫然不知,樹藝稼穡,亦非所習”,[1](P5)但進入母系氏族社會后,生產力發展,原始農業、原始畜牧業、原始手工業相繼產生并得到初步發展。特別是農業,成為史前湖州地區主要的經濟形態。有關研究表明,此時期,寧紹平原、杭嘉湖平原的沼澤地帶,已開始人工種植水稻。[2]在處于由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階段的邱城崧澤遺址中層,發現了一件菘澤文化時期較小的三角形犁型器。[3]這表明,當時湖州的農業已經從耜耕階段發展到犁耕階段了。
在原始農業發展的同時,原始手工業也產生并得到發展。在處于母系氏族時期的邱城馬家浜文化遺址中,出土了一些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生產工具以石器為主,如石錛、石斧。生活用具以陶器為主,有釜、鼎、陶罐等。此外,還有骨器,如狩獵用的骨鏃、切割或鉆孔用的鑿錐,及縫綴用的骨針等。遺址中還出土了三塊炭化的野生葛麻織成的織物殘片,這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織物,表明當時的手工藝已比較先進。到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過渡時,手工業水平進一步提高,崧澤遺址的墓葬證明了這點。該遺址發現了9座墓葬。在隨葬品中,發現了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兩大類型,如紡織工具石質、陶瓷質紡輪,石、骨質針等物。[4](P5)可見,母系氏族時期,人們的生活比原始人群時提高了很多。
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為交換提供了物質基礎。而且,由于各地區氏族、部落之間具有不同的經濟特點和文化面貌,再加上“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導致的暫時分工”,[2]使得交換成為必要。原始的物物交換就在這時產生了。
在湖州古遺址的出土文物中,我們可以發現湖州先民們進行物物交換的一些痕跡。如邱城遺址的下層出土了大量的作為裝飾品的玉器,安吉縣遞鋪鎮安樂村的安樂遺址中層菘澤文化層中,累計出土各類遺物數百件,其中有一些玉質佩飾。[5](P5)然而,湖州本地是不產玉的,在浙江境內,只有青田、昌化等處產玉。其他產玉地離浙江較近的有山東鄒縣、峰縣和萊陽等地。[2]很明顯,這些玉不是湖州所產,而是異鄉之物。這些玉可能是通過物物交換從附近部落或遙遠的氏族部落輾轉得到的。
當然,這個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社會分工也不太明顯,手工業還沒有從農業中分離成為專門性的生產部門,只是在農閑間隙中才進行一定的手工業生產。因此,這種交換只能是個別的、偶然性的。而且,限于當時有限的生產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基本上還是實行氏族公有,勞動還不是私人勞動,產品也還不是私人所有。雖然當時可能存在某種私有現象,但私有制尚未形成。所以,那個時期的物物交換只在氏族、部落之間進行,氏族成員之間基本上不可能產生交換。
二、父系氏族公社時期商品交換的擴大與商品生產的開始
大約在距今5 000年前,浙江進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階段。湖州屬于這個時期的文化遺址主要是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東林鄉良渚文化遺址。這一時期,社會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生產和生活水平較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大大提高,湖州已經進入初級文明社會。[6](P12)考古學家慎微之先生曾指出:古時之錢山漾,“其大部分為古城市之舊址”,“曾一度人煙稠密,嗣因洪水泛濫,古吾陸沉,始成今日一片汪洋”。[4](P4)
良渚文化時期,湖州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發展較快,開始呈現越來越明顯的分工態勢,為商品交換的擴大和商業生產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1.農耕農業的進一步發展 良渚文化時期,湖州耕作農業持續發展,水稻種植技術大大提高。在錢山漾遺址中,出土了成堆的稻谷。據鑒定,有秈稻和粳稻兩種。粳稻是秈稻經過長期栽培派生的品種,由此也反映出湖州水稻種植久遠的歷史。同時,湖州先民已經懂得人工灌溉和施肥技術,遺址出土了專門用來戽水和罱河泥的“千篰”。在稻作農業之外,蔬菜瓜豆的種植和果樹的栽培已是當時農業生產的一個重要內容。從錢山漾遺址中出土的蠶豆、芝麻、花生、甜瓜子、西瓜子、兩角菱、葫蘆等多種栽培作物的種子,酸棗和毛桃等水果類種子,及一些尚未辨識和鑒定出的植物種子等,就是很好的證據。
從湖州良渚文化遺址中,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幾點:(1)湖州原始農業發展較早,且技術較為先進。良渚文化時期,湖州農業生產已經進入犁耕農業時期,并步入犁耕農業的成熟階段,正在向著精耕細作的方向發展。(2)湖州原始農業內涵豐富,品種多樣,除了稻作之外,還有眾多的瓜果蔬菜。這些農作物與稻作種植相輔相成,保障了人們的生活需要。湖州的原始農業相當發達,且已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2.畜牧業的發展 在原始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家畜的飼養也發展起來。錢山漾遺址中,存在著大量的豬、狗、牛等骨骼,說明湖州先民已經飼養家豬、狗和牛等。
3.手工業的發展與分離 原始農業、畜牧業的發展,為湖州先民提供了比以前豐富的物質資料,也為手工業的發展及其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提供了條件。良渚文化時期,湖州地區的手工業發展到了較高水平,這主要表現在:(1)手工業生產規模較大,數量眾多,種類多樣。僅就竹器而言,在錢山漾文化遺址已發掘的700多平方米的范圍內,發現了200多件竹器,且品種較多,有農業和日常生活用的魚簍、谷籮、竹籃、簸箕以及竹席等。此外,在遺址中還發現紡織工具陶制紡輪57件,還出土了許多諸如斧、鉞、刀、鏃、鉆、鑿、矛、犁等石器。[4](P5)(2)手工業的技術水平較高。錢山漾文化遺址中的手工藝品竹制品,絕大多數是用刮光篾制成的。其編織方法多種多樣,有些編制部位與現在的“杭州籃”相一致,尤其是使用了“梅花眼”和“辮子口”等較復雜的花式。[4](P3-4)這必須具備相當熟練的技術水平。其中發現的一只1.8米長的木船槳,制作規則,刳制光潔,說明此時木器的制造有了較高技藝。陶器,美觀實用,胎質細膩,胎壁勻薄,已掌握并盛行快輪制陶術。此外,錢山漾遺址中出土了細絲帶、殘絹片和絲線等,其中出土的絹片采用平紋織法,其技術同現代一般的絲織品相近,反映了湖州先民在絲、麻織品的紡織技術上已獲得巨大的成就。[4](P5)東林鄉良渚時期的墓葬出土了斧、琮、鉞、璧、環、冠等制作精致的玉器。從這些玉器可以看出,在制玉行業,人們已經掌握了切割、磨制、拋光、雕鏤等工藝。
上述手工業品的生產不可能是農閑才進行生產的手工業者所能完成的,只有專業手工業者,才能生產出這些數量多、技術高、樣式精美的器物。湖州古遺址中的玉器也反映了手工業的發展與分工。1971年,湖州楊家埠良渚遺址出土了一件長條形玉鉞。該玉鉞近肩部有一大一小的圓孔,兩面各有若干道平行的陰線弦紋,并相交接成有規則的幾何紋。有關專家認為,玉鉞是禮器,是兵權的象征。由此可知,當時湖州已經處于軍事民主制階段。[6](P6)1986年,在東林鄉的一個良渚時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斧、琮、鉞、璧、環、冠等制作精致的玉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千金商墓村涇堂墩遺址也出土了玉璧、玉環、玉錐等良渚玉器。[5](P8)湖州古遺址出土的玉器不但數量多,品種豐富,有禮器、祭祀用器和裝飾品三大類,而且這些玉器的琢磨、雕刻都很精致,布局、花紋、表現手法各異,應當是專業人士制作。生產大量如此技藝精湛、高度規格化、社會化、標志化的玉器,從玉材的選擇、儲運、研制、轉運、交換、使用,沒有專業化的琢玉勞動儲備和嚴密的社會分工,是不可能的。有學者據此認為,“在這些多工序、高技能的專業化勞動中,折射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工的趨勢。”[7]所以,可以斷定,良渚文化時期,湖州手工業已從農業中分離了出來。
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的發展及相互分工,使剩余產品出現,私有財產也隨之產生;同時,也使商業經濟的發展成為可能和必要。馬克思在論述商業的起源時曾經指出:“隨著生產分為農業和手工業這兩大主要部門,便出現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8](P159)因此,父系氏族公社時,在出現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的情況下,不同氏族、部落之間,原來就已經存在的農牧產品、手工業品和土特產品的交換,呈現出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上述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器數量多,種類豐富,但正如前所述,湖州本地區是不產玉的,玉器或玉器原料只能依靠外地供應。可以肯定,如此大規模的需求,通過個別的、偶然的物物交換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這只能說明當時的商品交換發生頻繁,且已經比較正規地開展起來了。
隨著交換的擴大,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也出現了。這在錢山漾遺址下層出土文物中反映出來。考古人員在該遺址的甲區發現了兩處居住遺址:一處是呈長方形的房屋,東西長約2.5米,南北寬約1.9米,面積約為4.75平方米。房屋的正中有一根“檁脊”,上面蓋有大幅的竹席。在該遺址下層出土了200多件竹器和植物種子等。乙區的一座房屋,長約3.18米,屋頂蓋有大幅樹皮、蘆葦和竹席等。在它的東邊散亂地堆放著許多青木岡木,木材旁還發現了多處紅燒土灶穴。這兩座房屋呈南北向排列,相距約40米(中間尚有未發掘部分)。[9]“甲區的房子里和屋旁有大量的竹器,不大可能都是自己使用的。把它看作交換的商品,似乎比較恰當些。”[10](P322)這樣的分析是合理的。
綜上所述,隨著湖州地區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原始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發展與分工,剩余產品越來越多,私有化程度也越來越高,較頻繁、較大規模的正式的商品交換已經成為必需。母系氏族時期那種個別的、不經常的交換形式,逐漸被正規的、經常的、社會所必需的交換,即商品交換所代替。隨之,出現了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
三、傳說時期湖州商業的產生
到堯、舜、禹、防風氏傳說時期,湖州社會經濟大為發展,衣食居處較之洪荒之世,已截然不同。而且,為政者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推動著全國商業的發展。如黃帝時,政權一統,并采取措施,使“通商之途廣,物產之轉運易。”[1](P6)堯舜之時,商業上雖無大設施,但“其庶政之與商業有關者實多”,如“后稷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又使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即分工之制也,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即貿遷有元也;以風化未通,九州隔絕,命奚仲撓曲為了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即便利交通也。”以上種種,雖非專為商業,“然有裨于商業者甚大。”[1](P10)大禹平息水患,自是有利于交通和商業。同時,禹本人也十分重視商品交換的作用。據《尚書·皋陶漠》記載,禹在治理洪水之時曾說:“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丞民乃料,萬邦作義。”意為大水得治之后,要和稷一起教民播種百谷,使人們有充足的糧食和肉食;要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這樣,天下才得以太平,人民才能安居樂業。雖然,這些并不是具體針對湖州商業的有力措施,但也能為湖州商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在這種情況下,湖州商業產生了,并有一定的發展水平。
1.商品交換的范圍擴大 商品交換不僅在部落內部進行,也在部落邊界間進行,甚至可能已達更遠的地方。據《管子·揆度》篇說:堯舜的時候,“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這說明黃河流域的部落和西北、長江流域之間的部落已有交換。上海青浦福泉山9號墓出土了一根罕見的象牙雕刻,這可能是從南方通過交換得來的。[11](P11)這些雖然不是關于湖州商品交換的直接記載,但可作為當時湖州境內先民們商品交換產生的印證,說明交換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臨近的部落氏族之間,遠距離的商品交換已經產生。這種遠距離的商品交換自然也不再可能是原來那種直接的物物交換了。
2.商品交易的種類豐富、數量加增 此時,商品交換不再局限于此前的裝飾品玉器,糧食、家畜、陶器、竹器、麻布、絲織品等都被投到交換中去。而且,數量加增,遠非此前所能比擬。這從禹時各州所貢之物大體可見。大禹平息水患之后,乃分別九州*九州指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揚州地域約包括現在的安徽、浙江、江蘇南境、江西北境。湖州屬揚州。,任土作貢。《尚書·禹貢》記載: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筱簜、齒、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桔柚,錫貢。”
3.主要商品的發展情況 湖州絲綢歷史悠久,技術水平高,成為當時重要的商品。雖然對湖州絲綢商品的交換尚無直接史料記載,但《禹貢》的相關記載可作旁證。揚州上貢貢品中有“織貝”,乃“綿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雖然,現尚不明確揚州所貢“織貝”是否出自湖州,但湖州早在錢山漾文化中就已出現了平紋綢,所以,到禹時出現“貝錦”這種高檔絲織品應是可能的。而且,當時湖州絲織發達還有一個佐證:湖州屬古防風國。傳說中防風氏也是個治水英雄,而且是百越民族的創世神。大禹治水成功后在會稽慶功,《左傳·哀公七年》載:“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帛,絲織品的總稱,與會者都要“執玉帛”以貢禹王,這與《禹貢》寫的相符。防風氏當時所執之帛應是“織貝”了。另外,《禹貢》載:“揚州……厥篚織貝”,宋人蔡沈注曰:“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絲織入篚的事,湖州早有淵源。錢山漾遺址中出土的絹片、絲帶、絲線等物,在被發現時大部分都是存放在竹筐里。[4](P11)因此,《禹貢》中揚州所貢之織貝,極有可能產自或部分產自湖州。
竹或竹器是湖州傳統的商品,錢山漾遺址中發掘出200多件各式各樣的竹器,而且湖州竹器早已經進入商品流通領域。到此時期,竹或竹器的交換應更加頻繁。《禹貢》記載:九州中有六州進貢絲綢,在所貢絲綢之前都有“厥篚”二字。篚就是竹筐。蔡沈注釋,“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竹主要產于江南,因此揚州“厥貢筱簜”。北方幾州所用之篚,其產品或原料應主要來自揚州。而以產量和水平來說,湖州竹器和竹器編織應該已經通過商品交換到了其他六州或其中的某些州。
此外,這時已經出現了較為固定的通商道路,“蓋入貢之道,即通商之道也。”[1](P11)
綜上所述,湖州商業跟中國商業一樣“發達甚早”,且商業之發達,與文化相表里,[1](P3)洪荒之域,即已孕育商業之胚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湖州就存在偶然的物物交換。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加劇,私有制開始產生,交換逐漸擴大并成為經常的、正規的現象,而這又促進了湖州商品生產的出現。到傳說時代,湖州商業進一步發展,商品交換范圍日益擴大,絲織品和竹器成為主要的商品。隨著商品交易范圍的擴展,出現了以貢道為主的、固定的通商之路。可以說,在中原地區商業產生的同時,湖州商業也同步發生。這說明,以往我國商業只起源于黃河流域的說法過于片面。
參考文獻:
[1] 陳 燦.中國商業史[M].王孝通增訂.北京:團結出版社,2007.
[2] 王心喜.從出土文物看浙江的原始農業[J].浙江農業大學學報,1983,(4).
[3] 梅福根.浙江吳興邱城遺址發掘簡介[J].考古,1959,(9).
[4] 嵇發根.絲綢之府湖州與絲綢文化[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
[5] 沈 慧.湖州古代史稿[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
[6] 林正秋,陶水木,徐海松.浙江地方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7] 牟永抗.良渚玉器和中華文明起源研究[J].杭州考古,1994(1/2合刊).
[8]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浙江省文管會.吳興錢山漾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1960,(2).
[10] 林耀華.原始社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4.
[11] 朱國棟,王國章.上海商業史[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