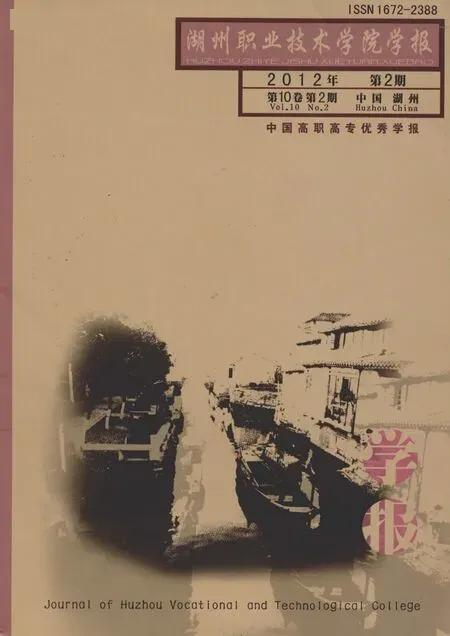國際化進程中地方性知識的性別主體創造
——以越南老街省達芬村紅頭瑤婦女為例
馬 燕 坤
(云南大學 國際關系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性別是一定社會關系及權力話語的表征物。隨著時代的推進,地方性知識在國際化市場中性別主體的創造上日益產生重大價值。在男權文化規制下的性別關系中,女性正在借助國際市場激活性別主體意識,重建性別文化,從而改變權力話語的構成方式。當今的女性不僅是物質身體的表達,更是指意身體的意義結點。通過對越南老街省民俗旅游村----達芬村其婦女的考察,可發掘當代女性憑借國際化際遇能動地打造性別主體角色,而力圖建構關系網絡并獲取權力話語的表述機制。
一、由地方性知識表征的達芬村紅頭瑤婦女
達芬村(Taphin)位于海拔1 500米的越南老街省沙巴鎮(Sa Pa Town)的東部,距沙巴鎮15公里。進入21世紀,因其獨特的民族文化,達芬村被越南政府遴選為民俗旅游開發的一角。目前,該村民俗旅游已進入如火如荼的階段,在境內外聲譽鵲起,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游客。
1.紅頭瑤是一個具有獨異文化色彩的民族 這不僅體現在外顯的型制上,而且也飽藏于內蘊的結構中。濃郁的文化不僅是紅頭瑤表征自我、模塑認同、區分他族的條件,而且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賺取利潤、獲得錢財、增加收入的籌碼。
2.豐富多姿的文化是紅頭瑤行為模式的基礎 聚族而居的格局使紅頭瑤成為對自身文化有共同理解,及生產和消費自己勞動成果的群落。紅頭瑤作為瑤族的一個支系,因婦女頭頂或裹紅色頭巾而獲其名。這既是紅頭瑤區別于其他民族的一個符號,也是紅頭瑤婦女在其民族社會中獲得性別話語的一個物件。紅頭瑤婦女因之對外建構了身份,對內模塑了認同。
3.紅頭瑤婦女之于黑苗婦女的身份建構 達芬村除紅頭瑤外,還有黑苗。紅頭瑤婦女頭頂或裹紅色頭巾的裝束,使其較易與同村鄰寨的黑苗婦女區分開來。黑苗婦女青衣藍布,衣褲背帶上無繡花。紅頭瑤除紅色頭巾的鮮明特質外,在穿戴上還密織著色彩繁多的繡花。另外,在飾物上,紅頭瑤和黑苗婦女也存在著區別:黑苗婦女的耳環和手鐲是銀質的,且數目有別。尤其是耳環,不僅模樣大且數量多,每只耳朵上少則兩個,多則七八個,甚至十個以上,老年婦女尤為突出。而紅頭瑤婦女無論年老年少,一般只戴一個,最多的也只戴三四個(一只耳朵上戴一個,另一只上戴兩個,或每只耳朵各戴兩個),為銅質的。紅頭瑤婦女因為穿戴,便同鄰近黑苗,甚至異域其他民族區別開來,從而樹立起本我形象。
4.紅頭瑤婦女在同族中的認同建構 在達芬村紅頭瑤社會中,所有女性,尤其是成年女性都有戴紅頭巾的習慣。這是一個性別標志,也是權力話語的體現方式。無論在家,抑或田間勞作或趕集買賣,她們都以此裝束出現。對于未婚女性,她們會戴著嶄新的紅頭巾或穿上刺繡密集精細的衣褲,同時蓄眉,向異性青年作出未婚示意。這一方面彰顯了自我狀況,同時預示了一定的社會關系,即達到對傳統既定社會關系的續接,同時又是一種超越既定關系而試圖拓展新穎社會關系的構擬。已婚女性,則以不留眉及暗淡的繡花色調裝束,向外界透露其角色特質,從而維系了既定的家庭關系。
5.紅頭瑤婦女在傳統生活中的地位 在達芬村啟動民俗旅游前,紅頭瑤婦女的生計活動限于家庭、族際之間。相夫教子、照顧老人、織布制衣、料理家務、插秧收谷等是她們的主要活動內容。種植蔬菜稻谷、摘拾山貨(如野生菌、雞樅、竹筍等)等則是她們補給家用的經濟方式。
基于傳統的農耕性,紅頭瑤婦女維持了既定的社會關系:家庭是社會關系的基礎;血緣是社會關系的半徑;自給自足是生產目的。特定的行為模式決定了紅頭瑤在傳統社會中的權力關系。
總之,紅頭瑤婦女憑借與生俱來的文化,形成了表征自我、彰顯社會關系及權力話語的行為機制。維系紅頭瑤社會的地方性知識,在展示其在國家、地域或部落中屬性的同時,也促動了權力話語的生成,進入新的時空中,因群體認同與國際環境的持續變遷,面臨著越來越難將紅頭瑤化約為代表地方性知識的單一公式。民俗市場化或國際化正在改寫著紅頭瑤婦女表征地方性知識的角色。
二、作為民俗旅游景點的紅頭瑤婦女:地方性知識與市場要素結合的載體
社會生產結構決定著文化模式。有什么樣的社會生產結構就有什么樣的文化模式。市場經濟的作用,使維系傳統社會的地方性知識獲得新的定義,創造出新的行為模式,并轉換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在傳統意義上,達芬村紅頭瑤婦女的生產生活集中于農耕方面。當越南政府在此啟動民俗旅游后,紅頭瑤婦女的社會角色由之轉變。這種轉變體現在生產方式上,也體現在行為內涵中。形式和內容造就了統一的現實。這是市場化下的身份再造,也是國際化中的角色開拓,更是有形與無形要素的動態交織。
民俗旅游的啟動使紅頭瑤婦女被置換成社會主體。在達芬村銷售手工藝品的幾乎都是紅頭瑤婦女。借助特殊的文化環境與市場條件,紅頭瑤婦女的性別主體地位由之從傳統的農業生產中置換出來,最終不僅獲得了特定身份,而且創造了新的關系結構。紅頭瑤婦女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既是手工藝品的推銷者、文化的溝通者,又是語言(她們能講英語)的傳承者;既是該村民俗旅游的主角,又是女性性別主體的代表,更是新時空中跨國關系建構的民間行為體,并在工作場所、交際對象等方面獲得表述。
1.工作場所 民俗旅游啟動后,村里的紅頭瑤婦女幾乎都參與進來。村頭的寨子是她們的主要賣場。每天天一亮,本寨的紅頭瑤或其他寨的紅頭瑤婦女就會背上填滿刺繡品的背簍來到村頭等候游客。環村的水泥硬化路面圈定了她們的行動范圍。當游客進入村子,紅頭瑤婦女便尾隨游客,向游客不斷推介產品。游客走動圈子的大小決定了她們活動場所的寬窄。與傳統的田間地頭的勞作比較,其工作環境得到新的界定。她們所遭遇的是一個流動性集市,推銷手工藝品是她們的本務,贏利是她們的目標。
2.交際對象 在工作環境變遷的同時,紅頭瑤婦女的交際對象也產生變化。隨著民俗旅游的啟動,紅頭瑤面對的不再是族際親朋,而是來自異域他鄉的游客;所尋求的不再停留于對情感或認同的滿足上,而是對產品銷售、錢幣增多的終極期待上。顯然,利潤動機是其與游客互動的驅力。由此,特定的交際模式決定了紅頭瑤婦女社會行動的價值歸屬。
3.語言構成 達芬村民俗旅游不僅贏得了越南國內各族人民的贊賞,且同樣受到了外國游客的青睞。為向遠道而來的游客推銷產品,英語成了紅頭瑤婦女的工作語言。據了解,在此的紅頭瑤婦女幾乎都會說英語。一些中年婦女十多年前就開始跟導游、游客學說英語,并用所學英語影響下一代。也有一些十多歲的女孩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她們從小就跟母親學。但是,紅頭瑤婦女很少能寫,即便是最為簡單的字母或單詞。盡管這樣,并不妨礙她們推銷手工藝品。然而,紅頭瑤男性卻幾乎都不會說英語。這是因為他們沒涉足民俗旅游之故,從而導致語言陌生而形成角色分化。另外,被動地以英語為媒介,長遠地,無形之中會造成紅頭瑤民族知識發展的障礙。這是否會最終導致紅頭瑤婦女無法以自己的語言思考問題,將是撲朔迷離的。這種對心理與精神潛在停滯的預示,暗蘊了言說媒介的現代性弊垢,但卻展示了生活在打造語言的同時,語言亦在打造生活的互逆性機理。盡管語言是溝通經驗的工具,也是定義經驗的概念,但卻對紅頭瑤的最初語言(中國話或越語)所建構的自我與個性構成了挑戰。
4.飾物產品 紅頭瑤婦女到村頭賣手工藝品時,在穿戴上比家居時講究。這主要體現在穿繡花密濃、色彩艷麗的衣褲。此種服飾制作時間較長,通常需一年。據說,居家時她們穿的是一些簡潔方便的衣服。當她們到村頭推銷產品時,便新裝上陣,修飾數番。即便在手鐲秩序上,她們也會照顧到體面得當,錯落有致,色澤有別。此番穿戴,極大增強了游客對紅頭瑤民族文化的興致,在鮮朗特質盡情展示的同時,作了無聲的民族文化宣傳,為將填滿背簍的手工藝品銷售殆盡開啟了綠色通道。也就是說,紅頭瑤的有形飾物打開了無形利潤的潛在閥門。
5.行為特點 在民俗旅游中,紅頭瑤的行為特點產生了新意。她們追求的不再是對認同、情感的滿足,而是轉到了利益動機上。能否讓更多的游客買走產品,獲取較多的經濟利潤則是期許焦點。在村頭等候游客并非為表演或展示文化,相反則是為了利潤價值。與傳統的農耕方式相較而言,其行為變得深富經濟性。通過與外國游客互動,她們卷入到小型的商貿交易中,使本土手工藝品的市場化成為不可逆之勢。
6.認同建構 自啟動民俗旅游始,紅頭瑤婦女就聚集村頭,一邊刺繡一邊靜候游客。一進村子,就可看到三三兩兩的紅頭瑤婦女或坐在廊檐下,或奔向游客,用緩和的英語向游客推薦手工藝品。頗具特色的服飾,成為村里流動的文化符號,將達芬村民俗旅游特點映襯了出來。“給我買”(You buy for me)的英語問詢,使她們的國際化經濟行為瞬時活現,民族傳統經濟化由之被激發,更為重要的是民族認同在與游客的比照中由之被強化。此種認同建構,在向游客渲染強烈民族韻味的同時,也在游客心底無聲地鏤刻下了民族認同的印記。
總之,達芬村民俗旅游的啟動,說明經濟利益既需要有計劃的組織生產者,同時也需要激活生產者的內在構成。紅頭瑤民俗旅游的開展,一方面是通過對其他群體(比如同村黑苗)建立邊界,另一方面則是通過依附其他經濟群體(主要指外來游客)來實現的。在有形與無形要素的作用下,作為民俗旅游景點的紅頭瑤婦女,在極大意義上成了地方性知識市場化定義與國際化開拓的產物。其行為較之傳統意義而言,彰顯出了極強的經濟性特質。
三、作為文化身份與交際角色的紅頭瑤婦女:社會關系與權力話語生產
民俗旅游在紅頭瑤生活中創造了一個超越日常互動的特殊空間,以至對傳統的維持及創新能發生其中,并最終使傳統文化在經歷社會化組織的生產和傳播后,而與不同的層級主體聯系起來。作為民俗旅游村的達芬村,為紅頭瑤個體間的聯系創造了紐帶,更為紅頭瑤婦女創造了超越自我范圍的參與體驗。
(一)社會關系建構
民俗旅游村的啟動,使紅頭瑤婦女的交際圈子不再限于傳統的交際范圍和半徑內,其關系網絡得以延展。她們不僅推銷了產品,傳遞了本土文化,還在市場化條件下憑借性別主體角色與身份而新建了社會關系。其營生方式的轉變,以及外國游客的興趣性光顧,建構出了一個簡化的臨時社會。這樣一個由一定數目人員構成的“社會”,“不是因為在每一個人身上都存在著一種由物質所決定的或者推動的他個人的生活內容,而是只有當這些內容的活力贏得相互影響的形式時,當一個個人對另一個個人----直接或者通過第三者的媒介----產生影響時,才從人的單純空間的并存或者也包括時間的先后,變成一個社會。”[1](P21)其間,必然蘊含著一套關系機制。這既是紅頭瑤婦女與游客交涉的結果,也是紅頭瑤婦女與同村互動的常態。而語言、手工藝品等則是轉換現實的決定性變量。
在傳統的家庭生活中,紅頭瑤婦女以越語為交流工具。而當她們到村頭推銷產品時,英語變成主要的交流語,成為建構交易圈的橋梁,締造買主與賣主、廓清市場與非市場閾限、凝析物品與商品區分的工具。“這里”和“現在”成為主導的認同空間。
紅頭瑤婦女與游客依靠相互支持行為而進入與對方產生聯系的狀態中。雙方在向對方施予影響的同時,由此也順應了對方的影響。在互動中,紅頭瑤婦女與外國游客,既明晰了身份,也整合了行動。雙方之間無需太多的默契與情感,而更多地需要以利益最大化為旨趣。作為整體的紅頭瑤婦女,以近似或一致的價值取向,抱著從游客身上獲得經濟利益的目的,而塑造了統一的臨時共同體。平時生活中,紅頭瑤婦女會是姐妹姑嫂、親朋好友;而當面對外國游客時,她們成了平起平坐的競爭者。競爭與利益將她們并置,同時又將她們區隔開來(畢竟每個人最終所獲的利潤大小是有別的)。同時,這一情勢還將沒有來推銷手工藝品的紅頭瑤婦女置入另類的范疇。推銷產品的紅頭瑤婦女講英語,與來客交談,超出習慣而擴展交際圈子。她們不僅比僅靠山茅野菜賺取少量錢財的婦女更具經濟優勢,而且還將一些偶然的事件整合為符合某種理念或邏輯的活動,并最終將游客以情緒和興趣釋放的行為賦予深意,使得存于其間的社會關系,涵括了豐富的創造性和解釋力。
傳統上,紅頭瑤的社會關系網絡只限于本村族人中。民俗旅游的啟動,其交際對象變成了國內外游客。這樣的臨時關系,在本質上是異趣于紅頭瑤鄉土血親網絡的。對于紅頭瑤婦女來說,需爭取的是更多的顧客和更多的利潤。對于游客,則是以享受民族文化和民俗風情為重。游客作為一群參與趣味文化的趣味公眾,其以保持獨有的行動方式,非組織化地聚集一起,并以“類別化”的社會定義,打破了文化主體的固定邊界。由此,社會并非是一切歷史事件的累積,社會關系的建構也不是僅賴于物理世界的翻版,指意符號相反耐人尋味。
紅頭瑤婦女的經驗生活是社會關系發生的前提。民俗旅游村的啟動,給紅頭瑤帶來了獲利的希望。但其本土知識由此受到沖擊,外部權威產生被內化的可能,公共領域的邊界隨之延伸。盡管如此,紅頭瑤婦女還是以媒介的功能,促動消費主義意識形態與被動文化行為產生聯系。紅頭瑤婦女,因此由表征民族文化的角色,轉換成建構社會關系的介質,塑造出了“我們”與“他們”、“我們”與“你們”的知識維度。藉此,市場化原則轉換成塑造非個人化的資源,并影響了紅頭瑤婦女的價值觀、情感及對世界的理解。
由民俗文化市場化的拓展,引出了一個理論意義上的疑點。民俗旅游的開啟,使民俗文化被貼上價格標簽,地方性知識的含義縮減得十分有限。不得不叩問的是:當民俗文化被作為一個可牟利的資源開發時,其內涵能否保持原生味道?雖然紅頭瑤婦女和游客通過面對面的互動和非正式的社會控制,表象上融為一體;但是,紅頭瑤民俗文化,對紅頭瑤自身和游客來說,在接觸文化的共同象征物時卻存在很大差異。
總之,鑒于任何社會或民族在當今世界都在不斷地尋找與外界建立聯系的契機,紅頭瑤婦女同樣難以免之。紅頭瑤婦女永遠不是一個有明確邊界的系統,而是在迎接世界洪流中模糊著邊界,在與他人的互動中顛覆著身份本質。
(二)權力話語生產
1.文化與權力的關系 達芬村民俗旅游是借助獨特的民俗文化啟動的。在民俗旅游中,紅頭瑤婦女對文化產品的擁有及市場范圍的控制,涉及到文化與權力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可從以下三方面理解:(1)民俗旅游村的運轉,可從紅頭瑤婦女爭取和釋放文化權力得到解釋。紅頭瑤婦女在民俗旅游中的貢獻,彰顯了文化是一套人工制品的生產機制。此舉在展示紅頭瑤婦女生活世界、改變紅頭瑤婦女經驗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亦推動了文化橫向與歷史縱向的有機結合,及文化在價值上的分化和整合。(2)可從紅頭瑤女性在本土與國際之間的溝通功能上來理解。作為傳統文化與國際社會的溝通使者,紅頭瑤婦女既是符號象征及文化傳人,也是國際關系中非國家行為角色的代表。紅頭瑤婦女的作用,使紅頭瑤女性的性別主體角色得以凸顯。(3)推銷產品是一種營銷活動,也是一種權力角逐。在家中,紅頭瑤婦女以超越丈夫的才能展示了對市場的駕馭能力。在市場上,每一個紅頭瑤婦女都期待能比別人爭到更多顧客,獲得更多利潤,達到在彰顯自我價值和意義的同時,推動意義的生產和傳播。
2.空間與權力的關系 達芬村從村頭到村尾縱貫著一條水泥路面。在路面兩側鑲嵌著寨子和水田。這是紅頭瑤婦女維護生存權力的空間。民俗旅游村基于此空間展開布局。市場化制造了旅游空間,規劃化的發展安排了權力構成。女性主體權力由此被展演,靜態形式與動態過程充斥其間。
3.權力構成單元 達芬村民俗旅游中的權力關系主要由紅頭瑤族與村政府、村莊與家庭、本土與國際,甚至旅游管理法規與紅頭瑤行為秩序之間的互動而推演著,并以國際化節奏確定著進度,從而使國際社會、越南地方和紅頭瑤寨子之間成為了一個臨時的關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甚至命運共同體。
由上,民俗旅游使紅頭瑤社會的性別話語發生轉變:由地方性知識主導的生活模式轉變成了由市場導向的話語模式。全球化的市場節律,一方面導致了地方性知識與國際社會的結合,另一方面
也促進了紅頭瑤婦女話語權的轉變。紅頭瑤婦女在民俗旅游中的文化身份凸顯,展示了女性性別主體意識在當代國際化進程中的凸起。總之,傳統文化對女性性別主體的塑造是根植于農耕文明的,同時輔于地方性知識動力的經久推助。也因為如此,才塑造了既定的權力關系。而當更多的紅頭瑤婦女走向村頭彰顯性別主體時,雖然并沒法規避行為從眾的可能,但是既定的權力關系已被悄然植入了危險的境地。
總之,達芬村紅頭瑤民俗旅游的啟動,對社會變遷、文化發展及個性解放都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價值和意義。通過達芬村民俗旅游,可以發現,在現代化進程中紅頭瑤婦女愈來愈社會化,越來越擺脫了傳統的束縛,不斷創造著個性,為自我爭取了更多的發展空間,努力推動著性別主體角色的再造及社會關系與權力話語的新建,既展示了自我,亦創造了世界。
參考文獻:
[1] [德]齊美爾.社會史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M].林榮遠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