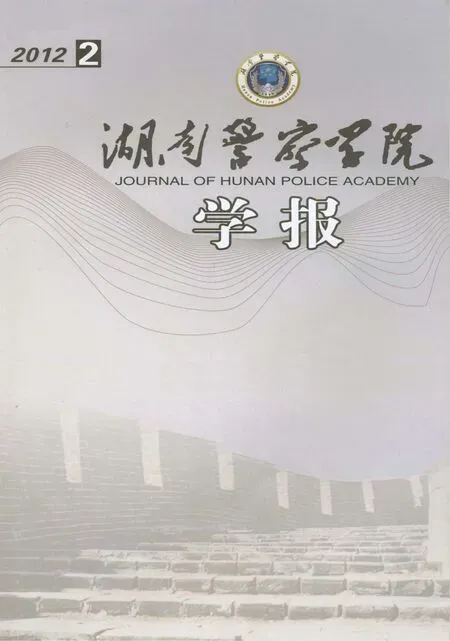“扒竊入刑”中若干爭(zhēng)議的消解
李竟芬
(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北京 100088)
“扒竊入刑”中若干爭(zhēng)議的消解
李竟芬
(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北京 100088)
扒竊入刑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其扒竊行為的特殊危害性,“扒竊入刑”客觀上無(wú)數(shù)額、次數(shù)、手段的限制,突破了盜竊罪以數(shù)額定罪的觀念,但主觀上應(yīng)是基于竊取較大公私財(cái)物的故意,應(yīng)從這兩個(gè)方面把握扒竊的入罪標(biāo)準(zhǔn)。扒竊的既遂標(biāo)準(zhǔn)與一般的盜竊差異不大,但扒竊入刑使得扒竊未遂也受處罰。總之,《刑法修正案(八)》關(guān)于扒竊的規(guī)定,確實(sh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司法實(shí)踐中打擊扒竊的困境。
扒竊;扒竊入刑;公共場(chǎng)所;隨身攜帶
前 言
《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全國(guó)各地都相繼有抓獲因扒竊而涉嫌盜竊罪的行為人,有部分地方法院也最終對(duì)扒竊行為人做了定罪處理。但是在司法實(shí)踐中,各地處理輕微扒竊案的做法不一致,扒竊入罪的標(biāo)準(zhǔn)不統(tǒng)一,筆者認(rèn)為,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公檢法機(jī)關(guān)對(duì)《刑法修正案(八)》關(guān)于盜竊罪的新規(guī)定認(rèn)識(shí)不統(tǒng)一。一些地區(qū)的公安檢察機(jī)關(guān)認(rèn)為一旦扒竊案件一律都入刑,那么案件將會(huì)成大量激增,使得原本就很緊張的司法資源越發(fā)緊張,所以對(duì)于扒竊案件持謹(jǐn)慎的態(tài)度,輕微的扒竊案不會(huì)進(jìn)入司法程序,而是給予行政處罰。有些地方則認(rèn)為所有的扒竊案件都應(yīng)入刑,雖然這種案件發(fā)案量較大,但通常案情簡(jiǎn)單,處理起來(lái)難度不大,司法部門可以對(duì)這類案件啟動(dòng)輕微刑事案件快速審理機(jī)制,短期內(nèi)都可以辦結(jié),即使盜竊有些許增多也不會(huì)造成公檢法系統(tǒng)的運(yùn)作負(fù)擔(dān)。其實(shí),《刑法修正案(八)》對(duì)于扒竊犯罪的規(guī)定是非常明確的,對(duì)于扒竊犯罪的定罪量刑給予了清晰的標(biāo)準(zhǔn),全國(guó)在處理扒竊案件時(shí)應(yīng)參照?qǐng)?zhí)行。對(duì)于實(shí)踐中的不同認(rèn)識(shí)可以通過(guò)對(duì)《刑法修正案(八)》的準(zhǔn)確解讀和相關(guān)的法理解釋來(lái)進(jìn)行提高,以下筆者試將對(duì)執(zhí)法中出現(xiàn)的對(duì)于扒竊犯罪定罪量刑的幾個(gè)困惑進(jìn)行厘清。
一、“扒竊入刑”的必要性分析
“扒竊”,是在人大常委會(huì)第二次審議《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時(shí)增加的進(jìn)盜竊罪的條款的,刑修八草案一次審議稿僅僅涉及盜竊罪死刑的廢除,并增加了“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的行為方式,并沒(méi)有將“扒竊”行為增加規(guī)定為犯罪。有的委員、部門和地方提出,“扒竊”行為嚴(yán)重侵犯公民人身和財(cái)產(chǎn)安全,社會(huì)危害性較為嚴(yán)重,且這類犯罪技術(shù)性強(qiáng),多為慣犯,應(yīng)當(dāng)在刑罰中作出明確規(guī)定。法律委員會(huì)經(jīng)同有關(guān)方面研究,采納了這一意見(jiàn)。于是,“扒竊”就出現(xiàn)在了人大常委會(huì)第二次審議《刑法修正案(八)》的草案稿中,并由《刑法修正案(八)》最終確認(rèn)了這一規(guī)定。[1]據(jù)有關(guān)媒體報(bào)道,“扒竊入刑”,確實(shí)有考慮到扒竊行為對(duì)公眾安全感的損害及其嚴(yán)重的社會(huì)危害性。[2]也就是說(shuō)“扒竊入刑”主要原因是立法者認(rèn)為扒竊行為的社會(huì)危害性比一般的盜竊罪大,達(dá)到了將它規(guī)定為一種特殊的盜竊行為的相當(dāng)程度。筆者認(rèn)為,扒竊行為的社會(huì)危害性是不是就一定比一般的盜竊行為大,這點(diǎn)有待研究。
但現(xiàn)實(shí)中,扒竊確實(shí)具有以下幾點(diǎn)特征:(1)扒竊的社會(huì)危害性確實(shí)很大,它直接極大地?fù)p害社會(huì)公信度,對(duì)社會(huì)風(fēng)氣影響極壞。在現(xiàn)代社會(huì),大部分要人經(jīng)常地出入公共場(chǎng)所,如果扒竊行為得不到有效遏制,每個(gè)人都是潛在被害人,且扒竊是可以在眾目睽睽之下進(jìn)行的,這樣不僅被害人損失了財(cái)物,很多社會(huì)公眾都可能受到恐嚇,一旦不幸遭遇扒竊將蒙受長(zhǎng)期陰影。(2)對(duì)于扒竊案?jìng)善频碾y度很大,扒竊的取證很難。扒竊都發(fā)生在人來(lái)人往的公共場(chǎng)所,很難留下證據(jù),且一般是團(tuán)伙作案,而且扒竊的對(duì)象一般體積微小,犯罪所得容易快速轉(zhuǎn)移。(3)目前對(duì)扒竊案的處理明顯打擊力度不大。由于一般只能在扒竊行為得手后方可對(duì)行為人進(jìn)行抓捕,在行為人被抓捕后被害人還通常不敢作證,扒竊案件舉證難度較大,很多扒竊只好抓了就放,得不到有效及時(shí)處理。就算能證明也只用社會(huì)治安的辦法來(lái)處理,給予輕微行政處罰對(duì)于頻發(fā)的扒竊案來(lái)說(shuō)打擊力度太小。[3]況且扒竊行為人多為慣犯,且改造難度大,如果不一律入刑,等同于放縱犯罪,破壞刑法的刑法的威懾力。當(dāng)然,扒竊的上述特點(diǎn)并不是說(shuō)要成立扒竊犯罪必須要具備以上所有的特征,這些特征只是大多數(shù)的扒竊案的外在特征,這些特征幫助我們更好地衡量“扒竊入刑”的立法成本和立法價(jià)值,但成立扒竊犯罪并不要求具備以上所有的特征,《刑法修正案(八)》并沒(méi)有對(duì)扒竊做過(guò)多的限制,在給扒竊犯罪定罪量刑時(shí)主要考慮是否符合扒竊的內(nèi)涵,而不是從起特征上做入罪的考量。
因此從構(gòu)成要件上來(lái)探究扒竊入刑的必要性主要是因?yàn)榘歉`行為的特殊性。盜竊罪是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cái)物的行為。盜竊罪成立的構(gòu)成要件有三個(gè),①非法占有公私財(cái)物的故意;②采用了秘密竊取的方法;③盜竊數(shù)額較大、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數(shù)額較大,是盜竊行為構(gòu)成犯罪的基本要件。如果盜竊的財(cái)物數(shù)額較小,一般應(yīng)當(dāng)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guī)定予以處罰,不需要?jiǎng)佑眯塘P。但對(duì)于一些特定的盜竊行為,只要實(shí)施了該盜竊行為,即使達(dá)不到數(shù)額較大的條件,因該行為本身的特殊社會(huì)危害性,也構(gòu)成犯罪。所以認(rèn)定扒竊構(gòu)成盜竊罪的關(guān)鍵是正確理解扒竊的內(nèi)涵。
二、“扒竊”的內(nèi)涵
“扒竊”一詞,產(chǎn)生于反扒實(shí)務(wù)中,雖然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實(shí)施前它只是在偵查抓獲犯罪以及治安管理法規(guī)中的概念,并非嚴(yán)格的刑法學(xué)用語(yǔ),但是如今進(jìn)入了刑法學(xué)領(lǐng)域,就應(yīng)當(dāng)對(duì)其含義進(jìn)行準(zhǔn)確界定,且《刑法修正案(八)》中規(guī)定的“扒竊”是一個(gè)空白的罪狀,為了保證準(zhǔn)確定罪和一致量刑,也必須讓這個(gè)概念內(nèi)涵清晰。
(一)歷史解釋
“扒竊”一詞,產(chǎn)生于反扒實(shí)務(wù),以前僅限于偵查學(xué)和犯罪學(xué)中使用,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刑事司法學(xué)院教授徐久生在接受《法制日?qǐng)?bào)》記者采訪時(shí),對(duì)扒竊的定義是:“扒竊”一詞不是法律用語(yǔ),而是公安機(jī)關(guān)特別是一線民警在工作總結(jié)時(shí)常用的詞匯,是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車站、碼頭等公共場(chǎng)所,行為人采用秘密竊取的方式,從他人身上獲取財(cái)物的行為。”[4]地方治安管理法規(guī)對(duì)“扒竊”也有過(guò)定義,如1990年《長(zhǎng)沙市懲治扒竊的規(guī)定》第二條將“扒竊”定義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車站、碼頭、商場(chǎng)、集貿(mào)市場(chǎng)、影劇院等公共場(chǎng)所秘密竊取他人隨身攜帶財(cái)物的行為。”這個(gè)定義有一定借鑒性但其合理性不充分。
經(jīng)過(guò)這次刑法修正后它將轉(zhuǎn)化為刑法學(xué)上的一個(gè)術(shù)語(yǔ)。需不需要司法解釋來(lái)進(jìn)一步明確具體含義?
(二)文義解釋
我國(guó)現(xiàn)代漢語(yǔ)將“扒竊”解釋為:從他人身上偷竊財(cái)物,[5]寫出了扒竊的明顯特征,但是沒(méi)有對(duì)其適用范圍和條件進(jìn)行必要界定。2011年國(guó)家司法考試教程中定義“扒竊”也有三個(gè)條件:①扒竊指的是近身盜竊;②竊取應(yīng)是對(duì)方緊密控制的財(cái)物;③行為發(fā)生在公共場(chǎng)所。
(三)學(xué)理解釋
權(quán)威學(xué)者張明楷將“扒竊”定義為:在公共場(chǎng)所竊取他人隨身攜帶的財(cái)物的行為。且認(rèn)為扒竊成立盜竊罪,客觀上必須具備三個(gè)條件:①行為發(fā)生在公共場(chǎng)所;②所竊取的應(yīng)是他人隨身攜帶的財(cái)物;③所竊取的財(cái)物應(yīng)是值得刑法保護(hù)的財(cái)物。[6]
筆者認(rèn)為,無(wú)論怎樣去給“扒竊”下定義,關(guān)鍵是要解決兩個(gè)問(wèn)題,就是怎樣去界定公共場(chǎng)所和隨身攜帶,這兩個(gè)問(wèn)題的不同答案是可以影響到定罪量刑的。我們舉個(gè)例子來(lái)說(shuō):
例一:行為人在紅綠燈處,趁被害人不備,從其放在電動(dòng)車腳踏板上的背包內(nèi)竊取其錢包一個(gè)(價(jià)值人民幣5元),內(nèi)有人民幣108元及身份證等物品,后被當(dāng)場(chǎng)抓獲。紅綠燈處算不算公共場(chǎng)合?被害人電動(dòng)車腳踏板上的背包算不算隨身攜帶,被害人對(duì)被竊取的錢包是不是緊密控制?
第一,關(guān)于公共場(chǎng)所范圍的界定。刑法中沒(méi)有對(duì)“公共場(chǎng)所”的明確解釋,行政性質(zhì)的《公共場(chǎng)所管理?xiàng)l例》也沒(méi)有對(duì)“公共場(chǎng)所”進(jìn)行定義。我國(guó)《刑法》第291條規(guī)定的聚眾擾亂公共場(chǎng)所秩序、交通秩序罪中出現(xiàn)的“公共場(chǎng)所”,學(xué)界多定義為“對(duì)公眾開(kāi)放,供其從事各種滿足其物質(zhì)文化生活需要的,帶有公益或商業(yè)性質(zhì)的場(chǎng)所。”[7]有觀點(diǎn)認(rèn)為所謂“扒竊”,一般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在車站、碼頭、商場(chǎng)等公共場(chǎng)所竊取他人隨身攜帶財(cái)物的行為。確實(shí),說(shuō)到“扒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公共汽車、車站和商場(chǎng)等地方。因?yàn)椤鞍歉`”一詞本來(lái)就產(chǎn)生于第一線廣大干警的反扒工作中。但是采取列舉式的定義方法將限制“公共場(chǎng)所”的范圍,一旦沒(méi)有被列舉,比如紅綠燈下、停車場(chǎng)、學(xué)校食堂等人流量不是特別大的地方算不算公共場(chǎng)所呢?
筆者認(rèn)為,對(duì)“公共場(chǎng)所”的定義,不應(yīng)采用列舉的方法,采用列舉的方法不僅影響刑法的簡(jiǎn)短的價(jià)值,我們也無(wú)法窮盡列舉,況且越詳細(xì)越具體的規(guī)定可能漏洞越多,因?yàn)榭陀^事物的復(fù)雜性往往難以被人們認(rèn)識(shí),而合理的使用模糊性的概念時(shí)任何法律都不可避免的,[8]所以在定義的方法上不要執(zhí)著于列舉。
在闡述“公共場(chǎng)所”的性質(zhì)上,也有不同觀點(diǎn):張明楷教授認(rèn)為公共場(chǎng)所是不特定人可以進(jìn)入、停留的場(chǎng)所以及有多數(shù)人在內(nèi)的場(chǎng)所,而且只要行為發(fā)生在公共場(chǎng)所,即使公共場(chǎng)所的人不是很多,也不影響扒竊的成立。例如,在公共汽車上只有少數(shù)幾人時(shí),行為人實(shí)施扒竊行為的,也應(yīng)認(rèn)定為盜竊罪。[9]反對(duì)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對(duì)公共場(chǎng)所的含義應(yīng)結(jié)合刑法條文做個(gè)別的解釋,認(rèn)為扒竊行為侵犯的是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在凌晨空無(wú)一人或僅有數(shù)人的車站竊取他人隨身攜帶的物品就不應(yīng)認(rèn)定為扒竊。[10]
筆者認(rèn)為公共場(chǎng)所不應(yīng)在場(chǎng)所的人流量和場(chǎng)所的性質(zhì)上進(jìn)行嚴(yán)格限制。公共場(chǎng)所的認(rèn)定不能單單從人流量的大小來(lái)考慮的,不特定人可以進(jìn)入、停留的場(chǎng)所以及有多數(shù)人在內(nèi)的場(chǎng)所都應(yīng)算公共場(chǎng)所,只要有可能出現(xiàn)人流量較多的地方都可以算公共場(chǎng)所。也不是單從場(chǎng)所的性質(zhì)來(lái)考慮的,娛樂(lè)、商業(yè)和其他服務(wù)性質(zhì)的公共場(chǎng)所都可以認(rèn)為是刑法里的公共場(chǎng)所。綜上,筆者將公共場(chǎng)所定義為:不特定人多數(shù)人可能進(jìn)入、停留的場(chǎng)所。那么以上的例子中,行為人在紅綠燈處行竊也算在公共場(chǎng)合行竊。
第二,關(guān)于隨身攜帶的理解。多數(shù)論者認(rèn)為對(duì)隨身攜帶應(yīng)做擴(kuò)張解釋,包括他人帶在身上或者置于身邊附近的財(cái)物。例如,在公共汽車上竊取他人口袋內(nèi)、提包內(nèi)的財(cái)物,在火車、地鐵上竊取他人置于貨架上、床底下地財(cái)物的,都屬于扒竊。也有論者認(rèn)為,既然是“扒”,對(duì)象就應(yīng)當(dāng)是與他人緊密聯(lián)系并受他人實(shí)際控制的物品,如貼身衣服口袋里裝的錢包、隨身攜帶的手提袋等。在火車、長(zhǎng)途汽車、飛機(jī)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與被害人分離的行李箱里的物品就不屬于扒竊了。
筆者認(rèn)為,隨身攜帶包括置于身邊的財(cái)物。要求一般公眾在公共場(chǎng)所都將自己的財(cái)物握在手中或綁在身上是不切實(shí)際的,在很多公共場(chǎng)所大部分人都會(huì)將體積稍微大點(diǎn)的財(cái)物放在目光可及或容易照看的地方,竊取這種財(cái)物也將造成民眾的社會(huì)安全感的缺失,且難以取證,所以將這種行為也認(rèn)定為“扒竊”是符合《刑法修正案(八)》的精神的。所以筆者筆者認(rèn)為,扒竊的對(duì)象是被害人隨身攜帶和近身放置的財(cái)物。扒竊是指在公共場(chǎng)所竊取他人占有的近身物品的行為。那么以上的例子中,被害人電動(dòng)車腳踏板上的背包也算隨身攜帶。
三、“扒竊入刑”客觀上無(wú)數(shù)額、次數(shù)和手段限制
在明確了扒竊的內(nèi)涵后,還是會(huì)有人對(duì)扒竊是否一律入刑存在疑問(wèn)。先分析一下以下案例:
例二:行為人在馬路上看到一名女子單獨(dú)行走,看見(jiàn)該女子兜里露出來(lái)一個(gè)MP4,就跟著這女孩身后走,趁該女子不注意的時(shí)候,把該女子兜內(nèi)的MP4偷走了,行為人被警察抓抓住,警察從嫌疑人上衣口袋里起獲了MP4,經(jīng)物價(jià)部門認(rèn)定該MP4價(jià)值50元人民幣。行為人竊得的財(cái)物數(shù)額太低,手段太平和,社會(huì)危害性也不大,還應(yīng)不應(yīng)該承擔(dān)盜竊罪的刑事責(zé)任?
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扒竊行為被認(rèn)定為盜竊罪要么是扒竊所得達(dá)到盜竊罪法定的犯罪數(shù)額要么是扒竊三次以上。也就是說(shuō)在扒竊行為沒(méi)有獨(dú)立成盜竊罪的一種行為前入罪是有數(shù)額和次數(shù)的要求的。數(shù)額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guān)于盜竊竊罪數(shù)額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問(wèn)題的規(guī)定》[法釋(1998)3號(hào)]對(duì)“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特別巨大”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數(shù)額較大”,以五百元至二千元為起點(diǎn)、“數(shù)額巨大”,以五千元至二萬(wàn)元為起點(diǎn)、“數(shù)額特別巨大”,以三萬(wàn)元至十萬(wàn)元為起點(diǎn)。而多次的要求體現(xiàn)于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huì)第942次會(huì)議通過(guò)《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該司法解釋第四條的規(guī)定:對(duì)于一年內(nèi)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chǎng)所“扒竊”三次以上的,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多次盜竊”,以盜竊罪定罪處罰。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對(duì)于“扒竊”的規(guī)定,使得這兩個(gè)司法解釋關(guān)于盜竊罪數(shù)額和次數(shù)的標(biāo)準(zhǔn)不再適用于扒竊犯罪。
根據(jù)《刑法修正案(八)》三十九項(xiàng),將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修改為:“盜竊公私財(cái)物,數(shù)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yán)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yán)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wú)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méi)收財(cái)產(chǎn)。”仔細(xì)分析這個(gè)條款,可以發(fā)現(xiàn),“扒竊”通過(guò)“或者”與“盜竊公私財(cái)物,數(shù)額較大的”并列,可見(jiàn)“扒竊入刑”是沒(méi)有數(shù)額要求的,“扒竊”通過(guò)頓號(hào)與多次盜竊并列,那么“扒竊入刑”是沒(méi)有次數(shù)要求的,同時(shí)也于“攜帶兇器盜竊”,說(shuō)明“扒竊入刑”也沒(méi)有作案手段的特殊要求,只要符合扒竊的內(nèi)涵就可以了。筆者認(rèn)為這樣的規(guī)定是非常合理的,可以避免現(xiàn)實(shí)操作中的不少問(wèn)題。比如“扒竊入刑”如果還用次數(shù)來(lái)限制,就會(huì)產(chǎn)生另一個(gè)問(wèn)題,對(duì)于次數(shù)的認(rèn)定是采用主觀認(rèn)定還是客觀認(rèn)定不好選擇。只主觀上去認(rèn)定,如果行為人不記得自己是第幾次扒竊就不好定罪了,這樣可能記性好的行為人就被認(rèn)定為犯罪而追究刑事責(zé)任而記性不好的就不能成立犯罪。如果采用客觀標(biāo)準(zhǔn)去認(rèn)定,扒竊行為本身不好被證明,在現(xiàn)有證據(jù)只能證明行為人有一次的扒竊時(shí)候,即使行為人交代自己有幾次扒竊的行為,也不能光依靠口供定罪。所以說(shuō)“扒竊入刑”采用各種限制是非常不利于打擊扒竊的,這也是實(shí)踐中為何對(duì)于扒竊行為人抓了就放,得不到合理處理的原因。用次數(shù)去限制犯罪的范圍是不合理的,同樣地,如果在數(shù)額、手段上進(jìn)行限制,在司法實(shí)踐中也是不好操作的。《刑法修正案(八)》對(duì)“扒竊入刑”的規(guī)定沒(méi)有數(shù)額、次數(shù)、手段的限制,確實(shí)合情合理、易于操作。回到案例中,既然沒(méi)有數(shù)額限制,行為人所扒竊的財(cái)物雖然價(jià)值只有50元,如果不考慮其他方面的情節(jié),那也是成立盜竊罪的。當(dāng)然,如果行為人是初犯、偶犯、少年犯或者有其他的顯著輕微的情節(jié)可以用刑法第一十三條的規(guī)定來(lái)出罪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主要是從行為的客觀方面進(jìn)行分析的,可以說(shuō)“扒竊入刑”客觀上對(duì)于扒竊所得沒(méi)有數(shù)額的要求,但盜竊罪是財(cái)產(chǎn)性犯罪,是故意犯罪,不法獲取他人的財(cái)物是盜竊罪的不成文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扒竊入刑”,在主觀上是要求行為人有意欲竊取數(shù)額較大財(cái)物的故意的。
筆者對(duì)“扒竊入刑”的簡(jiǎn)明規(guī)定,持贊成態(tài)度,《刑法修正案(八)》這樣的規(guī)定體現(xiàn)了對(duì)盜竊罪構(gòu)成要件的適當(dāng)揚(yáng)棄,同時(shí)也符合長(zhǎng)久以來(lái)我國(guó)犯罪論所要求的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基本原則,也使得現(xiàn)實(shí)中扒竊行為得到有效遏制,對(duì)于完善我國(guó)刑法典,有效地實(shí)現(xiàn)刑法的目的和任務(wù)不無(wú)裨益。
四、“扒竊”既遂與未遂的爭(zhēng)議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前,扒竊案因?yàn)槠湫袨榕c抓捕的特殊性,取證的難度,大多地被認(rèn)定為未遂而被擱淺,大量扒竊行為人都是抓了只能放,這樣造成了警力資源的浪費(fèi),扒竊案得不到處理,又使得扒竊行為人更加地猖狂。當(dāng)然,《刑法修正案(八)》增加扒竊型的盜竊罪后,扒竊未遂的也要處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司法實(shí)踐中打擊扒竊的困境,提高了打擊扒竊的有效性。
(一)普通盜竊既未遂的標(biāo)準(zhǔn)
普通盜竊罪是結(jié)果犯,其既遂與未遂認(rèn)定的標(biāo)準(zhǔn)有很多學(xué)說(shuō),至今也存在不少爭(zhēng)議。常用的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主要有接觸說(shuō)、轉(zhuǎn)移說(shuō)、控制說(shuō)、移動(dòng)說(shuō)、失控說(shuō)、失控加控制說(shuō)等幾種學(xué)說(shuō),現(xiàn)在理論界的爭(zhēng)議的焦點(diǎn)主要集中在失控說(shuō)和控制說(shuō)上,并且失控說(shuō)在理論界更為流行。[11]筆者認(rèn)為失控說(shuō)更為合理,因?yàn)槭Э卣f(shuō)更多的是從被害人的角度去考慮既遂的標(biāo)準(zhǔn),刑法的目的主要是保護(hù)法益,其次才是懲罰犯罪,失控說(shuō)更符合這個(gè)目的。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guó)法院審理經(jīng)濟(jì)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huì)紀(jì)要》中明確了控制說(shuō)是區(qū)分盜竊罪未遂與既遂的界限標(biāo)準(zhǔn),所以,司法實(shí)踐中更傾向于控制說(shuō),而以失控說(shuō)為補(bǔ)充。
(二)扒竊犯罪的既未遂標(biāo)準(zhǔn)
犯罪未遂是指已經(jīng)著手實(shí)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為。既然扒竊犯罪是沒(méi)有數(shù)額限制,就不管竊取金額的大小甚至沒(méi)有金額都可能成立既遂。但是這里應(yīng)注意,扒竊行為是一個(gè)過(guò)程而不是一個(gè)時(shí)間點(diǎn),并不是說(shuō)行為人一觸及被害人財(cái)物就成立既遂。盜竊罪是財(cái)產(chǎn)犯罪,既未遂的標(biāo)準(zhǔn)應(yīng)該看財(cái)產(chǎn)的占有是否發(fā)生了轉(zhuǎn)移。扒竊的既未遂認(rèn)定時(shí),可以將扒竊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小件扒竊,扒竊的對(duì)象是被害人隨身攜帶的體積較小的物品,以行為人的手或者作案工具接觸到被害人身上的背包或口袋的外側(cè)時(shí)為著手,在取的過(guò)程中出現(xiàn)了其他情況是可以成立中止和未遂的,但一旦行為人取出錢包、現(xiàn)金或其他財(cái)物,不管財(cái)物的價(jià)值大小,也不論行為人是不是馬上逃離了現(xiàn)場(chǎng)都算控制了財(cái)物,成立盜竊既遂。第二類是大件扒竊,扒竊的對(duì)象是被害人近身放置的體積較大的物品,以行為人的手或者作案工具接觸到被害人的放置在身邊的或者在一定固定空間的財(cái)物為著手,一旦行為人有效轉(zhuǎn)移了被扒竊的大件物品就算控制了財(cái)物。比如扒竊火車架上的行李包,如果行為人提著行李包還沒(méi)有出本車廂就被抓獲了就只能認(rèn)定為未遂。普通盜竊罪的既遂認(rèn)定是以控制說(shuō)為標(biāo)準(zhǔn)以失控說(shuō)為補(bǔ)充的,按照這樣的標(biāo)準(zhǔn),確定犯罪人是否已經(jīng)控制所竊取的財(cái)物,也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盜竊財(cái)物本身的大小、空間和環(huán)境條件以及監(jiān)控條件的不同具體情況分析。對(duì)于扒竊大件而沒(méi)有效轉(zhuǎn)移的情況,按普通盜竊處理時(shí)也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行為人沒(méi)有實(shí)際控制財(cái)物,是未遂,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shuō),即使將扒竊犯罪與普通盜竊認(rèn)定既未遂的標(biāo)準(zhǔn)差異也不大。
筆者認(rèn)為,還應(yīng)該注意扒竊犯罪的不能犯未遂。不能犯的未遂是指行為人對(duì)有關(guān)犯罪事實(shí)認(rèn)識(shí)錯(cuò)誤,其犯罪行為根本不可能完成犯罪達(dá)到既遂。未遂是法定的減輕量刑情節(jié),認(rèn)定既遂與未遂對(duì)于行為人的量刑影響極大。扒竊犯罪在不能犯未遂的情況下,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樣也可以起到均衡量刑的作用。《刑法修正案(八)》的目的不在于單純地?cái)U(kuò)大犯罪圈的、增加處罰面。一種行為是不是值得動(dòng)用刑罰去規(guī)制,要綜合地是看行為人的主觀罪過(guò)和客觀犯罪行為這兩個(gè)犯罪構(gòu)成中的最基本的因素,二者的齊備和內(nèi)在統(tǒng)一,決定了行為具有值得刑法處罰的相當(dāng)程度的社會(huì)危害性。扒竊犯罪的不能犯未遂也應(yīng)綜合考量行為人行為的社會(huì)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人身危險(xiǎn)性,統(tǒng)一犯罪構(gòu)成的主客觀要件。當(dāng)然這里的對(duì)象不能犯并不是扒竊金額的大小去認(rèn)定的,而是看行為人有沒(méi)有取得值得刑法保護(hù)的財(cái)物。例如,扒竊他人口袋內(nèi)的餐巾紙、名片、廉價(jià)手帕等物品的,不應(yīng)認(rèn)定為盜竊罪。
五、“扒竊”出罪無(wú)需依賴于“但書”的適用
回到本文例二中的問(wèn)題,行為人的扒竊行為可不可以用刑法第13條來(lái)出罪?以往我們常用民事或行政的手段來(lái)處理扒竊案件,扒竊未達(dá)到較大數(shù)額的或達(dá)到3次以上的,一般給予行政拘留或被報(bào)送勞動(dòng)教養(yǎng)。但是根據(jù)《刑法修正案(八)》規(guī)定,一旦被認(rèn)定為扒竊就都會(huì)被追究刑事責(zé)任,哪怕最后判決只是被判處拘役或罰金,都與之前的行政處罰有天壤之別,因?yàn)榍翱浦贫葘?duì)個(gè)人的發(fā)展影響極大,行為人一旦被追究了刑事責(zé)任,那么他的人生履歷就永遠(yuǎn)地多了一個(gè)不可抹去的污點(diǎn)。“扒竊”出罪和之前的“醉駕”出罪問(wèn)題是一樣的,《刑法修正案(八)》實(shí)行第二周,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zhǎng)張軍在全國(guó)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huì)上表示,對(duì)醉酒駕駛者追究刑責(zé)應(yīng)慎重,應(yīng)與行政處罰注意銜接,稱醉駕如果行為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是一律追究刑事責(zé)任。這樣的考慮確實(shí)是考慮到醉駕一律入刑之后,醉駕案件一下子激增,給公檢法、監(jiān)獄系統(tǒng)都造成極大的壓力,而有些醉駕行為人沒(méi)有造成實(shí)際危害即被抓獲也確實(shí)情節(jié)輕微,如果不區(qū)分情節(jié)一律認(rèn)定為犯罪會(huì)導(dǎo)致法益保護(hù)的過(guò)度前移,刑罰的正當(dāng)性和必要性就值得質(zhì)疑了。雖然各國(guó)的刑法立法基本上都是沿著“風(fēng)險(xiǎn)刑法”理論預(yù)設(shè)的軌跡在前進(jìn),但“風(fēng)險(xiǎn)刑法”理論的劣勢(shì)更應(yīng)該令我們警醒,每一次犯罪圈的擴(kuò)張都應(yīng)當(dāng)經(jīng)受得起更多的正當(dāng)性詰難。[12]成功的一點(diǎn)是,雖然醉駕入刑本身沒(méi)有情節(jié)惡劣的要求,醉駕卻并非不區(qū)分情節(jié)一律入刑,而且出罪的方法也并不僅僅依賴刑法總則13條的規(guī)定,有論者認(rèn)為在認(rèn)定是否醉駕的時(shí)候可以給醉酒的血液酒精含量值解釋在一定的幅度內(nèi),給予警察和檢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間。[13]相對(duì)于“醉駕入刑”,“扒竊入刑”沒(méi)有次數(shù)、數(shù)額、手段的限制,無(wú)法設(shè)定一個(gè)可以自由裁量的幅度值。扒竊犯罪是沒(méi)有罪量要素的,“在刑法分則中沒(méi)有規(guī)定罪量要素的犯罪,并不表示只要行為一經(jīng)實(shí)施就一概構(gòu)成犯罪。因?yàn)樾谭倓t關(guān)于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rèn)為是犯罪的規(guī)定同樣也適用于這些犯罪,因而司法解釋對(duì)這些犯罪規(guī)定了罪量要素。”[14]所以,扒竊犯罪,如果行為人在主客觀兩方面都符合情節(jié)顯著輕微的條件,可能會(huì)適用但書來(lái)出罪。但筆者并不支持運(yùn)用但書來(lái)出罪,因?yàn)樾谭ǚ謩t條文在制定時(shí)就受到了但書的約束,但書的作用更多的是立法上的指導(dǎo),那些顯著輕微的行為在立法時(shí)就被排除了,不會(huì)成為刑法分則具體罪名的犯罪構(gòu)成。如果一個(gè)行為本身已經(jīng)符合刑法分則的犯罪構(gòu)成,再用但書來(lái)出罪,是嚴(yán)重的違反罪刑法定原則邏輯的。但是要注意,扒竊入刑,對(duì)行為客觀上雖然沒(méi)有數(shù)額、具體情節(jié)、手段的要求,但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有扒竊數(shù)額較大財(cái)物的故意。所以,行為人客觀上竊取的財(cái)物極少,主觀上又沒(méi)有竊取較大財(cái)物的故意,是不構(gòu)成盜竊罪的,也就不存在如何出罪的問(wèn)題了。而對(duì)于那些初犯、偶犯、少年犯或存在被脅迫、被控制等情形的可以改造的行為人實(shí)施的扒竊的未遂和竊取的財(cái)物極少的行為,應(yīng)綜合犯罪的事實(shí)、情節(jié)和數(shù)額、悔罪表現(xiàn)、認(rèn)罪態(tài)度等多方面因素判斷,對(duì)于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應(yīng)視具體情況做定罪免刑、緩刑、減刑等合理處理,使刑罰最大限度發(fā)揮其預(yù)防和矯正犯罪的作用。
六、結(jié)論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后,盜竊罪就有了五種類型的盜竊行為:盜竊公私財(cái)物,數(shù)額較大的、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單獨(dú)作為盜竊行為的一種,“扒竊入刑”是沒(méi)有數(shù)額、次數(shù)和手段的限制的,但是在認(rèn)定扒竊的時(shí)候要注意把握“公共場(chǎng)所”和“隨身攜帶”的內(nèi)涵。“扒竊入刑”并沒(méi)有對(duì)盜竊的既遂標(biāo)準(zhǔn)構(gòu)成較大沖擊,反而使得未遂的扒竊行為得到刑法的規(guī)范,這為實(shí)踐中打擊未遂的扒竊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jù)。公檢法機(jī)關(guān)必須準(zhǔn)確把握“扒竊”內(nèi)涵,統(tǒng)一執(zhí)法尺度以消解“扒竊入刑”的各個(gè)爭(zhēng)議,使得“扒竊入刑”確實(shí)有利于打擊扒竊犯罪,保護(hù)人身財(cái)產(chǎn)權(quán),維護(hù)社會(huì)秩序,提高社會(huì)安全感。
[1]高銘暄,陳璐.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法修正案(八)》解讀與思考[M].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119.
[2]周婷玉等.擬明確“扒竊”行為入罪[N].北京日?qǐng)?bào).2010-12-21(2).
[3]李振林.盜竊罪中的法律擬制問(wèn)題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 39條的規(guī)定為視角[J].西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1,(3).
[4]陳平.對(duì)扒竊入罪的理性思考[J].政法論壇.2011,(15).
[5]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語(yǔ)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第5版[Z].北京:商務(wù)出版社,2006.1014.
[6]張明楷.刑法學(xu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1.
[7]高銘暄,馬克昌.中國(guó)刑法解釋(下卷)[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5.
[8]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227.
[9]張明楷.刑法學(xu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1.
[10]陳家林.論刑法中的扒竊——對(duì)《刑法修正案(八)》的分析與解讀[J].法律科學(xué).2011,(4).
[11]阮齊林.刑法學(xué)[M].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8.616. [12]于志剛.“風(fēng)險(xiǎn)刑法”不可行[J].法商研究,2011,(4).
[13]曲新久.醉駕不一律入罪無(wú)需依賴于“但書”的適用[J].法學(xué),2011,(7).
[14]陳興良.規(guī)范刑法學(xué)(上)[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191-192.
Resolution of Several Disputes about“Pick-pocketing Crime”
LI Jing-fen
(Criminal Justice Colleg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China,100088)
The reason of writing pick-pocketing crime into criminal law is mainly because of its special hazards.Pickpocketing crime break through the ideas that larceny conviction is usually based on the amount of money involved,and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standards of pick-pocketing crime from the two following aspects:objectively,there is not limits as to the amount of money,the times and the means of stealing;subjectively,there must have a purpose to steal larger public or private property.The standard of accomplishment of the pick-pocketing crime and general larceny is similar,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re are penalty for theft even though the pick-pocketing crime is not accomplished.In short,the provisions about pick-pocketing crime in“Criminal Law Amendment(eight)”did break the dilemma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against pickpockets.
pick-pocketing;pick-pocketing crime;public place;portable
D924.35
A
2095-1140(2012)02-0099-06
2012-02-25
李竟芬(1987-),女,湖南寧鄉(xiāng)人,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刑事司法學(xué)院刑法學(xué)專業(yè)2010級(jí)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guó)刑法研究。
葉劍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