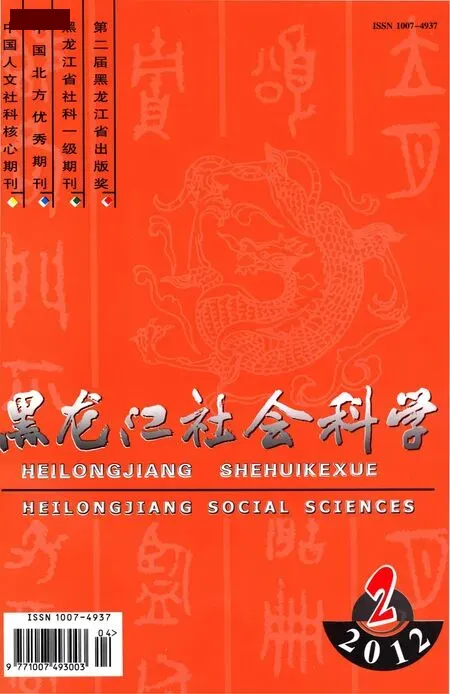鄉村社會治理中的國家法與民間法
段緒柱
(1.天津師范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天津300074;2.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哈爾濱150080)
鄉村社會治理中的國家法與民間法
段緒柱1,2
(1.天津師范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天津300074;2.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哈爾濱150080)
中國鄉村社會正處于有史以來最為深刻的變革之中,國家正式制度全面進入鄉村社會,但鄉村社會依然保有若干鄉土社會的特征,無論是國家法還是民間法都無法保障鄉村社會的和諧有序。在鄉村社會治理中,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存在著張力與協同的可能,只有使國家法與民間法相互協同,才能實現鄉村社會的善治。
國家法;民間法;鄉村治理;善治
中國鄉村社會正處在有史以來最為深刻和急劇的變革之中,持續的革命、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正式制度全面進入鄉村社會,新的行為方式、價值準則與現代國家的話語體系伴隨著廣播、電視和一次次的革命進入了鄉村社會,影響和改變著鄉村社會的風俗、習慣。但鄉村社會依然保有若干鄉土社會的特征,加之中國社會龐大而又復雜,各地資源稟賦千差萬別,風俗習慣各異,傳統的地方性規范、革命的話語、市場經濟下新的價值標準并存于鄉村社會。所有的這一切構成了復雜而又特殊的鄉村社會場閾,決定了鄉村社會治理的特殊行為邏輯。無論是國家法還是鄉村社會的民間法都不足以實現鄉村社會的和諧與發展,只有國家法與民間法實現良性的互動與協同才能使雙方共生共強,實現鄉村社會的善治。但總體而言,當前鄉村社會治理過于注重國家法的制定,忽視甚至歧視民間法,總認為民間法是過時的、落后的,哪怕是依然生效的民間法也有意無意地被忽略了。
一、鄉村社會治理中民間法與國家法間的張力
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協同是鄉村社會和諧有序的根本需要與保證,但兩者間存有一定的張力。
1.國家法的統一性與民間法的地方性之間的沖突。普遍性和一致性是現代國家法律的基本特征,現代國家為維護公民權益、保障變革社會的基本秩序,必須建構超越地方性的全國性規則體系,為人們在更大范圍內的活動提供基本規則。而中國的鄉村社會千差萬別,各地社會發展水平、資源稟賦、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各異,地方性知識是鄉村社會運行的邏輯基礎。民間法是鄉村社會長期傳承、積淀和整合而形成的規范形式,它代表和滿足了一定區域、一定社會關系網絡中成員的需要,能維持小共同體社會預期的穩定。但民間法的很大一部分已與現代社會脫節,甚至侵害公民的基本權益,無力促進一個急劇變化的社會良性向前發展,一定程度上,民間法的地域性使不同地區的人不能對彼此行為形成穩定的預期,不利于更大范圍內統一共同體的形成。而現代國家為維護公民權益、保障變革社會的基本秩序,必須建構超越地方性的全國性規則體系,為人們在更大范圍內的活動提供基本規則。
2.理想與現實、現代與傳統、觀念與現實的沖突。法律的建構與運作以人人都是陌生人為前提和假設,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是一個“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的地方,甚至是可見的若干輩后代依然要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地方,每個人都處于錯綜復雜的關系網絡中,行為選擇時都要考慮如此行為的后果,要保證自己及后輩能立足,能有尊嚴地生活,面子是重要的,甚至比利益還要重要。“國家法與民間法追尋的法律價值取向是不同的。作為國家法來說,它注重和追求的是法理秩序,而民間法注重的是道德與人倫的禮法秩序。”[1]一般而言,國家法以懲惡為目標,以侵犯合法權益為處置對象,但問題在于村民不僅僅需要懲惡,更需要向善、揚善,日常狀態下大量不能為人們所接受的行為并沒有達到違法犯罪的程度,這時的國家權力是無力的,而本土性、內生性的自治權力熟知成員的品行與行為選擇,了解其行為選擇的背景,有能力對其行為作出準確的評價和判斷,熟人社會的內在壓力可以規范和約束成員的行為,深入成員的心靈,保證社區內部的和諧有序。
3.鄉村社會的地方性知識與以城市社會交往規則為主導的現代國家法律體系間的沖突。“現代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適用于城市社會、工商社會和陌生人社會。”[2]國家法代表的一套鄉土社會所不熟悉的知識和規則,與鄉土社會的生活邏輯是不一致的,“在歷史淵源上,中國現行的法律是一套外來的知識和制度。作為西方工商業社會的產物,其所倡導的是一種以城市文化為主導。崇尚個人主義的知識理念。所謂的‘現代法律’在引入之初就存在著與中國現實無法適應的問題。在國家法大規模進入鄉土地區之前,村民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知識傳統,與之相比,國家法律不但是一種后來的知識,而且還是一種異己的和難以理解的知識。”[3]鄉村社會人們交往規模較小、內部信息透明度高、成員間相互熟悉、行為預期明了,社區成員有足夠的能力將不合作者邊緣化。具有地方性共識并且相互熟悉的人們不會完全按規則、契約、法律或者利益行事,在通常狀態下更多地以人情、面子的邏輯來行動。
4.國家法律供給不足。國家法是社會的基礎性規則,普遍無差別地適用于整個政治共同體,因而必然具有高度的原則性、宏觀性,難以對差異性給予足夠的回應。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國家權力維護的必然是基本權益,回應的是普通的大多數,既滿足所有人的基本訴求但又未使所有人得到滿足,剩余的空間就需要民間法來填補。形式上國家法已經覆蓋鄉村社會,也為鄉村社會提供了全面的法律規范和規則執行者(法官、檢察官等),但由于受財力制約和空間距離的影響,國家權力常常鞭長莫及,無法及時準確獲取基層社會信息,當農民權益需要救濟時,政府往往無法及時提供,而且通過國家法律來解決問題成本太高(既有交通費、訴訟費等實體成本,還有人情世故等無形成本)。而民間法根植于基層社會,運行成本低,回應針對性強,一定程度上為鄉村社會提供了日常規則與秩序。
二、鄉村社會治理中國家法與民間法協同的可能
國家法與民間法雖存有一定張力,但兩者不是非此即彼、你強我必弱的零和博弈關系,兩者各有所長又各有不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建構,既相互超越又相互彌補。
1.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力量源泉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法律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但它的最終力量來自于法律的內在說服力。沒有規制對象整體的心理認同,法律就是一紙空文,“一旦社會失去了超驗紐帶的維系,或者說當它不能繼續為它的品格構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種終極意義時,這個制度就會發生動蕩。”[4]心理認同不是憑空產生的,它來自于人們對于公平正義的共同體認,法律需要與人們日常生活習慣、道德觀念、行為規則兼容。法律的力量根植于人們的社會經驗,人們感覺法律內容是有益的,才能夠從內心支持和擁護法律。
2.國家法與民間法均有自己的限度。法律一般只能有效控制外顯的、公開的社會行為,立法只能是對已經規律性認識的事務的規范,而人類無法在一個具體的時間點窮盡世界,即便人類處處考慮周全,他也無法使自己的想法表達到每一個看到法律文本的人與自己的理解相一致。法律總是針對未來的,法律必須保持相對的穩定,而人類是不可能完全預知未來的一切,結果就是法律內容可能滯后。人類畢竟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上帝,制定的法律也可能是“惡法”。
民間法的作用范圍有限,超出一定的邊界就喪失了效力。民間法是長期生產、生活中自然生長出來的,具有自發的內生性,主要依靠情感、心理認同等保證執行,沒有嚴格的制定程序和文本形式,這導致了民間法的某種不確定性。有些民間法甚至違法,侵害人們的權利。國家法與民間法各有適用領域、存在的正當性,國家法能力不及之處,恰是民間法用武之所。國家法進入鄉村社會時,必須考慮已經長期存在并規范農民生活的民間法,考慮農民們的接受程度和承受能力。在復雜無比的中國鄉村社會,不顧一切地強行推行國家法可能會適得其反,導致國家法的危機,當然,也可能是一陣風吹過,一切依然如故,但法律的尊嚴亦隨之而去。
三、國家法與民間法相互協同,實現鄉村社會的善治
依靠風俗習慣已不能保證越來越外向化的鄉村社會秩序,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建立制度化、中立化的程序和規則作為社會博弈的基本準則,并以國家強制力為最后的保障。這一方面是國家權力進入鄉村社會,展現自己意志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人們生活空間擴大、交往復雜化、異質化的需要。一個客觀中立的、大家都遵守(可能是主動的選擇,也可能是恐懼武力的強制)的“游戲規則”讓各種社會力量進入一個預設的規則,可以穩定地預期對方的行為選擇及自己的得失,是鄉村社會秩序穩定、達成博弈均衡的基礎。但這不意味著民間法沒有存在的空間。
1.明確國家法與民間法各自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如公民的權利、刑事領域等,由國家法以強制性或者禁止性、義務性的法律規范予以確定和調整,民間法無權干預與分享。與農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民事社會關系,可以考慮由民間法調整,但應不排斥當事人引入國家法。“在國家法與民間法都可以適用時,要通過兩者的交錯實施,使居于主導地位的國家法和居于補充地位的民間法相互兼容、相互補充、有機結合,實現國家法與民間法的良性互動。”[5]
2.吸納民間法入國家法。“法律作為一種調規著人們交往與交換的正式規則系統,追根溯源,大多是從社會現實中的人們行事方式、習俗和慣例中演化而來。”[6]立法機關尤其是地方立法機關在制定法律及規范性文件時應尊重民間的傳統與習慣,吸納有益的民間規范,將習慣轉化為法律的一部分。“在中國法治追求中,也許最重要的并不是復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視中國社會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許并不起眼的習慣、慣例,注重經過人們反復博弈而證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否則的話,正式的法律就會被規避、無效,而且可能會給社會秩序和文化帶來災難性的破壞。”[7]習慣法還可能在司法過程中被引入。法律的普遍性使其表述高度抽象,針對具體的案件可能帶來不明確,法官需要通過他的解釋來明確法律內容,適用于案件的裁決,這種解釋多以習慣法為基礎。實際上,鄉村社會的司法機關日常裁判中多以鄉村社會習慣處理日常的社會矛盾,也就是說,在基層司法層面,民間法事實上是被普遍引入的。
3.充分發揮國家法的引導、建構功能。依靠風俗習慣已不能保證越來越外向化的鄉村社會秩序,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建立制度化、中立化的程序和規則作為社會博弈的基本準則,并以國家強制力為最后的保障。國家法不能無原則地向民間法妥協,兩者之間需要加強對話與合作,建構融合的通道與空間。國家法普遍長期地適用后,慢慢也就轉化為人們的習慣,甚至最終從法律規范中消失,因為它已內化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習慣與法律的距離并不遙遠。民間法轉向國家法,國家法轉向民間法,兩者雙向的調適是中國鄉村社會實現善治的必由之路。
[1]田成有.鄉土社會中的國家法與民間法[J].思想戰線,2001,(5):84.
[2]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8.
[3]田成有.鄉土社會中的民間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76.
[4][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M].趙一凡,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67.
[5]馬永華.民間法與國家法的關系——兼論鄉村社會法治秩序的建構[J].山東省農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6):122.
[6]韋森.經濟學與哲學:制度分析的哲學基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03.
[7]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36.
D601
A
1007-4937(2012)02-0039-03
2011-12-23
段緒柱(1973-),男,黑龍江五大連池人,副教授,政治學博士,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從事公共管理學和基層社會治理研究。
〔責任編輯:王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