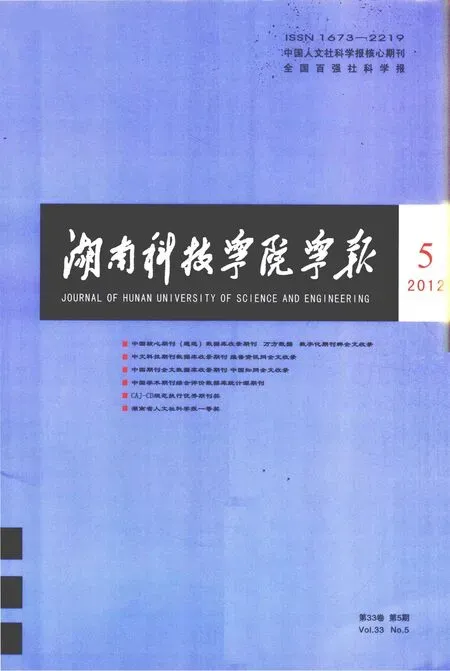論《秀拉》的生存?zhèn)惱?/h1>
2012-04-08 02:13:50姚佩芝
湖南科技學院學報 2012年5期
姚佩芝
(湖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論《秀拉》的生存?zhèn)惱?/p>
姚佩芝
(湖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托尼·莫里森的小說具有豐富的倫理意蘊。在《秀拉》中,她不僅觸及和呈現(xiàn)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黑人女性的生存?zhèn)惱碛^,而且還揭示了生存需要與倫理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因此,從倫理批評角度來審視《秀拉》,可以發(fā)現(xiàn)其獨特的藝術(shù)價值和魅力。
生存?zhèn)惱恚弧缎憷罚缓谌伺?/p>
《秀拉》是托尼·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說,發(fā)表于1973年。小說以秀拉和奈爾的友誼和成長經(jīng)歷為主線,描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至20世紀五六十年間發(fā)生在俄亥俄州梅德林市一個黑人社區(qū)——“底層”的故事。雖然小說的篇幅1不長,故事簡單,但內(nèi)涵十分豐富。自問世以來,眾多的批評家分別采用神話-原型批評、心理分析、女權(quán)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方法研讀這部作品,涉及的話題有主題、女性、文本結(jié)構(gòu)和后現(xiàn)代性等。毫無疑義,這些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秀拉》,但仍有尚未觸及、需要闡釋的問題,比如說,是什么力量促使伊娃奮不顧身去搶救烈火焚身的女兒漢娜,又是什么促使她“縱火”燒死自己半醒半睡的兒子李子?為什么秀拉親眼目睹自己的母親葬身火海卻無動于衷?當我們采用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方法來解讀時,這些問題不但能得到合理解答,還能進一步挖掘作品的主題:生存?zhèn)惱怼?/p>
一 老一代黑人女性的生存?zhèn)惱恚夯钕氯?/h2>
我們知道,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活著是人和社會發(fā)展的前提和基礎(chǔ)。然而,對于長期身處惡劣環(huán)境,生活在社會邊緣的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來說,活著是一個最為沉重的話題。《秀拉》的開篇,莫里森通過一個黑奴笑話為我們描述了黑人艱難的生存環(huán)境。黑人生活的小鎮(zhèn)原本在山上,但被白人命名為底層(Bottom)。其實,名字的由來本身就是黑人遭受種族歧視的一個歷史見證。一個白人農(nóng)場主對他的黑奴說,只要黑奴能夠干好一件難辦的活計,就會許給他人身自由和一塊低地。當奴隸要求主人履行諾言時,白人奴隸主便玩起了文字游戲,欺騙他。就這樣,白人住在了土地肥沃、風景優(yōu)美的山下,而黑人被趕到了水土流失嚴重,土地貧瘠的山頂。這樣的生存境遇造就了黑人堅忍、獨立和自尊的性格,同時也形成了一種“以生存為中心”的自我保護倫理觀——活下去。
小說中的伊娃是主人公秀拉的外婆,一個生存意識和倫理意識極強的女性。丈夫棄她而去時,她和孩子的生存陷入絕境:家里僅剩下“一塊六毛五分錢,五只雞蛋,三顆甜菜”和“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大的五歲,最小的只有幾個月大”(托妮·莫瑞森《秀拉》,31,以下僅標注頁碼)。為了讓孩子能夠活命,伊娃選擇了隱忍地活下來,承擔著“既是船,又是港”母親職責。(McKay,1988:176)每天她起早貪黑,終日勞作,但無怨無悔。即便如此,她的孩子們?nèi)匀皇巢还埂F扔跓o奈,她只好將三個大孩子托付給鄰居,自己置身一人外出打拼。18個月后回來后,她丟失了一條腿,但有了撫養(yǎng)孩子長大的錢。對于她的腿,社區(qū)里有著種種傳言:有人說她賣了自己的腿,也有的人說她讓火車壓斷一條腿而獲得了一筆賠償金等等,但絕沒有人因此而輕視她,相反她成了鄰居們尊崇的對象,缺失的腿也成了一種象征,一種體現(xiàn)深沉母愛和犧牲精神的象征。從倫理的層面來說,伊娃的行為雖然有悖于黑人所崇尚的愛自己、愛自己身體的傳統(tǒng)倫理,但她完全是出于是對生命的保存,因而干出不顧尊嚴、不合常規(guī)、常理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否則,那些幼小、稚嫩的生命怎能抵擋饑餓的考驗。
不過,伊娃也是一個頗受爭議的人物。她的“縱火食子”令不少的讀者和批評家困惑不解。伊娃選在一個晚上對精神恍惚的李子動手:她先用煤油澆濕他全身,隨后點著一些卷成紙棒的報紙,最后將火把扔向李子。等大火把他吞噬(44)時,她便把房門鎖死,痛苦地、慢慢地離開。女兒漢娜和鄰居們發(fā)現(xiàn)后,由于打不開房門,他們只能眼睜睜看著熊熊大火把他活活燒死。此時的伊娃冷酷無情,與之前那個充滿著濃烈的舔犢之情、為了孩子不惜傷害自己身體的伊娃有著天壤之別。可是,當女兒漢娜遭遇危險,被火包圍時,伊娃則奮不顧身,從樓上跳了下來,上演了一幕舍身救女的英雄壯舉。她“跳出了窗口。破玻璃劃得她混身是傷,遍體流血,她兩手在空中撲騰著,掙扎著拼命朝火焰和那著了火的女兒落下去”。她“給摔得暈頭轉(zhuǎn)向,不過還沒有失去知覺,仍然拖著身子朝她的大女兒爬去”。(71)
同樣是孩子,伊娃的行為前后反差如此巨大,實在讓人有些費解。如果我們以黑人母親/母性的職能觀照,就不難理解了。在黑人文化中,母親占據(jù)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保存生命是母親的首要職責。也就是說,在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下,黑人女性要盡可能地維持生命的存活,因為孩子是黑人社區(qū)中最有價值卻又最脆弱的部分。所以,伊娃的斷腿和救女行為完全是出于對生命的保護,這是母親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活下去”的第一倫理,即為了生存可以冒任何危險,甚至包括付出生命的代價。至于燒死兒子,伊娃說,她是為了“讓他死得像個男子漢,不致于在我的子宮里揉得皺皺巴巴的,而是要像個男子漢”。(67)伊娃道出了她殺死兒子的原因。她是不愿看到李子喪失責任感,在毒品中消耗生命。她無法忍受兒子人格萎縮,精神墮落,迫于無奈,她才結(jié)束兒子的生命,讓他死得像個男子漢,在烈火中得到救贖和重生。套用聶珍釗教授在評述塞斯殺死女兒時的話說,在伊娃的意識里實際上存在兩個兒子:一個屬于客觀的有生命的兒子,一個屬于抽象的存在于倫理意識形態(tài)中的兒子。她殺死了有生命的兒子,但是她卻保護了倫理意識形態(tài)中的兒子的尊嚴。(聶珍釗,2005)她堅信:伴隨著肉體的死亡,兒子能進入一種精神上的自由和尊嚴的永恒。
實際上,在殺戮之前,伊娃曾經(jīng)歷過一番痛苦而艱難的倫理抉擇:她一搖一擺地來到了李子的門前,坐在床上,把李子緊緊地摟在懷里,她“伸出舌頭,把流下的淚水在唇邊接住,以免流到嘴里,搖啊,晃啊。后來,她把他放下,瞅了他很長時間”(44)。盡管伊娃主觀上認為自己將生存從活下去提升至有自由、有尊嚴地活,但客觀上卻抑制不住對兒子濃烈的愛。李子死后不久,漢娜問起此事時,伊娃依舊痛苦不堪,她“淚眼模糊”,嘴里“呼喚著兒子的名字”,“一邊用手指上下摸索著自己的衣裙皺褶”。(68)
誠然,當我們重返倫理現(xiàn)場,站在伊娃的立場上審視其動機與目的,她的行為有其合理之處,但也折射出人的生存與倫理意識之間的矛盾。(修樹新,2009:42)因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代,“食子”都是公認的社會犯罪和倫理犯罪。這一行為不但觸犯了骨肉相殘的倫理禁忌,逾越了人與動物的界限,同時也違反了社會的法規(guī)。因此,這種生存?zhèn)惱碛^是值得反思的。
二 新一代黑人女性的生存?zhèn)惱恚嚎範幍鼗钪?/h2>
如果說,“活下去”代表的是以生存需要為中心的老一輩黑人女性的生存?zhèn)惱碛^,那么抗爭地活著則彰顯了現(xiàn)代黑人女性以實現(xiàn)自我價值為中心的生存?zhèn)惱怼_@種倫理觀認為,人不僅僅是為了活著,還必須構(gòu)建自我,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價值。
作為一個現(xiàn)代女性,秀拉沒有選擇“底層”社會為其設(shè)定的恒定生活,而是要塑造一個全新的自我。早在童年時代,她就意識到了黑人女性生存處境的尷尬:“由于自己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性,所有的自由和成功都與她們無緣,所以她們便著手把自己創(chuàng)造出另外一個自我來。”(49)
在好友奈爾結(jié)婚后,秀拉離開了家鄉(xiāng),開始了長達十年追尋自我的歷程。對于她在外的游歷,作品中僅留下一些只言片語。讀者只知道她上了大學,去過納什維爾、底特律、新奧爾良、紐約、費城、梅肯與圣地亞哥等地方。作者雖沒有提到她在城市的具體生活情況,但是都市造成她心靈的荒漠是不言自明的。正是由于厭倦了城市的生活,她才決定回到自己出生的小鎮(zhèn)生活,以尋求肉體的充實來擺脫自己精神的困境。這種與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完全背離的生活方式最終使她成了社區(qū)的“他者”,被人們視為蟑螂、女巫、害群之馬等等,因為她的行為不僅破壞了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而且也擾亂了規(guī)范的生活秩序。
首先,秀拉蔑視傳統(tǒng)倫理,拒絕接受結(jié)婚-生子-照顧家庭的生活模式。她年齡很大依然單身。而她這個年齡的黑人女性早已是家庭主婦,她的祖母表示很擔憂:“你啥時結(jié)婚?你需要養(yǎng)幾個孩子,這樣你就會安生。”(87)但秀拉回答說,“我不要成為其他什么人,我要成為我自己。”(87)在秀拉看來,身體是自己的,何時結(jié)婚,與誰結(jié)婚完全是她自己的事。于祖母而言,身體雖是自己的,但個人仍是社區(qū)中的一部分,理應遵循它的行為準則與價值規(guī)范。
由于不愿束縛自己的自由,聽祖母的嘮叨,秀拉與伊娃發(fā)生了唇槍舌劍般的爭吵,她不惜揭伊娃的傷疤,以“斷腿”和“燒死李子”之事來攻擊她,還強行把她送到了養(yǎng)老院。作者借奈爾之口表達了對她的行為的譴責:“白人才不在乎把他們的老人趕出家門呢。要是黑人讓老人走可就費事啦,即使某個上年紀的人無依無靠,別人也會進屋串門、掃地做飯。只有那些神智不清和無法治理的老人才會送到養(yǎng)老院。”(154-155)奈爾的話隱含著對白人家庭觀念的批判,并且表明,秀拉的行為不僅違背了黑人對待老人的常規(guī),而且還是有悖人倫、漠視親情的不孝行為,原因很簡單,此時的伊娃身體依然健康,完全能夠料理自己。
其次,也是社區(qū)的人最難以忍受的是,秀拉為發(fā)現(xiàn)自我所采取的極端生活方式——以身體為媒介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價值。她與男人濫交,幾乎和社區(qū)里的每一位男性都有染,連好友奈爾的丈夫裘德也不放過。當奈爾問及此事時,秀拉回答說,“在我的腦袋里,在我前面,在我后面,有這么塊地方。一些空地。而裘德填滿了這個空子。就是這么回事。他只是填滿了這個空子。”(103)顯然,秀拉與男性的關(guān)系是以充分張揚自我、滿足自我為根本目的的。(修樹新,2009:89)但激情過后,她更感孤寂:“在那寂靜的中心,那種孤獨感如此深沉,以致這個字眼本身已經(jīng)沒有意思了。”(116)秀拉的性行為“既不屬于道德的范疇,也不屬于婚姻制度之內(nèi)的合法行為,它屬于感官經(jīng)驗的范圍,是她探索自我、了解自我的手段”。(Bloom,1990:156)
彌留之際,奈爾不計前嫌地來到秀拉的床前,噓寒問暖。秀拉對她說:
你以為只是因為我沒有過你那種日子我就不知道你的生活是個什么樣子嗎?我了解這個國家里每個黑人女人在做些什么,等死罷了。就像我現(xiàn)在這樣。不過區(qū)別在于她們是像樹樁一樣死去。而我,我像一株紅杉那樣死去。我敢說我確實在這個世界上生活過。(134)
在這里,秀拉道出了黑人女性群體的命運和自己的生存價值觀。秀拉認為,她之所以不會像樹樁一樣漸漸地枯竭,憔悴,熬至生命的終結(jié),而像紅杉那樣,堅定,挺拔,是因為她能夠按自己選擇的方式生活;是因為她對自我和自由有著不懈的追求,在鄙視和唾棄的逆境中實現(xiàn)著個人價值。(周小平,1998:67-68)
三 黑人女性生存?zhèn)惱淼闹毓?/h2>
由于身處不同的時代,新、老兩代黑人女性在生存?zhèn)惱碛^上出現(xiàn)了較大的差異。不過,這兩種生存?zhèn)惱碛^雖有值得借鑒的現(xiàn)實價值,但不可避免地也具有歷史局限性。下面我們從這兩個方面予以分析。
伊娃生活在19世紀末,黑人的生存境遇異常艱辛。在丈夫出走、生活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她表現(xiàn)得十分堅強,責無旁貸地挑起生活的重擔。在五年的時間里,她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擺脫貧困、兒女們的溫飽上。憑借著斷腿換來的錢,她先后蓋了許多房子,吸引來了許多房客,使兒女們過上了衣食無憂的日子:樓下放著甜瓜,餐桌上出現(xiàn)了魚、烤面包和點心,桶里儲備著豬肉,壇子里盛滿了咸蛋。同時,她還幫助女兒漢娜養(yǎng)育了秀拉。由于生存壓力,她“除了把孩子喂飽外,無法向孩子們表達自己的愛,她對自己都沒有時間和精力表達任何情感”(Chantharothai,2003:133-134)。漢娜曾這樣問伊娃:
“媽媽,你是不是愛過我們?”“你是不是哄我們玩過?”
“玩?1895年沒人玩,就因為你過得不錯,你就認為總這么好?1895年可是要人命的,閨女。太糟糕了,黑鬼死起來像蒼蠅一樣多。”
“但是,媽媽,總有些時候你不想這些……”“沒什么時間。沒時間。剛做完白天的事就天黑了……”(68-69)
在生活的重壓下,伊娃把對孩子們的愛和交流看作“是一種浪費時間。”她無暇顧及在精神上養(yǎng)育漢娜,漢娜也沒有在精神上養(yǎng)育秀拉。(hooks,1999:134-135)作為母親和唯一的監(jiān)護人,她認為把兒女們撫養(yǎng)長大就是最大的愛。由于她對孩子們“疏于管教”,于是就出現(xiàn)了在兩性關(guān)系上自由自在的漢娜,吸毒成癮的李子和親眼目睹母親自焚而袖手旁觀、像紅杉一樣長大的秀拉。可見,伊娃的生存?zhèn)惱碛^患有胡克斯所說的精神養(yǎng)育缺乏癥。
到了秀拉這一代,黑人的生活情況和社會地位相應得到了提高和改善。在物質(zhì)生活基本能滿足的情況下,她們更多的是關(guān)注精神的自由和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特別是秀拉,她接受了高等教育,還受到了50、60年代的民權(quán)運動和女性主義思想的洗禮,因而自我意識更加強烈。但是,在外出闖蕩的十年中,秀拉的精神是孤獨的。正是因為精神的孤獨,她才回到底層來尋找當年的精神盟友奈爾,希冀能與其溝通,但此時的奈爾已經(jīng)被黑人社區(qū)徹底同化,完全泯滅了自我,從而阻隔了她唯一可能聯(lián)系到的精神安慰。沒有了對話者和同路人,秀拉不得不在自我實現(xiàn)的道路上孤軍奮戰(zhàn),即不惜任何代價地反抗傳統(tǒng)的男權(quán)社會、特立獨行地追尋著自我。
固然,在顛覆男權(quán)、爭取男女平等,無怨無悔地追求自我等方面,秀拉的行為具有深遠的意義,她獨自一人在底層發(fā)動一場反性別主義、反倫理道德的戰(zhàn)爭,其勇氣和精神也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個人的追求不能排斥對同胞的責任感,不能割裂與本民族文化的聯(lián)系,因為沒有了語境,自我就會失去成長的依據(jù),并且走向死亡和毀滅。(Samuels,1990:43)亦如莫里森所說:“如果我們不和我們的祖先保持聯(lián)系,我們就會迷失方向,你殺了祖先就等于殺了你自己”。(Peach,1995:78)
需要指出的是,秀拉把身體當作實現(xiàn)自我的惟一途徑,從一開始就預示著她的悲劇,原因在于身體的愉悅不具備任何種族對抗與性別征服的色彩。她不但找不到自我,反而會陷入男性強加于女性的傳統(tǒng)性別模式之中,導致更深的自我迷失。事實上,秀拉所追求的自我并非是黑人女性真正的自我,只不過是在弘揚女性的生命力量,讓生命擺脫種族和社會倫理規(guī)范的制約罷了。這種反抗并不是積極地抗爭,既不被白人社會所接受,也不為黑人社會所容納,盡管它“可以揭示社會壓抑的力量,但無法為人們提供或積累可以借鑒的精神資源。”(王玉括,2005:135)當然,這兩種倫理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與土地有關(guān),與白人的種族歧視所造成的黑人物質(zhì)匱乏有關(guān),也與黑人自身的精神生活有關(guān)。
四 結(jié) 語
作為一個具有敏銳觀察力和深邃洞察力的作家,莫里森看到了新、老兩代黑人女性生存?zhèn)惱硭枷肴毕荨R镣薜纳鎮(zhèn)惱碛^雖“簡單、質(zhì)樸”,“透著偉大、高尚”,但忽略了精神資源引發(fā)問題;而秀拉的生存?zhèn)惱碛^雖張揚自我,但與黑人文化斷裂,從而導致歷史意識、文化意識的缺失,造成精神匱乏的大問題。因此,黑人的生存?zhèn)惱碛^理應有所承傳,應隨環(huán)境變化而有所發(fā)展,以適應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需要。莫里森通過自己的作品向黑人傳達出這樣的觀點:在美國社會中,黑人只有保持自己的傳統(tǒng)和文化特色,敢于向命運抗爭,才能使自己和自己的文化得以發(fā)展和延續(xù)。
[1]托妮·莫瑞森.秀拉[M].胡允桓,譯.海口:南海出版社,2005.
[2]bell hooks.Sister of the Yam:Black Women and Self-Discovery[M].Boston:Southend,1993.
[3]Bloom,Harold(ed.)Toni Morrison[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90.
[4]Chantharothai,Sasitorn.Transforming Self,Family,and Community:Women in the Novels of Anne Tyler,Toni Morrison, and Amy Tan[D].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3.
[5]McKay,Nellie Y. (ed.)Critical Essays on Toni Morrison[A].Boston:G.K.Hall,1988.
[6]Peach,Linden.Toni Morrison[M].Hampshire: Macmillan,1995.
[7]Samuels,Wilfred D.and Hudson Weems Clenora.Toni Morrison.Boston:Twayne,1990.
[8]杜志卿.《秀拉》的死亡主題[J].外國文學評論,2003,(3):34-43.
[9]聶珍釗.論莫里森小說《寵兒》的倫理價值[Z].美國文學研究會第四屆專題研討會發(fā)言稿,2005.
[10]托妮·莫瑞森.秀拉[M].胡允桓,譯.海口:南海出版社,2005.
[11]王玉括.莫里森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2]修樹新.托妮·莫里森小說的文學倫理學批評[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09.
[13]周小平.“我早該想到那些鳥意味著什么了”——讀托妮·莫瑞森的《秀拉》[J].外國文學與研究,1998(2):68-69.
I106.4
A
1673-2219(2012)05-0038-03
2012-03-31
本論文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美國黑人小說中的城市書寫”(項目編號11BWW057)資助。
姚佩芝(1958-),女,湖南衡陽人,文學博士,湖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非裔美國文學和英美文學。
(責任編校:張京華)
姚佩芝
(湖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論《秀拉》的生存?zhèn)惱?/p>
姚佩芝
(湖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托尼·莫里森的小說具有豐富的倫理意蘊。在《秀拉》中,她不僅觸及和呈現(xiàn)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黑人女性的生存?zhèn)惱碛^,而且還揭示了生存需要與倫理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因此,從倫理批評角度來審視《秀拉》,可以發(fā)現(xiàn)其獨特的藝術(shù)價值和魅力。
生存?zhèn)惱恚弧缎憷罚缓谌伺?/p>
《秀拉》是托尼·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說,發(fā)表于1973年。小說以秀拉和奈爾的友誼和成長經(jīng)歷為主線,描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至20世紀五六十年間發(fā)生在俄亥俄州梅德林市一個黑人社區(qū)——“底層”的故事。雖然小說的篇幅1不長,故事簡單,但內(nèi)涵十分豐富。自問世以來,眾多的批評家分別采用神話-原型批評、心理分析、女權(quán)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方法研讀這部作品,涉及的話題有主題、女性、文本結(jié)構(gòu)和后現(xiàn)代性等。毫無疑義,這些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秀拉》,但仍有尚未觸及、需要闡釋的問題,比如說,是什么力量促使伊娃奮不顧身去搶救烈火焚身的女兒漢娜,又是什么促使她“縱火”燒死自己半醒半睡的兒子李子?為什么秀拉親眼目睹自己的母親葬身火海卻無動于衷?當我們采用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方法來解讀時,這些問題不但能得到合理解答,還能進一步挖掘作品的主題:生存?zhèn)惱怼?/p>
一 老一代黑人女性的生存?zhèn)惱恚夯钕氯?/h2>
我們知道,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活著是人和社會發(fā)展的前提和基礎(chǔ)。然而,對于長期身處惡劣環(huán)境,生活在社會邊緣的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來說,活著是一個最為沉重的話題。《秀拉》的開篇,莫里森通過一個黑奴笑話為我們描述了黑人艱難的生存環(huán)境。黑人生活的小鎮(zhèn)原本在山上,但被白人命名為底層(Bottom)。其實,名字的由來本身就是黑人遭受種族歧視的一個歷史見證。一個白人農(nóng)場主對他的黑奴說,只要黑奴能夠干好一件難辦的活計,就會許給他人身自由和一塊低地。當奴隸要求主人履行諾言時,白人奴隸主便玩起了文字游戲,欺騙他。就這樣,白人住在了土地肥沃、風景優(yōu)美的山下,而黑人被趕到了水土流失嚴重,土地貧瘠的山頂。這樣的生存境遇造就了黑人堅忍、獨立和自尊的性格,同時也形成了一種“以生存為中心”的自我保護倫理觀——活下去。
小說中的伊娃是主人公秀拉的外婆,一個生存意識和倫理意識極強的女性。丈夫棄她而去時,她和孩子的生存陷入絕境:家里僅剩下“一塊六毛五分錢,五只雞蛋,三顆甜菜”和“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大的五歲,最小的只有幾個月大”(托妮·莫瑞森《秀拉》,31,以下僅標注頁碼)。為了讓孩子能夠活命,伊娃選擇了隱忍地活下來,承擔著“既是船,又是港”母親職責。(McKay,1988:176)每天她起早貪黑,終日勞作,但無怨無悔。即便如此,她的孩子們?nèi)匀皇巢还埂F扔跓o奈,她只好將三個大孩子托付給鄰居,自己置身一人外出打拼。18個月后回來后,她丟失了一條腿,但有了撫養(yǎng)孩子長大的錢。對于她的腿,社區(qū)里有著種種傳言:有人說她賣了自己的腿,也有的人說她讓火車壓斷一條腿而獲得了一筆賠償金等等,但絕沒有人因此而輕視她,相反她成了鄰居們尊崇的對象,缺失的腿也成了一種象征,一種體現(xiàn)深沉母愛和犧牲精神的象征。從倫理的層面來說,伊娃的行為雖然有悖于黑人所崇尚的愛自己、愛自己身體的傳統(tǒng)倫理,但她完全是出于是對生命的保存,因而干出不顧尊嚴、不合常規(guī)、常理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否則,那些幼小、稚嫩的生命怎能抵擋饑餓的考驗。
不過,伊娃也是一個頗受爭議的人物。她的“縱火食子”令不少的讀者和批評家困惑不解。伊娃選在一個晚上對精神恍惚的李子動手:她先用煤油澆濕他全身,隨后點著一些卷成紙棒的報紙,最后將火把扔向李子。等大火把他吞噬(44)時,她便把房門鎖死,痛苦地、慢慢地離開。女兒漢娜和鄰居們發(fā)現(xiàn)后,由于打不開房門,他們只能眼睜睜看著熊熊大火把他活活燒死。此時的伊娃冷酷無情,與之前那個充滿著濃烈的舔犢之情、為了孩子不惜傷害自己身體的伊娃有著天壤之別。可是,當女兒漢娜遭遇危險,被火包圍時,伊娃則奮不顧身,從樓上跳了下來,上演了一幕舍身救女的英雄壯舉。她“跳出了窗口。破玻璃劃得她混身是傷,遍體流血,她兩手在空中撲騰著,掙扎著拼命朝火焰和那著了火的女兒落下去”。她“給摔得暈頭轉(zhuǎn)向,不過還沒有失去知覺,仍然拖著身子朝她的大女兒爬去”。(71)
同樣是孩子,伊娃的行為前后反差如此巨大,實在讓人有些費解。如果我們以黑人母親/母性的職能觀照,就不難理解了。在黑人文化中,母親占據(jù)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保存生命是母親的首要職責。也就是說,在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下,黑人女性要盡可能地維持生命的存活,因為孩子是黑人社區(qū)中最有價值卻又最脆弱的部分。所以,伊娃的斷腿和救女行為完全是出于對生命的保護,這是母親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活下去”的第一倫理,即為了生存可以冒任何危險,甚至包括付出生命的代價。至于燒死兒子,伊娃說,她是為了“讓他死得像個男子漢,不致于在我的子宮里揉得皺皺巴巴的,而是要像個男子漢”。(67)伊娃道出了她殺死兒子的原因。她是不愿看到李子喪失責任感,在毒品中消耗生命。她無法忍受兒子人格萎縮,精神墮落,迫于無奈,她才結(jié)束兒子的生命,讓他死得像個男子漢,在烈火中得到救贖和重生。套用聶珍釗教授在評述塞斯殺死女兒時的話說,在伊娃的意識里實際上存在兩個兒子:一個屬于客觀的有生命的兒子,一個屬于抽象的存在于倫理意識形態(tài)中的兒子。她殺死了有生命的兒子,但是她卻保護了倫理意識形態(tài)中的兒子的尊嚴。(聶珍釗,2005)她堅信:伴隨著肉體的死亡,兒子能進入一種精神上的自由和尊嚴的永恒。
實際上,在殺戮之前,伊娃曾經(jīng)歷過一番痛苦而艱難的倫理抉擇:她一搖一擺地來到了李子的門前,坐在床上,把李子緊緊地摟在懷里,她“伸出舌頭,把流下的淚水在唇邊接住,以免流到嘴里,搖啊,晃啊。后來,她把他放下,瞅了他很長時間”(44)。盡管伊娃主觀上認為自己將生存從活下去提升至有自由、有尊嚴地活,但客觀上卻抑制不住對兒子濃烈的愛。李子死后不久,漢娜問起此事時,伊娃依舊痛苦不堪,她“淚眼模糊”,嘴里“呼喚著兒子的名字”,“一邊用手指上下摸索著自己的衣裙皺褶”。(68)
誠然,當我們重返倫理現(xiàn)場,站在伊娃的立場上審視其動機與目的,她的行為有其合理之處,但也折射出人的生存與倫理意識之間的矛盾。(修樹新,2009:42)因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代,“食子”都是公認的社會犯罪和倫理犯罪。這一行為不但觸犯了骨肉相殘的倫理禁忌,逾越了人與動物的界限,同時也違反了社會的法規(guī)。因此,這種生存?zhèn)惱碛^是值得反思的。
二 新一代黑人女性的生存?zhèn)惱恚嚎範幍鼗钪?/h2>
如果說,“活下去”代表的是以生存需要為中心的老一輩黑人女性的生存?zhèn)惱碛^,那么抗爭地活著則彰顯了現(xiàn)代黑人女性以實現(xiàn)自我價值為中心的生存?zhèn)惱怼_@種倫理觀認為,人不僅僅是為了活著,還必須構(gòu)建自我,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價值。
作為一個現(xiàn)代女性,秀拉沒有選擇“底層”社會為其設(shè)定的恒定生活,而是要塑造一個全新的自我。早在童年時代,她就意識到了黑人女性生存處境的尷尬:“由于自己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性,所有的自由和成功都與她們無緣,所以她們便著手把自己創(chuàng)造出另外一個自我來。”(49)
在好友奈爾結(jié)婚后,秀拉離開了家鄉(xiāng),開始了長達十年追尋自我的歷程。對于她在外的游歷,作品中僅留下一些只言片語。讀者只知道她上了大學,去過納什維爾、底特律、新奧爾良、紐約、費城、梅肯與圣地亞哥等地方。作者雖沒有提到她在城市的具體生活情況,但是都市造成她心靈的荒漠是不言自明的。正是由于厭倦了城市的生活,她才決定回到自己出生的小鎮(zhèn)生活,以尋求肉體的充實來擺脫自己精神的困境。這種與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完全背離的生活方式最終使她成了社區(qū)的“他者”,被人們視為蟑螂、女巫、害群之馬等等,因為她的行為不僅破壞了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而且也擾亂了規(guī)范的生活秩序。
首先,秀拉蔑視傳統(tǒng)倫理,拒絕接受結(jié)婚-生子-照顧家庭的生活模式。她年齡很大依然單身。而她這個年齡的黑人女性早已是家庭主婦,她的祖母表示很擔憂:“你啥時結(jié)婚?你需要養(yǎng)幾個孩子,這樣你就會安生。”(87)但秀拉回答說,“我不要成為其他什么人,我要成為我自己。”(87)在秀拉看來,身體是自己的,何時結(jié)婚,與誰結(jié)婚完全是她自己的事。于祖母而言,身體雖是自己的,但個人仍是社區(qū)中的一部分,理應遵循它的行為準則與價值規(guī)范。
由于不愿束縛自己的自由,聽祖母的嘮叨,秀拉與伊娃發(fā)生了唇槍舌劍般的爭吵,她不惜揭伊娃的傷疤,以“斷腿”和“燒死李子”之事來攻擊她,還強行把她送到了養(yǎng)老院。作者借奈爾之口表達了對她的行為的譴責:“白人才不在乎把他們的老人趕出家門呢。要是黑人讓老人走可就費事啦,即使某個上年紀的人無依無靠,別人也會進屋串門、掃地做飯。只有那些神智不清和無法治理的老人才會送到養(yǎng)老院。”(154-155)奈爾的話隱含著對白人家庭觀念的批判,并且表明,秀拉的行為不僅違背了黑人對待老人的常規(guī),而且還是有悖人倫、漠視親情的不孝行為,原因很簡單,此時的伊娃身體依然健康,完全能夠料理自己。
其次,也是社區(qū)的人最難以忍受的是,秀拉為發(fā)現(xiàn)自我所采取的極端生活方式——以身體為媒介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價值。她與男人濫交,幾乎和社區(qū)里的每一位男性都有染,連好友奈爾的丈夫裘德也不放過。當奈爾問及此事時,秀拉回答說,“在我的腦袋里,在我前面,在我后面,有這么塊地方。一些空地。而裘德填滿了這個空子。就是這么回事。他只是填滿了這個空子。”(103)顯然,秀拉與男性的關(guān)系是以充分張揚自我、滿足自我為根本目的的。(修樹新,2009:89)但激情過后,她更感孤寂:“在那寂靜的中心,那種孤獨感如此深沉,以致這個字眼本身已經(jīng)沒有意思了。”(116)秀拉的性行為“既不屬于道德的范疇,也不屬于婚姻制度之內(nèi)的合法行為,它屬于感官經(jīng)驗的范圍,是她探索自我、了解自我的手段”。(Bloom,1990:156)
彌留之際,奈爾不計前嫌地來到秀拉的床前,噓寒問暖。秀拉對她說:
你以為只是因為我沒有過你那種日子我就不知道你的生活是個什么樣子嗎?我了解這個國家里每個黑人女人在做些什么,等死罷了。就像我現(xiàn)在這樣。不過區(qū)別在于她們是像樹樁一樣死去。而我,我像一株紅杉那樣死去。我敢說我確實在這個世界上生活過。(134)
在這里,秀拉道出了黑人女性群體的命運和自己的生存價值觀。秀拉認為,她之所以不會像樹樁一樣漸漸地枯竭,憔悴,熬至生命的終結(jié),而像紅杉那樣,堅定,挺拔,是因為她能夠按自己選擇的方式生活;是因為她對自我和自由有著不懈的追求,在鄙視和唾棄的逆境中實現(xiàn)著個人價值。(周小平,1998:67-68)
三 黑人女性生存?zhèn)惱淼闹毓?/h2>
由于身處不同的時代,新、老兩代黑人女性在生存?zhèn)惱碛^上出現(xiàn)了較大的差異。不過,這兩種生存?zhèn)惱碛^雖有值得借鑒的現(xiàn)實價值,但不可避免地也具有歷史局限性。下面我們從這兩個方面予以分析。
伊娃生活在19世紀末,黑人的生存境遇異常艱辛。在丈夫出走、生活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她表現(xiàn)得十分堅強,責無旁貸地挑起生活的重擔。在五年的時間里,她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擺脫貧困、兒女們的溫飽上。憑借著斷腿換來的錢,她先后蓋了許多房子,吸引來了許多房客,使兒女們過上了衣食無憂的日子:樓下放著甜瓜,餐桌上出現(xiàn)了魚、烤面包和點心,桶里儲備著豬肉,壇子里盛滿了咸蛋。同時,她還幫助女兒漢娜養(yǎng)育了秀拉。由于生存壓力,她“除了把孩子喂飽外,無法向孩子們表達自己的愛,她對自己都沒有時間和精力表達任何情感”(Chantharothai,2003:133-134)。漢娜曾這樣問伊娃:
“媽媽,你是不是愛過我們?”“你是不是哄我們玩過?”
“玩?1895年沒人玩,就因為你過得不錯,你就認為總這么好?1895年可是要人命的,閨女。太糟糕了,黑鬼死起來像蒼蠅一樣多。”
“但是,媽媽,總有些時候你不想這些……”“沒什么時間。沒時間。剛做完白天的事就天黑了……”(68-69)
在生活的重壓下,伊娃把對孩子們的愛和交流看作“是一種浪費時間。”她無暇顧及在精神上養(yǎng)育漢娜,漢娜也沒有在精神上養(yǎng)育秀拉。(hooks,1999:134-135)作為母親和唯一的監(jiān)護人,她認為把兒女們撫養(yǎng)長大就是最大的愛。由于她對孩子們“疏于管教”,于是就出現(xiàn)了在兩性關(guān)系上自由自在的漢娜,吸毒成癮的李子和親眼目睹母親自焚而袖手旁觀、像紅杉一樣長大的秀拉。可見,伊娃的生存?zhèn)惱碛^患有胡克斯所說的精神養(yǎng)育缺乏癥。
到了秀拉這一代,黑人的生活情況和社會地位相應得到了提高和改善。在物質(zhì)生活基本能滿足的情況下,她們更多的是關(guān)注精神的自由和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特別是秀拉,她接受了高等教育,還受到了50、60年代的民權(quán)運動和女性主義思想的洗禮,因而自我意識更加強烈。但是,在外出闖蕩的十年中,秀拉的精神是孤獨的。正是因為精神的孤獨,她才回到底層來尋找當年的精神盟友奈爾,希冀能與其溝通,但此時的奈爾已經(jīng)被黑人社區(qū)徹底同化,完全泯滅了自我,從而阻隔了她唯一可能聯(lián)系到的精神安慰。沒有了對話者和同路人,秀拉不得不在自我實現(xiàn)的道路上孤軍奮戰(zhàn),即不惜任何代價地反抗傳統(tǒng)的男權(quán)社會、特立獨行地追尋著自我。
固然,在顛覆男權(quán)、爭取男女平等,無怨無悔地追求自我等方面,秀拉的行為具有深遠的意義,她獨自一人在底層發(fā)動一場反性別主義、反倫理道德的戰(zhàn)爭,其勇氣和精神也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個人的追求不能排斥對同胞的責任感,不能割裂與本民族文化的聯(lián)系,因為沒有了語境,自我就會失去成長的依據(jù),并且走向死亡和毀滅。(Samuels,1990:43)亦如莫里森所說:“如果我們不和我們的祖先保持聯(lián)系,我們就會迷失方向,你殺了祖先就等于殺了你自己”。(Peach,1995:78)
需要指出的是,秀拉把身體當作實現(xiàn)自我的惟一途徑,從一開始就預示著她的悲劇,原因在于身體的愉悅不具備任何種族對抗與性別征服的色彩。她不但找不到自我,反而會陷入男性強加于女性的傳統(tǒng)性別模式之中,導致更深的自我迷失。事實上,秀拉所追求的自我并非是黑人女性真正的自我,只不過是在弘揚女性的生命力量,讓生命擺脫種族和社會倫理規(guī)范的制約罷了。這種反抗并不是積極地抗爭,既不被白人社會所接受,也不為黑人社會所容納,盡管它“可以揭示社會壓抑的力量,但無法為人們提供或積累可以借鑒的精神資源。”(王玉括,2005:135)當然,這兩種倫理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與土地有關(guān),與白人的種族歧視所造成的黑人物質(zhì)匱乏有關(guān),也與黑人自身的精神生活有關(guān)。
四 結(jié) 語
作為一個具有敏銳觀察力和深邃洞察力的作家,莫里森看到了新、老兩代黑人女性生存?zhèn)惱硭枷肴毕荨R镣薜纳鎮(zhèn)惱碛^雖“簡單、質(zhì)樸”,“透著偉大、高尚”,但忽略了精神資源引發(fā)問題;而秀拉的生存?zhèn)惱碛^雖張揚自我,但與黑人文化斷裂,從而導致歷史意識、文化意識的缺失,造成精神匱乏的大問題。因此,黑人的生存?zhèn)惱碛^理應有所承傳,應隨環(huán)境變化而有所發(fā)展,以適應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需要。莫里森通過自己的作品向黑人傳達出這樣的觀點:在美國社會中,黑人只有保持自己的傳統(tǒng)和文化特色,敢于向命運抗爭,才能使自己和自己的文化得以發(fā)展和延續(xù)。
[1]托妮·莫瑞森.秀拉[M].胡允桓,譯.海口:南海出版社,2005.
[2]bell hooks.Sister of the Yam:Black Women and Self-Discovery[M].Boston:Southend,1993.
[3]Bloom,Harold(ed.)Toni Morrison[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90.
[4]Chantharothai,Sasitorn.Transforming Self,Family,and Community:Women in the Novels of Anne Tyler,Toni Morrison, and Amy Tan[D].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3.
[5]McKay,Nellie Y. (ed.)Critical Essays on Toni Morrison[A].Boston:G.K.Hall,1988.
[6]Peach,Linden.Toni Morrison[M].Hampshire: Macmillan,1995.
[7]Samuels,Wilfred D.and Hudson Weems Clenora.Toni Morrison.Boston:Twayne,1990.
[8]杜志卿.《秀拉》的死亡主題[J].外國文學評論,2003,(3):34-43.
[9]聶珍釗.論莫里森小說《寵兒》的倫理價值[Z].美國文學研究會第四屆專題研討會發(fā)言稿,2005.
[10]托妮·莫瑞森.秀拉[M].胡允桓,譯.海口:南海出版社,2005.
[11]王玉括.莫里森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2]修樹新.托妮·莫里森小說的文學倫理學批評[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09.
[13]周小平.“我早該想到那些鳥意味著什么了”——讀托妮·莫瑞森的《秀拉》[J].外國文學與研究,1998(2):68-69.
I106.4
A
1673-2219(2012)05-0038-03
2012-03-31
本論文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美國黑人小說中的城市書寫”(項目編號11BWW057)資助。
姚佩芝(1958-),女,湖南衡陽人,文學博士,湖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非裔美國文學和英美文學。
(責任編校:張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