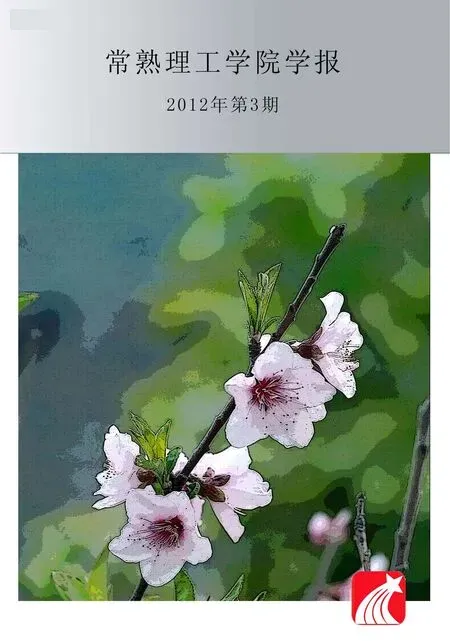貝克的“自反現代化”論
鐘一軍
(云南師范大學 哲學與政法學院,昆明 650500)
自社會學誕生以來,現代性一直是該學科關注的核心主題之一。現代性有其時代內涵,畢竟,經典社會理論提出的現代性在當代起了變化。在當代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中,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提出的“自反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論①現代性指現代社會特征,指向一種狀態。與其相對應,現代化則是走向現代性的一種過程,二者是同一現象的不同方面。所以,貝克的“自反現代化”理論可看作是對一種生成中的現代性的研究。獨具特色,本文試對這一理論作一番系統解讀。
一、現代化的“自反”內涵
貝克提出的“自反現代化”理論的核心在于現代化的“自反”(reflexive)特性,理解“自反”內涵成為理解貝克理論的關鍵。關于“自反現代化”概念,貝克至少在兩處作了較為明晰的說明。在《自反性現代化》一書中貝克指出,“自反現代化應該指這樣的情形:工業社會的變化悄無聲息地在未經計劃的情況下,緊隨著正常的、自主的現代化過程而來,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完好無損,這種社會變化意味著現代性的激進化,這種激進化打破了工業社會的前提,并開辟了通向另一種現代化的道路。”[1]6在《風險社會》一書中,他寫到:“正如現代化消解了19世紀封建社會的結構并產生了工業社會一樣,今天的現代化正在消解工業社會,而另一種現代性則正在形成之中。”[2]3從這兩段話可以看出,貝克指出了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新特征,即“自反”特性,這種“自反”既是一種轉型機制,又是一種轉型過程。
(一)作為轉型機制的“自反”
貝克眼中的這種“自反現代化”轉型非常獨特:它“(首先)指自我對抗(self-confrontation)。現代化……的過渡是不受歡迎的、看不見的、強制性的,它緊緊跟隨在現代化的自主動力之后,采用的是隱性副作用的模式。”[1]9這段話集中反映了“自反”獨特的轉型機制:(1)轉型的動力。貝克指出,“現代化利用自主的現代化的力量挖了現代化的墻角”[1]224,現代化轉型的力量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自身,進一步說,是源于自身的激進化②貝克認為他的這一觀點不能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是其自身掘墓人”的觀點等同,在他看來,馬克思筆下資本主義轉型的動力是資本主義的危機以及階級斗爭,而他認為的現代社會轉型的動力是資本主義勝利的成果以及非暴力的進一步的現代化。。(2)轉型的方式。與上述的自我動力相聯系,因為是“自挖墻角”,所以是在不易被察覺、在意料之外的情況下發生的,以一種看不見的方式進行,貝克稱之為“隱性副作用”①貝克和吉登斯、拉什在《自反性現代化》一書中一起提出了相近的概念,即“reflexive modernization”,但理解各有側重。前者主要強調“自反”,即在不被察覺下的自我消解、自我對抗,貝克也稱為“隱性副作用”;而后二者則主要強調“反思”,即在認知層面上的自我反思。。(3)轉型的后果。現代化在經過上述一番不可思議的“自我對抗”后,產生了一系列自身的后果,這種后果體現在后文要討論的“個體化”對工業社會制度的消解和現代風險對科學技術的消解中。
(二)作為轉型過程的“自反”
“自反現代化”也是貝克對現代化轉型過程的一種判定。(1)進程的界定。與后現代主義者不同,貝克認為當前社會并不是對現代化的背離而進入另一個時代,它仍然在現代化軌道上運行。貝克指出:“我們正在見證的不是現代性的終結,而是現代性的開端——這是一種超越了古典工業設計的現代性。”[2]3正因為如此,貝克又將自反現代化稱為“再現代化”和“第二次現代化”。(2)特征的雙重性。轉型的自反現代化意味著新舊重疊的兩重性,一方面舊式的工業現代性正在被消解,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另一方面,新的現代性正在形成之中,尚未定型,新舊因素同時并存。(3)預示著現代性的重建。進行中的第二次現代化暗示著一種現代性重建的努力,表現為一種應對,乃至一種超越。在這一點上,貝克與另一位社會學家吉登斯達成了一致,“吉登斯和貝克承認現代社會已達到了極限。但他們認為現代工程并沒有陷落,它只是變得激進化并得以重建。”[3]232
二、工業社會模式的“自反”:加速中的“個體化”社會
貝克指出,“自反現代化”體現在一種“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的社會生活狀況中。吊詭的是,這種“個體化”在工業社會內部生成,現在,它又轉而動搖著工業社會傳統生活模式的根基——工業社會正在進行著一場“自反”。
(一)自反的動力:制度化的個體化
貝克對于當代“個體化”現象的理解,既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個體概念,也不同于個性化和個體互不依賴的觀點,也與18、19世紀作為資產階級反抗封建統治的形式出現的個體化現象相區別。他提出了“制度化的個體化”概念,認為“個體化”現象是工業社會制度造成的,而促成這種現象的直接“馬達”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化的勞動力市場。他進一步指出,與勞動力市場相關的三個因素加速了“個體化”進程。(1)教育。教育的時間在延長,對教育的重視重塑了傳統的目標取向、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求人們有向上流動的預期,“學校和大學的正規教育為個人提供了資格證書,使他們能夠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個體化的職業機會。”[4]38(2)流動。勞動力市場通過職業流動、居住地變動、雇傭關系變動及其初始位置的變動,使人們獨立于傳統的行事方式,成為個體化的動力源。“由于獨立于傳統的紐帶,人們的生活有了新的特征,這第一次使個人命運體驗成為可能。”[4]38(3)競爭。勞動力市場迫使人們為自己做宣傳,不斷增長的競爭壓力加速了個體化。盡管人們可能有共同的競爭資源(如相似的教育、經歷與知識),但這種共同體已在相互競爭中被削弱,競爭“導致同質性社會群體中個體的相互隔離。”[4]38
(二)自反的后果:“個體化”對工業社會模式的消解
“個體化”在加速進行,它反過來消解造就它的工業社會的“參數”,正如貝克所言,“‘教育擴張’政策最初并無意瓦解家庭,也無意使勞動市場靈活化”[5]71,這種政策的后果是非預期的。貝克認為,這種非預期的自我消解突出表現在:(1)階級的消解。在階級社會中,雇員必須受制于勞動法以及社會政治范疇的相關規定。但在當前轉型期,社會認同、社會不平等、社會沖突等問題已經脫離了傳統范疇,而必須在個體意義上加以理解,我們正通向一個“雇員的個體化社會”。(2)社會文化的轉變。與遵循特定軌道的階級文化不同,個體化帶來一種“自我文化”,它不再以階級為根基,而是崇尚一種“為自己而活”的文化。這“意味著標準化的人生軌跡成為一種可選擇的人生,人們可以選擇‘隨自己意愿而過的人生’、充滿風險的人生、破碎的人生等。”[4]28(3)生活的全球化。人們的生活開始跨出國界,這是一種生活軌跡的全球化,一種旅行生活和跨國生活。(4)個體能動性增強。個體化意味著個人越來越掙脫集體生活的束縛,人們為了生存要迫使自己去思考、行動,在這個意義上,個體的能動性和反思能力得到增強。(5)家庭領域的變化。一方面是女性角色的變化。婦女生活處在從“為他人而活”邁向“一點屬于自己的生活”的矛盾進程中,其前景既飽含機會又充滿風險。另一方面是家庭模式的變化。家庭由基于團結的義務而結合在一起的“需要共同體”,正在變成一種基于個人生活設計邏輯的“選擇關系”。如跨國跨文化的夫妻組成的文化多元家庭,就意味著一種個體的聯合。
(三)自反的應對:自我發明和社會再造
貝克指出,指向一種“自主人生”的個體化具有雙重面孔,體現為“不確定的自由”。“機會、危險和人生的種種不確定因素,此前已經在家庭紐帶和村莊共同體中被事先規定好了,或是被社會等級或階級規則事先規定好了,如今卻必須被個體本身所感知、解釋、決定和處理。”[4]5思考、計算、計劃、適應、協商、定義、取消,這些都是“不確定的自由”的要求,它正在掌控著生活。換句話說,我們雖然更自由了,但個人生活卻變得難以適從。如何應對這種個體化社會的不確定性?貝克指出,可能的四條社會重新整合道路——民族主義的復歸、超驗共識基礎上的價值整合、建立在共同物質利益上的整合、國族意識——并不可行,他認為至少還有另外一種整合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的前提是“首先必須對這種狀況(個體化——筆者注)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其次,人們在面對生命中的重要挑戰(失業、自然災害等)時必須能夠被成功動員與激發。”[4]21在此基礎上,“在舊有的社會性正在‘蒸發’的地方,必須對社會進行再造。”[4]21-22這種再造如何實現?貝克從科尼格那里受到啟發,認為“如果說這種社會還可能整合,那就只能憑借其自我解釋、自我觀察、自我發現、自我開放來完成,即通過自我發明來完成。”[4]22而社會自身的開拓能力和創造能力是衡量其整合度的標尺。當然,貝克認為這種自我發明只是一種可能,成功還未有定數。
三、科學技術的自反:形成中的風險社會
在貝克那里,“自反現代化”也體現在不斷呈現的現代風險中。科學技術的成功已經使得自己不再可靠,原先被遮蔽的風險開始凸顯,科學開始了一邊解決風險又一邊制造風險的歷程,風險社會正在形成。現代社會風險是科學發展的產物,卻與科學的預設——確定性、進步性背道而馳,科學開始陷入自我對抗的矛盾之中。
(一)自反的動力:科學制造風險
貝克認為現代社會充滿了風險,而這種風險根源于科技。“在發達的現代性中,財富的生產系統地伴隨著風險的生產。相應地,與短缺社會的分配有關的問題和沖突,同科技發展所產生的風險的生產、界定、分配所引起的問題和沖突,相互重疊。”[2]15貝克將科學產生風險的邏輯歸納為兩個階段:(1)初級科學化階段。這一階段科學的發展邏輯“依賴于一種被截削的科學化,在其中,對知識和啟蒙的科學理性吁求仍舊排除了科學懷疑論的自我應用。”[2]190人們對科學信仰不疑,“人們遭受的疾病、危機和遭難”被歸因為“野蠻的不可理喻的自然和牢不可破的傳統的強制”[2]195,而很難被歸因為科學,從而使科學免遭批判,進而使其超穩定地發展,而錯誤和風險卻正在悄無聲息地生成、積累。(2)自反科學化階段。但是,隨著科學的成功,風險越來越暴露,科學不得不接受外來批判和進行自我批判,科學進入自反科學化階段,其邏輯是“基于一種完全的科學化,它同樣將科學懷疑論擴展到科學自身的固有基礎和外在結果上。”[2]190于是科學的自我反思開始了,“科學自身是它們要去加以分析和解決的現實和問題的產物和生產者。以這種方式,科學不僅被當作一種處理問題的源泉,而且是一種造成問題的原因。”[2]191一方面,面對風險,只有科學能去解決,這種解決推動了科學自身的發展;另一方面,科學又是造成風險的始作俑者,其越發展,制造的風險越多,從而形成了“風險推動科技,科技產生風險”的不斷循環。
(二)自反的后果:現代風險對科學預設的消解
科學產生的現代風險意味著危險的不確定性,這無疑是對科學預設的進步性、確定性的自反。這種自反可以從貝克對風險的分析中得到進一步說明,突出表現在:(1)風險的不確定性。風險“使這個行星上所有的生命形式處于危險之中。標準的計算基礎——事故、保險和醫療保障的概念等等——并不適合這些現代威脅的基本維度。”[2]19換句話說,風險產生的后果是不可計算的,因此也是無法預料的、不確定的。(2)風險數量的無限性。“饑餓和需要都可以滿足,但文明的風險是需求的無底洞。它們無法滿足,是無限的和自我再生的。”[2]21(3)風險的災害性。風險不僅是一種生態威脅,也是一種社會威脅。它不僅帶來關于自然和人類健康的問題,還帶來市場崩潰、資本貶值等嚴重的社會、政治、經濟后果,“風險社會是一個災難社會。”[2]22(4)風險范圍的全球化。風險具有全球蔓延的特征。“9.11”事件后貝克指出,“全球風險社會的新涵義依賴于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運用我們的文明的決策,我們可以導致全球性后果,而這種全球性后果可以觸發一系列問題和一連串的風險。”[6]72風險越是增多、越具災難性、越是擴散,其不確定性也越加呈現出來,對科學預設的消解也就越是深入。風險社會形成的過程就是科學自反的過程。
(三)自反的超越:亞政治和生態民主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通過“自反”,科學產生的全球風險越來越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如何超越風險社會?貝克提出了兩個方案:(1)現實性超越——亞政治。隨著風險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到,這種風險意識激發了一種政治上的爆發力。“在哪里現代化風險被承認……在哪里風險就發展出一種難以置信的政 治 動 力 。”[7]93貝 克 稱 這 種 新 型 政 治 為“ 亞 政 治(sub-politics)”,它與傳統的議會政治相比有兩個特征:一是直接性。即“特有的對政治決策的個人參與,繞過代表性的意見形成的機構(政黨、議會)。”[7]50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社會政治力量。二是全球傾向。“其‘全球性’無論在社會方面,還是在道德或意識形態方面并不排斥任何人或者任何事。”[7]51這是一種“無敵政治”。貝克認為綠色和平組織就是一種“亞政治”形式,該組織成功地使殼牌公司將它的廢棄石油裝置在陸地上處置,而不是在海里。(2)規制性超越——生態民主。貝克認為,工業社會制造了一種技術專家政治,這是“一種‘刪節’的民主,其中社會的技術變遷問題是政治議會決策永遠束手無策的。”[7]91也就是說,技術專家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人們對技術的倫理訴求難以奏效,風險難以制止。對此貝克提出,我們需要一種擴展協商機制的“生態民主”,對科學的擴張起到真正的規制。一方面,要實行權力劃分,即解除科學對自身的壟斷權威,實現“危險制造者和危險評估者之間權力的分離”[7]91;另一方面,創造可以對科學進行討論的公共領域,“只有一場強有力的、充分的、用科學的論據‘武裝’起來的公眾討論,才能夠將科學的麥粒從糠殼中脫出。”[7]92
四、結 論
作為一種社會轉型理論,貝克的“自反現代化”論以“自反”為邏輯起點,對當代社會的新變化進行了精辟分析,向我們揭示了一種時代特質,即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與產生它的確定性進行著對抗。這種自我對抗在“個體化”中表現為一種“不確定的自由”,在“風險社會”中表現為難以預測的現代風險。
[1]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M].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2]烏爾里希·貝克,安東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M].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3]尼格爾·多德.社會理論與現代性[M].陶傳進,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4]烏爾里希·貝克,伊利莎白·貝克-格恩斯海姆.個體化[M].李榮山,范譞,張惠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烏爾里希·貝克,約翰內斯·威爾姆斯.自由與資本主義[M].路國林,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6]烏爾里希·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風險社會[J].王武龍,編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2).
[7]烏爾里希·貝克.世界風險社會[M].吳英姿,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