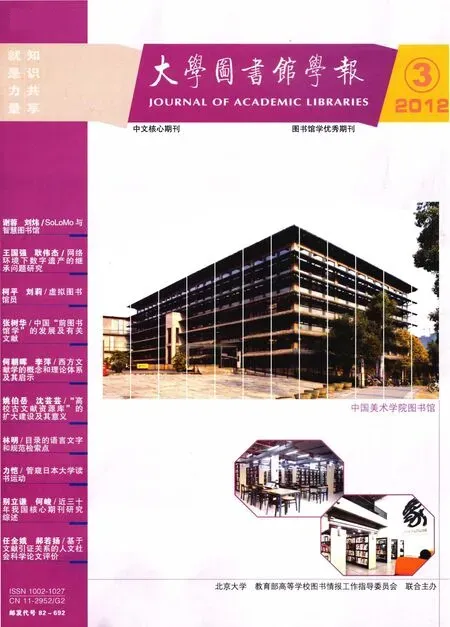中國“前圖書館學”的發展及有關文獻
□張樹華
中國的圖書館學誕生于20世紀初期。但中國的藏書事業卻有悠久的歷史。遠在周朝,我國就有藏書工作的記載。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老子曾為“守藏室之史”。說明遠在周朝,就有專門的藏書機構——“藏室”和專門管理藏書的“史官”。經過歷朝歷代,我國的藏書事業不斷發展,書籍越積越多。有了這么多的圖書,就必須加以整理,使之系統化。于是有關整理圖書的知識發展為“目錄學”,有關鑒定圖書的知識發展為“版本學”、“校勘學”。公私藏書家有關圖書的訪求、整理、庋藏、保管、管理及利用的知識和理論也日益增長,并日趨完善。這些知識和理論可以說是中國圖書館學的一部分,我稱之為“前圖書館學”。
中國的“前圖書館學”經歷了從“圖書整理理論”到“藏書管理理論”的發展過程。這是因為:圖書積累到一定程度后,人們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將大批雜亂無章的圖書,整理成有序化的圖書體系。所以圖書整理工作以及在整理工作中逐漸積累起來的知識和理論——“圖書整理理論”,就成為中國“前圖書館學”的初期理論體系。其代表作主要有:《漢書·藝文志》序、《隋書·經籍志》總序、《通志·藝文略》和《通志·校讎略》以及《校讎通義》等。
隨著雕版印刷的推廣和應用,刻書事業逐漸繁榮。書籍的增多,使得隋、唐以后我國的藏書事業日益發達。宮廷藏書和官府藏書經過各朝代的建設,至宋朝歷時一千多年,已日臻完善,逐漸建立起一整套管理藏書的組織機構、人員設置及工作制度等。私人藏書也日益發展起來,一些大的私人藏書家收藏的各種珍貴書籍往往達幾萬、十幾萬卷。例如,北宋的宋敏求,家藏書籍3萬卷。南宋的葉夢得,有人說他的藏書達10萬卷。此外,書院藏書也日益發展。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均有規模較大的藏書。皇帝及官府時常賜與書院各種官刻書籍,使其藏書量不斷增加。據《鶴山書院始末記》記載,鶴山書院藏書達10萬卷。
不同類型藏書樓的發展,使得唐、宋以后的藏書工作逐漸成為一種社會事業。而“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術愈精”(見《古今典籍聚散考》第3卷第2章)。伴隨著藏書事業的發展,有關藏書的訪求、入藏、分類、編目、庋藏、保管、建筑、設備以及繼承、傳播等“措理之術”的理論和實踐也日益充實。于是,出現了一批以公、私藏書樓的整體管理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逐漸形成了“藏書管理理論”。其代表著作有:①反映官府藏書制度和管理體制的《麟臺故事》、《南宋館閣錄》、《南宋館閣續錄》等;②反映私人藏書管理經驗和理論的《澹生堂藏書約》、《藏書記要》、《流通古書約》、《古歡社約》等。下面分別述之。
1 有關“圖書整理理論”的著作
我國歷史上歷代王朝都有聚書、整書的措施,其中規模較大的整理圖書活動有三次,即漢朝、唐朝和清朝。每次大規模地整理圖書,其結果不僅是編成某一個歷史時期的圖書目錄,而且也使圖書整理的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所發展、有所前進,從而使“圖書整理理論”日益充實,不斷完善。
1.1 《漢書·藝文志》序,(漢)班固撰[1]
自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宮廷藏書日漸增多。至漢成帝,“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于是,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下詔,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校訂完一種書,劉向就寫一篇提要。提要的內容包括:
①將經過整理、校定的每一種書,著錄其書名及篇目。
②敘述校讎的經過。將版本的異同、篇數的多少、文字之訛謬、簡策之脫略、書名之異稱、校書人的姓名等,均予著錄,使讀者了解該書的編校經過。
③介紹著者的生平、學術思想及時代背景。
④敘述全書大意,說明書名的含義、著書的原委及該書的性質。
⑤辨別書的真偽。
⑥評論該書的學術思想或史實的是非。
⑦敘述學術源流。
⑧判定該書的學術價值。
將上述八方面的敘述和評論,合為一篇文字,這就是一書的“敘錄”。劉向把這些“敘錄”匯編起來,遂成為《別錄》(別集眾錄,而成《別錄》)。所以劉向所做的工作就是整理圖書和編制目錄,其最后成果就是匯編成一部反映每種圖書的思想內容、著者事跡、評論一書的學術源流和價值的提要目錄——《別錄》。
劉向死后,其子劉歆根據當時所存圖書的情況及當時學術發展的情況,將各種圖書分為七大類(七略),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每大類下,又分若干小類(稱為“種”),共計38小類(38種)。劉歆所擬定的這個分類體系,每一大類有“大序”,每一小類有“小序”,講述每個學術范疇內的學術源流。所以劉歆所做的工作就是圖書分類。他首先編制了一個七大類、38小類的分類表,其次,將各種圖書分別歸入有關的類目中去,從而形成了一套分類目錄。
劉向、劉歆所編寫的“別錄”、“七略”,是我國最早的整理圖書的經驗和知識的總結。它的成就在于:
①它以詳細的著錄、科學的評論、嚴密的結構和系統化的體系,提供了我國漢代一套分類提要目錄。
②開創了圖書編目和圖書分類的實踐和理論知識,對后世整理圖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③積累了大規模整理圖書的工作組織、工作程序和技術方法等方面的經驗。
④通過分類體系、分類表中的大序、小序以及對每一種書的學術評價,反映出當時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流派,將圖書史、學術思想史和科學技術史結合為一體,成為后人閱讀古代文化典籍、研究古代學術思想發展的指南。
“別錄”、“七略”早已失傳,但“七略”分類體系、分類目錄及對各大類、小類所作的“大序”、“小序”,被班固收錄在《漢書·藝文志》中,使我們從中可以得知它的原貌。
班固根據“七略”編撰《漢書·藝文志》時,作了“刪其要,以備篇籍”的工作。他所作的刪取工作主要有:
①把“七略”中的六略(除去輯略),38種的分類體系和各類中所著錄的圖書,基本上按照原樣保留下來。在凡有刪改、移易和補充的地方,都在“自注”中加以說明。
②把“輯略”的內容分散附于六略和38種的后邊,成為對各大類和小類的學術源流的說明。
③把“七略”中對圖書的簡單提要,進行了必要的節取,作為《藝文志》的自注。
④增加了“七略”編成以后新出版的一些圖書。所以班固編成的《漢書·藝文志》,反映了整個漢代藏書之盛況。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的“序”中,除對先秦學術思想的流派演變作了簡要的敘述外,還對劉向、劉歆整理圖書的工作情況、組織情況以及編寫敘錄、制訂分類體系等方面,作了扼要的總結和概括,為我國后世的圖書整理理論奠定了基礎。
1.2 《隋書·經籍志》總序,(唐)魏征撰[2]
《隋書·經籍志》是唐朝魏征做秘書監兼領五代史纂修職務時(629~634年間)編纂成的。魏征運用了班固依“七略”改編《漢書·藝文志》的方法,以隋代官府藏書的目錄《隋大業正御書目錄》(9卷)為底本,參考了唐初秘書監所整理的《隋代遺書目錄》而編成此書。《隋書·經籍志》總序云:“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并刪去之。其舊錄所遺,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這里所說的舊錄即指《隋大業正御書目錄》,《隋書·經籍志》用遺書目錄作為“刪去”和“附入”的參考,遺書目錄即指唐秘書監所編的《隋代遺書目錄》。編制成為“分為四部,合條為14466部,89666卷”的目錄。《隋書·經籍志》與《漢書·藝文志》的區別是:漢志僅記錄漢朝一代的藏書情況,而隋志除記錄隋代的藏書情況外,還記錄了六朝時圖書流傳的情況。它以隋代現存書為主,對六朝時曾經流傳的圖書,用“梁有……今無”作注解,并將“梁有”的圖書列于相應的類目之下,這樣就能使后人了解到六朝時曾經流傳的圖書了。
在圖書分類體系上,《隋書·經籍志》沿用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發展起來的四部分類法,并正式命名四部為經、史、子、集。《隋書·經籍志》仿“七略”的做法,有總序、每大類有大序、小類有小序,對各個部類與學術發展史的關系,各部類內圖書的沿革、內容和意義,都作了歷史的分析和理論上的闡述。
《隋書·經籍志》總序中,對隋代及以前歷代官方收集圖書、整理藏書以及書籍聚散等情況,進行了系統的論述,是對我國隋代及以前圖書整理工作的發展和沿革所作的全面性的總結和系統的分析,在我國古代目錄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后代“圖書整理理論”的發展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3 《通志·校讎略》、《通志·藝文略》,(宋)鄭樵撰[3]
《通志·校讎略》和《通志·藝文略》是宋代鄭樵所著。鄭樵生于1104年(宋徽宗崇寧三年),死于1162年(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是宋朝著名的史學家、目錄學家。他一生寫了84種著作,《通志》是他寫的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通志》共計200卷,包括:帝紀;皇后列傳、諸臣列傳;年譜及略四部分。其中的“略”又有20種,是鄭樵學術思想的精華。《校讎略》、《藝文略》兩略將歷代搜集圖書、整理圖書的經驗進行了理論上的概括,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通志·藝文略》不是紀一代藏書之盛,而是“紀百代之有無”、“廣古今而無遺”。在“紀百代之有無”時,采取了“詳今略古”的原則。他認為“漢晉之書最為希闊,故稍略;隋唐之書于今為近,故差詳;崇文四庫及民間之藏,乃近代之書,所當一一載也。”在《藝文略》中共著錄了圖書10912部,110972卷,所著錄圖書數量比宋代以前各家目錄都多出許多。
鄭樵十分重視圖書分類工作,他對圖書分類的意義、作用、原則等,在理論上提出了許多前人所未有的見解。在實踐上,他在《藝文略》中采用了“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種”,具有三級類目的一個圖書分類體系。他認為,圖書分類“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他認為,分類的目的在于“使之上有源流,下有沿襲”,“使學者亦易學,求者亦易求”。為此,他說:“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因此,“欲明書者,在于明類例。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所以他明確指出圖書分類的最主要的意義在于明確學術源流,“觀其書可知其學之源流”。通過明確學術源流,幫助人們辨別一書的內容、性質、學術價值等,并便于人們去“因類求書”方便查找和檢索圖書。
在圖書編目方面,他提出“通錄古今”和“通錄圖、書之有無”的主張。鄭樵認為,不僅要著錄現存的圖書,也要著錄亡佚的圖書。這樣,該書即或散失或亡佚,但由于在目錄中保留著書名,則“雖有亡而不亡者”,“名亡而實不亡者”,可為后世求書和考察學術源流提供依據。在著錄圖書時,他認為應通錄“圖”和“書”之有無。他說:“圖經也,書緯也。”“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影;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故應對一部書的“圖”和“書”都要著錄。
在圖書搜集方面,鄭樵總結了前人搜集、訪求圖書的經驗,概括為“求書八道”。即:即類以求,旁類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他搜集圖書的經驗概括為一點,即“求”。
鄭樵將我國自漢朝至宋朝一千多年間有關整理圖書的工作進一步作了理論上的總結和概括,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和觀點,把我國“圖書整理理論”的學術水平提高到一個新階段。
1.4 《校讎通義》,(清)章學誠撰[4]
《校讎通義》是清代章學誠撰寫的。章學誠(1738—1801年)字實齋,號少巖,浙江會稽人。他在《校讎通義》一書中,繼承并發揚了鄭樵的理論和方法,使“圖書整理理論”得到進一步發展。
在圖書分類方面,章學誠認為圖書分類的主要作用在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他認為,圖書經過分類,可以“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可以說是章學誠的“圖書整理理論”的核心思想。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主要目的在于“欲人因類求書,因書究學”。也就是說,圖書分類是為了后人按類查找書籍,為研究學問提供源流和線索。
章學誠從客觀實際出發,認為分類體系應根據學術的變遷和書籍出版情況的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他說:“七略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己者也。”從這里也反映出章學誠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2 有關“藏書管理理論”的著作
2.1 反映官府“藏書管理理論”的著作
官府藏書自漢、唐至宋代,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雖然歷代官府藏書的規模不同,且更迭頻繁,但在管理上已逐漸形成一整套制度,對官府藏書的設置、性質、職能、任務、人員的配備、錄用及薪俸等均有規定。在這種形勢下,系統地總結官府藏書管理制度的書籍,至宋朝以后便陸續出現了。它們主要有:
(1)《麟臺故事》,(宋)程俱撰[5]
以藏書樓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并撰寫成書的早期專著就是程俱所寫的《麟臺故事》。
程俱,字致道,浙江衢州開化人。北宋時歷任編修《國朝會要》的檢閱官、著作佐郎等職務。紹興元年(1131年)任秘書省的秘書少監。這部書就是他任秘書少監時寫成的。
“麟臺”即指“秘書省”。“故事”是專輯一官、一人、一地或一事,在政治上或學術上起典范作用的一種文體。《麟臺故事》主要是記述宋朝初期宮廷中的三館(即史館、昭文館、集賢院)及秘閣的職能及各種典章制度的一部著作。程俱撰寫此書時,除根據他自己的所見所聞外,還參考了當時官府中的各種舊章。所以從該書中,“宋初館閣之事,典章文物,燦然可見”。該書系統地記述了宮廷館閣的沿革,各種職能,人員的配備、錄用及待遇,書籍的搜集、整理、校讎、儲藏,官方纂修各種類書、史書的職責等,是記述宮廷館閣的管理情況和管理制度的一本專著,它開創了我國“藏書管理理論”的先河。
《麟臺故事》全書分為12篇。每篇下按年月的先后編排史料,記述史實。這12篇是:官聯、選任、書籍、校讎、修纂、國史、沿革、省舍、儲藏、職掌、恩榮、祿廩。
官聯、選任、恩榮、祿廩4篇是記述館閣工作人員的設置、錄用、地位及待遇的。宋元豐年間官制改革以后,將崇文院改為秘書省。內設秘書監、少監各一人,丞二人,秘書郎二人,通掌省內各種事情;著作郎、佐郎各二人,專修日歷;校書郎四人、正字二人,負責校對、抄寫書籍。宋代擔任館閣職務的多為有學問的人,宋仁宗認為:“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故擔任館職者“必試而后命”。洪邁在《容齋隨筆》一書中說:“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后命。一徑此職,遂為名流。”說明當時館閣人員的錄用、任選條件比較嚴格。此外,館閣人員的地位、待遇也很高,程俱在本書中多次指出:“太宗皇帝待遇三館特厚。”“時三館之士固已異于常僚,其后簡用益高,故恩禮益異。以至治平、熙寧之間,公卿侍從莫不由此途出。”由此可見,三館人員不僅待遇高,地位也高。這是因為通過館閣工作,接觸大量書籍后,知識益豐,眼界益寬,所以館閣是培育人材的良好場所。難怪宋仁宗說:“館閣所以待俊賢。”宋英宗也說:“館職所以育俊材。”他們都把館閣作為培育人材之地。
書籍、校讎、修纂、國史、儲藏、職掌6篇是記述三館、秘閣的職責及工作內容的。三館、秘閣除具有搜集、訪求、編目、校勘、儲存書籍的職責外,還有編纂和刊刻書籍的任務。“修纂”一篇記載了宋代修纂的《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國朝會要》、《崇文總目》、《新唐書》等書的修纂過程及情況。“國史”一篇記載了編纂本朝的國史、會要、實錄、日歷等史書的情況。
省舍和沿革兩篇則記述了三館的建筑、歷史沿革及三館、秘閣所藏書籍、古畫、墨跡的情況。
須要指出:《麟臺故事》一書早已佚亡。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時,四庫史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9篇殘文,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上世紀20年代,發現《麟臺故事》6篇殘卷本,陸心源將兩個本子加以校訂,以6篇3卷本為底本,參校《永樂大典》本,編成全書4卷,附《補遺》1卷本,收在《十萬卷樓叢書》中。這個本子較接近原著,校勘也較精細。姚伯岳根據此本對該書作了點校工作(見《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徐雁、王燕均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98~161頁)。
(2)《南宋館閣錄》(又名《中興館閣錄》),陳骙撰寫[6]
大約在《麟臺故事》撰寫后四十年,南宋秘書監陳骙又寫成《南宋館閣錄》一書。該書是對南宋高宗建炎元年至孝宗淳熙四年(1127—1177年)這五十年間秘書省各項工作的總結和論述。
陳骙(1128—1203年),字叔進,宋臺州臨海人(今浙江),累任秘書省的秘書監。在他任職期間完成了兩部有關南宋前期館閣的著作:一部是《中興館閣書目》,是當時的官修書目,共分為52類,收錄圖書44486卷;另一部是《中興館閣錄》(即《南宋館閣錄》)。宋神宗“元豐改制”以后,館閣均并入秘書省,所以后來“館閣”一詞實際上成了秘書省的代稱。《南宋館閣錄》一書記錄了南宋館閣機構——秘書省的重建和發展情況。該書在結構和體例上均承襲了程俱的《麟臺故事》一書,但在具體篇卷劃分和撰述方式上有些新的特點。全書分為9篇:沿革、省舍、儲藏、修纂、撰述、故實、官聯、廩祿、職掌,分別對南宋秘書省的建制演變、遷徙分布、典藏修撰、職官任用和俸祿等級等,進行了系統的而詳細的總結和論述。李燾在“序”中評價此書曰:“凡物巨細,靡有脫遺,視程氏誠當且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認為該書“典故條格,纖悉畢備,亦一代文獻之藪之。”該書以史料翔實、論述細膩為特點。
(3)《南宋館閣續錄》(又名《中興館閣續錄》),撰寫人不詳
該書與《南宋館閣錄》在時間上銜接。記述了自孝宗淳熙五年至度宗咸淳五年(1178—1269年)九十余年間秘書省館閣工作的情況。該書亦分為9篇,與《南宋館閣錄》在體例上完全一致,即:沿革、省舍、儲藏、修纂、撰述、故實、官聯、廩祿、職掌,記述了南宋中、后期館閣的歷史發展、建筑結構、文獻收藏情況、官書的纂修、人員的設置及歷任館職人員的姓名、籍貫、官職等情況。全書的史實及論述亦十分詳盡。
上述三部書連貫地勾畫出整個宋代官府藏書機構的工作情況、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等,是研究宋代官府藏書事業的管理和文獻工作概況的珍貴著作,是宋代官方撰寫的有關“藏書管理理論”的代表作。但上述三部書的共同缺點是:情況描述多,史實羅列多,而理論論述較少。
2.2 反映私人“藏書管理理論”的著作
私人藏書經過宋元,至明、清兩代時更為發達。一些著名的私人藏書家,藏書數量達數萬卷,甚至十幾萬卷,而且多為珍稀版本。私人藏書家在畢生搜集、整理、保護藏書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有許多深刻的認識。他們將自己藏書的經驗加以整理,有些認識上升為理論,遂給后人留下了私人藏書家關于藏書管理的系統化的理論著作。主要有下列幾種著作:
《澹生堂藏書約》除前面有序言外,共分三部分,即:讀書訓、聚書訓和藏書訓。其中讀書、聚書二訓是抄集“古人聚書、讀書足為規訓”的事跡而成,故多為史料的輯錄。“藏書訓略”一節,則是密士老人自敘其平生購書、鑒書的經驗談,其中有許多獨到之處。
“藏書訓略”一節中,又分為“購書篇”和“鑒書篇”兩篇。
在“購書篇”中,他很推崇鄭樵提出的“求書八道”。在此基礎上,他又提出了購求圖書的三條主張,即:①“眼界欲寬”,是指對書籍要有廣泛的了解,要放開視野來認識人世間藏書的博大精深,即“曠然宇宙,自有大觀”,然后在此基礎上來從事聚書、購書的活動。②“精神欲注”,是指購求圖書要有專心致志的精神,要養成一種嗜書的職業特點。他認為:“古今絕世之技,專門之業,未有不同偏嗜而致者。”所以必須嗜書,奇書異本才能聚集起來。在聚書態度上要求有專注鉆研的精神。③“心思欲巧”,是指要多動腦筋,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去搜集、訪求圖書。他除了引用鄭樵的“求書八道”之外,又提供了三道,即:①輯佚(如果一書已亡佚,可從類書中輯錄出來);②分析(將一書的注釋析出,另成一書);③將各書中的“序”著錄成為一種目錄,可以了解各種書的出版情況及購求的地點、方向等)。他認為“古書有名存而實不傳者”,這種書“必不可致”;也有一些書“求之苦而得之艱者”,就需要“力求”和“苦購”;還有些書則可以隨時隨地購得。總之,在“購書篇”內,論述了書籍購求的要求、態度和方法等各方面,是對我國古代購求圖書理論和方法的全面總結。這些思想對今天購求和搜集文獻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2)《藏書記要》,(清)孫從添撰[7]
孫從添,字慶增,號石芝,江蘇常熟人。生于清康熙三十年(1692年),死于乾隆三十一年(1767年),是清朝的著名藏書家之一。他的藏書樓名為“上善堂”,藏書一萬余卷。
《藏書記要》一書分為購求、鑒別、抄錄、校讎、裝訂、編目、收藏、曝書8篇。其中鑒別、抄錄、校讎3篇偏重版本、校勘方面的論述,其他幾篇偏重藏書的管理。
在“購求”一篇中,他列舉了購求圖書的“六難”,認為購求圖書是最難事。但如能得到一本好書,又是最美、最樂的事。孫從添和祁承在購求圖書中,都突出一個“求”字,說明古人搜集藏書的指導思想在于有目的地“訪求”圖書。
在“編目”一篇中,他論述了藏書家應具備四種目錄:①按分類編排的總目錄;②宋、元刻本、抄本等稀有珍貴書籍的目錄;③分類書柜目錄(即典藏目錄);④書房架上書籍目錄及未訂、裝訂、補抄、批閱書籍的目錄(即書庫排架圖及待入藏目錄)。孫從添較全面地論述了私人藏書的目錄體系,這在我國“藏書管理理論”的書籍中還是第一次。
在裝訂、收藏、曝書3篇中,詳細地論述了藏書保護問題,可以說是我國古代一千多年有關藏書保護經驗的全面總結。在這3篇中,詳細地論述了書籍裝幀的要求;書庫的通風、防火、防潮、防蟲、防蟻等措施;書柜的用料、款式及牢固措施;曝書的程序及注意事項等。這些藏書保護措施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由于這部書的內容全面,論述細致、系統,所以譚卓垣在《清代圖書館發展史》一文中,對該書的評價是:“這本書是整個19世紀時代唯一的一本向私人藏書家交待圖書館學術的參考書。令人驚奇的是,他所提出的建議,一向為收藏家們所謹守不渝。直至今日,對現代的中國圖書館猶具有影響。”
如果說《澹生堂藏書約》、《藏書記要》是論述私人藏書的內部管理工作的理論和方法,那么《流通古書約》、《古歡社約》、《儒藏說》則是三部論述私人藏書的流通、傳抄、使用方面的理論著作。
我國古代公、私家藏書均重保存,很少流通使用。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文化的發展,至明朝以后,一些明智之士開始倡導流通圖書,提出將私人藏書公開的主張。
(3)《流通古書約》,(清)曹溶撰[8]
曹溶,字潔躬、秋岳,號倦圃,浙江秀水人。明崇禎十年進士,官至御史。1644年歸附清朝,歷任戶部侍郎等職。曹溶鑒于古代藏書往往遭受兵災火厄而散失、焚毀,使“其書十不存四五”。又鑒于珍貴書籍“一歸藏書家,無不綈綿為衣,旃檀作室,扃鑰以為常”。而“稍不致慎,形蹤永絕,只以空名掛目錄中”。所以他提出“流通古書”的主張。他提出:藏書家們的職責不僅在于保存,更重要的在于流通,以使古人竭一生辛苦所著之書,不致因秘藏而湮滅。曹溶提出的圖書流通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有無相易,精工繕寫”;另一種是“出未經刊布者,壽之棗梨”,將稀有的古籍付之版刻。曹溶提出的流通古書就是用傳抄和出版兩種辦法,使古書沖出原有藏書家的“秘藏”,得到傳播、擴大。他的主張對后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據說當時的藏書家“皆謂書流通而無藏匿不返之患,法最便”(見《絳云樓書目題辭》)。而清代藏書家也認為此約“為流通古書創一良法,藏書家能守此法,則單刻為千百化身,可以不致湮滅,尤為善計”(見繆荃蓀《流通古書約》跋)。
(4)《古歡社約》,(清)丁雄飛撰[9]
丁雄飛,字菡生、璽孫,江蘇江浦人,是清初知名的藏書家,其藏室名“心太平庵”,平生編著90多種著作。他與同代著名藏出家黃虞稷互訂協約。黃虞稷,字俞邰,號楮園,福建晉江人,僑居上元。康熙十八年(1679年)被舉為博學鴻儒,以母喪不試。后被薦召,入翰林院,先后纂修《明史·列傳》、《明史·藝文志》和《大清一統志》等書。丁雄飛與黃虞稷二人互訂的協約內容是:“每月十三日,丁至黃(家),二十六日,黃至丁(家)。盡一日之陰,探千古之秘。或彼藏我缺,或彼缺我藏,互相質證,當有發明。”并互訂借書條約:“借書不得逾半月”。“還書不得托人轉致”(見《古歡社約》)。
《流通古書約》和《古歡社約》的作用在于號召藏書家打破“秘不示人”的陳規,將書籍由私人秘藏,經過傳抄與刊刻,使之流通傳播。他們所講的“流通圖書”與現代圖書館所講的“流通圖書”的含義有很大不同。他們所倡導的流通圖書只不過是將私人藏書公開,允許別人觀看、傳抄或出版而已。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思想和見解還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5)《儒藏說》,(清)周永年撰[10]
周永年,字書昌,晚號林汲老人,山東歷城人。清乾隆年間進士(1771年),被徵為翰林,曾參加過四庫全書的修纂工作。
周永年在《儒藏說》中提出了“公開使用藏書”的思想。他認為“公開藏書”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使貧寒士子得到看書的機會,是培養人材的好辦法。他說:“窮鄉僻壤,寒門窶士,往往負超群之資,抱好古之心,欲購書而無從。”如果千里之內,有“儒藏”數處,讓這些異敏之士前來看書,則“數年之內,可略窺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豈不事半而功倍哉”。另一好處是公開藏書是保全書籍的重要途徑。他說:“蓋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長據,公之而不能久存者。”如果能將私人藏書公開,那么“古人著述之可傳者,自今永無散失,以與天下萬世共讀之。”
周永年在《儒藏說》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思想:一是變“一家之藏”為四方之士“共讀之藏”;一是所藏書籍四方異敏之士皆可來讀。他的這些思想中孕育著初期公共使用藏書的思想。周永年的這些思想可以說是對歷代藏書家的一次大膽挑戰,在我國藏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并為后世圖書館的公共使用藏書,作了早期輿論準備工作。
藏書公開與藏書的公共使用理論是“藏書管理理論”的另一個側面,它使“藏書管理理論”的內容更加充實,體系更加全面。
從“圖書整理理論”到“藏書管理理論”各種著作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前圖書館學”的發展和進步的歷程。
上述這些見解和理論,也為我國近代圖書館學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1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55:序
2 長孫無忌等撰.隋書經籍志 新1版.北京:中華書局,1985:總序
3 鄭樵撰.通志 影印版.北京:中華書局,1987
4 章學誠撰;王重民注.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程俱撰.麟臺故事.上海:上海書店,1984
6 陳骙撰.南宋館閣錄,中興館閣錄.北京:中華書局,1998
8 曹溶撰.流通古書約.見:楊守敬著.藏書絕句.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9 丁雄飛撰.古歡社約.見:楊守敬著.藏書絕句.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10 周永年撰.儒藏說.見:胡應麟等撰;王嵐,陳曉蘭點校.經籍會通 外四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