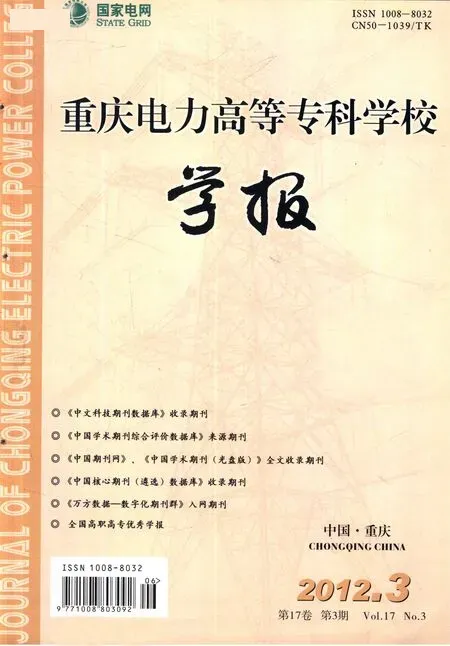傳統(tǒng)儒學(xué)主體人格思想與西方主體性原則的異同比較
楊智慧
(重慶外國語學(xué)校,重慶400039)
國內(nèi)有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儒學(xué)人學(xué)體系中所蘊(yùn)含的主體人格化的思維方式,與西方哲學(xué)的主體性原則思想如出一轍。而事實上,二者在思維路徑上并非完全等同,因為中國古代哲學(xué)中并無“主體性”一詞,只是傳統(tǒng)儒家強(qiáng)調(diào)的識理之“心”與西方“主體性”的基本思維有著一定的共性。在西方哲學(xué),特別是在德國古典哲學(xué)中,“主體性”一詞主要是指獨(dú)立自主,自我決定,以個人自由意志和才能為根據(jù)等等含義。人的主體思維影響著世界的變遷,雖然前者并非后者發(fā)展的根基,但其價值取向卻在意義世界中改變著后者所存在的意義和方式。
1 西方主體性思想的發(fā)展
作為一種改變時代的思維方式,主體性原則有著其深厚的歷史背景。古代希臘是西方哲學(xué)和科學(xué)的搖籃,哲學(xué)的主體性原則亦開始于此。歷史總是在不斷循環(huán)中演進(jìn),最后找到理想的歸屬和定位。西方哲學(xué)由古希臘階段經(jīng)中世紀(jì)到近代的演繹,可解讀為人類精神由素樸的主體意識在異化為對象意識之后重新回到主體意識的過程。
古希臘哲學(xué)的素樸性首先表現(xiàn)在尚未注意到主體與客觀的對立。和中國先秦哲學(xué)將天和人看為一體一樣,他們將人和自然,主體與客觀視作一體。這時候的哲學(xué)家們把世界的存在當(dāng)作自然而然的前提,并沒想到對世界的存在提出疑問,對人能否認(rèn)識世界即人的認(rèn)識能力問題,沒有作為一個專門問題來進(jìn)行思考。中世紀(jì)哲學(xué)中宗教與世俗的對立,窒息了人的精神和人的主體性。不過也正是神的無上權(quán)威,使得人們有勇氣為自己提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主體性也才獲得完全意義。而擔(dān)此重任的始作俑者便是文藝復(fù)興運(yùn)動。文藝復(fù)興回歸人性,強(qiáng)調(diào)了對自我的價值關(guān)懷,主體性哲學(xué)大門由此打開。18世紀(jì)末19世紀(jì)初,德國唯心主義哲學(xué)家們再一次為維護(hù)人的主體性而斗爭。世界的本質(zhì)從遙遠(yuǎn)的自然理性回到了人自身,回到了思維著的主體精神,主客的一體化再次凸顯。從西方哲學(xué)史角度看,主體性意識的獲得,標(biāo)志著兩千多年西方傳統(tǒng)哲學(xué)發(fā)展過程的真正開始。
綜上所述,西方主體性原則的形成,經(jīng)歷了主客渾然一體到主客分離,最后回到主客對立統(tǒng)一的過程。
2 中國哲學(xué)史上主體人格的演繹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在傳統(tǒng)中國哲學(xué)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主體性概念,但其對人的主體作用的重視,卻同樣是經(jīng)歷了一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huán)過程。
在先秦以前原始宗教盛行,“天”以無比的權(quán)威籠罩著萬物生靈。那時天與人與萬物渾然一體,而在這一體中天命神權(quán)代表著一切,人們對“天”只有敬畏和恐懼,毫無自我意識。
從先秦開始,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對天神的權(quán)威表示懷疑,把目光從對天的關(guān)注轉(zhuǎn)向?qū)θ说年P(guān)注。對人自身的價值的反省,便構(gòu)成儒家人學(xué)體系的邏輯起點(diǎn)。這種反省一開始就關(guān)聯(lián)著天人關(guān)系,包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早在2000多年前春秋時期,鄭國大夫子產(chǎn)就指出:“天道遠(yuǎn),人道彌,非所及也。”此思想雖極其簡單樸素,但也表明子產(chǎn)對人的作用和價值充分重視和肯定,成為人的主體精神的最早追問與呼喚。之后,孔子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不是從天神那里尋求神道,而是從人自身尋求人道,這顯然也是對人的重視。孔子雖然提出人道,卻又有很多束縛主體言行的限制理論,而且在他的人學(xué)體系中,產(chǎn)生一種新的絕對控制,那就是克己復(fù)禮。孔子的“克己復(fù)禮”人性論成為幾千年封建社會束縛個性自由的倫理依據(jù)。與此相反,老子則成為中國哲學(xué)史上最早明確將人的主體地位提升到與天地并肩的思想家。“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城中有四大,而人具一焉。”老子哲學(xué)中明顯可見“主體人格”的閃光,但閃光畢竟不是全部,主體人格思想仍未得到全面展開。繼之,荀子重天人之分,人主宰著自然。荀子主張涂之人可以為禹,肯定人有價值自覺的主體能動,其“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更是把主體的能動意識推向新階段,充分體現(xiàn)著宇宙生命的精神,在宇宙中打上主體道德的烙印。
亞圣孟子從多層次、多側(cè)面地探討了個體在物質(zhì)生活、精神生活過程中的情感和意志,突出強(qiáng)調(diào)了個體情感和意志的力量。社會是由單個人組成的,要維護(hù)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當(dāng)然首先應(yīng)該在人們內(nèi)心奠定一種尊重秩序、承認(rèn)價值的意愿,這種“意愿”是指克制個人過分情欲,遵守彝倫規(guī)則的“善”。孟子提出“人與天地參”,“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成,樂莫大焉”。“萬物皆備于我”反映了孟子所言主體自我的“心”與性、天、命的關(guān)系。人人只要自覺遵從那天賦的良知良能,盡了自己作為人的本性,就圓滿地實現(xiàn)了“天”所給予生命的意義,也就達(dá)到了人生的終極境界。在此意義上“天地萬物皆備于我”,實際上體現(xiàn)了儒家認(rèn)識論與倫理觀的一致性。
然而,盡管孟子充分發(fā)揮人的主體能動作用,剔除了天命的神秘形式,但在正統(tǒng)儒學(xué)中,天命仍然被界定為一種超驗的力量,因而主體性仍受到壓制,而這種壓制則在漢代董仲舒“天人感應(yīng)”學(xué)說籠罩下表現(xiàn)得更徹底。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數(shù)”,“天人相類”,以天人感應(yīng)為基礎(chǔ),用神權(quán)和君權(quán)壓制人權(quán),壓制人的主體性。
漢代的神權(quán)束縛使人們在狹縫中呼吸,文人志士們欲沖破名教的壓抑,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充分地張揚(yáng)了人的主體精神,注重個體人格的發(fā)展,注重人對宇宙的重要作用。但是到魏晉時期,特別是隋唐中期,佛道二教風(fēng)行,對神的膜拜漸漸使人自身的價值變得模糊,儒家的人學(xué)體系再一次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于是對人自身價值的重新確認(rèn),便成了宋明理學(xué)的歷史使命。思想家們在道德主體的實踐基礎(chǔ)上,對天人合一有了新的定位,試圖對天人的緊張關(guān)系加以協(xié)調(diào),從而營造一個和諧的社會秩序。
宋明時期,占據(jù)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程朱理學(xué)為樹立人之為人的終極根據(jù),進(jìn)一步提出道德形上本體“天理”,在一定程度上為天人合一找到了可靠憑據(jù),防止了人的非自因的沉淪。朱熹主張通過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的方法來達(dá)到心與理的貫通,使人心復(fù)歸于道德理性、封建倫理。但在這一識理過程中,心作為天理的被動承受者,已失去了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其將生命個體與至善本性簡單同一的理論路數(shù)就產(chǎn)生裂變性反應(yīng),到南宋時期被陸王心學(xué)思想所替代。
陸王一反程朱向外尋理的思維路數(shù),主張在凈化心靈田地的基礎(chǔ)上,皆備萬物道理,然后擴(kuò)大和充實心智能量,以致在無窮的宇宙內(nèi)“此心至靈”、“此理至明”。由于“我”是依從于天理的,天理又是至上,因而“我”也就至高無上。顯然這是對天人關(guān)系作了新的定位,從新的視角呼喚著人的主體價值。
程朱“存天理而壓人欲”使得主體的“天然之美”受到了壓抑。陸王心學(xué)則在其認(rèn)識領(lǐng)域和思維方式中充分展現(xiàn)主體的創(chuàng)造之美。客觀天理雖然神圣不可侵犯,但“我”作為道德主體可以在實踐過程中修行自身德行,并利用必然之理實現(xiàn)主體的目的。這種認(rèn)識天理的方式確認(rèn)了人在塑造自我中的能動作用,并相應(yīng)地摒棄了對人性的宿命理解,在更廣的歷史視野上展示了主體的創(chuàng)造能力。
綜上所述,從孔孟到陸王一系儒學(xué)思想家在一定意義上突出了主體人格的力量,尤其是心學(xué)家將“自在之物”化為“為我之物”,在更深層的意義上發(fā)掘了主體自我發(fā)展及實踐活動的內(nèi)在作用,這在中國哲學(xué)思維方式及其認(rèn)識領(lǐng)域中開辟了新的價值取向。
3 中西主體論思想的差異
通過以上對中國傳統(tǒng)儒學(xué)人學(xué)體系演變過程的分析,我們清楚地看到其思維方式中所透顯的主體精神,這和西方主體性原則有著共同的人性關(guān)懷和價值關(guān)注。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把中國傳統(tǒng)儒學(xué)的主體人格思想等同于西方哲學(xué)概念上的主體性原則,因為它和西方哲學(xué)的“主體性”概念還有一定距離。
第一,西方主體性原則強(qiáng)調(diào)主客對立,中國傳統(tǒng)儒學(xué)主體人格思想強(qiáng)調(diào)天人合一。雖然在傳統(tǒng)儒學(xué)的主體人格思想中,也有道德主體與外在天理的區(qū)分,但是縱觀整個傳統(tǒng)儒學(xué)的人學(xué)體系,主要強(qiáng)調(diào)人與自然的和合,天理與人情的和合。在天與人的渾然一體中,所謂主體人格的存在,更多的是體現(xiàn)在對道德綱常倫理這種所謂的客觀理性的自覺體認(rèn)上。事實上,這里的客觀并非西方哲學(xué)意義上的客體性,而是占據(jù)話語權(quán)的官方所制定的道德原則。我們知道,西方主體性原則的實質(zhì)是近代哲學(xué)中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關(guān)系之爭的產(chǎn)物。人作為獨(dú)立自主的自由自覺的能動的主體與客體相對立和關(guān)聯(lián),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性原則。宋明理學(xué)時期的“理氣之爭”,似乎有一些主客對立的意味,但實際上,程朱所講的理也是封建社會的道德原則,天理與人心的和合,最終也就是讓人順從道德原則,從而達(dá)到束縛人性的目的而已。即使是陸王心學(xué)強(qiáng)調(diào)人心的主動,有反外在權(quán)威之意,但也沒有逃出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的范疇,這無疑是主客二分的最大障礙。
第二,西方哲學(xué)中的主體性原則,建立在主客體相互對立的基礎(chǔ)上,是基于認(rèn)識論意義上的主客二分。人作為認(rèn)識的主體,站在世界之外,研究世界,研究客體,研究自然。而中國傳統(tǒng)儒學(xué)所體現(xiàn)的主體人格,則是從主體內(nèi)在的需要、評價和態(tài)度出發(fā),通過主體意識的意向活動,獲得世界和人生的意義。這說到底是從道德論意義上的相對主體論。在其主體論中,更加重視的是對人生的研究。無論是先秦儒家的“天”,還是宋明理學(xué)的“理”,其實質(zhì)都是道德理性的存在,都是將人的道德意識推衍為形而上學(xué)的終極依據(jù)。“吾心即是宇宙”,陸王將人即主體自身看作宇宙的中心,人的存在就是世界的根本存在。認(rèn)識自身也就認(rèn)識了自然界或宇宙的根本意義,就思維指向而言,它是返回到心靈自身,是思維的自思維。雖然他們也同樣承認(rèn)客觀世界的存在,但傳統(tǒng)的天人合一觀念讓他們始終堅信客觀世界同思維主體是同一的,而不是對立的。和西方將自然界具象化的思維模式相反,他們是將自然界人化,從內(nèi)在的主體意識出發(fā),按照主體意識的評價和取向,賦予世界以某種意義,所以“我不看此花時此花即無”,“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山高”。這分明是將自然界轉(zhuǎn)化為人的內(nèi)部存在,在人的心靈中種植著自然界的法則。人不必對自然界進(jìn)行客觀化、概念化的分析,自然界的存在和意義就內(nèi)涵在人的心理結(jié)構(gòu)中。只要對人的存在和本質(zhì)的自我了解,就是認(rèn)識天道的根本途徑和方法。和西方主體性原則中以對象認(rèn)識為基礎(chǔ)的反思方式不同,傳統(tǒng)儒學(xué)從主體的感知存在出發(fā),建構(gòu)思維模式,其思維定勢是認(rèn)識自我,實現(xiàn)自我并超越自我,達(dá)到外在天理倫常與內(nèi)化于我心的天理同一。
第三,西方主體性原則在尊重自我意識的同時,充分肯定自然在人以外并與我對立。而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儒學(xué)主體人格思想則單純重人,并不重視自然。從西方哲學(xué)發(fā)展歷程,我們看到主體性原則的確立,經(jīng)歷了主客一體、主客二分、主客對立統(tǒng)一的過程。人們在重視人的同時,也不斷地發(fā)現(xiàn)自然的規(guī)律并遵守它。主體與客體相互為用,相互促進(jìn),只有重視自然,才能意識到真正的自我,意識到人,也才能促進(jìn)人的主體性的發(fā)展。單純地談人而不重視自然則會阻礙主體性的發(fā)展。這在中國傳統(tǒng)儒學(xué)主體人格思想中得到了實證:孔子大談人倫,不講自然,結(jié)果壓制了人的主體性;宋明理學(xué)重道德虛靜,忽略自然,也抹殺了人的主體性,即使是心學(xué)家們的心性之學(xué),大講“主體之心”,但也因否認(rèn)自然的客觀存在,而使得所謂的主體心性淪為天命皇權(quán)的主宰之物。如果不推翻君權(quán),人的主體性就永遠(yuǎn)不會建立。
4 結(jié)語
綜上所述,一方面我們無可否認(rèn)的是,中國傳統(tǒng)儒學(xué)注重對內(nèi)的自我訴求,有志于通過道德實踐實現(xiàn)理想人格的塑造,使人在超越自然、超越自我中實現(xiàn)自我的主體價值,這與西方主體性原則對主體精神的張揚(yáng)是不謀而合的。但是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中國傳統(tǒng)儒學(xué)主體人格思想和西方近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主體性原則,在思維路徑上是大相徑庭的。
[1] 張世英.天人之際——中西哲學(xué)的困惑與選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
[3] (宋)邢昺.論語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8.
[4] 陳鼓應(yīng).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1984.
[5] (日)西田幾多郎.善的研究[M].何倩中,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5.
[6] 劉述先.中國文化論文集[M].臺北:臺灣幼獅文化事業(yè)公司,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