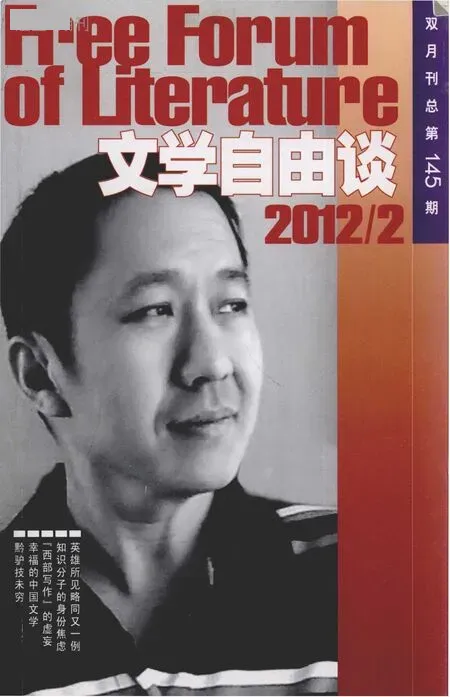總是失敗的諸神
●文 何 英
1926—1937年的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寫道:因此我們可以說所有人都是知識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
在這樣的語境下看嚴歌苓的《陸犯焉識》,覺得了一種距離。也許,東西方對于知識分子的范型規(guī)約不一樣。中國自然也有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說法,也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走上街頭就義的知識分子。一直以來也有到底是胡適還是魯迅的爭論。西方后現代派理論家更是紛紛重回政治的視域來解剖一切真理。所以,歷來關于知識分子的論述是最麻煩的。畢竟信仰是一回事,面對強權和屠刀是另一回事。恐懼是本能。自古以來能戰(zhàn)勝本能的人,又有著崇高的信仰和正義的行止,才配得上卓然獨立于世而后為人景仰的尊崇。對知識分子而言,賽義德的總結更通俗明了:特立獨行、能向權勢說真話、耿直、雄辯、極為勇敢及憤怒的個人。即使面對艱難險阻也要向大眾表明立場及見解;知識分子的言行舉止也代表再現自己的人格、學識與見地。
陸焉識的一生夠悲催的。民國的牢坐過,共和國的牢坐過,中國的牢底都快讓他坐穿了。智力超群、語言奇才、留美的語言學博士,認真地做一名普通的大學老師,惟純學術研究為正途。在那個每時每刻身邊遠處都是政治的險惡環(huán)境中,一名頂尖的知識分子,卻能夠不聞不問世事。作家熱內說過,在社會發(fā)表文章的那一刻就已經進入了政治生活。陸焉識大概深諳此理,他從不主動發(fā)表時事文章更不主動發(fā)表意見。但他追求自由,在大多數人水深火熱一觸即發(fā)的時代里,在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解放的時候,他追求個人的自由。他的追求超前了,必然不得實現,也必然由別人決定他是否自由。強權也總是把他的自由踩得粉粹,自由終于以自由的反面反諷了他。他不關心公共事務,不對公共事務發(fā)言(作為那個時代的留洋博士,同時代留美的胡適、留日的魯迅是背景的話,陸焉識的表現似乎乏善可陳)。社會的風云激蕩席卷一切,他作為一個受害者被迫害。他的恩娘痛心地說,你是一個沒用場的人。這不奇怪,百無一用是書生。我們的傳統已經把知識分子弄成了沒用的書生。同時他不得不而且必然成為一個虛無主義者。要自由,卻缺乏勇氣,總是被女人的眼淚羈絆;除了出國留學,他的人生都是被動的,被動地卷入同學大衛(wèi)的文字陣,以及后來的政治斗爭,被動地從民國起一直挨整到七十年代末。這個人物可憐,卻無法激起一揾英雄淚的壯烈之美,因他實在沒有多少光彩奪目的時刻。如果用葛蘭西關于知識分子的描述來看,陸焉識恐怕只能是一位沒有起到知識分子作用的知識分子,一個有機的知識分子。最后連當一名有機知識分子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所幸的是,按法國人班達關于知識分子的定義,因真正的知識分子要承受的受難殉難式命運,女人被排除在了真正知識分子的范圍之外。所以,也敢就知識分子話題發(fā)些以上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議論。
作者的筆墨于兩大塊內容最集中,一是陸焉識的監(jiān)獄生活,一是陸焉識的家庭生活。陸焉識怎樣艱難地去見小女兒丹玨寫了77頁,當然這中間還穿插著交代了好些事情,但仍然還是在監(jiān)獄生活和家庭生活這兩大塊內容上打磨。作為上世紀初留學美國的博士,他的學術或者文字生涯,在我們關于現代文學的背景語境想象中,應該是多么的風生水起跌宕起伏。這部分最能體現陸焉識風采的內容較為缺失,大衛(wèi)和凌博士是作者惟一較多筆墨寫到的文化圈人物,一個是有著斗爭激情的革命者,窮且餓,要向陸焉識借論文,并沒有“為四萬萬同胞”的崇高目的,總是幾筆帶過地略寫。就在這不多的,幾乎可以說是珍稀的幾筆中,大衛(wèi)的形象以小丑和漫畫人物為特征。另一個形象就更模糊了,似乎是一個心胸狹窄冷酷無情的學閥政客。也許嚴歌苓為防他人對號入座引來名譽糾紛甚至訴訟官司,一切都隱晦含糊地寫來。讀者想看一部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看他們頭腦中如何掀起知識或權力的風暴,看他們的小宇宙如何勾連起知識分子的前世今生。卻只看到于作者來說,最擅長的那些內容:嚴歌苓早年的《雌性的草地》,關于大西北荒漠生活的描寫就爛熟于心。就算是青海人,大概都挑不出她關于這塊地域的小說描繪有什么瑕疵,作者于這一部分內容非常自信。關于知青或者犯人改造的歷史掌故她也掌握不少第一手資料,也寫過電影《天浴》。小說的開頭對于大草漠的描寫,簡直顯出一位語言強手的表達力,令人嘆為觀止。光看開頭,以為一部真正的巨著要誕生了。正當讀者激起全部的熱望,要看看陸焉識這位主人公,如何在時代風云的激蕩中著書立說也好,左沖右突也好,前后矛盾也好,榮辱沉浮的一生。最能展示這個人物的重點也在于這里。遺憾的是,作者又順著她寫慣的、能寫好的那一部分內容去了:陸焉識在獄中惟一思考的是他的娘子,一個不自由硬塞給他,他從未愛過的女人。作者倒敘起夫妻二人的家庭生活也表現得津津有味,婆媳關系家長里短地寫來寫去。這部分內容自然令人想起她寫過的《小姨多鶴》、《寄居者》等,寫兩個人一個屋檐下的愛情,虛構一段電影式的愛情傳奇,嚴歌苓是一把好手呢。
當葛蘭西寫《獄中札記》的時候,陸焉識在給妻子寫隨筆散文。其實即便是隨筆散文,作者也可以把這部分內容亮出來,讓我們看看這位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但我們看到的卻是,這個人物似乎并不以愛智求真、公理正義的信仰或野心為自己的身份歸屬,更遑論民族國家之類的宏大議題了。
本書的宣傳語:將知識分子陸焉識的命運鋪展在政治這塊龐大而堅硬的底布上,檢視了殘酷歲月里生命可能達到的高度。似乎重慶監(jiān)獄和后來的青海監(jiān)獄就是他全部的“政治底布”。這些細節(jié)自然有其價值,作者在其中幾次寫到驟然降臨的死亡,陸焉識的反應,那些恐懼、掙扎以及求生的本能,和最后放棄生命的坦然,都是真實可信的。而這一深度也確實如一次次的檢驗刀鋒——死亡最大。在這個物質的死亡面前,精神似乎早已先期死亡,這才是知識分子陸焉識的悲劇。盧卡契將生命分為現實生命和真正生命,現實生命混沌可悲,生不如死,真正生命便表現為否定形式,死亡。普通人怕死,可在希臘悲劇中,死亡凸顯生命意義。悲劇功能在于揭示現實生命中的“偉大瞬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知識分子陸焉識的生命意義也許從沒有得以凸顯出來。
作者電影協會專業(yè)編劇的身份,使她總在不經意間把一部小說弄成好看的電影。《陸犯焉識》似乎在比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電影《布拉格之戀》。兩個民族國家的政治背景有著驚人的相似,這種相似性構成了一種對比。《陸犯焉識》鋪設的“政治底布”確實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酷烈得多。政治犯的監(jiān)獄生活直追《古拉格群島》。在《古拉格群島》里,對于殘忍的刑訊、荒謬的司法、淪喪的社會道德以及超強度的死亡勞改都有極其精練真實的描述。而作品的意義更在于知識分子對于加諸自身命運的思考。在集權面前,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卻始終只能以懦弱的社會屬性存在。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陸焉識也讓我們看到了相似的懦弱。可是,一切止于此了。作者對于牢獄生活的物質描繪說得太多太細,不知怎么就失去了恐怖震攝的效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托馬斯、弗蘭茨、薩賓娜從未受到直接或者殘酷的政治迫害和打擊。托馬斯只是因為言論被當局從一名醫(yī)生弄成擦玻璃的工人。《陸犯焉識》的幽默是語言上的,是作者中年風度的體現。不可能再像年輕時一樣文風峻急,一切都可以娓娓道來甚至加一點無傷大雅的自嘲以及東方美學的自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卻使人時時沉浸在一組一組的哲學辨論里“:輕與重”“、靈與肉”,《誤解的詞》以及關于記憶、虛弱、眩暈、牧歌、天堂等生存暗碼的深思和想象。作品探討愛的真諦,男女之愛、朋友之愛以及祖國之愛。每個人對于愛皆有自由抉擇的權利,但也應負起對于愛的義務。在歷代的愛情詩中,女人總渴望承受一個男性身體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成了最強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負擔越重,我們的生命越貼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實在。相反,當負擔完全缺失,人就會變得比空氣還輕,就會飄起來,就會遠離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個半真的存在,其運動也會變得自由而沒有意義。那么,到底選擇什么?是重還是輕?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提出的問題,小說最后也以與愛人一起死亡作為承擔愛的責任的承諾兌現。《陸犯焉識》關于愛情的想象是有限的,似乎是一種沒有達成的愛使陸焉識在回憶中完成了愛情。她花了那么多的篇幅來寫的愛情,像沒有對手的單方拉力賽,漫長而單調,相比較起來托馬斯的愛情則張力十足。
嚴歌苓的小說從沒有真實性的堪憂。《第九個寡婦》是作者聽聞過在中原發(fā)生的一個真實事件作底子;《小姨多鶴》是作者采訪過日本侵華戰(zhàn)爭后留在中國的日本女孩故事;《一個女人的史詩》也有著家族故事的影子;《金陵十三釵》自然也是在真有其事的基礎上寫的。這一次的《陸犯焉識》直稱是其祖父人生遭際和精神世界的探尋。這要是為祖父立傳,作者必得更加遵循其真實性的原則。但作為一部小說,讀者要說,確實有很多真正精神的內容作者沒有提供。這不得不說是這部小說的缺憾。
賽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將自己的第六章命名為“總是失敗的諸神”——對于眾神來說,對大神宙斯的反抗總是失敗的。這或者就是知識分子宿命的暗示與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