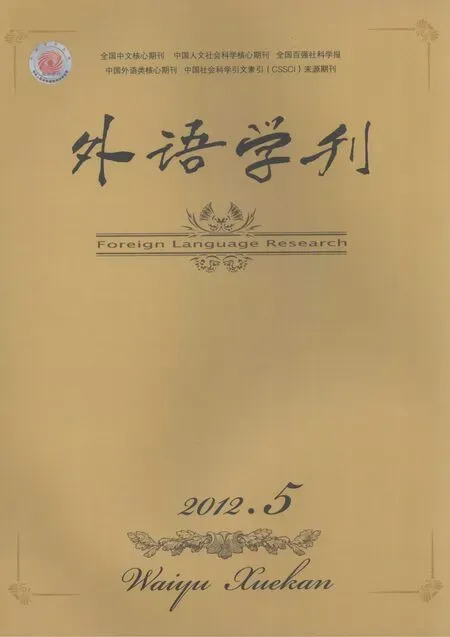從索緒爾的言語到哈貝馬斯的語言交往:語言的在與是*
馮文敬
(蚌埠學院,蚌埠 233000)
〇引進與詮釋
從索緒爾的言語到哈貝馬斯的語言交往:語言的在與是*
馮文敬
(蚌埠學院,蚌埠 233000)
哈貝馬斯普遍語用學建立在索緒爾語言與言語的區分上,但索緒爾語言與言語的二元對立在哈貝馬斯的人與人的交往中已發展為一元統一,即語言與言語在人的交往中交織在一起,構成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與索緒爾一樣,哈貝馬斯的理論同樣具有語言本體論思想。以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為基礎,可以揭示出,語言是一種獨立存在的本體;語言活動是人在自己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其本質是交往;語言本體的“在與是”通過語言交往過程實現,同樣通過語言交往同人與人的世界相聯系。
哈貝馬斯;普遍語用學;本體論語言哲學;語言哲學
語言哲學的中心問題有兩個:一是語言與世界的關系;二是語言或語詞的意義問題。本體論語言哲學指“與分析性語言哲學對應,把語言視為在者/是者,探討語言如何在如何是,通過語言分析和解釋來揭示人和人的世界(包括人生活的外在物理世界)的科學”(李洪儒 2011:3)。該學派涵蓋的范圍主要包括歐洲大陸的一些哲學流派,如結構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解釋學、法蘭克福學派和后現代主義。從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普遍語用學中的交往行為理論出發,可以從新的角度闡釋語言本體及其“如何在如何是”,闡釋人、語言和世界的關系。
1 語言與言語:二元對立還是一元統一
桑德拉·哈里斯認為,“普遍語用學理論都企圖確立互動交往的根本和內在規則”(Harris 1995: 117)。如果從廣義上說,語用學是語言使用的研究,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或形式語用學(formal pragmatics)則尋求在必要的抽象層次上定義這些規則,排除不同主題、語境甚至文化。格萊斯的合作原則是普遍語用學的一種嘗試,但卻沒有將其理論上升到社會和政治層面,而哈貝馬斯將語言研究置于社會行為理論中,提供格萊斯所缺失的普遍語用學的社會和政治維度,將語言交往行為與社會現實的重要方面聯系起來。
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理論建立在索緒爾的語言與言語的二元區分基礎上。“語言是人類代代相傳的符號系統,包括詞法、句法和詞匯。它潛存于特定語言共同體所有成員的意識中,是共同體約定俗成的社會性產物……言語則是說話人說出或者理解的全部具體內容。”(李洪儒 2010 :18)據此區分,索緒爾建議設立分別研究語言和言語的兩門不同的語言學,前者是主要的,后者則是次要的。這種二元對立思想和二元對立范疇的區分成為索緒爾給后人留下的“疑難”(利科 1988:372-375)。哈貝馬斯則認為,語言的形式語用研究與形式語義分析同樣可能,而且同等重要。形式語用學的目標是要系統重建有能力主體的直覺性語言知識,有能力言說者對自己語言所擁有的直覺性規則意識(Habermas 1998:2)。哈貝馬斯的思路與喬姆斯基有某些相似:“類似于喬姆斯基對于言說者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語言運用(linguistic performance)的區分”(Commings 2007:199)。言語行為理論對言語的要素單位(話語)主題化的態度類似于語言學對語言的單位(句子)主題化的態度。重建性語言分析的目標在于對這樣一類規則的清晰描述:有能力言說者必須遵從這些規則,以便構造語法性句子,并用一種可接受的方式言說他們。言語行為理論與語言學共同擔負這項任務。“語言學是從每一個成年言說者都擁有某種內在的重建性知識(其中,他的構造語句的語言學規則資質
普遍語用學認為,一個交往過程的參與者以達到理解為指向的活動只能在下述條件下進行:參與者在其言語行為中使用可領會的句子時,需要通過某種可接受的方式同時提出3項有效性要求:(1)對一個被陳述的陳述性內容或被提及的陳述性內容的存在性先決條件,它要求真實性(validity claim of truth);(2)對規范(或價值)——在一個給定的關聯域中,這些規范或價值將證明一個施行式建立起來的人際關系為正當——他要求正確性或適宜性(validity of rightness);(3)對被表達的意向,它要求真誠性(validity of truthfulness)。依據3個有效性要求,在對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分類批判的基礎上,哈貝馬斯將言語行為劃分為3個基本類型:記述式言語行為(constative speech act)、調節式言語行為(regulative speech act)和表現式言語行為(expressive speech act)。在此交往過程中,語法性句子通過普遍有效性要求被嵌入與現實的3種關系中,并由此承擔卡爾·畢勒(Karl Buhler)在語言功能圖式中提出的語言的3種語用學功能:呈示事實,建立合法的人際關系,表達言說者自身的主體性。這樣,語言就可以作為相互關聯的3種世界的媒介物而被設想,即對每個成功的言語行為來講,都存在下列3重關系:話語與(1)作為現存物的總體性的外在世界的關系;(2)作為所有被規范化調整的人際關系總體性的我們的社會世界的關系;(3)作為言說者意向經驗總體性的特殊的內在世界的關系。也就是說,交往者使用語言進入具體的語言交往過程,使人與人的外在物理世界、內在世界和社會世界聯系起來。可見,雖然哈貝馬斯在概念上仍然遵循索緒爾的語言、言語二元區分,但在他的交往模型中,語言與言語已經統一為一個整體。
2 語言本體的本質:在與是
在古代和近代哲學中,語言只是表達思想、傳遞信息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即語言的工具論思想。而在現代哲學中,語言被看成人的存在方式,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家園。所謂本體論或存在論,按亞里士多德的定義,就是討論to on hen on(所是之為所是,存在者之為存在者)(陳嘉映 2003:37)。蒯因和卡爾納普都主張我們有不同的語言系統,這些語言系統的本體論地位相同:“語言行為在性質上不同于草履蟲對營養液的反應,除了在‘以言行事’這種特定的情況中,我們不是用語詞對環境作出反應,而是在語詞的層面上反應”(陳嘉映 2003:271)。借用比克頓的話說,語言是一個獨立存在的表征體系,而不僅僅是一種交流手段或技巧。哈貝馬斯提到,在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繼承的狄爾泰和胡塞爾的傳統中,主體間性中達成的言語理解具有本體論的特征:“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1927)中把理解看作是人類此在的基本特征;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1960)中則認為,理解是歷史生活的基本特征……我不想對這個觀點展開系統的論述,但想肯定一點,在過去幾十年里,關于社會科學基礎的方法論討論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上都是一致的:……理解必須被看作不是一種特殊的對于社會世界、社會科學的記載方法,而是通過社會成員進行的生產與再生產的人類社會的本體論條件”(哈貝馬斯 2004:107)。哈貝馬斯所構建的交往模型首先承認語言本體的存在,即語法性語句的存在,通過語言本體的使用,人與世界在交往中發生關聯,“交往行為概念中所出現的是另外一個語言媒介前提,它所反映的是行為者自身與世界之間的關聯”(哈貝馬斯 2004:94)。也就是說,語言成為獨立存在的實在,不依附于任何實在,而是一種“處于人與世界之間,屬于多元世界中的一元”(李洪儒 2008:2)。
3 語言活動的本質:交往——人在人的世界中的存在方式
哈貝馬斯把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結構劃分為認知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工具理性(teleological rationality)和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分別對應著3種語言使用樣態:認知性應用、工具性應用和交往性應用。其中,語言的交往性應用依賴于交際情景中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的人際關系。在對韋伯的社會行為理論批判的基礎上,哈貝馬斯指出,交往行為是語言應用的原初狀態,其他社會行為,如與工具理性相對應的策略行為等,則是附屬行為,“以溝通為取向的語言應用是一種原始形態,間接溝通(讓人理解或迫使理解)處于寄生狀態”(哈貝馬斯 2004:275)。所以,以語言本體為中心的語言活動本質上由交往互動雙方的交往行為組成,也就是說,語言本體的“如何在如何是”其實通過溝通行為(交往行為)實現。“溝通是人類語言的終極目的。語言與溝通之間的關系盡管不能比作手段與目的,但如果我們能夠確定使用交往命題的意義,我們也就可以對溝通作出解釋。語言概念和溝通概念可以相互闡釋。”(哈貝馬斯 2004:275)可見,哈貝馬斯反對語言工具論,語言這種本體并不是溝通交往的工具,而是與溝通(交往)互相闡釋、不可分離。即語言活動的本質就是交往,是人在人的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因為沒有語言交往,人就不成其為人。而語言意義的解釋和理解都必須在主體間性的交往中實現,“意義理解與對物理對象的感知之間究竟有什么區別?它要求與表達的主體建立起一種主體間性的關系……意義理解是一種交往經驗,因而不能從唯我論角度加以貫徹。理解任何一種符號表達基本上都要求參與到一個溝通過程中去”(哈貝馬斯 2004:112)。
溫奇認為,所謂“語言”,就是語言構成的世界觀及相應的生活方式。“世界觀中蘊藏著文化知識,依靠文化知識,不同的語言共同體又來分析各自的世界。每一種文化都用它的語言建立起與現實的聯系。”(哈貝馬斯 2004:57)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探討語言自身問題時,如果不把生活世界概念納入考慮范圍,就不會真正解決問題,找到答案的原因。如前所述,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模式把語言看成一種達成全面溝通的獨立存在的人與人的世界聯系的媒介,言語者和聽眾在溝通過程中同時從他們的生活世界出發,與其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及主觀世界發生關聯,以求進入一個共同語境。這樣,與人相關的生活世界劃分為3個部分: 客觀世界(外在自然),意指成年主體能夠(盡管僅僅是間接地)感知、能夠操縱并在現實中客觀化了的那一部分;社會世界,意味著成年主體可以在某種非遵從性態度中加以理解的——作為一個交往行為中的人、一個交往系統的參與者而理解的——現實中前符號化結構的那一部分,合法的人際關系就隸屬于此,例如,制度、傳統、文化價值等等;主觀世界,即內在自然,是全部欲望、感覺、意向等等。關于內在自然,我們認為,哈貝馬斯所說的“全部欲望、感覺、意向”在具體交往過程中是某個個人的,而上升到宏觀層面應該是整個人類共同體的內在世界,一種通過交往達成共識的主體間性的世界,并且與整個人類共同體組成的社會世界和自然世界緊密相連。可見,這3個世界都體現人的因素,或者可以說“人的世界”劃分為3個世界。而人在人的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就是以溝通交往為本質的語言活動。通過語言交往,人與人的世界統一起來,“交往行為最終依賴的是具體的語境,而這些語境本身又是互動參與者的生活世界的片段。依靠維特根斯坦對背景知識的分析,生活世界概念可以成為交往行為的補充概念”(哈貝馬斯 2004:266)。
4 語言本體的“如何在如何是”:語言交往過程
4.1 交往目標
哈貝馬斯把語言交往的目標區分為達成一致(agreement)或共識(consensus)和達成理解(understanding)。只有當交際者能以同樣的理由接受一個有效性時,交際參與者關于一個存在事實才能達成一致,以此為目標的交往行為稱為強交往行為。而在一方交際者看到另一方交際者在給定語境中對于他所宣稱的意圖有好的理由,交際雙方關于說話人意向的嚴肅性的相互理解就可達到,以此為目標的交往行為稱為弱交往行為。
但有些交往行為并不是單一類型。如警察詢問互動,是以達成理解為目標的弱交往行為,即警察關于被詢問人意向的嚴肅性僅僅達成理解而非一致,因為嚴格意義上的一致只有當警察與被詢問人以同樣的理由接受一個有效性時才能達到。而警察在單次詢問過程中,互動雙方只能就部分事實達成一致,要通過后續調查,才能最終確定整個事實,所以在調查期間,詢問筆錄中的“事實”的一部分真實性是懸置的,只能達成理解。所以,此時的交際目標在整體上是達成理解,而部分上就某些事實是達成一致或共識,即交際目標應該是一個從達成理解到達成一致或共識的連續體,即交際者期待的交際成功程度是一個連續體。而達成一致或共識應該進一步區分為達成弱共識(agreement or consensus in weak sense)和達成強共識(agreement or consensus in strong sense)。以達成弱共識為目標的是介于弱交往行為和強交往行為之間的交往行為,如警察詢問互動。所以,弱共識也可稱為一致理解(agreed understanding)。
4.2 語言交往過程
“語言是一個具有自己組成單位及其運作規則的特殊存在,其核心要素是創造、發展、運作(使用)語言本體的關鍵要素——人,包括說話人(speaker)、受話人(hearer)和他者(others)。”(李洪儒 2010:22)哈貝馬斯的交往模型正是從說話人、受話人角度對語言本體的“如何在如何是”,即應用過程的全面闡釋,但他沒有把語言的運用過程(溝通過程)當作發送者與接受者之間傳遞信息的客觀主義觀念,而是面向“一種關于互動的形式語用學概念,這種互動發生在具有言語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并以溝通行為作為中介”(哈貝馬斯 2004:263-264)。可見,這是一個具有主體間性的互動模式。
同語用學其他交際模式如斯波伯與威爾森的明示-推理模式比較,哈貝馬斯的交際模式對語言的抽象意義和字面意義如何從語言層面通過交際進入生活世界層面產生出最終說話人意義和聽話人意義的微觀推理過程語焉不詳,但是哈貝馬斯不僅關注聽話人對說話人話語的理解問題,而且關注聽話人對話語的反應:接受或拒絕有效性要求(交際成功或失敗的深層原因),將語言交際上升到宏觀社會規范層面。他對語言交往的描寫從語言本身到實際交際過程都提出有效性要求,意義理解在交際雙方(有時還有他者)的主體間性中實現,交往不是一個單向過程,而是雙方不斷提出、批判、論證有效性要求而最終達成理解或共識的動態過程,而此過程也正是語言本體“在與是”的實現過程。
5 結束語
從索緒爾的言語到哈貝馬斯的語言交往,語言與言語在交往行為中得到統一。從主體間性的交往行為出發,可以闡釋語言本體及其“如何在如何是”。也可以從新的角度闡釋人、語言和世界的關系:語言是一種獨立存在的本體;語言活動的本質是交往,人與人的世界通過語言交往聯系起來,即語言活動是人在自我世界中的存在方式;語言本體“如何在、如何是”通過語言交往過程實現。語言與人同在。
陳嘉映. 語言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M]. 重慶:重慶出版社, 1993.
利 科. 哲學主要趨向[M].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
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
李洪儒. 現代歐洲大陸語言哲學研究——站在流派的交叉點上[D]. 黑龍江大學博士后工作報告, 2008.
李洪儒. 索緒爾語言學的語言本體論預設——語言主觀意義論題的提出[J]. 外語學刊, 2010(6).
李洪儒.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之路——語言哲學理論建構之一[J]. 外語學刊, 2011(6).
潘文國. 從哲學研究的語言轉向到語言研究的哲學轉向[J]. 外語學刊, 2008(2).
Habermas, J.OnthePragmaticsofCommunication[M]. 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8.
Commings, L.Pragmatics:AMultidisciplinaryPerspective[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Harris, S. Pragmatics and Power[J].JournalofPragmatics, 1995(23).
【責任編輯李洪儒】
FromSaussure’sParoletoHabermas’sCommunication:theBeingofLanguage
Feng Wen-jing
(Bengbu College, Bengbu 233000, China)
Habermas’s Universal Pragmatics is based on Saussure’s binary division between langue and parole, but Saussure’s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langue and parole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one unary unity, that is, langue and parole interwind and become an indivisible unity in the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of human beings. Just as Saussure, Habermas’s theory also has a feature of language ontology. Based on Habermas’s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we hold that language is a kind of independent beings, and linguistic activity, whose nature is communication, is the way of living of human beings in our world. Through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the being of language beings is realized, and human beings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with our world.
Habermas; Universal Pragmatics;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089
A
1000-0100(2012)05-0016-4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俄語主觀意義研究”(10BYY099)和教育部重點基地重大項目“語言哲學與語言學的整合性研究”(10JJD740004)的階段性成果。
2012-03-31
編者按:目前,學術界受英語國家主流學者觀念的影響,一般認為,語言哲學是廣義分析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只包括分析哲學和日常語言哲學中用分析方法分析語言的部分。其實,這是誤讀。本刊有充分根據認為,語言哲學不僅應該包括分析性語言哲學,而且應該包括以語言為對象、以人及人的世界為學科目的的所有學說、學派。馮文敬和李會民的文章雖然短小,甚至難免簡單之嫌,但是昭示我們:索緒爾、哈貝馬斯和洪堡特等人對語言哲學的貢獻同樣巨大,值得并且應該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