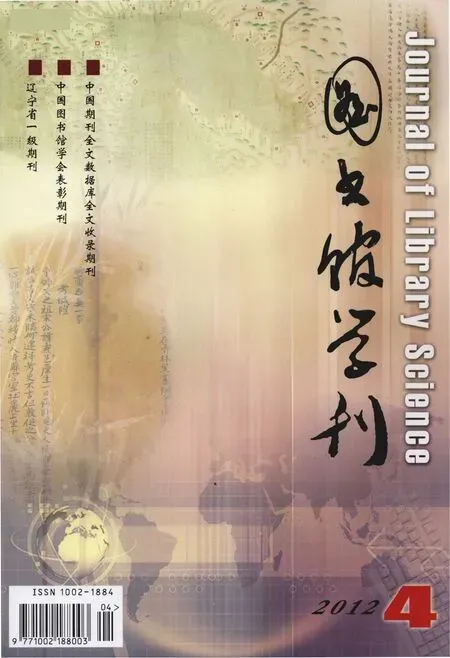《七略》與《別錄》釋名
孫顯斌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七略》、《別錄》是我國最早的兩部綜合目錄,同時它們也是劉向、劉歆父子西漢校書活動的成果。實際上從二錄的名稱就可以看出當時典籍分類的觀念和單書敘錄形制,但是二錄尤其是《別錄》歷來別稱不少,筆者試從稱引文獻入手,辨析二錄的得名由來和別稱情況。
《七略》之名,雖然諸家稱引也有差異,但《漢書》記載明確,其原名如此,沒有異辭。《漢書·藝文志敘》稱:“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1]章太炎《七略別錄佚文征序》:“略者,封畛之正名,傳曰:天子經略,所以標別群書之際,其名實砉然。”[2]《說文》:“略,經略土地也。”“略”有分界之義,在“七略”之名中則有分類之義,所以“七略”為七“略”之合稱。姚名達[3]、呂紹虞[4]以“略”為簡略之義,這是說不通的,因為這樣對“輯略”的解釋必然牽強。
但是《別錄》的情況就不同了,學界有不同意見。如李解民認為《別錄》的原名為《七略別錄》:“正史《經籍志》或《藝文志》專門著錄書目,講究書名的規范、完整,與平常稱引只圖簡潔、方便而慣用省稱不同。”[5]筆者認為其說值得商榷。實際上,《別錄》最早被稱引是東漢應劭《風俗通》引稱劉向《別錄》,后世稱引也大多用此名稱,為了討論方便,我們將《隋書·經籍志》以前諸書稱引《別錄》的例子列舉如下:
李善《文選注》卷四十三《重答劉秣陵沼書》引《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6]
葛洪《抱樸子外篇·自敘》:案《別錄》、《藝文志》眾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7]
劉孝標《世說新語注·言語篇》: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8]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六:劉向《別錄》以稷為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故曰稷下也。[9]
《廣弘明集》卷三《七錄序》: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10]
宗懔《荊楚歲時記》:按劉向《別錄》曰:寒食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于戰國,案鞠與同,古人蹋蹴以為戲也。[11]
《隋書·經籍志·薄錄類》:《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七略》七卷,劉歆撰。[12]
《隋書·經籍志·薄錄類小序》: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跡,疑則古之制也。[12]
《隋書·音樂志》: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12]
《隋書·牛弘傳》: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并說古明堂之事。[12]
姑且不論正史經籍、藝文志多由舊目編成,少加校訂,新舊唐書以下多有訛竄,就拿《隋書》本書來說,《隋書·經籍志·薄錄類小序》、《音樂志》、《牛弘傳》皆稱劉向《別錄》,如果說正史不及正史目錄規范,恐怕自相矛盾。并且應劭《風俗通》、阮孝緒《七錄序》、葛洪《抱樸子外篇·自敘》稱引皆為劉向《別錄》,尤其《七錄序》更稱“今之《別錄》是也”,所以認為《七略別錄》為正名,難以讓人信服。
另外,李解民認為《別錄》有別稱《七略》、《七錄》,也難成定論,因為棄常用名《別錄》不用,而用容易與劉歆《七略》、阮孝緒《七錄》相混淆的別稱,徒增混亂,實在是不合乎情理的用法,出現這些稱引只能是對劉歆《七略》、劉向《別錄》或阮孝緒《七錄》稱引之誤。現將諸書稱引“劉向《七略》”及相關引文列舉如下:
①《北堂書鈔》卷一〇一:劉歆《七略》云:“古文或誤以典為與,以陶為陰,如此類多。”[13]
《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見為典,以陶為陰,如此類多。”[14]
③裴松之《三國志注》卷三十八: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16]
《藝文類聚》卷五十五:劉歆《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17]
司馬貞《史記索隱·五帝本紀》: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為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并入《大戴記》。”[18]
④李賢《后漢書注》卷四十: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19]
⑤《太平御覽》卷二二一:劉向《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14]
⑥《初學記》卷七:劉向《七略》曰:“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20]
⑦《太平御覽》卷四:劉向《七略》曰:“京房《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即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已后,光見東方,皆日所照也。”[14]
⑧《冊府元龜》卷六〇四: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而載《薛虞記》。”[21]
由于劉歆《七略》是采用劉向《別錄》內容而作,所以二者引文如果相同,很難斷定是引《別錄》而非引《七略》。但是參考相關引文亦可有所分辨。第一條似應為“劉歆《七略》”之誤,而第二條則應為“劉向《別錄》”之誤。第三條裴松之所引“劉向《七略》”文字與司馬貞所引劉向《別錄》文字不同,而恰恰與《藝文類聚》引劉歆《七略》文字相同[15],則此處應為“劉歆《七略》”之誤。后5條引文雖無其他引文參照,但也只能是“劉歆《七略》”或者“劉向《別錄》”之誤。所有這些引文都不能說明“《七略》”是“《別錄》”的別名,只是稱引失誤而已。
至于李解民以為《別錄》有別名為“《七錄》”,其文論述如下:《史記·殷本紀》裴《集解》云:“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行。’”司馬貞《索隱》云“:按注劉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顯然,《索隱》所稱“《七錄》”即《集解》之“劉向《別錄》”。姚振宗《七略別錄佚文》指出:“按《索隱》此一段所載九主次序,與《集解》所引不同。《七錄》殆《七略別錄》之省文,非指阮氏《七錄》。”
實際上姚氏與李氏的論證是有問題的,既然《索隱》所引“《七錄》”之文與《集解》所引“劉向《別錄》”之文不同,自然“《七錄》”不應該是《別錄》。另外根據《索隱》引《七錄》對“九主”的解釋,然后稱“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則所引“《七錄》”文字也不應是《別錄》之文,若是《別錄》之文,則劉向以《伊尹》內容言之,司馬貞不當說劉向所言無憑據。所以此處司馬貞所引《七錄》應為阮氏《七錄》,而非劉向《別錄》之誤,更不是《別錄》的別名。
劉向校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21],從今天所存較完整的《荀子敘錄》、《晏子敘錄》即可知劉向所奏敘錄的體例,乃先錄篇目,再講校讎情況,最后言作者及書要旨,與班固、阮孝緒所言不差。劉向所敘原本作為該書目錄“皆載在本書”,簡稱為“錄”,此“錄”離書別行,“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遂稱為“別錄”,姚名達等已有申說。所謂“別錄”這個普通意義的用法,還有兩例如下,這里也順便討論一下。
顏師古《漢書注·藝文志》“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引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劉向,能屬文,后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1]
余嘉錫引洪頤煊曰:“……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余篇。’……班彪《別錄》、班固《目錄》,疑是一書。或疑‘《別錄》’為劉向《別錄》之訛,非是。”按:洪說是也。劉向《別錄》,《漢書敘錄》亦謂之“目錄”。班彪《別錄》蓋彪所作《后傳》之《敘傳》,班固續成之,故又稱《目錄》。《隋志》有“后漢徐令《班彪集》二卷”,此當在《彪集》中。[22]
班彪《別錄》稱馮商所續10余篇,而《漢書·藝文志》稱7篇,則班彪《別錄》不為劉向《別錄》可知,而篇數不同可能是因為馮商在劉向校書之后又續若干篇。則班彪《別錄》只能是其所作《續太史公書敘錄》,所以余嘉錫猜測韋昭見之于《班彪集》。今《漢書敘錄》無馮商,則班固《目錄》不為《漢書敘錄》,因班固曾于宮內校書,此“班固《目錄》”可能是指其整理馮商所續《太史公書》的書錄,或者為“班彪《目錄》”之訛。
孔穎達《尚書正義·堯典》曰:其百篇次第,于《序》孔、鄭不同……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23]
聞思認為“賈氏所奏《別錄》”乃為劉向所撰《別錄》[24],其說值得商榷。我們先看《漢書》的如下一段記載: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征,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后樊并謀反,乃黜其書。[1]
根據《漢書》的這段記載,百篇《書序》最早出于張霸,但成帝時張霸獻書已廢。再者,據蔣善國《尚書綜述》考證今古文《尚書》皆有《書序》并行,百篇《書序》在廢張霸《百兩篇》后再次被提到已經是平帝以后的事了,那時校書早已結束。[25]則劉向校書沒有理由將百篇《書序》記入《別錄》。從《漢書·藝文志》可知,內府有劉向《別錄》之書留存,并且不大可能是因賈逵所獻而留存,所以此《別錄》非劉向《別錄》之書。進一步講,它也不大可能是劉向所作《古文尚書敘錄》,因為劉向敘錄載在《別錄》之書,不需要賈逵上奏,并且細玩文義,“奏”一般指自作,如果是劉向所作,用“上”或者“獻”應該更恰當。那么此《別錄》只能是賈逵所作《古文尚書敘錄》,東漢馬融、鄭玄所傳《古文尚書》有百篇《書序》,即疑是賈逵整理編次并作《敘錄》之本,這也正是孔穎達稱“賈氏所奏”的原因。
此兩處“別錄”即是班彪所作《續太史公書敘錄》以及賈逵所作《古文尚書敘錄》,由于離書別行,所以稱為“別錄”。劉向《別錄》的名稱取義正源于此。
[1]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1701,1715,3607.
[2] 章太炎全集(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81.
[3]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4] 呂紹虞.中國目錄學史稿[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5] 李解民.《別錄》異稱考[J].文史,1994(29):58.
[6] 蕭統.文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50.
[7] 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7:660.
[8] 余嘉錫.世說新語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3:125.
[9]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7:627.
[10] 釋道宣.廣弘明集[M].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2:52 卷:209.
[11] 宗懔.荊楚歲時記[M].影印明寶顏堂秘笈.上海:文明書局,1922:6.
[12] 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991,992,288,1302.
[13] 虞世南.北堂書鈔[M].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212 冊:471.
[15] 歐陽詢.藝術類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184,983.
[16] 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974.
[17]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888冊:287.
[18]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4.
[19] 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1342.
[20] 徐堅.初學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4:160.
[21] 王欽若.冊府元龜[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6965.
[22] 余嘉錫《.漢書藝文志索隱》選刊稿(序、六藝)下[A].中國經學(三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6.
[23] 孔穎達.尚書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8.
[24] 聞思“.賈氏所奏<別錄>”辨[J].文史,1990(33):200.
[25] 蔣善國.尚書綜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