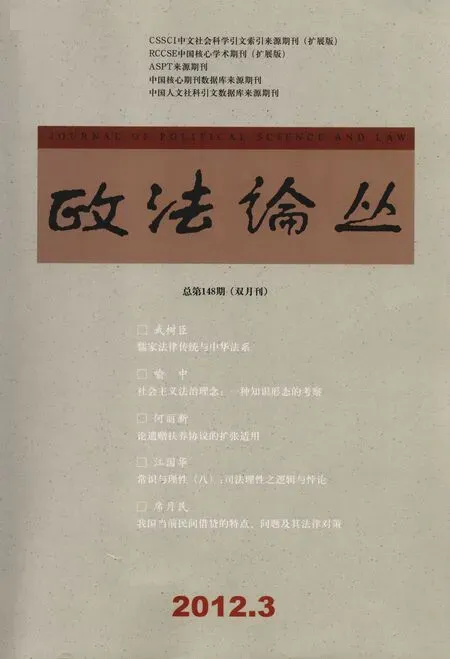我國當前民間借貸的特點、問題及其法律對策
席月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北京100720)
2011年,我國浙江、江蘇、福建、河南、山東、內蒙古等省區接連發生民間借貸信用危機,出現了債務人出逃、中小企業倒閉等事件,對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了較大沖擊。由于在短期內起訴到法院的相關糾紛案件大量增加,最高法院及時發出了妥善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的通知以及司法建議。①雖然政府的最終介入及其扶持政策暫時穩定了市場信心,但民間借貸的制度風險及其法律規制問題已然無法回避。這一危機表明,法律的阻嚇作用因其內在的不完備性受到明顯削弱,司法機構利用有限的剩余立法權進行能動司法實非長遠之計。加強監管立法和監管機構主動執法,依法規范民間借貸行為,嚴厲打擊高利貸,已成為金融生態建設中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必然選擇。
一、我國當前民間借貸市場發展狀況與突出特點
(一)民間借貸進入高級階段,其產生發展具有內生化特點
民間借貸在我國自古就有。我國春秋時期已有放債取利的記載,[1]P35隨后的歷朝歷代,民間借貸也一直存在著。尤其是明清時期,錢莊、票號、典當行等成為其主要組織形式。新中國成立后,計劃經濟時期雖建立了高度集中統一的國家銀行信用,但個人之間仍存在著互助型臨時小額資金借貸。20世紀80年代中期,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私人錢莊、合會、標會、搖會、抬會等民間融資形式。特別是浙江溫州等地,在中小企業創辦和發展過程中,民間借貸十分活躍。[2]P263-26420世紀90年代末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民間借貸開始受到國家嚴格管制,但進入21世紀后,民間借貸的重要作用被重新認可,隨著2005年國家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2010年國家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民間借貸再次活躍,成為眾多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當前,民間借貸的發展已經進入高級階段,其一改初級階段的無組織性、一次性和分散化特點,表現出交易上的有組織性、連續性、集中性和專業化特征。②總體而言,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體系之外自發形成的、受資金供需規律自由支配的、一種非標準化的資金融通活動,其產生和發展具有內生化的特點,完全取決于市場資金供求雙方的意愿與合意,能快速適應和滿足民間投融資需求。
(二)民間借貸資金供需兩旺,其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特征
實踐證明,單靠正規金融無法滿足社會日益多樣化的投融資需求。[3]長期以來,我國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型微型企業融資難問題一直突出,受城鄉二元結構與正規金融的偏好影響,其很難得到銀行間接融資支持和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受生存壓力制約選擇民間借貸實為無奈之舉。同時,2010年國家對非公有資本金融政策的調整正向激勵了民間借貸活動,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直接加大了民間借貸的市場供給。而從資金需求角度看,隨著國際上主權債務危機的不斷升級,我國經濟受到的不利影響持續加深,企業的用工成本增加,原材料價格上漲,節能減排壓力增大。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市場萎縮,資金緊張,中小企業直接面臨生存困境。尤其在銀行信貸收緊的情況下,企業為脫困不得不選擇民間借貸,從而導致民間借貸市場異常活躍,借貸利息一路瘋漲。民間借貸市場在吸引來眾多個人和家庭資金的同時,也吸引來一些上市公司、銀行、國企的資金,甚至一些公務員也積極參與其中。在高息和資金需求饑渴等因素作用下,有些人甚至將借入資金又快速轉手借出進行漁利。民間借貸市場規模的擴大以及參與主體的多元化和廣泛化,為企業資金鏈斷裂最終引發信用危機埋下了伏筆。
(三)民間借貸走紅網絡經濟,其交易形式實現電子化轉型
近年來,民間借貸走紅網絡經濟,使傳統的民間借貸業務被搬到網絡平臺上進行,民間借貸逐漸失去其隱蔽性,有關交易認證、記賬、清算和交割等均通過網絡完成,借貸雙方足不出戶即可實現借貸目的,快速完成交易。目前,網絡借貸資金主要用于個人初期創業、短期信用卡資金周轉或裝修、購物等消費領域。雖然其交易額度受到一定限制,但因雙方屬于無擔保的信用借貸,因而在實踐中還是倍受推崇的。以人人貸為例,作為實名認證平臺,用戶可以在該平臺上獲得信用評級,發布借款請求;也可以把自己的閑余資金通過該平臺出借給信用良好的個人。從其貸款審核與保障看,該平臺在審核借款項目時,要求借入者把身份證掃描上傳,提交信用報告、工作認證、學歷認證、房產證明、結婚證書以及收入認證等,并按照自己的信用審核標準和方法,對借款用戶進行信用風險分析及信用等級分級,同時通過包括貸前審核、貸中審查和貸后管理在內的自身風險管理體系,控制借款逾期違約的風險。③除人人貸外,我國還有宜信、拍拍貸、天天貸、搜好貸、e借通、紅嶺創投、融資城等網絡借貸平臺。客觀地看,網絡民間借貸在我國的發展目前尚處于初級階段,其中不乏爭議存在。有些人將其譽為“網絡版孟加拉鄉村銀行”,認為這是一種全新的金融模式;也有人提出,處在監管空白下的網上借貸,無疑是金融詐騙的滋生地,是高利貸的溫床。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網絡實名制的推行,民間借貸交易方式的電子化轉型正在成為一種新趨勢。
(四)民間借貸相關立法滯后,其法律規則暴露零散化缺陷
從根本上說,民間借貸的正當性,源自《憲法》中有關公民合法財產權利保護的基本規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后完成了金融體系市場化和金融機構商業化的蛻變,金融法律體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有關民間借貸的立法卻一直滯后于社會實踐,相關法律規則散見于《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法》、《擔保法》、《刑法》以及《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貸款通則》等法律、法規和規章中。其中,民法的規定認可民間借貸的合法地位,為其提供了一定保護;刑法的規定側重于打擊關聯犯罪,盡力消除非法民間借貸的副作用;經濟法的規定偏重于政策性一面,出于金融安全和穩定考慮,基本采取嚴格限制甚至否定態度。通觀現有規定,我國《民法通則》相對比較原則,只規定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對此并無具體的解釋性條款。我國《合同法》雖有借款合同一章,但民間借貸合同卻被局限于自然人之間的要物合同,并實行無息推定原則。至于自然人與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民間借貸合同在該法中并無規定。我國《物權法》和《擔保法》確立了民間借貸合同的擔保規則,債權人可以設定保證、抵押、質押、留置以及定金等擔保方式。我國《刑法》主要規定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集資罪等罪名,著力打擊關聯犯罪。國務院《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旨在取締非法金融機構及其業務活動,實踐中成為認定民間借貸行為非法或無效的最主要依據。《貸款通則》屬于部門規章,明令禁止非金融企業從事借貸行為。此外,還有最高法院的一些司法解釋和批復意見。民間借貸法律規則的零散化和不協調,模糊了實務中處理相關糾紛案件時的合法性標準,凸顯了我國民間借貸活動的制度性風險。
(五)民間借貸市場監管缺位,其法律地位陷入尷尬化境地
在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民間借貸基本游離于正規金融體系之外,不受國家信用控制和監管機構的直接管制。1998年,國務院發布《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標志著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建立起了有關民間借貸行政取締與刑事懲罰相結合的雙重管制模式。該辦法明定未經批準擅自設立從事或主要從事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融資擔保等金融業務活動的機構為非法金融機構,明定未經批準擅自非法發放貸款等活動為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明定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由中國人民銀行予以取締。1999年,央行對該辦法的實施做出了具體解釋。④隨后,2004年又把取締資格移交給了銀監會。⑤目前看來,取締辦法本身體現了國家對民間借貸的壓制性政策,一刀切的結果徹底使民間借貸的法律地位陷入尷尬,即便僥幸存在也失去了市場監管。2003年“孫大午事件”⑥等即為其中的典型案例。對民間借貸采取的壓制性政策,不僅導致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發展,降低了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而且還進一步增加了我國金融體系運行的風險,抵消了宏觀調控的實際效果,并且也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公平價值目標的追求。[4]應該說,2011年這場民間借貸信用危機,正是民間借貸市場監管缺位的直接結果。取締辦法忽視了民間借貸具有內生性、正當性、補充性及其需要監管的一面,由于監管立法滯后,實踐中不但使監管主體和監管規則缺失,而且造成民間借貸利率水平高企,投機盛行,救濟乏力,個別地區民間借貸資金流向六合彩、賭博等非法領域,并有借助黑社會勢力暴力追貸的現象出現。與此同時,民間借貸在正規金融體外循環,直接弱化了國家產業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由于民間借貸行為存在交易隱蔽、監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確定、風險不易控制等特征,有些甚至以“地下錢莊”的形式存在,致使非法集資、洗錢等犯罪充斥其間。
(六)民間借貸司法主導突出,其裁判結果依賴指導性解釋
隨著近年民間借貸規模的擴大,大量的民間借貸案件涌入法院,訴訟標的額也越來越大。雖然我國民間借貸立法嚴重滯后但司法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法律的不足,同時還引導、規范并推動了民間借貸的發展。其中,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和批復在該類糾紛解決中填補了民間借貸法律漏洞,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了具體、明確的規則依據。包括:1.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⑦2.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⑧3.1996年《關于企業相互借貸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約定利息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裁決問題的解答》;⑨4.1996年《關于對企業借貸合同借款方逾期不歸還借款的應如何處理的批復》;⑩5.1999年《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6.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7.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8.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上述解釋把合法的民間借貸明確限定在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而對于企業之間的借貸效力問題,則仍然堅持企業之間不得相互拆借資金的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高院近年來也紛紛出臺當地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指導意見。以民間借貸活動相對活躍的江浙滬一帶為例,上海高院2007年制定了《關于審理民間借貸合同糾紛案件若干意見》,江蘇高院2009年制定了《關于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下依法妥善審理非金融機構借貸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浙江高院2009年制定了《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嚴格意義上講,這些指導意見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對地方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卻具有直接規范和指導價值。問題在于,這些指導意見針對民間借貸具體法律問題所給出的處理方案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甚至超越或者背離了現行法律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國民間借貸法律適用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
二、我國當前民間借貸法律規制面對的重點問題
(一)民間借貸組織的主體地位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間資本不斷發展壯大,在促進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繁榮城鄉市場、擴大社會就業方面發揮出了重要作用。2010年《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要繼續深入貫徹落實2005年《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民間資本發起或參與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金融機構,放寬村鎮銀行或社區銀行中法人銀行最低出資比例的限制。應該說,取締辦法雖具有強行法性質,但與當前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政策是相沖突的。表面上看,這是行政執法與國家經濟政策的正面沖突,其實質是國家經濟政策對行政法規的重大突破,而這種突破必須經過法律法規的肯認才能具有強制效力。司法介入使這種沖突某種程度上得到緩解和調和,但實踐中,在民間借貸主體的認定問題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各高級法院的指導意見與國家現行經濟政策之間仍存在一定距離,對民間借貸的法律定性需從根本上做出調整。從目前情況看,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企業之間以及企業之間的借貸行為其實在行為性質方面并不具有明顯的差異性,立約目的、訂約過程、履約狀況以及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等基本相同,人為地基于主體差異而將其割裂為合法與非法,依據并不充分,反而暴露了對其行為評價的忽視,暴露了對法律所具有的保護與懲罰雙重功能的忽視。簡單地取締民間借貸組織并非上策,我國近年來小額貸款公司、汽車金融公司、消費金融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的涌現就是明證。從世界范圍看,各國在民間金融制度設計上都隱含著民間金融自由的法律取向。雖然美國特別重視監管制度的完善,而英國的市場選擇、德國的法人化模式和法國的“聯邦式”十分強調民間金融的組織,但是其最根本的追求都不是取締民間金融,而是用立法確立民間金融的法律地位。[5]
(二)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認定問題
民間借貸的存在是市場化選擇的必然結果。由于傳統意義上的金融監管難以跟蹤其運行過程并對之有效約束,因而其活動往往比受國家管制的正規金融具有更強的市場性。民間借貸的市場性決定了其對私法制度的依賴,對契約自由和誠實信用原則的膜拜。由于我國《合同法》對民間借貸合同的調整僅鎖定于自然人之間,因而司法實踐中,在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認定問題上便出現了多重標準。按照我國《合同法》第52條第(五)項的規定,只要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即應認定為無效合同。這里的“強制性規定”,被最高法院解釋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而事實上,除了我國《刑法》對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金融犯罪有所規定外,并未見其他現行法律、法規有針對民間借貸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司法實踐中,1999年最高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是認定民間借貸合同效力的重要依據之一,但該批復只列舉了四類非法借貸關系,其對實踐中出現的其他民間借貸合同顯然無能為力。在前文提到的江浙滬三地高院的指導意見中,在這一問題上也遠未達成共識。只有江蘇高院列舉了無效民間借貸的情形,具體包括:以“標會”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數人非法籌集資金的行為;以向他人出借資金牟利為業的“地下錢莊”等從事的借貸行為;以及其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借貸行為。該院同時列舉了非金融企業有效的借貸行為類型,具體包括: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募集資金的;為企業的生產經營需要向特定的自然人進行的臨時性小額借款;企業非以獲取高額利息為目的,臨時向自然人提供的小額借款。浙江高院強調指出,自然人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中,企業將借款資金用于合法生產經營活動,不構成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金融犯罪活動的,不宜認定借貸合同無效。上海高院對該問題則未提及。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認定事關當事人的切身利益,目前在認定標準上的不統一,不利于對民間借貸的引導、規范和保護。
(三)民間借貸利率的法律管制問題
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中小企業通過國有商業銀行融資的平均利率為8%左右,通過股份制銀行融資,利率超過了10%,而通過民間借貸方式,利率高達35%。[6]央行溫州中心支行監測統計,溫州民間借貸年化最高利率在40%左右。一些地方的民間拆借年息甚至超過100%,達到近年來的最高水平。民間借貸利率高,使中小企業融資成本明顯上升,因高利貸而引發的血案也不斷出現。為遏制高利貸和惡勢力蔓延,上海嘉定公安分局還專門抽調精干人員組建了“打擊高利貸辦公室”,創造性地設立了全國公安系統中絕無僅有的特殊機構。[7]然而,究竟如何界定高利貸行為,民間借貸利率受保護的法律邊界在哪里,目前在實踐中仍然存疑。我國《刑法》及其修正案中除了“高利轉貸謀利罪”以外,并沒有其他刑法條文直接將高利貸定性為犯罪。2010年,南京出現首例高利貸入罪案,法院將高利貸以非法經營罪判刑定讞,認為高利貸行為屬于違反國家規定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8]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確立了民間借貸利率的具體限制標準,即民間借貸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最高法院的這一規定,通常被看作是認定是否屬于高利貸的具體標準。?但問題在于,除現有規定對高利貸打擊不力外,變相高利貸行為的認定及處罰也不夠具體明確,如逾期利息與約定違約金能否超出四倍,超出四倍利率的部分當事人自愿支付是否應受保護等。
(四)網絡借貸平臺的風險控制問題
網絡借貸平臺的定價機制靈活,在提高風險覆蓋水平和發揮價格篩選功能上優勢明顯。不同主體、用途、數額、期限及行業的民間借貸,其利率水平存在著一定差異,呈現出較大彈性,投融資雙方都可以基于平臺的便利性隨時捕獲信息,做出適合自身的投融資選擇。然而,由于網絡借貸平臺公司在我國尚處在監管真空地帶,因此,其風險控制問題尤為突出:一是平臺公司本身可能不具有合法資質。如有的網站可能未在工商、通信管理以及公安等部門辦理注冊登記,或者登記資料不真實。二是平臺公司本身可能會涉嫌詐騙。盡管多數聲稱只提供借貸居間服務,不吸儲不放貸,但不排除個別網站通過收取保證金或服務費等方式從事金融詐騙活動。三是貸款人很難控制交易資金安全。由于交易雙方互不相識,且缺乏擔保,加上網上資金的技術安全保障可能存在隱患,因此一旦借款人逾期不還款,貸款人救濟和舉證都將面臨實際困難。四是可能遭遇網絡借貸虛假信息。一些網站提供的借貸信息,盡管都強調“低息”、“免抵押”等誘人條件,但不少借貸信息中聯系地址模糊,有的只留有QQ號或手機號,從而可能陷入欺詐。五是借款人可能遭遇高利貸陷阱。一些投機者利用網絡借貸平臺蓄意從事高利貸活動,借款人稍有閃失即可能背負巨額債務,導致麻煩纏身。六是平臺公司可能演化為非法金融機構。不排除平臺公司在業務經營中演變為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非法金融機構,甚至變成非法集資。七是平臺公司可能隨時主動或被動關閉網站。綜上,有效控制網絡借貸平臺的風險,并防止此類風險向銀行體系轉移,已成為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現實問題。
(五)民間借貸交易的信息監測問題
加強民間借貸交易的信息監測日益重要。目前,民間借貸中不但偷逃稅問題嚴重,而且在國家對房地產及“兩高一剩”行業?的調控政策趨緊背景下,民間資金可能通過民間借貸市場流入限制性行業,使宏觀經濟調控效果被打折扣。針對金融調控所面臨的新環境和新要求,2011年央行提出了“社會融資總量”這一概念,并在多種場合頻繁提及,而信貸總量控制卻被悄然擱置,這一轉變值得特別注意。社會融資總量是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總量指標,其具體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9]央行強調“社會融資總量”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信貸規模”的做法,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2010年銀行信貸以外的融資方式發展很快,銀行表內貸款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占比在下降。同時,銀信理財合作中的“表外信貸”出現快速增長,發行股票和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穩步擴大。二是商業銀行資金運作能力明顯提高,管理層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控制越來越難。商業銀行既可以通過發行債券和股票來補充資本金,也可以通過在貨幣市場拆借來調節資金頭寸,還可以通過在貨幣市場融資的方式來調節自身頭寸。[10]從長期來看,隨著金融改革創新的深化,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體系將發生變化,直接融資規模及所占比重會逐漸增加。“十二五”期間,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動,直接融資將會得到進一步發展,從調控銀行信貸總量到控制社會融資總量已成為一種發展趨勢。由于長期以來我國資金流量表的統計滯后,因此,加強民間借貸交易的信息監測和分析已成為社會融資總量統計分析的要務之一。銀監會等相關部門應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實時民間借貸動態信息監測體系,定期對其資金規模、來源、流向、分布以及現行的利率和市場風險等進行監測、分析和評估,主動把握民間借貸資金走向,及時發現并解決問題,引導民間借貸市場健康發展,并適時制定法律規則進行制度約束。
三、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現實選擇
(一)盡快出臺《放貸人條例》,加強對民間借貸市場的主體監管
隨著2008年5月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推出,民間借貸在監管層開始獲得一定程度的肯認。小額貸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業法人與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不吸收公眾存款,專門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非金融機構,無需辦理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試點至今,小額貸款公司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金融機構信貸資金的不足,但問題在于,由于國家一直未出臺專門立法,因此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前景不夠明朗。近年來,《放貸人條例》一直被寄予厚望。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2007年央行專門成立課題組研究起草《放貸人條例》,以期引導和規范民間借貸的發展,使一批符合條件的放貸人注冊放貸,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2009年,國務院法制辦將《放貸人條例》列入了立法工作計劃,明確要抓緊研究、待條件成熟時提出。然而,此后連續兩年的立法項目中,《放貸人條例》接連被擱置,這不免使相關民間借貸主體以及中小企業頗為失望。
目前看來,盡快出臺《放貸人條例》,加強對民間借貸市場的主體監管已經刻不容緩。從國際經驗看,在銀行業金融機構之外,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通過專門立法允許放債人(money lenders)進行專業的放債活動。如英國1900年的《放債人法》(Money Lenders Act)、日本1968年的《放貸業務法》(Loan Business Act)、香港地區1980年的《放債人條例》(Money Lender Ordinance)以及南非2007年的《國家信貸法》(National Credit Act)等。[11]經驗表明,通過專門立法完善民間借貸主體制度,規范和監管民間借貸行為,豐富和完善多層次、多元化借貸體系,是依法保護包括小額貸款公司在內的各類民間借貸主體合法經營行為的需要,這不但有利于改變民間借貸市場的監管缺位現狀,而且有利于降低民間借貸潛藏的巨大信用風險,有利于依法維護企業生產經營和社會環境的穩定。
就《放貸人條例》的制度設計而言,在有關市場準入條件、利率以及稅收政策等幾個主要問題上,應合理吸收小額貸款公司的政策性規定,充分體現寬松、優惠的導向;應合理確定民間借貸主體的投資人資格、業務范圍,規范放貸資金的來源和運用;應明確要求建立財務會計制度、貸款管理制度、資產分類和撥備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風險控制制度等,并明晰單一客戶放貸比例、資產負債比例、計提風險準備金等風險管理要求;要對貸款利率、資金流向等進行跟蹤監測,并規定放貸人有義務定期報告基本業務信息,將其全面納入信貸征信系統;要建立健全市場退出機制,明確民間借貸主體的法律責任;要建立健全民間借貸糾紛防范和解決機制,防范可能引發的群體性、突發性事件等。
與此同時,還需要及時修改前述取締辦法,取消對非法發放貸款的限制,合理劃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變相吸收公眾存款行為、非法集資行為等與合法民間借貸行為之間的界限,依法制裁金融違法行為;修改《貸款通則》,廢止其中關于禁止非金融企業之間借貸的規定。
(二)適時修改《民法通則》、《合同法》以及《擔保法》等民事法律,注重對民間借貸交易的合同規范
在深化金融改革的過程中,我國需要建立一個多種信用機構、多種信用工具、多種信用形式并存的復合型金融體系。民間借貸優勢明顯,對民間借貸關系的調整和保護,顯然離不開民法部門。有關民間借貸合同的訂立、內容、效力、履行、擔保、解除、終止等法律問題,均需要《民法通則》、《合同法》以及《擔保法》等民事法律在私法體系中作出詳細周密的規定。如前所述,雖然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中對民間借貸問題有所涉及,但其不足之處在于,對民間借貸合同關系的界定不夠清晰、完整;對民間借貸合同效力的規定不夠細致,尤其是對無效合同的列舉不夠全面、統一;有關自然人與企業之間以及企業相互之間的借貸關系缺乏明確規定,尤其對企業之間資金拆解行為一概持否定態度;對怠于辦理民間借貸抵押登記的行為缺乏救濟,抵押登記時應否進行公證前置或批準前置不夠確定,諸如此類的問題造成司法實踐中過分依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和地方高院的指導意見的現象,致使民間借貸當事人難以依法開展借貸活動并切實保護自身利益。為使民事法律規則體系盡快擺脫這種不確定性和不系統性,必須適時修改《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等民事法律,吸收現有司法解釋和指導意見的合理規定,有條件地承認企業間借貸的合法性,并具體從貸款額度、期限、利息、擔保、登記以及資金來源等方面做出特別規定,同時要制作合同示范文本,加強對民間借貸交易合同及其擔保的法律指引和規范,加大對擔保機構的扶持力度,建立統一的民間借貸擔保登記制度。
(三)及時補充《刑法》罪名,強化對高利貸犯罪行為的刑事制裁
高利貸的社會危害有目共睹,但一直以來,我國《刑法》并沒有明確將高利貸行為入罪,致使各地司法機關在打擊該類活動時常常陷入無法可依的窘迫境地。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刑法學界便開展了對“高利貸”入罪的理論研究。?近年來,將高利貸入罪的呼聲越來越高。?《刑法》中涉及高利貸行為的有兩個具體罪名,其一是高利轉貸罪,即指借款人套取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后高利轉貸他人;其二是賭博罪,在賭場內放高利貸的,以賭博罪的共犯論處。?這兩個罪名只解決了高利貸中的兩種特殊形式的定罪處罰問題,并未從根本上解決高利貸的刑法適用問題。司法實踐中,武漢、南京、上海等地法院將高利貸行為認定為非法經營罪,定罪依據是《刑法》第225條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這種做法受到了廣泛質疑,在罪刑法定原則下,這樣難免會使非法經營罪有被劃定為小口袋罪之嫌。[12]
用非法經營罪來規制民間高利貸行為,一方面反映了非法經營罪本身所具有的“口袋”功能,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運用現有《刑法》條款去規制民間高利貸行為確實存在一定的障礙。[13]因此,及時補充《刑法》罪名,明確規定“高利貸罪”,強化對高利貸犯罪行為的刑事制裁尤為重要。從其犯罪構成看,宜將該罪歸入《刑法》第三章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中。作為違反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組成部分,高利貸犯罪從其本質上說,應當屬于數額犯。在具體定罪中,應當將其定罪標準分為非法放貸額和非法獲利額兩部分,只要有一個達到標準,即可定罪。即使行為人沒有獲得利益,如果非法放貸額達到一定標準,亦可定罪量刑。同時,應當設置從重處罰條款,對與黑惡勢力相勾結或直接是黑惡勢力的斂財手段的,能夠或采取犯罪手段索債、逼債的,或為他人的犯罪行為提供資金的,以及造成被害人死亡等嚴重后果的,應當在量刑時從重處罰。[14]
注釋:
①201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同時向有關國家機關和部門發出關于規范公務員參與民間借貸活動的建議、關于加強民間借貸規范監管的建議、關于有條件放開企業間借貸的建議、關于完善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的建議、關于規范國有資產轉讓行為的建議、關于制定特殊交易登記辦法的建議等司法建議。
②從現有的文獻看,民間借貸隨著經濟發展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一是屬于初級階段類型的無組織民間借貸,其交易特點是一次性和分散化;二是屬于高級階段的有組織民間借貸,其交易特點是連續性、集中性和專業化。參見陳蓉:《我國民間借貸研究文獻綜述與評論》,《經濟法論壇》第四卷,群眾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頁。
③人人貸的借貸流程包括借入者發布借款列表、借出者競相投標、借入者借款成功、借入者獲得借款以及借入者按時還款。如果用戶逾期未歸還貸款,該平臺貸后管理部門將第一時間通過短信、電話等方式提醒用戶進行還款;如果用戶在5天內還未歸還當期借款,則將會聯系該用戶的緊急聯系人、直系親屬、單位等督促用戶盡快還款;如果用戶仍未還款,則交由專業的高級催收團隊與第三方專業機構合作進行包括上門等一系列的催收工作,直至采取法律手段。參見《人人貸平臺機制》、《貸款審核與保障》,2011年11月27日訪問,人人貸網站:http://www.renrendai.com/aboutP2P.action.
④參見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取締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中有關問題的通知》。
⑤參見《關于監督實施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清理》(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04]第20號),附件二,第9頁。
⑥孫大午是河北徐水縣知名民營企業大午集團的董事長。大午集團從事畜牧業和農產品加工業,因長期無法從銀行獲取貸款,轉而采取向親朋好友、員工甚至向附近村莊的村民打借據的方法募集資金。孫大午于2003年7月被捕,并被指控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同年10月被當地法院判決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罰金10萬元。
⑦該解答對名為聯營實為借貸的行為作出了規定。
⑧該意見把公民之間的借貸糾紛,公民與法人之間的借貸糾紛以及公民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糾紛,作為借貸案件受理。
⑨該解答對企業之間相互借貸的出借方或者名為聯營、實為借貸的出資方尚未取得的約定利息,明確由人民法院依法向借款方收繳。
⑩該批復再次強調企業借貸合同違反有關金融法規應屬無效合同,約定利息應予收繳。
?該批復進一步限定了自然人與企業之間合法借貸關系的范圍,明確其中四類關系屬于非法借貸,不受法律保護。這四類非法借貸關系分別是:企業以借貸名義向職工非法集資;企業以借貸名義非法向社會集資;企業以借貸名義向社會公眾發放貸款;其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行為。
?該解釋進一步明確了擔保規則體系
?該解釋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非法集資犯罪作出了細致規定。
?該解釋從十個方面對民間借貸案件的審理作出了規定,強調各級法院要高度重視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判執行工作、做好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立案受理工作、依法懲治與民間借貸相關的刑事犯罪、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加大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調解力度、依法保護合法的借貸利息、注意防范制裁虛假訴訟、妥善適用有關司法措施、積極促進建立健全民間借貸糾紛防范和解決機制以及加強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新情況新問題的調查研究等。
?參見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對企業間借貸問題的答復》(銀條法[1998]13號)、《關于對銀行職工參與企業非法借貸有關法律問題的答復》(銀條法[1996]44號)等。
?《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的通知》(銀發[2002]30號)也做出了同樣規定。
?兩高行業即高污染、高能耗的資源性行業;一剩行業即產能過剩行業。
?如陳澤憲:《高利貸犯罪探討》,《政治與法律》1987年第2期;鄒偉、楊靜:《應增設“放高利貸罪”》,《現代法學》1988年第2期;陳興良:《論發放高利貸罪及其刑事責任》,《政法學刊》1990年第2期。
?如徐德高、高志雄:《增設“職業放高利貸罪”確有必要》,《人民檢察》2005年第9期;黃建波:《關于增設高利貸罪的建議》,《人民法院報》2009年11月18日第7版;閔俊芳:《關于增設高利貸罪的立法建議》,《江蘇經濟報》2011年3月16日第B03版;等。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5]3號)第4條。
[1] 葉世昌.中國金融通史(第一卷:先秦至清鴉片戰爭時期)[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2] 楊希天.中國金融通史(第六卷: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3] See Meghana Ayyagari,Asli Demirgüc-Kunt,Vojislav Maksimovic,Formal versus Informal Finance:Evidence from China,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vol.23,2010,p.3048.
[4] 張書清.民間借貸的制度性壓制及其解決途徑[J].法學,2008,9.
[5] 高晉康.民間金融法制化的邊界和路徑選擇[J].中國法學,2008,4.
[6] 工信部:支持中小企業需區別對待[EB/OL].2011年11月29日訪問,中國廣播網:http://gb.cri.cn/27824/2011/11/28/5005s3452871.htm.
[7] 趙進一.“打高辦”:無奈中的創新之舉[J].檢察風云,2011,22.
[8] 孟亞生.再放高利貸判刑定罪沒商量——南京首例高利貸入罪案追蹤[J].學習月刊,2011,2(上半月).
[9] 盛松成.社會融資總量的內涵及實踐意義[EB/OL].2011-12-04日訪問,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http://www.pbc.gov.cn/publish/diaochatongjisi/866/2011/20110217180043605992604/20110217180043605992604_.html.
[10] 李若愚.央行為何注重社會融資總量[N].上海證券報,2011-02-10.
[11] 劉慧蘭.關于完善我國民間借貸法律體系的思考[J].金融發展評論,2010,4.
[12] 張天虹.罪刑法定原則視野下的非法經營罪[J].政法論壇,2004,3.
[13] 劉偉.論民間高利貸的司法犯罪化的不合理性[J].法學,2011,9.
[14] 黃建波.關于增設高利貸罪的建議[M].人民法院報,2009-11-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