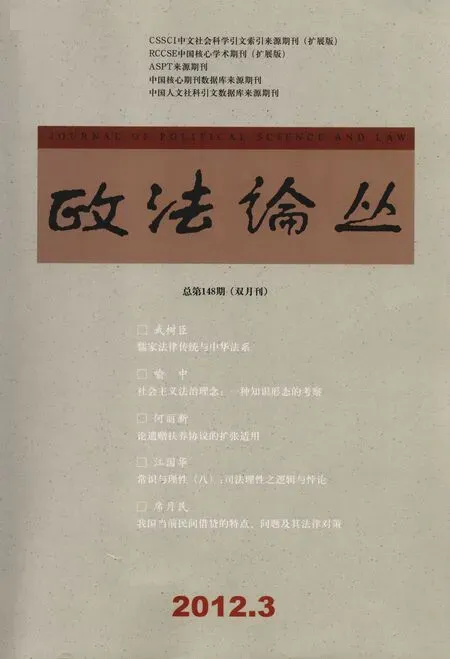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一種知識形態的考察*
喻中
(四川大學法學院,四川成都610064)
一、引論:從知識形態的角度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就法學的知識形態而論,近年來,已經出現了一些旨趣各異的研究文獻。譬如,陳興良認為,由于法的形態包括價值、規范、事實三個方面,因此,法學的形態就包括法哲學、法理學和法社會學,這三種形態的法學知識分別對應于法的價值、規范、事實;三種形態的法學知識相互聯系,構成了一個法學知識的體系。①蘇力以亞里士多德的知識分類理論(詳下)為依據,主張“法學決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理性的、思辨的學科”,“法學是一門具有高度實踐性的學科,它并不只是一些普遍正確的命題構成,而且需要大量的‘實踐理性’,需要許多難以言說難以交流的知識”,[1]這就是說,法學知識包括純粹理性,但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實踐理性與技藝。梁治平著眼于法律人與中國知識界之間的隔膜,論述了律學與法學之間的關系,并認為,“在我們這里,律學的傳統依然強大,從律學到法學的知識轉變遠未完成,這就是為什么‘法學界’與知識界一直彼此暌隔難以溝通。”[2]換言之,法學家應當成為知識分子,法學知識應當與其他知識相互貫通,等等。②已經出現的這些論述,雖然切入點各不相同,關于知識的分類標準也大相徑庭,但是,這些初步的討論還是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反思法學作為一種知識形態的屬性。
既然整體性的法學及其知識形態已經受到了一定關注,那么,新興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個具體的、相對單一的法學主題,它是一種什么樣的知識形態?這是一個疑問。這也許還是法學界、法律界乃至于社會各界共同面臨的一個困惑。在某些法學家的意識或潛意識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似乎染上了過于濃厚的政治色彩,似乎不能歸屬于專業性的法律理論、法學知識。這樣一些法學家立足于專業性的法學立場,對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還沒有產生足夠的思想認同、情感認出。在日常交往過程中,即使是一些法律實務界人士,也僅僅是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個流行一時的政治口號,不太愿意認真對待。雖然,居于權威地位的政治機構一直都在宣揚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但是,當代中國的法律人共同體,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之間,卻存在著一種揮之不去的隔膜感。為什么會形成這種隔膜的心態?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對于知識形態的完整把握,因而對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在知識形態中的定位與歸屬,還沒有自覺而清晰的認知。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為了夯實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種知識的合法性依據、正當性基礎,有必要從知識社會學,特別是從知識類型的角度,來考察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種知識的屬性,其目的就在于弄清楚,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知識形態。本文相信,這種關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知識形態的考察,可以深化我們這個時代對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理性認識、理論認同。為了實現這個預設的學術目標,本文借用了亞里士多德關于知識分類的原創性思想,對知識的三種形態——純粹理性、實踐理性、技藝——分別進行了理論上的辨析。以此為基礎,再來討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三種知識形態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種純粹理性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種實踐理性嗎?以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種技藝嗎?本文希望,通過這樣的分類考察,可以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知識形態和性質,進行恰當的定位。最后,根據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知識屬性,我們還可以對法律人共同體——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種知識的承載者——的社會角色進行探討,以延伸本文的研究視角。
二、純粹理性、實踐理性與技藝:關于知識形態的思考
關于知識的不同類型,代表性的思想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及其《形而上學》。在這本經典著作中亞氏提出了自己的知識形態觀。他在討論“物學”時指出:“如謂一切思想必為實用、制造與理論三者之一,則物學應是一門理論學術”。[3]P118-119他在討論“自然哲學”時又說:“自然學術既非為實用,亦不從事制造,這就成為一門理論學術(凡學術,三者必居其一)。”[3]P222這就是說,亞里士多德眼中的“物學”與“哲學”,都屬于理論學術。關于理論學術與實用學術的區別,亞里士多德還有一個更簡明的論斷:“理論知識的目的在于真理,實用知識的目的在其功用。”[3]P33至于“制造學術”,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更加言簡意賅:“一切制造技術均稱潛能”。[3]P172把亞里士多德的相關論述綜合起來,可以歸納出他的關于知識形態的基本思想:一切人類知識都可以分屬于三類,它們分別是理論知識、制造知識、實用知識。其中,理論知識包括物學、數學、哲學;實用知識包括倫理、政治、經濟等;至于制造知識,則包括建筑、雕塑、音樂、醫學、健身術、衛生等等,它們都屬于技術與藝術。[3]P246
在現代人的視野中,亞里士多德所講的“理論知識”、“實用知識”與“制造知識”,一般被稱為純粹理性、實踐理性與技藝。③不過,無論是純粹理性、實踐理性還是技藝,都是邊界模糊的多義詞。正如波斯納在論及“實踐理性”時所言:“不幸的是這一術語沒有一種標準含義。它最經常是用來指人們用以做出實際選擇或倫理選擇——諸如是否上影院,是否對熟人撒謊——的一些方法。這種意義上的實踐理性注重行動,它相對于以‘純粹理性’來決定一個命題真假、一個論點有效或無效的方法。實踐理性涉及到確立一個目標——愉悅、善良生活或任何其他——和選擇達到目標的最便利手段。”[4]P91-92在這句話中,波斯納一方面強調了實踐理性一詞的多義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實踐理性“注重行動”;至于純粹理性,則主要是指邏輯學或認識論。
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和技藝確實充滿了歧義,④其含義總是變動不居。但是,它畢竟還是一種有價值、有潛力的知識分類理論。為了挖掘這種知識分類理論的理論闡釋能力,為了把這種古老的知識分類理論有效地“用”起來,我們有必要對它們做出進一步辨析。按照本文的理解,這三種知識各有其特點,分而述之則可發現:第一,純粹理性的表現形式是觀察與思考,主要體現為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客體的對象世界之間的關系。作為主體的人在觀察和思考某種對象,但是,人與對象之間的關系僅僅止于觀察與思考,人并不觸動或改變他所觀察、思考的對象。這就是純粹理性。這種知識的典型形態,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金岳霖的知識論,以及亞里士多德的范疇論等等。這種品性的知識就屬于純粹理性,亦即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理論知識或理論學術。第二,實踐理性的表現形式是交往與行動,主要體現為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相互交往關系。用一個流行的哲學詞匯來表達,也可以說是一個事關主體間性的知識。因為,無論是倫理、政治還是經濟,它的本質都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都體現為主體的行動及其對于其他主體的影響。因此,有關主體之間的行動與交往的知識,就可以歸屬于實踐理性。這種知識的典型形態,有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以及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倫理學等等。第三,技藝的表現形式是制作與生成。它主要體現為主體針對某種客觀對象所采取的行動。通過主體的行動,客觀的對象被改變了,這就是技藝的本質。這種知識的典型形態包括建筑藝術、演奏藝術、醫療術、航海術等等。
為了進一步厘清三種知識形態之間的界限與差異,還有必要把這三種知識進行“一對一”的比較。相信在“短兵相接”、“狹路相逢”式的比較與對照中,可以更清晰地凸現出每一種知識的內在本性。
首先,我們來看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之間的差異。兩者之間的差異,盡管很像、但并不是梁啟超所說的“學與術”之間的差異。⑤雖然純粹理性近似于探究原理的“學”,但實踐理性卻不能等同于與“學”相對應的“術”——因為梁啟超所講的“術”,主要是“技藝”。在康德的經典著作中,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分別對應于人的認識能力與人的意志。正如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一書的“導言”中對此所作的區分:“理性的理論應用處理單純認識能力的對象,并且著眼于這種應用的理性批判根本上只涉及純粹的認識能力,因為這個能力激起疑慮,這個疑慮后來也得到證實:這個能力容易逾越它的界限而迷失于不可達到的對象或者甚至相互沖突的概念之中。至于理性的實踐應用,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在這種情況下,理性處理意志的決定依據,而意志或者是產生與表象相符合的對象的一種能力,或者竟然就是決定自身而導致這些對象(不論自然的能力是否足以勝任)的能力,亦即決定其自身的因果性的能力。”[5]P13在綜合吸收這些見解的基礎上,本文認為,這兩種知識之間的差異在于“場域”的不同。其中,純粹理性是主體對于客體或對象的察看。這里的主體,是指作為純粹理性之載體的人(譬如亞里士多德本人);客體則是某種或某個有待探究的對象、事物。當然,作為探索、察看對象的“事物”是多樣化、多元化的——既可以是“范疇”,也可以是“時間”,還可以是人自身。不過,無論是哪種對象,在主體面前都是自在地呈現出來,主體并不影響或觸動對象;對象也不會反作用于主體。但是,實踐理性所寄生的“場域”則是主體與主體之間,而且,主體與主體之間是互動的,是相互影響的。因為,一個主體的具有實踐性的行為,總是會影響到另一個主體。譬如,“父慈子孝”作為一條倫理規范,就體現了父與子兩種主體之間的交往關系,父如何對待子,子如何對待父,都具有倫理規范的意義。倫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實踐理性,都存在于主體與主體之間這種特定的“場域”之中。
其次,再看純粹理性與技藝的差異。表面上看,這兩種知識似乎都體現了主體與對象之間的關系。但是,這兩種知識也具有質的差異。一方面,是主體作用于對象的方式不同。就純粹理性而言,主體作用于對象的方式是察看、審視、琢磨、思考。對于主體的這種察看,對象通常是沒有知覺的。譬如,被察看的范疇、天體、時間等等,它們就不會因為主體的察看而有任何反映。即使是對人或神的察看,被察看的人或神也會處于無知無覺的狀態。譬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就可以歸屬于純粹理性,盡管它察看了人的心理狀態,但是,由于被察看的對象是不特定的,因而,在通常情況下,它并不會對人產生觸動。但是,就技藝而言,主體作用于對象的方式則是觸動、影響、修改、完成對方,對象會因主體的行為而發生某種改變。譬如,醫療術之所以成為了一種技藝,就是因為它會修正某個對象的健康狀況。即使是心理分析醫師,在實踐中,也會對他的患者或客戶產生某種影響,譬如,緩解對方的焦慮或緊張情緒。另一方面,這兩種知識之間的差異還體現在:兩者的個性化程度不一樣。在通常情況下,純粹理性具有客觀的品質,便于交流,便于傳播。譬如代數、幾何,就屬于典型的純粹理性,這樣的知識,最容易體現出知識本身的“純粹性”。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有符號邏輯,都可以體現出純粹理性的“純粹性”。這樣的純粹理性,作為一種知識,無論掌握在誰的手上都是一樣的。但是,作為技藝的知識,通常都會體現出明顯的個性特征。譬如醫療術,嚴格說來,任何兩個醫生的醫療術都不會是絕對等值的;任何兩個醫生的醫療術都會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差異,哪怕是極細微的差異。這就是技藝的個性特征。作為技藝的鋼琴演奏、文學創作、烹調、繪畫、駕駛、航海等等,都會打上“技藝”這種知識的承載者的個性特征。因此,技藝雖然也是可以傳授的,但是傳授技藝(譬如彈琴)與傳授純粹理性(譬如幾何),還是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前者通常會走樣——無論是變得更好、變得更壞,還是變成無從判斷好壞的另一種風格。至于后者,則通常不會走樣——無論是誰,都無法使二加二不等于四。
最后,是實踐理性與技藝的差異。兩者之間最明顯的差異也是“場域”的不同。如前所述,作為一種知識形態的實踐理性,常常寄生于主體與主體之間,因而具有主體間性。但是,技藝卻并不寄生于主體之間(當然也有例外,譬如兩人合作的相聲或雙人舞),而是由特定的主體獨立承載,而且還體現為特定主體所具有的一種稟賦,——或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潛能”。因而,實踐理性作為知識的一種類型,常常要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過程中來驗證。譬如經濟學知識,就需要在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過程中來檢驗。但是,技藝則可以由這種知識的承載者獨立地展示出來。譬如,掌握了某種醫療術的醫生可以把傷口治愈,掌握了某種雕刻術的技師可以雕出一朵玻璃花,等等,都可以體現出技藝的主體性。除了所寄生的“場域”不同,這兩種知識的評價標準也不一樣。通常說來,實踐理性的評價標準是恰當。這里的恰當,就是被其他主體接受、認同。因為,實踐理性主要在于處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行動關系。因而,這種知識的核心價值,就在于消除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障礙,為交往創造出更多的機會與空間。換言之,得到參與交往的相關主體的接受與認同,就是這種知識的核心價值。但是,技藝作為一種知識,主要在于滿足特定主體的特定需要。譬如,醫療術主要在于滿足患者的需要,演奏技藝主要在于滿足愛樂人的需要,航海術在于滿足遠洋者的需要,裁判術在于滿足人們對公平正義的需要。可見,技藝作為一種知識,其評價標準,主要在于這種知識能否滿足主體的特定需要。即使是不同的主體對同一種技藝的評價各不相同,也無損于技藝的價值。譬如,臭豆腐的制作技藝,在不喜歡臭豆腐的人看來,就沒有價值;但是,在喜好臭豆腐的人看來,那就是一種有價值的技藝。
以上分析表明,由亞里士多德開其端緒的知識分類理論,是可以進行“銳化”處理的,是可以“翻新”的,它的理論闡釋能力也是可以進一步挖掘的。在辨析了三種知識的性質和差異之后,我們就可以在此基礎之上,對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知識形態、知識屬性做出初步的考察。
三、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種純粹理性嗎
如果我們把純粹理性視為“理論學術”、“理論知識”的同義詞,那么,如前所述,亞里士多德是以“真理”作為純粹理性的目的。后來,康德專門寫成了《純粹理性批判》一書,根據羅素的歸納,“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證明,雖然我們的知識中沒有絲毫能夠超越經驗,然而有一部分仍舊是先天的,不是從經驗按照歸納方式推斷出來的。”[6]P249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所“批判”的“純粹理性”,據本文的理解,其實就是人的純粹的認識能力。
綜合亞里士多德與康德的思想,以及上文對于純粹理性的分析與界定,我們可以發現,純粹理性作為一種知識(譬如,像“二加二等于四”這樣的知識),它具有自足性、普適性,在相當程度上,也具有先天性。按照這樣的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種新興的、具體的知識,雖然明確標出了“理念”一詞;雖然在西方哲學史上,“理念”是一個基石性的范疇,帶有明顯的思辨性,似乎還帶有某種先天性、自足性或普適性。⑥但是,從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實際內容來看,它在整體上,不宜歸屬于純粹理性。為了論證這一判斷,讓我們做一些具體的分析。
首先,依法治國的理念是“從經驗按照歸納方式推斷出來的”,它不具有先天性。從依法治國理念的產生來看,直至20世紀末期,它才在政治與公共領域取得了主導地位;直至2004年,它才正式寫進憲法。在漫長的傳統中國,雖然也有刑、法、律,但在“德主刑輔”、“出禮則入刑”的框架下,德與禮成為了建構文明秩序的主導性規范,刑律則長期處于附屬或從屬的地位。在現代中國,雖然引進了西方傳過來的法治觀念,但在持續不斷的革命時期,依法治國的理念不大可能成為一個實踐中的主導性選擇。從實踐過程來看,只有當高調的革命時期轉向低調的建設時期之后,依法治國的理念才應時而生、應勢而成,上升成為一個主導性的觀念。依法治國理念的孕育、萌生過程表明,它作為一種知識,是特定條件、特定環境的產物,甚至是“痛定思痛”的產物,并不是一個自足的、先天的知識形態。
其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的“執法為民”理念,從思想淵源來看,甚至可以追溯至《尚書》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等思想因子;當然也可以直接追溯至“現代傳統”中的“為人民服務”。這就意味著,執法為民理念是一個古老的文化傳統在當代法治領域內的一個回響。但是,即使它由來已久,執法為民理念亦不能稱為純粹理性,因為它不具有普適性。至少,我們在中華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傳統中,很難找到這樣的主流性的思想傳統。而且,按照當代中國政治上的主流意識形態,“執法為民”、“為人民服務”還是當代中國政治區別于其他政治類型的一個主要標志。譬如,按照《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讀本》中的論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執法為民,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執政理念在法治工作領域的直接體現和最終落實,是執法機關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⑦由于在其他的政治文明形態中,并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等主導性的政治意識形態,這就意味著,作為當代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衍生物的執法為民理念,也是一種個性化、本土化的知識形態,因而也不屬于純粹理性的范圍。
相對于“依法治國”與“執法為民”,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義”理念,也許是最靠近純粹理性的知識形態了。從表面上看,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具有通約性、普適性。但是,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當我們仔細查看這張臉并試圖解開隱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時,我們往往會深感迷惑。從哲學的理論高度上來看,思想家與法學家在許多世紀中業已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不盡一致的‘真正’的正義觀,而這種種觀點往往都聲稱自己是絕對有效的。”[7]P252然而,眾多聲稱“絕對有效”的正義理論卻又是相互歧義的。譬如,柏拉圖的正義觀強調各盡其本份,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強調比例平等,康德的正義觀強調自由,羅爾斯的正義觀強調自由與平等,霍布斯的正義觀強調安全,馬克思恩格斯的正義觀則偏好經濟地位的平等,等等。雖然在這些經典作家的潛意識里,他們的正義理論都試圖闡述一種普適性、自足性的知識形態。但是,倘若把這些變幻無常的正義理論匯聚到一起,人們還是會感到無所適從。換言之,各種各樣的正義理論雖然都立足于終極性的探索,但是,這種“一人則一義,十人則十義”的知識形態,與確定無疑的純粹理性還是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至于服務大局理念,甚至就這個概念本身來看,它都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說法,是立足于司法、法治而對中國文明秩序中政治與司法關系的一種概括。其中,“大局”是主政者確定的,而且是不斷地變遷的;“服務大局”則是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實際承擔的一種政治功能。對于這樣一種理念,一些學界人士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有學者認為,“司法與政治屬于兩個不同的系統,具有不同的目標追求,二者保持適當距離有助于增進政治的合法性。司法相對獨立于政治是司法良好運行的基本前提,通過司法控制政治是現代政治規范發展的重要模式。”[8]這樣的論述在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界極具代表性。這樣的觀點,雖然描述了某種理想化的司法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模式,但卻主要體現了某種流行的西方模式在當代中國學界的折射。考之于實踐領域,“服務大局”恐怕才是對司法與政治關系的一種更加真實的概括:早年,中國的司法要為階級斗爭服務。后來,中國的司法要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現在,中國的司法則在想方設法地“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不僅如此,服務大局的理念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西方的法治實踐。譬如,美國的卡多佐法官作為一個標志性的法律人,就曾以自己的司法實踐服務于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當然,由于中西方對于司法、對于政治的理解都各不相同,譬如,西方的司法并不外在于政治,司法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司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貴族政治”的痕跡,在一定程度上還是約束民主的一種政治裝置,⑧因而,司法服務于政治的方式主要是以“制衡”的方式。相比之下,中國的司法雖然也有政治屬性,也是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卻主要體現為政治的一種方法、手段、路徑,一般來說,對政治并不具有制衡的作用。可見,東西方的司法雖然都有“服務大局”的成分,但是,由于服務的方式各不相同,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服務標準”。這就意味著,服務大局的理念確實是“從經驗按照歸納方式推斷出來的”一個知識點,不宜歸之于純粹理性。
最后是黨的領導。一方面,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經驗;作為一個知識點,它完全源出于當代中國的政治法律實踐。但另一方面,近現代以來,政黨政治已是一種普遍的政治形態,西方政治文明中也有執政黨對于政府的領導。只是,東西方的政黨政治在實踐過程中表現為不同的特征:西方的政黨政治體現為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中國的政黨政治則體現為一個政黨的長期執政。因而,從實質上看,西方也有“黨的領導”——執政黨對國家事務、社會公共事務的領導。而且,西方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演變成為了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競爭、輪流執政;在這個黨與那個黨之間,已經看不出有什么本質上的差異,每個政黨的核心目標,都在于想方設法贏得選民的支持,從而在競選中脫穎而出,成為居于執政地位的執政黨。這就意味著,西方的政黨要成為居于領導地位的執政黨,離不開民眾的支持。與之相類似,中國的執政黨要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也離不開民眾的支持。因此,雖然形式、過程、特點不同,但是,“黨的領導”都體現了中西政治文明實踐過程的一個維度。這就意味著,“黨的領導”是一種可以傳授、可以讓人理解的知識,但又不是一種先天性的、普適性的、像“二加二等于四”那樣的知識。
以上分析表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的“五句話”,基本上都是“從經驗按照歸納方式推斷出來的”,由五句話組成的這個新興的知識體系,從知識形態的角度上看,特別是從它所寄生的語境來看,不宜歸屬于純粹理性的領域。
四、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種實踐理性嗎
如果說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不是一種純粹理性,那么,它是一種實踐理性嗎?對此,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知識形態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體現了實踐理性的特征與屬性。
首先,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個主體間性的概念,體現了實踐理性這種知識形態的特征。
所謂主體間性,主要在于強調不同主體之間的共生性或共同存在,就像海德格爾所言:“由于這種有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來已經總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與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內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9]P138這句漢譯的核心旨意就是,“我”與“他”之間的共同存在。存在主義的另一個代表人物薩特也指出:“我們已知道,他人的實存是在我的對象性的事實中,并通過這一事實明確地體驗到的。而且我們也已看到,我對我自己的為他人異化的反應是通過把他人理解為對象表現出來的。簡而言之,他人對我們來說能以兩種形式存在:如果我明白地體驗到他,我就沒有認識他;如果我認識了他,如果我作用于他,我就只達到他的對象存在和他的沒于世界的或然實存;這兩種形式的任何綜合都是不可能的。”[10]P376在薩特看來,只有突出“我”與“他”的共生性,才可能解除“我”與“他”之間的對抗,才可能走出“他人就是地獄”的泥淖。換言之,主體間性這個新的概念,旨在凸顯多個主體之間的相互關聯、共生性。這樣的思維模式,正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所體現出來的知識屬性。因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突出了三個相互關聯的主體:政黨、人民、國家。其中,“黨的領導”強調了政黨這個主體,“執法為民”既突出了“人民”這個主體,同時也蘊含著“執法為民”的主語——“政黨”,它的意思是,政黨執掌法律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服務大局”之“大局”則是政黨和國家確定的“大局”。“依法治國”的要義,則是政黨領導人民運用法律來治理國家,三大主體都在其中了。至于“公平正義”,則是對作為治國準繩之法律所提出的要求,同時也是為法治設定的目標。正是因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同時強調了三個主體之間的關聯,在通行的文本中,才特別指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屬性。”⑨正是因為政黨、人民、國家之間的共生關系,才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種新的知識體系,體現了主體間性的旨趣。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這種主體間性不同的是,還有一些流行的法治理論,在這些法治理論的知識框架中,主要突顯了“人”這種主體,主要突出了個人的自由、權利、尊嚴,較少注意個人之外的國家、政黨等相關主體,⑩這樣的法治理論,雖然突出了個體的主體地位,但是,它卻僅僅止于一種主體性的概念。
其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個交往與行動的概念,也體現了實踐理性的特征。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既然是一個主體間性的概念,它當然會著眼于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與行動,因而是一種以交往、行動、商談為重心的概念。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實踐理性也可以視為一種交往理性。所謂交往理性,可以理解為:“制度框架層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語言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過消除對交往的限制才能實現。在認識到了目的理性活動的進步的子系統在社會文化方面所起的反作用的情況下,關于適合人們愿望的、指明行為導向的原則和規范的公開的、不受限制的和擺脫了統治的討論,才是‘合理化’賴以實現的唯一手段。一句話,在政治的和重新從政治上建立的意志形成過程中的一切層面上的交往,才是‘合理化’賴以實現的唯一手段。”[11]P76按照本文的理解,政治的合理化源出于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行動,主體的權力轉化為交往權力,主體的重要性轉化為商談與交往的重要性。正是在這樣的視野中,哈貝馬斯根據交往理性與商談理論的內在邏輯,對法治原則的具體內容進行了新的探索,闡述了人民主權、全面保護個人權利、行政合法、國家與社會分離等四大法治原則。[12]P207其中,人民主權原則要求國家權力來源于公民在政治自主性基礎之上的相互交往;全面保護個人權利的原則,主要是對司法權力提出的要求;行政合法原則要求行政權力遵守法律,接受議會和法院的監督;國家與社會相分離的原則,旨在防止社會權力不經過商談與交往就直接轉化成為行政權力。可見,哈貝馬斯提出的法治國原則,與其說是針對法律的原則,還不如說是關于權力的準則。在法治國諸原則中,盡管涉及到權力的各種類型,但是,人民主權原則在其中居于基礎性的地位,其他原則都是人民主權原則延伸、擴展的產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些法治國原則共同構成了一個原則的體系。把哈貝馬斯從商談和對話理論中提出來的法治原則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兩者的具體內容雖然不同,但是,在知識形態這個特定的維度上,卻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都強調了多種主體之間的行動與交往。在哈貝馬斯的法治原則中,強調了國家與社會的交往關系,國家與公民的關系,個體與司法的關系,行政與議會、法院的關系等等。這就是說,法治原則,主要寄生于諸多主體相互交往的關系中。從這個角度來看,哈貝馬斯的法治理論,可謂交往行動與相互商談的理論。?同樣,如前所述,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也聚焦于政黨、人民、國家之間的交往關系,它強調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辯證地統一起來,本質上是要在三種主體之間建立起有效、有序的交往關系。
再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體現的是一種意志,在這個角度上看,它也是一種實踐理性。
康德就把實踐理性歸結為人的意志。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把實踐理性的基本法則定位于:“這樣行動,你意志的準則始終能夠同時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則。”[5]P31這個判斷的意思是,“實踐法則完全出于自身的緣故而決定意志。”[13]P119鄧曉芒也注意到,“在《實踐理性批判》的導言中,康德再次重申了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區別,并且是一開始就重申了這個區別,強調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不同。理論理性處理的是認識能力。……那么實踐理性呢?它處理的是欲望的能力、人的欲求能力,也就是意志,它的最高表現形式、集中表現形式、最純粹的表現形式就是意志、意志能力。”[14]P75換言之,實踐理性不僅表現為主體間性、交往行動,而且還表現為意志。實踐理性的這個品性,恰好反映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一個側面。因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種知識體系,是當代中國的主政者提出來的,直接表達了政治主導者的意志。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五個要素,都寄托了政治主導者對于法治秩序乃至于全局性文明秩序的一種安排。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個理論,但它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相反,它具有強烈的規范意義,是相關主體的行動指南。譬如,主政者應當依法治國,執法者應當執法為民,司法者應當服務大局,等等。如果把“體現主權者的意志”作為法的核心特征,那么,在一定意義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就具有法的意義與功能,至少可以從“軟法”、“不成文法”等相關角度來認知。?對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這個維度,應當給予充分的注意。
最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也體現了實踐理性的特征。
在相當程度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概括了當代中國政治的核心命題: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其中,“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直接成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基本要素,“人民當家作主”則以“執法為民”的形式融入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體系中。從總體上看,“社會主義法治建立在社會主義民主基礎上,并確認和保障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將服務大局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將黨的領導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要求全面服務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及生態文明建設,不斷增強黨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能力,實現了講法治與講政治的統一”,因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具有鮮明的政治性。”?換言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個政治性的概念,按照上文述及的亞里士多德對于實踐理性(實用學術、實用知識)的認知,正好可以歸屬于實踐理性的范圍。?
以上分析雖不可能窮盡,但也大致列舉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實踐理性之間的共通性。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種知識形態,具有實踐理性的特征與品性。
五、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種技藝嗎
如果說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種實踐理性,那么,它同時還是一種技藝性質的知識。
關于技藝與實踐理性的不同,亞里士多德的看法是:“可變化的事物中包括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實踐的事物。但是制作不同于實踐(我們甚至從普通討論中也能看出這種區別),實踐的邏各斯的品質同制作的邏各斯的品質不同。其次,它們也不互相包含。實踐不是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種實踐。例如,建筑術是一種技藝,是一種與制作相關的、合乎邏各斯的品質。如果沒有與制作相關的品質,就沒有技藝;如果沒有技藝,也就沒有這種品質。所以,技藝和與真實的制作相關的合乎邏各斯的品質是一回事。所有的技藝都使某種事物生成。學習一種技藝就是學習使一種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技藝的有效原因在于制作者而不是被制作物。因為,技藝同存在的事物,同必然要生成的事物,以及同出于自然而生成的事物無關,這些事物的始因在它們自身之中。”[15]P171亞里士多德的這段話,主要分辨了技藝與實踐理性之間的差異,同時也指出了技藝的特質,那就是:主體作用于對象,使某種事物生成。正是在技藝的層面上,亞里士多德討論了養成“具體德性”的技藝,以及實現“公正”的技藝;運用這些技藝,都可以使“具體的德性”、“公正”得以養成。
事實上,在亞里士多德關于德性及其養成技藝的論述過程中,我們可以領略到:技藝的核心其實是“分寸”,更簡而言之,是一個“度”。前面我們提到,亞里士多德把技藝的本質歸屬于“潛能”,其根據也許就在這里。因為,只有通過發揮人的“潛能”,才可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度”,才可能免于偏執、極端。譬如,德性要求人們勇敢、節制、明智,但是,勇敢是怯懦與魯莽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節制是冷漠與放縱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明智則是單純與狡猾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等等。實現“中道”的藝術,就是“中庸”、“分寸”與“度”的藝術。因而,“每一個匠師都是這樣地避免過度與不及,而尋求和選擇這個適度,這個不是事物自身的而是對我們而言的中間。如果每一種科學都要尋求適度,并以這種適度為尺度來衡量其產品才完成得好(所以對于一件好作品的一種普遍評論說,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這意思是,過度與不及都破壞完美,唯有適度才保存完美);如果每個好技匠都在其作品中尋求這種適度;如果德性也同自然一樣,比任何技藝都更準確、更好,那么德性就必定是以求取適度為目的的。”[15]P46
這種中道或中庸的技藝,孔子也極為推崇,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道德經》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對于這種尋求中庸的技藝,李澤厚直接就用“度”這個詞來概括。在《歷史本體論》一書中,他開篇就指出,“‘度’來自生產技術。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處’。為什么?因為這樣才能達到目的。”[16]P1就技藝所具有的這些品性、特質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種知識,恰好可以體現出技藝的特點。
首先,如果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屬性定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那么,要在實踐中實現這三個要素的統一,尤其是要實現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之間的有機統一,關鍵就是要掌握一個“度”。這個要點,也許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所蘊含的核心技藝,也許是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的技藝領域,因而,也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最緊要的技藝問題。
從歷史上看,自從“五四”運動提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以來,民主(人民主權或人民當家作主)一直都是一個普遍性的政治訴求。緊隨著“五四”運動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把人民民主或人民主權作為自己堅定不移地追求的一個政治目標。譬如,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宣言中,所確定的黨的最低綱領就包括“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因而,在相當程度上,民主或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與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步產生的。但是,時至今日,在人民當家作主與黨的領導之間,又存在著一種微妙的關系:人民當家作主意味著在我們這個政治共同體中,人民居于主權者的地位,或者說,人民就是主權者;但是,黨的領導則意味著黨是這個政治共同體的主導者。在通行的政治理論中,雖然習慣于以“黨是人民的先鋒隊組織”等觀念來解釋兩者之間的關系,但是,兩者之間的某種緊張卻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看,這種緊張關系更為明顯。
事實上,在本文看來,黨的領導主要是一個客觀事實,人民當家作主則主要是一種價值。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的關系,在相當程度上就是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因而,在處理兩者的關系問題上,一方面,要尊重黨的領導這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們只能在既有的現實條件、現實框架下討論問題,才可能有效地回應事實,促成某個事物的形成。反之,如果不尊重黨的領導這個客觀的事實,雖然也可以展開某些學術上的討論,但由此展開的討論卻可能流于隔靴搔癢,根本就撓不到癢處。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追求應然的價值目標。如果沒有價值目標的指引,客觀的事實就可能出現倫理資源的流失或虧空,或者,就像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所言:“在發展的過程中,以前的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17]P212恩格斯的這個著名論斷提醒我們,應當不斷地夯實現實事物的倫理資源。這就意味著,應然的價值目標還應當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地逼近,否則,應然的價值目標就會因過于縹緲而趨于虛幻。因此,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就是一個“度”的問題。顯然,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技術或藝術問題,需要技術或藝術層面上的智慧。
除了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之間實現統一的技藝,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處理好法律與其他規范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具有藝術或技術的性質。譬如,法律與黨的政策的關系問題。按照依法治國的理念,法律是治理國家事務、社會公共事務的依據,但是,法律并不是唯一的依據,黨的政策事實上也是治理國家事務、社會公共事務的依據。那么,在實踐中,如何協調法律與黨的政策的關系,法律與黨的政策的聯結點在哪里,也是一個以“度”為核心的技藝問題。再譬如,在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上,在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如果還要發揮道德準則對于文明秩序的調整功能,也需要“兼顧”、“中庸”、“度”的藝術。此外,規則的多元化、多樣化甚至就體現在廣義的法的范圍內,在實踐中,在成文的法律規則與不成文的慣例之間,在國家制定法與民間習慣法之間,都不是涇渭分明的關系;相反,在相當程度上,它們是交錯在一起的。因此,在法治實踐中,如何處理多元規則之間的關系,也可以體現出技藝的品性。
還有,單就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義理念而言,要把它運用于實踐,要把它變成一個現實性的存在,也是一個極其需要藝術與技術的內容。因為,不同的主體站在不同的立場上,都會形成各自不同的關于公平正義的理解與期待。在這個主題上,筆者曾以“誰之法理”作為主題,區分過法學家的法理與法律家的法理、官方的法理與民眾的法理、辯護者的法理與批判者的法理、原創者的法理與繼受者的法理,?這樣的區分同樣也適用于公平正義的“制作”過程。因為,對于公平正義的理念,法學家與法律家、官方與民眾、辯護者與批判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因而,無論是哪種主體,都應當理解其他主體對于公平正義的理解,并進而協調不同主體之間對于公平正義的相異的訴求,最大限度地滿足全社會日益增長的對于公平正義的需要。顯然,按照上文對于技藝的認知,這是一種技術與藝術。
除了以上幾個較為突出的方面,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度”的技藝性知識,還體現在法治所涉及到的幾乎所有領域。譬如,司法機關主動服務大局與司法機關尊重司法規律的關系,執法為民與通過執法引導民眾的關系,司法能動與司法克制的關系,法治的功能與法治的局限的關系,法治的中國性與世界性的關系,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些不勝枚舉的“關系”,都需要“分寸”上的把握,都需要“度”的斟酌,都體現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技藝品性。在法學理論界,已經產生了大量的有關法律方法或法律技術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所提供的其實就是關于法治的技藝性知識。因此,如果要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踐之于行,以改造我們這個世界,以“制作”、“養成”一個法治的社會、法治的國家,那就應當進一步充實社會主義法治的技藝之維,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知識框架下,培育出更多的技藝性知識。
六、結論及延伸性討論:知識的分類與法律人的分類
把以上幾方面分析結合起來可以發現,如果將人類的知識劃分為純粹理性、實踐理性、技藝,那么,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種新興的知識,既可歸屬于實踐理性,也可歸屬于技藝;但在一般情況下它不能歸屬于純粹理性。因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個知識體系,它涉及到主體的行動與交往,涉及到主體的技術與藝術,但它不是形而上學,也不是邏輯學。這就是本文通過研究得出的基本結論。
從這個結論出發,以這個結論為基礎,如果我們把當代中國的法律人視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種特定知識的承載者(載體),那么,我們對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所屬的知識類型的考察,是否還可以延伸至對于這種知識的承載者的分類考察?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承載者統稱為法律人或法律人共同體,那么,可以看到,當代中國的法律人作為一種特定的知識人,他們在履行社會角色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某種類型化的趨勢。
波蘭社會學家茲納涅茨基的《知識人的社會角色》一書中,把知識人的社會角色分成四類:首先是技術顧問,包括技術專家與技術領導者;其次是圣哲,主要是為他們的團體、教派、階層提供知識上的證明;再次是絕對真理的承擔者,主要是學院中的學者,包括神學學者與世俗學者;最后是新知識的創造者,包括事實的尋找者與擅長歸納的理論家。?在茲納涅茨基的視野中,“知識”指涉甚廣,“知識人”的范圍也相當寬泛。通過這樣的辨析,他為我們揭示了知識形態、知識類型與知識人之社會角色之間的相互關聯。
那么,當代中國的法律人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種知識的承載者,他們在公共生活中承擔著什么樣的社會功能?履行著什么樣的社會角色?對此,我們認為,法律人當然可以歸屬于知識人,但是,法律人顯然不能完全等同于茲納涅茨基筆下的“知識人”。這兩個概念既分享了某些共性,但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按照本文關于知識形態的認知,以及茲納涅茨基的知識社會學分析路徑,我們可以對法律人所承擔的社會角色做一些初步的分類考察。
首先,正如知識形態中包括了技藝這種類型,作為知識人的法律人,承擔的社會角色首先也是技術專家。特別是那些熟悉具體的法律細節問題的法律人,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是為個體、社會和國家提供專業性的法律服務,因而,他們主要是以技術專家的角色呈現在社會公眾面前。譬如,關于公司的治理結構,關于有效合同的構成要件,關于罪與非罪的界限,關于刑事指控與刑事辯護的技巧,關于法律解釋的方法,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專業性的法律技術問題。在法律人群體中,這種技術專家的充任者主要是法律實踐者與學院中的一些“部門法學者”。法律實踐者人數眾多,他們中的律師,主要是為社會主體(自然人、法人)服務的;他們中的檢察官,主要是為國家服務的——他們是國家聘請的“律師”;他們中的法官,當然要為國家服務,但同時還應當恪守中立的仲裁人的社會角色。此外,在政府系統中,還有專門的法制部門,供職于這種法制部門的法律人,主要是為政府服務的——他們的社會角色主要是“政府的律師”。至于學院中的“部門法學者”,他們一方面是法律專業技術的研究者與傳承者,另一方面,他們也愿意充當法律的實踐者,譬如,他們以兼職律師的名義為社會主體提供專業性的法律服務;他們以“政府法律顧問”的名義為政府提供專業性的法律服務;他們還以“立法咨詢委員”的名義,為立法機構提供專業性的法律服務,等等。在這樣一些法律實踐活動中,“部門法學者”的社會角色其實是“高級技術專家”。
其次,知識類型中還包括實踐理性,承擔這類知識的法律人,大體上可以對應于茲納涅茨基所謂的“圣哲”。雖然,在通常情況下法律人不大可能成為“圣哲”,但是,也有一些法律人充當了既有的社會秩序與政治秩序的辯護者。這一類法律人的主要旨趣,是對現有秩序進行合理化論證。這樣的社會角色讓人聯想到為國家服務的檢察官。但這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角色。檢察官為國家服務的方式是處理個案,是以技術專家的角色出現的。但是,現行秩序的辯護者與論證者并非技術專家,而是“正當性”或“合法性”的生產者,是某種價值的守護者。這種角色的功能在于:把自然形成的文明秩序裝進一個自足的理論框架中,從而將自然形成的文明秩序置于某種理論基礎之上,這就類似于:為某個人縫制了一件得體的外衣,讓他穿在身上,以免他赤身裸體地在外面行走。這樣的社會角色,與多數法律人無關;承擔這種角色的法律人主要是法哲學家。如果要舉出一個略顯負面的代表,那么,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卡爾·施米特,庶幾近之。施米特作為一個憲法學家,所發表的“領袖守護憲法”之類的論著,?試圖為當時的德國政治穿上一件還算體面的外衣,體現了他所承擔的作為既存政治秩序的維護者與辯護人的社會角色。至于正面的例子,也許可以舉出西方中世紀初期的奧古斯丁,西方近代初期的洛克,中國古代的董仲舒,等等。當然,在當代中國的法政哲學領域,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法哲學家。因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特別是歷史轉型過程中,每一種新的政治秩序、文明秩序形成之際,都需要這樣的法哲學家予以理論上的闡釋與論證,否則,新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名正而言順”。
當然,法律人群體中的法哲學家并非都是既存秩序的辯護人。法律人群體中的一些人還履行了另一種重要的社會角色:既有秩序的質疑者與批評者。近現代以來,在廣義的法律人群體中,承擔這種社會角色的典型代表前有馬克思,后有昂格爾。縱觀馬克思的一生,雖然不能算是一個純粹的法律人,但是,至少在青年時代,他曾一度把法律作為自己的專業。翻開馬恩全集第一卷,可以看到里面大多數論著都是批判既有秩序的法學論著,它們體現了馬克思作為質疑者與批判者的角色意識。在當代,以昂格爾為代表的批判法學理論,同樣恪守了質疑與批判的角色意識。批判法學理論的當代精英雖然不可能像馬克思當年那樣尖銳、徹底,更不可能產生像馬克思那樣深遠的社會影響,但是,從馬克思經過法蘭克福學派再到昂格爾的這一條線索,足以代表法律人所承擔的一種重要的社會角色。從人類社會的進程來看,這種旨在質疑、批判既有秩序的法律人,雖然在數量上并不是很多,但卻不可缺少。因為,他們對既有秩序中“有毒有害成份”的批判,可以產生類似于殺毒軟件那樣的功能。如果一套精良的殺毒軟件對于電腦系統的正常運轉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一種旨在清除社會病毒、政治病毒的批判法學,同樣是不可缺少的。
再次,知識類型中還有純粹理性,這種知識的承載者,可以對應于茲納涅茨基所說的“絕對真理的承擔者”。但遺憾的是,當代中國的法律人共同體中這種知識的承載者較為罕見;?如果嚴格局限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種特定的知識體系之內,那么,“絕對真理的承擔者”,更是無處可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也許在于:在法律人的視野中,較少純粹理性這種知識形態;某個法律人倘若進入了純粹理性的知識領域,也許他(她)就已經身不由己地走出了嚴格意義的法律人共同體了。
以上分析表明,當代中國的法律人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種知識的承載者,他們承擔的社會角色,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承載著技藝的技術專家;二是承載著實踐理性的法哲學家(其中既包括現行秩序的辯護者,也包括既有秩序的批評者)。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承載者作為技術專家,主要是社會分工的產物,同時也是商業社會、陌生人社會的必然結果。如果中國社會的商業化、“陌生化”程度進一步加劇,那么,法律人作為技術專家的角色還將進一步凸顯——社會公眾就會像依賴醫生那樣依賴作為技術專家的法律人。相比之下,法哲學家作為既有秩序的辯護者和批評者,盡管立場不同,但都體現了一種超越于專業技術的公共追求,體現了交往、商談的主體間性的旨趣。在西方,這種公共追求主要繼承了知識分子或公共知識分子的旨趣;在中國,這種公共追求主要繼承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情懷。
注釋:
①詳見陳興良《法學:作為一種知識形態的考察——尤其是以刑法學為視角》,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7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頁。
②關于法學的知識形態的討論還有,王麟:《法學知識的屬性與進步》,《法律科學》2000年第2期;鄭戈:《法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嗎?——試論“法律科學”的屬性及其研究方法》,載《北大法律評論》第1卷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劉星:《法學“科學主義”的困境——法學知識如何成為法律實踐的組成部分》,《法學研究》2004年第3期,等等。
③譬如,龍宗智:《論司法改革中的相對合理主義》,《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以及,前引蘇力的文章。
④譬如,關于實踐理性,在凱爾森看來,“實踐理性在概念上自我矛盾,基本就不可能有實踐理性,自然也就談不上如何運用的問題。”詳見顏厥安:《法與實踐理性》,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頁。
⑤詳見,梁啟超:《學術與》,載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1頁。
⑥譬如,康德把理性心理學的謬誤推理所推出的靈魂實體稱為“理念”(德文Idee,英文idea)。柏拉圖提出,理念在彼岸世界,它是現實世界的原型,現實世界是模仿這個理念才形成了現實的萬事萬物。而且,理念世界是不變的,現實世界的任何東西都是對它的模仿,而且是不精密的模仿,理念具有一種不可達到的超驗性的特點(詳見,鄧曉芒:《康德哲學講演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頁)。西方哲學史語境中的這種“理念”,顯然不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的“理念”。因此,不僅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的“理念”不能等同于柏拉圖、康德所說的“理念”,就是本文所使用的其他關鍵詞,譬如純粹理性、實踐理性、技藝,其含義在亞里士多德的筆下、在康德的筆下、在本文中,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因為,語境、問題意識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雖然在本文中,筆者也試圖“打通”亞里士多德的,康德的,以及當代中國語境下的純粹理性或實踐理性,但我們必須注意,它們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同義詞。就這三種語境下的純粹理性或實踐理性而言,最多只能說,它們共享了某種知識分類的旨趣。
⑦詳見,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讀本》,中國長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頁。
⑧詳見,喻中:《中國法治觀念》,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頁。
⑨譬如,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讀本》,中國長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
⑩詳見,喻中:《中國法治觀念》,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頁。
?雖然有學者在解讀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時寫到:“哈貝馬斯認為,由于實踐理性脫離了文化傳統和社會歷史因素,致使個人和社會相分離,并和實踐之間存在著過于直接的聯系,因此它在解決人和人之間的社會整合問題上失去了作用,進而被思想家們所拋棄。而他所提出的交往理性的方案就是要把法律和社會規范的制定問題放在話語的交流過程中,用對話中的恰當理由來證明社會規范的正當性。”詳見,王曉升:《從實踐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貝馬斯的社會整合方案》,《云南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但是,在本文看來,實踐理性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概念,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并非外在于實踐理性,而是在實踐理性的框架內提出來的新觀點。哈貝馬斯的貢獻就在于以“交往理性”豐富了實踐理性的內涵。
?在內容與功能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憲法的序言也有一定的可比性,至少,它們都表達了憲法和法律制定和實施的政治背景。
?詳見,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讀本》,中國長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6頁。
?也許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既然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就表明它是一政治性的知識,而不是一種純粹的知識。但在本文看來,政治性的知識也是知識。關于這一點,薩義德有精到的分析,他專門論述了“純粹知識與政治知識的區分”,他說:“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關于莎士比亞或華茲華斯的知識是非政治性的知識,而關于當代中國或蘇聯的知識則是政治性知識。”針對這種流行的見解,他又特別強調:“我現在想做的是提醒大家注意:‘真正’的知識本質上是非政治性的(反之,具有明顯政治內含的知識不是‘真正’的知識),這一為人們廣泛認同的觀點忽視了知識產生時所具有的有著嚴密秩序的政治情境(盡管很隱秘)。”換言之,知識都有政治性。詳見,[美]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2~14頁。
?《論語·雍也》。
?《道德經》,第77章。
?詳見,喻中:《自由的孔子與不自由的蘇格拉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頁。
?詳見,[波蘭]茲納涅茨基:《知識人的社會角色》,郟斌祥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
?參見,[德]施米特:《論斷與概念》,朱雁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頁。
?在法學界,少數研究法律邏輯的學者生產出來的偏重于邏輯方面的“法律邏輯”,也許接近于知識形態中的純粹理性。
[1] 蘇力.知識的分類[J].讀書1998,3.
[2] 梁治平.法治進程中的知識轉變[J].讀書1998,1.
[3]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4] [美]波斯納.法理學問題[M].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5] [德]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韓水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6] [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冊)[M].馬元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7] [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8] 楊建軍.法治國家中司法與政治的關系定位[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1,5.
[9] [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
[10] [法]薩特.存在與虛無[M].陳宣良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7.
[11] [德]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M].李黎、郭官義譯,南京:學林出版社,1999.
[12] [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與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M].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
[13] 韓水法.批判的形而上學:康德研究文集[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4] 鄧曉芒.康德哲學講演錄[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15]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6] 李澤厚.歷史本體論[M].北京:三聯書店,2002.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