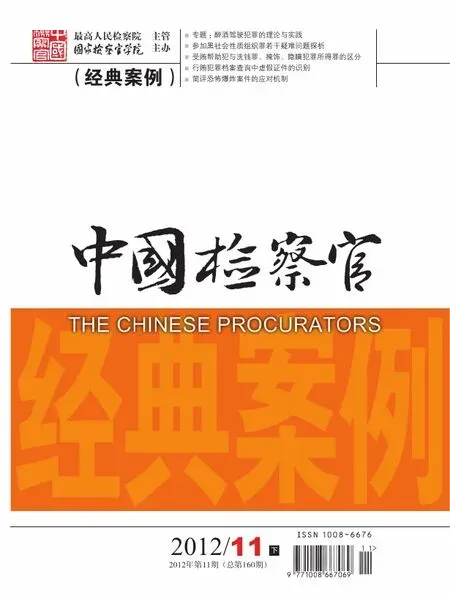明知是艾滋病感染者而與他人發生一夜情的行為定性
文◎劉培志祁濤
明知是艾滋病感染者而與他人發生一夜情的行為定性
文◎劉培志*祁濤**
一、基本案情
2010年5月,犯罪嫌疑人李女在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測出HIV-1抗體陽性,即艾滋病感染者。2010年7月李女和陳男偶然相識后即發生性關系,并保持情人關系。2010年8月,李女通過網絡“同城聊”軟件認識張男,當日兩人即發生性關系,發生性關系前李女要求張男使用避孕套,張男拒絕使用。2010年秋李女又通過QQ聊天認識王男,當晚二人發生性關系并保持情人關系。在聊天時李女曾告知王男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王男以為李女開玩笑并未當真。之后陳男經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測,被感染艾滋病毒。
二、分歧意見
針對該案中李女在明知自己是艾滋病毒攜帶者的情況下,先后與三名男子發生性關系,并至陳男感染艾滋病毒的行為該如何定性,產生三種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李女視他人健康、生命為草芥,其在發生性關系之前雖要求張男采取安全措施,也告知王男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但在張男拒絕、王男以為其開玩笑的情況下,李女并沒有切實采取充分的保護措施,其對他人身體的傷害具有預見的可能性,主觀上具有放任傷害的間接故意,客觀上至陳男感染艾滋病毒,應當以故意傷害追究李女的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李女作為艾滋病患者,通過QQ、一夜情軟件等網絡工具認識陌生男子,在事實上并未采取切實有效保護措施的情況下與他們發生性關系,可見其對另一方身體健康毫無顧忌,極可能導致被害人感染并產生二次傳播,最終可能導致危害擴大,因此其行為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要件。
第三種意見:自由是一種權力,它包含性的自由,即是否發生及和誰發生性關系的自由。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艾滋病感染者不能與他人發生性關系,事實上也不應禁止艾滋病者的性自由。該案中李女雖然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并與他人發生性關系,但是并不能證明李女具有傷害他人身體和報復社會的主觀故意,而且在與張男、王男發生性關系前其告知了危害性或要求采取措施。故意傷害屬結果犯,艾滋病屬于何種傷情法律上并無定論,而且李女的行為并非針對不特定對象。因此,李女的行為并不符合故意傷害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要件,而屬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要做到正確認定該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是關鍵。
(一)李女的行為不構成傳播性病罪無異議
根據我國《刑法》第360條規定,傳播性病罪是指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嚴重性病賣淫、嫖娼的行為。可見,判定傳播性病罪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是嚴重性病患者,是否實施了賣淫、嫖娼行為。只有兩者同時具備才能據此定罪。對于艾滋病是否屬于“嚴重性病”范疇,有人認為我國刑法并未明文規定,也沒有相關的司法解釋,因此艾滋病不應納入“嚴重性病”范疇。對此筆者不敢茍同。1991年中國衛生部發布的《性病防治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性病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乙類傳染病中的艾滋病、淋病、梅毒、軟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腫、非淋菌性尿道炎、尖銳濕疣和生殖器皰疹。”由此可見,從醫學上講艾滋病已經被定為比淋病、梅毒更加嚴重的性病。舉輕以明重,淋病、梅毒尚且納入“嚴重性病”的范疇,比二者更加嚴重的艾滋病何以被排除在外,因此筆者以為艾滋病應當屬于“嚴重性病”的范疇。但是,我國刑法對于傳播性病罪的實施方式規定了嚴格限制,即僅限于以“賣淫、嫖娼”而傳播的行為,本案中李女的行為顯然不屬于賣淫、嫖娼行為,因此不應以傳播性病罪定罪處罰。
(二)李女行為的傷害故意和傷害結果都不確定
首先,該案中李女雖然明知自己是艾滋病毒攜帶者,并與他人發生了性關系,但是在與他人發生性關系時,李女并沒有明確的傷害他人身體的故意。其在與張男發生性關系時要求張男采取安全措施,但是張男拒絕;其在與王男發生性關系前曾告知王男其有艾滋病,但王男并不相信,仍與其發生性關系。這些行為細節完全可以佐證李女并沒有傷害他人身體的直接故意。當然持構成故意傷害觀點的人,認為李女在主觀上對他人可能因為自己而感染艾滋病的后果持放任態度。而事實上,從認識因素講李女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致他人感染艾滋病毒,但是從其意志因素講李女是反對他人感染艾滋病毒結果出現的。因為通過性行為傳播艾滋病毒并不是必然的,尤其是由女性傳播給男性的幾率會更小,從李女行為時的細節看,其并不希望他人感染艾滋病毒的結果發生,其寄希望于一次性行為對方可能不會感染。因此,如果只是認為李女明知自己是艾滋病毒攜帶者而與他人發生性關系,并致其中一人感染艾滋病毒,就武斷地認為其主觀上具有傷害他人的主觀故意,而不去具體考察當時的環境因素,難免會陷入客觀歸罪境地。
其次,從司法實務操作層面上講,我國刑法規定了故意傷害輕傷、重傷以及致人死亡的加重后果,而且針對何為輕傷、何為重傷制定了專門的鑒定標準,從而形成了從立法到司法對故意傷害罪認定的完整操作程序。但是致他人感染艾滋病屬于哪一種傷害結果尚無定論,如果我們武斷地界定為輕傷、重傷、或者是致人死亡,都缺乏立法的依據。而且艾滋病毒具有一定的潛伏期,有的長達十至二十年,在這一過程中,存在外在因素阻斷因果關系的可能。因此,致他人感染艾滋病這一行為,從刑法層面講其傷害結果的認定處于不確定狀態。
再次,從本案具體情況來講,陳男感染艾滋病的結果是否為李女所致,缺乏足夠的證據予以證實。因為,艾滋病感染的途徑有血液、母嬰、性行為等多條途徑,因此陳男的艾滋病毒是否通過性行為傳播的不確定,即使確定為性行為傳播,那么其是否因與李女發生性行為而感染還是因與其他人發生性行為感染亦不確定。
(三)李女沒有針對不特定公眾實施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故意
實踐中確有為報復社會而采取諸如扎針、捐送(賣)血液或血制品、人體組織或器官移植等方式,把艾滋病毒傳播給不特定公眾的行為,對于這類行為定性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無不當。因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行為犯,故意把艾滋病毒傳播給不特定公眾,其社會會危害性是存在的,即使在上文筆者在論述致特定個人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形時,也并沒有否認社會危害性的存在,只是這種危害性在認定方面缺乏立法的支持。
但是,該案中李女首先在主觀上沒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上文中筆者已經論述,李女沒有故意傷害他人的故意,也就是說李女對與她發生性關系者感染艾滋病毒的結果是持反對態度的,其對待特定對象尚不具有傷害的故意,又怎么可能具有危害不特定對象犯罪故意呢?因此,說李女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故意從邏輯上講不通。
其次,李女的行為并未針對不特定公眾。該案中李女先后與三人發生性關系,雖然其認識的方式、途徑并不相同,但是其行為明顯不同于賣淫行為。賣淫行為實質是一種買賣關系,其不管買主是誰,只要給錢就行,因此其對象是不特定的。但是李女無論通過什么方式認識其他男子,都經過了一個認識的過程,雖然這個過程是短暫的。也正因為如此李女才與其中兩名男子保持了一定的情人關系。我們不能單純從李女先后與三名男子發生性關系就認為其發生性關系的對象是不特定的,這只能證明李女在性觀念方面比較開放和自由。
*江蘇省連云港市人民檢察院[222001]
**江蘇省連云港市海州區人民檢察院[22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