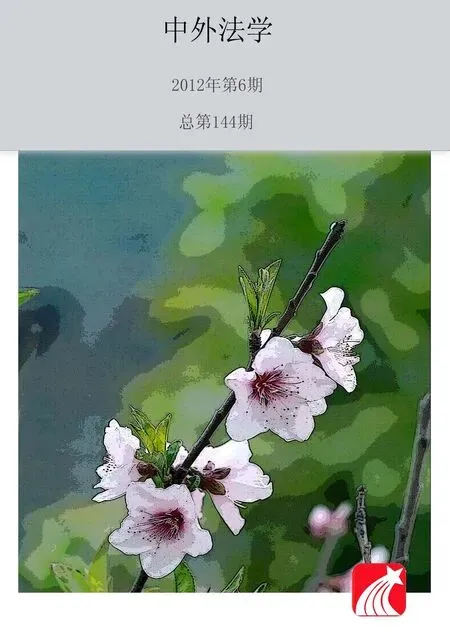公司擔保法律規則的價值沖突與司法考量
羅培新
在通常情況下,法律規則的頒行,當可定分止爭;但在少數情況下,法律規則本身卻成為了爭議的制造者。公司法關于公司擔保的規定即屬其一。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部門,對于公司擔保問題的爭議,并沒有隨著200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稱“2005年《公司法》”)對于原《公司法》相關規定[注]原《公司法》第60條第3款規定:“董事、經理不得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的全面取代而偃旗息鼓,相反卻呈升級之態勢。對于2005年《公司法》中的相關擔保規范,諸多公司法學者在著述中的不同學理闡釋,[注]關于2005年《公司法》有關擔保規范的學理解釋,可謂歧見叢生,具體可參見趙旭東:《商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頁222;劉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創新:立法爭點與解釋難點》,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頁108;葉林:《公司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頁150;甘培忠:《企業與公司法學》(第5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245。這些論著對于公司擔保法律規定的不同闡釋,本文將在論及具體問題時一一述及。以及若干次學術會議的激烈論爭[注]筆者參加的多次商法學術會議,但凡涉及公司擔保效力這一命題的,必定爭論不休。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11月由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舉辦的“公司法適用高端論壇”。在該次會議上,學者之間、法官之間、學者與法官之間對于2005年《公司法》第16條屬性的理解,存在相當大的分歧。表明,學界對于此一論題的見解遠未達成一致。類似地,法院在2005年《公司法》頒布后審理公司擔保案件所顯現的司法意見之殊異,[注]筆者曾應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等法院系統的邀請,為法官們講授公司法,聽課對象多為從事審判第一線工作的法官,他們對公司法有關擔保規范的理解,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后文亦將述及的是,統計結果表明,事實上,有關公司擔保的案件,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比比皆是。同樣表明實務界對相關法條的理解亦歧見迭出。
一、 問題:2005年《公司法》相關擔保規范的爭議
2005年《公司法》關于公司擔保的規定,集中體現在第16條。該條共設三款:第1款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投資或者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投資或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第2款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第3款規定:“前款規定的股東或者受前款規定的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加前款規定事項的表決。該項表決由出席會議的其他股東所持表決權的過半數通過。”
對于第1款,學界不存疑義的是,公司作出擔保,必須按照章程對于公司擔保權限的分配,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易言之,公司擔保須以決議方式進行[注]當然,議決方式未必要求一定要召開會議。2005年《公司法》第38條第2款規定,股東以書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開股東會會議,直接作出決定,并由全體股東在決定文件上簽名、蓋章。,即便是身為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長,亦無權以公司名義對外作出擔保行為。此種管制立場,應當是為了回應2005年之前公司高管濫用擔保、損害股東利益的行為。然而,這里的問題在于,公司的內部行為(公司章程和決議)是否具有外部效力?能否構成訴訟中的請求權基礎?進而言之,該款究竟是屬于效力性規范,還是非效力性規范?[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下稱《合同法解釋二》)第14條將強制性規范分為“管理性規范”與“效力性規范”,并以此將《合同法》第52條“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范的合同無效”限縮解釋為“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范中的效力性規范無效”。擔保公司的股東能否以擔保違背公司章程為由主張擔保無效?以上問題可以抽象為以下簡單的案例:
案例一:A有限公司章程規定,董事會有權做出500萬元以內的擔保,超過500萬元的,由公司股東會決定。2007年某日,A公司董事會作出決議,為B公司向C銀行的借款600萬元提供擔保,C銀行接受了這份擔保。最后,B公司無法履行債務,C銀行要求A公司履行擔保責任。A公司股東以董事會不是600萬元擔保的適格決議主體、因而擔保合同不成立為理由,拒不履行擔保責任。C銀行訴至法院。
本案的核心有二:其一,A公司董事會決議違反了章程規定,決議是否有效?其二,假設該董事會決議無效,是否影響公司擔保的效力?對此,學界內部意見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第16條第1款應為效力性規范,擔保合同將因公司決議違反章程而無效;[注]例如,趙旭東教授在其主編的著作中稱:“公司對外擔保是直接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項,而公司法又明確授權公司章程對公司擔保做出規定,此時章程就成為決定公司對外擔保效力的唯一規范。法律的規定是所有當事人都應知曉的,它產生當事人知道或應當知道的法律效果。如果擔保決定的作出以及擔保數額違反了公司章程的規定,第三人就不得以沒有審查公司章程為理由進行抗辯。”趙旭東,見前注〔2〕,頁222;又如,劉俊海教授認為:“任何人不得以其不知公開的法律規則為由而主張抗辯,根據第16條可以推定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與擔保公司簽訂擔保合同時,應當要求擔保公司出具股東會或者董事會的決議。”劉俊海,見前注〔2〕,頁108。有學者進一步指出,“應當將第16條所定擔保事項的‘內部審議程序’解釋為強制性規范”。[注]葉林,見前注〔2〕,頁150。另有學者認為,該款的立法原意是保證交易安全,約束董事和高級經理的行為,但該款并非效力規定。[注]參見王保樹、崔勤之:《中國公司法原理》(第3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頁42。《合同法解釋二》第14條將強制性規范分為“管理性規范”與“效力性規范”,以此將《合同法》52條“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范的合同無效”限縮解釋為“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范中的效力性規范無效”。公司法學界有學者認為合同法中此項規定可以延伸至公司法規范,《公司法》第16條雖然為強制性規范,但其事實上應當是為管理性之目的而設立,違反此項規定并不導致合同無效。同時,還有學者認為,第16條第1款僅僅是賦權型規范。[注]參見董慧凝:《公司章程自由及其法律限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頁158。而此種見解,又與以下案件的處理息息相關:
案例二:A有限公司章程未對擔保權的分配作出規定。2007年某日,該公司董事會作出決議,為B公司向C銀行的借款600萬元提供擔保,C銀行接受了這份擔保。后來B公司無法履行債務,C銀行要求A公司履行擔保責任。A公司股東以董事會未獲得公司章程的授權因而不是600萬元擔保的適格決議主體、故而擔保合同不成立為理由,拒不履行擔保責任。C銀行訴至法院。
對此,有學者認為:“債權人在接受公司擔保時應當審查公司的章程;章程沒有明確規定決議機構權限的,股東會和董事會作出的決議都是可以接受的有效文件。”[注]甘培忠,見前注〔2〕,頁245。對于這一觀點,本文稍后將進行分析。
無論學界如何聚訟紛壇,法院對于違反2005年《公司法》第16條第1款而作出擔保的案件,卻傾向于判處擔保有效。法院的這一立場,集中反映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宋曉明庭長在《人民司法》(2007年第13期)的訪談之中。其意旨是:實踐中傾向于認為,公司章程關于公司擔保能力、擔保額度以及擔保審批程序等方面的規定,系調整公司內部法律關系的規范,在公司內部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通常不能對抗擔保債權人等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對以擔保違反公司章程為由主張擔保關系無效的,除非涉及公司為內部人員提供擔保,一般不予支持;《公司法》第16條第2款是公司為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應當遵守的特殊規定,該規定是強制性的,應為擔保協議生效的必要條件。[注]宋曉明庭長亦指出,當公司為董事、監事和高管人員的債務而與債權人簽訂擔保協議時,債權人應當注意《公司法》第149條對董事、監事和高管人員交易行為的規定,了解股東對相關人員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若擔保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應認定擔保協議缺乏生效要件。參見孫曉光:“加強調查研究 探索解決之道——就民商事審判工作中的若干疑難問題訪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人民司法》2007年第13期。
由此看來,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場是,2005年《公司法》第16條第1款為管理性規范,第2款則為效力性規范。為印證此種立場,筆者通過北大法律信息網檢索了所有援引《公司法》第16條的裁判文書,并統計了50個有限公司作出瑕疵擔保決議的案例。[注]更為詳細的數據分析,可參見趙穎潔:“閉鎖公司瑕疵擔保裁判彌補模糊性立法的路徑分析”,載羅培新執行主編:《金融法苑》,2011年總第83輯。從2007年到2010年的數據可以看出,法官援引《公司法》第16條裁判的案件逐年增多,而認定擔保有效的比重也在增加(參見表一)。
〔1〕 由于裁判文書轉化為網絡資源存在時滯,2010年的數據并不全面。
以上擔保,又可以根據公司是否為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和高管人員(通稱為“內部人士”)提供擔保,分為對內擔保和對外擔保。對于對內擔保,法院判處擔保無效的比重高達90.6%;而對外擔保,法院判處擔保無效的比重,僅僅為33.3%(參見表二)。

表二 對內擔保和對外擔保中法院對擔保決議效力的裁判結果對比
以上情況表明,盡管全國法院關于公司擔保案件的裁判與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場大致吻合,但是,仍有9.4%的對內擔保被判處有效、33.3%的對外擔保被判處無效。它表明,無論是對于第16條第1款還是第2款,法官的理解均存在一定的分歧。例如,有法院以第16條第1款為管理性規范為由認定違反此規定的擔保決議仍然有效,如在“尤賽珍訴寧波開匯電子產業有限公司等民間借貸糾紛案”中,寧波市江東市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認為“根據法律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范才是導致合同無效的法定事由之一,而2005年《公司法》第16條系管理性強制規范,而非效力性強制規范”。但又有法院直接以擔保決議違反第16條第1款為由認定其為無效,如在“馮尚君訴林明龍等民間借貸糾紛案”中,浙江省臨海市人民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本案中,被告五洲大酒店為林明龍借款提供擔保未經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的決議,應當確認為無效。”
盡管法院對于2005年《公司法》第16條的理解存在差異,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法院對于各方賠償責任的判處卻非常吊詭。如表二所示,50個案件中有35個案件的結果均為擔保無效,占樣本總量的70%。但在對最終清償責任的統計中,如表三所示,50個案件中,除了一個未提及清償責任的分擔外,其余49個案件中僅有2個案件中的公司不承擔清償責任,僅占樣本的4%。

表三 法院對于做出擔保的公司之清償責任的裁判情況
〔2〕 對內擔保案例中,有一個案例(新疆溫州港大酒店有限公司與新疆新油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保證合同糾紛上訴案)未提及最終清償責任分擔方式,因而原有的32個對內擔保案例變為31個,總數原有的50個案例也相應變為49個。
通過進一步的分析可知,包括對內擔保和對外擔保總計共有34個案件被法院判處擔保無效,但僅有2個案件被法院判處擔保人不承擔清償責任,占樣本總數的5.9%(參見表四)。

表四 擔保無效案件中做出擔保的公司責任承擔情況[注] 擔保無效案例中有一個案例并未提及最終清償責任分擔方式,因而原有的35個案例縮減為34個。
進而言之,對內擔保總計32個案件中,被法院判處擔保無效的案件為29個,其比重高達90.6%(參見表五)。

表五 對內擔保中公司瑕疵擔保的效力
對此,一個合理的推斷是,既然公司擔保決議無效,公司就不應承擔清償責任。但是在責任承擔中,只有3.1%的案件中公司不承擔清償責任,判處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或承擔二分之一清償責任的案件所占比例,高達93.8%(參見表六)。

表六 對內擔保中擔保公司的責任承擔
為什么一方面認定擔保無效,另一方面卻又要求擔保方承擔清償責任?筆者注意到,法院在作出此類裁決時,都會援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稱“《擔保法司法解釋》”)第7條的規定:“主合同有效而擔保合同無效,債權人無過錯的,擔保人與債務人對主合同債權人的經濟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債權人、擔保人有過錯的,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部分,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
無論如何,這是一種非常曖昧的判決。就法理而言,擔保合同無效抑或沒有成立,擔保公司應承擔的僅僅是締約過失責任,而不是就擔保權人的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但法院對無效擔保的擔保人,判處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或二分之一清償責任的比重高達93.8%,委實令人費解:既然無論如何擔保人均要承擔清償責任,判處擔保合同是否有效并不重要;依此邏輯,對于2005年《公司法》第16條的屬性的理解也并不重要。
于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產生了:學者對于第16條的屬性的理解差異懸殊,法院對于該條的理解亦歧見叢生,但這絲毫不影響法院關于責任承擔的最終裁判的一致性。案件裁決看似異曲同工的背后,折射的卻是法院在諸多價值觀沖突之下作出了權宜的選擇。這種選擇的結果,絲毫未能掩蓋法院深深地陷入未能準確把握公司法條的屬性、在擔保法與公司法產生價值沖突時無法妥為權衡的困局之中,以至于最后通過援引因未區分締約過錯責任和擔保責任、因而在法理上存在重大欠缺的《擔保法司法解釋》,來作出權宜的裁決。最終,法院在社會資源的再分配方面,未能發揮積極的導向作用。
二、 在賦權與強制之間:2005年《公司法》第16條的屬性辨析
我國《合同法》第52條規定,合同生效的前提之一是“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因而,在判斷違反2005年《公司法》第16條第1款的擔保合同是否有效之前,必須解釋該法條是否為強制性規范。另外,根據《合同法解釋二》第24條,此處的強制性規范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根據通說,強制性規范可分為兩種,一種為效力性規范(或稱禁止性規定),另一種為管理性規范(或稱取締性規范),只有違背效力性規范才會導致合同無效。[注]史尚寬教授認為,強制性規定有取締規定和效力規定之別。其中,效力規定著重違反行為的法律行為價值,以否認其法律效力為目的;取締規定則著重違反行為的事實行為價值,以禁止其行為為目的:“自法律規定之目的言之,惟對于違反者加以制裁,以防止其行為,非以之為無效者,此種規定,稱為取締的規定,與以否認法律之效力為目的之規定相對稱。”“強行規定,是否為效力規定抑為取締規定,應探求其目的以定之。即可認為非以為違反行為之法律行為為無效,不能達其立法目的者,為效力規定,可認為僅在防止法律行為事實上之行為者,為取締規定。”參見史尚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330。2005年《公司法》第16條第1款是否為強制性規范?如果是,則其究竟屬于效力性規范還是管理性規范?
如前所述,有學者認為其屬于效力性規范,[注]趙旭東,見前注〔2〕,頁222;劉俊海,見前注〔2〕,頁108。還有學者認為其屬于管理性規范,[注]王保樹、崔勤之,見前注〔9〕,頁42。更有學者有人認為其屬于賦權型規范。[注]董慧凝,見前注〔10〕,頁158。在世界范圍內,不同的學者對于公司法規范的劃分各有不同,但都大同小異。[注]加拿大的布萊恩·R.柴芬斯教授將公司法規則分為強制適用、推定適用、補充適用三類。參見(加)布萊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論、結構與運作》,林華偉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頁245-284。美國法學教授梅爾文·阿倫·愛森伯格(Melvin Aron Eisenberg),對公司法規范的分類有獨到的見解。[注]Melvin Aron Eiesnberg, “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ion Law, 1461-1529”, Columbia Law Review, 1989.對其的批評集中見于 Fred S. Mcchesney, “Economic, Law, and Science in The Corporate Field: A Critique of Eisenberg”, 1530-1549, Columbia Law Review, 1989.愛森伯格認為,公司法規范可分為以下三類:其一,賦權性規則(Enabling Rules)。這種規則授權公司參與各方通過章程約定而自由設定規則,規則一旦設定,即當然地具有法律效力;[注]我國2005年《公司法》大大增加了此類規則,但凡包含“可以”、“由公司章程規定”、“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同意,還可以……”等詞句的法條,一般情況下屬于賦權性規則,這些字眼在新《公司法》中總共出現115處。其二,補充性規則(Supplementary Rules)。即除非公司參與各方另有約定,公司法的規則當然地具有效力,又稱為“缺省的”或“推定適用”的規范。如法國《商事公司法》第100條第2款規定,“公司章程沒有規定更高的多數的,董事會的決定以獲得出席或由他人代理的董事的多數票通過”,即為典型的補充性規則。[注]我國2005年《公司法》中包含“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全體股東約定……的除外”詞句的規則,為補充性規則,計有4條。其三,強制性規則(Mandatory Rules)。這些規則不允許公司參與各方以任何方式加以修正。英國《1985年公司法》第352條第1款規定,“每家公司都必須保存其股東的注冊記錄”,并且該法還就有關注冊記錄的格式和一些事項規定了一系列強制性義務。[注]我國2005年《公司法》在股東出資、高管義務、債權人保護等方面,設定了大量的強制性規則,“不得”、“應當”、“必須”這些標識性的字眼總共出現271處。一般而言,賦權型規則和補充性規則屬于任意性規則。
然而,美國公司法學者弗蘭克·伊斯布魯克、丹尼爾·費希爾提醒我們,“任何關于公司法的理論,都必須考慮到公司法‘強制性’與‘賦權性’共存的特征。”[注]參見(美)弗蘭克·伊斯布魯克、丹尼爾·費希爾:《公司法的經濟結構》,張建偉、羅培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4。而2005年《公司法》第16條第1款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依文義解釋,該款可依次做以下層面的理解:
第一個層面: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須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進行。易言之,公司可以在章程中設定擔保權的分配。這是一種典型的賦權型安排,根據法律對公司的此種賦權,存在以下兩類可能:
可能性之一:章程對于公司擔保事宜未置一詞。這種情形產生了如下問題:公司有沒有擔保權?如果公司有擔保權的話,應當經哪個內部機關作出擔保決議?這是前文案例二所要解決的問題。
可能性之二:章程對于公司擔保作出了規定,具體情形又包括以下數種:①章程規定公司不得對外擔保,換言之,股東通過章程約定排除了公司的擔保能力;②章程規定公司可以對外擔保,但必須經股東會(或股東大會)作出決議;③章程規定公司可以對外擔保,且只須董事會作出決議;④章程規定公司可以對外擔保,低于一定數額的擔保由董事會作出決議,超過一定數額的擔保由股東會(或股東大會)決議;⑤章程規定公司可以對外擔保,且只須經董事長作出決定;⑥章程規定公司可以對外擔保,且只須經總經理作出決定;⑦章程規定公司可以對外擔保,低于一定數額的擔保由總經理作出決定,超過一定數額的擔保由董事長作出決定;⑧章程規定公司可以對外擔保,低于A數額的擔保由總經理作出決定,超過A數額但低于B數額的擔保由董事長作出決定,超過B數額但低于C數額的擔保由董事會作出決議,超過C數額的擔保由股東會作出決議……
以上是第一個層面——也就是賦權型層面——所衍生的可能性。但事實上,根據2005年《公司法》第16條,公司擔保還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兩個層面的要求:
第二個層面: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必須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這是一項強制性規定。
第三個層面:公司章程對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這亦是一種強制性規定。
綜合前述三個層面,第16條第1款應當是賦權性與強制性相結合的條款。其強制性體現在:公司擔保須依章程而進行;章程應規定公司擔保的決議機關;公司擔保應遵守章程關于擔保總額及限額的規定。其賦權性體現在:公司章程可在法律提供的備選機關中選擇公司擔保的決議機關;公司章程可就擔保總額或者擔保數額進行限制。而一旦公司行使了法律的賦權,在章程中設定了擔保決議機關以及擔保限額,則這些議定條款亦產生強制性。當然,至于該強制性是否會影響到擔保合同的效力,是下文將要探討的另一個問題。
這里要先期探討的問題是,如果章程對于公司擔保事宜未置一詞,則公司有沒有擔保權?如果公司有擔保權的話,應當經哪個內部機關作出擔保決議?對于這一問題的回應,直接關系到前述案例二的處理。
首先,2005年《公司法》第25條和第82條并沒有規定公司擔保屬于公司章程的必要記載事項,是否記載擔保并不影響公司章程的效力。故而,有些公司的發起人的確忽略了在公司章程中記載擔保權限事宜。然而,就私法自治的角度而言,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民事主體均有為他人債務設定擔保的民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與公司捐贈一樣,公司對外擔保本身是公司權利能力的一部分,在公司章程沒有明確排除性規定的情況下,公司仍然享有這一概括性權利。這也符合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通例。[注]總的來說,絕大多數國家對公司對外擔保都作出了相對寬松的規定。如1984年《美國標準公司法》第3.02條規定:除非公司的組織章程中另有規定,每家公司都有權力像一個自然人那樣去做一切對經營公司業務和處理公司業務有必要或有利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權力——對外保證之權能。以《美國標準公司法》為藍本的美國各州公司法也普遍賦予公司對外擔保權,包括公司為股東擔保。美國多數州的公司法都采取原則上允許公司得為保證的立法模式。參見劉連煜:《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頁177。
其次,2005年《公司法》第16條將“董事會”與“股東(大)會”通過“或者”一詞并列,從語義解釋的角度,似乎兩者具有同等的擔保決策權。然而,根據公司法理,董事會只是公司的經營管理機構,而非最高權力機關,除非法律、公司章程和股東(大)會另有授權,其職權僅限于公司的正常經營管理活動。相反,股東(大)會則擁有包括修改章程、決定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權力。2005年《公司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公司章程可以就擔保權限在股東會和董事會之間進行分配。公司章程由股東(大)會制定并修改,如果章程保持沉默,則意味著股東(大)會并沒有通過章程授權董事會行使擔保權的意愿。
最后,董事會基于股東委托對公司進行經營管理,對外擔保不屬于普遍意義上的經營管理行為(專業擔保公司除外),而在本質上是處分股東權利的行為,[注]筆者認為,對外擔保只會給公司帶來或然損失,進而減損股東權益,它不屬于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公司經營行為。在公司章程沒有規定且股東(大)會沒有對董事會進行個別授權的情況下,董事會無權對擔保事項進行決議。
因而,本文針對案例二的回應是,如果公司章程沒有明確規定決議機構權限,則只有股東(大)會作出的決議是可以接受的有效文件。
本文接下來探討公司內部行為與其外部行為在效力方面的牽連性。
三、 法院裁判的迷思:公司內部行為與其外部效力的牽連關系
就性質而言,無論是公司章程還是公司內部機關的決議,均是公司的內部行為;與之相反,公司與第三人訂立的擔保合同,卻是公司的外部行為。在法理上,公司內部行為與外部行為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判然有別。違反公司內部規范的行為,并不必然導致與該內部行為有牽連的外部行為必然無效。舉例而言,如果董事會的擔保決議違反章程規定,甚至股東會作出的擔保決議存在程序瑕疵,股東均有權依據2005年《公司法》第22條的規定,向法院申請撤銷該決議,進而依據第113條、第150條的規定追究董事的責任。但決議被撤銷之后,公司依據該決議對外簽訂的擔保合同是否有效?這取決于兩者的牽連關系是否足夠強。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法院對相關案件的裁判。而在認定牽連關系時,關于擔保行為的性質及其經濟功能的認識,起著前提性的重要作用。
(一)擔保行為的性質及其經濟功能
有學者認為,公司章程的規定與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效力之間不存在牽連關系,其理由在于,如果賦予第三人查閱公司章程的義務,則會降低交易效率。[注]持此種觀點的一位學者認為,從交易經濟的角度分析,如果規定第三人有查閱章程的義務,為了避免交易風險的發生,他不得不在每次交易前到有關部門查閱公司章程,并對隱晦、模糊、曲折的語言表達進行仔細研究,那么他將被迫為資訊搜索付出巨大代價。久而久之,就會大大打擊第三人交易的積極性,束縛社會整體的經濟發展。參見劉玲伶:“章程對公司對外擔保的效力影響”,《安徽大學法律評論》2008年第1輯。然而,這種觀點卻忽視了擔保的以下雙重性質:其一,擔保的設定使擔保人承擔了或然債務,是一種處分擔保人財產的行為。在公司提供擔保的情況下,擔保在一定意義上剝奪了話語權相對弱小的少數股東的財產;其二,擔保的設定稀釋了擔保人對于其它債權人(甚至包括公司雇員)的償債擔保,間接地處分了其它債權人的財產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偏重于擔保行為本身的效率,而忽視其帶來的負的外部性,在法益保護的考量方面,至少是不周全的。
析言之,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因為擔保使擔保權人在債務人破產時處于有利的地位,它可能會使借款人從某一本來不愿批準貸款的特定出借人中獲得貸款,或者至少從該出借人中獲得比沒有擔保的情況下更低的利息,因而改善了借款人的待遇。[注]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項目風險越高,貸款利率也越高。但信息不對稱創建了不完美的市場和信貸配給理論,該理論稱,就給定利率而言,貸款并不會分配給所有需要它的人。參見J Stiglitz and A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1981) 7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93。轉引自Eilís Ferran,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48-349.另外,對于債權人而言,由于設定了擔保,擔保債權人無須通過合約來對債務人的整體業務進行監督,而只須核查作為其擔保權標的物的資產沒有被耗散即可,從而降低了對擔保債務的監督成本,并且改善了利息的收取。[注]TH Jackson and AT Kronman, “Secured Financing and Priorities Among Creditors” (1979) 88 Yale Law Journal 1143.這是有利于擔保債權人的方面。
對于無擔保債權人而言,從理論上說,在一個完美的市場中,無擔保債權人在妥當考量各種外部性之后,會準確地調整其對公司的債權融資價格,以補償其借款給已把資產抵押給其它人的公司的額外風險;易言之,其他無擔保債權人可能會要求收取更高的利息,以補償其在借款公司破產時求償權劣后于擔保債權人的風險。[注]A Schwartz, “Security Interests and Bankruptcy Priorities: A Review of Current Theories” (1981) 10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 A Schwartz, “The Continuing Puzzle of Secured Debt” (1984) 37 Vanderbilt Law Review 1051.另外,“擔保的存在減少了公司可供利用的資產,提高了公司對無擔保債權人預期違約的成本,因而激勵著這些主體更為全面地實施監督”。[注]關于擔保債務“監督”的變化的解釋,參見S Levmore, “Monitors and Free riders in Commercial and Corporate Settings” (1982) 92 Yale Law Journal 49; RE Scott, “A Relational Theory of Secured Financing” (1986) 86 Columbia Law Review 901, 925.如果不考慮信息和談判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說,擔保的設定是一個效率事件,博弈各方將會自行通過博弈達到均衡。
然而,擔保債務的市場仍然是不完備的,關于擔保債務的效率也未有定論。[注]JL Westbrook, “The Control of Wealth in Bankruptcy” (2004) 82 Texas Law Review 795, 842. L LoPucki, “The Unsecured Creditor's Bargain” (1994) 80 Virginia Law Review 1887; LA Bebchuk and JM Fried, “The Uneasy Case for the Priority of Secured Claims in Bankruptcy” (1996) 105 Yale Law Journal 857.具體說來,由于存在貸款人提供了非自愿性信用,或者不夠老練的貸款人缺乏正確定價風險的能力而提供了信用的情形,在這些情況下,都不會發生價格調整的結果。相反,擔保機制可能會帶來社會福利的減損,因為它們會導致無法補償的風險落到最不知情、調整貸款條款的能力最差、在借款公司破產時得到的保護最弱,并且最沒有能力承擔財務風險的債權人頭上。[注]同上注。而且,在公司提供擔保的情況下,擔保公司的小股東與大股東存在表決權重、信息占有等方面的不對等,以強調擔保行為本身的效率為由,忽略章程對擔保行為的約束,相當于允許大股東或董事會恣意處分小股東的財產權益,也相當于允許擔保公司通過隨意設定擔保,從而選擇性地侵害債權人的利益。
總之,違背公司章程的規定而設定擔保,處分了公司的財產權益,并且間接地損傷了公司其他債權人的利益。故而,在裁判公司擔保行為的效力時,如果片面追求交易的效率,而忽視股東、其他債權人等多元法益的保護,難免給人以“一葉障目不見森林”之惑。
(二)法律公知力及其對章程效力的提升
主張公司章程關于擔保事項的規定對于第三人具有拘束力的觀點,最早源于公司章程的對世效力理論,后者則以英美法上的推定通知理論(the principle of constructive notice)為基礎。該理論認為,公司章程一旦公開,就意味著向第三人發出了通知,進而推定第三人應當知道并理解其中的內容,因而章程中有關公司的業務范圍、擔保約定等內容均可對抗第三人,并由此發展出了越權原則。也就是說,公司違背股東意愿超越章程的行為均屬無效。
然而,由于越權原則給公司行為的效力帶來了不確定性,破壞了交易第三方的合理預期,故而,現代各國的立法趨勢是拋棄推定通知理論及越權原則。例如,1968年《歐共體第一號公司法指令》第9條第1款就規定:“成員國可以規定,如果公司能夠證明第三人當時不可能不知道其行為超越了公司的目的范圍,那么公司不受超越公司目的范圍的行為的約束。但是,章程的公開行為本身不構成第三人知道的證據。”第2款進一步規定:“公司章程或者有決議權的公司機關對于公司機關權力的限制,不得被公司利用來對抗第三人,即使這些限制已經公告也是如此。”[注]劉俊海:《歐盟公司法指令全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頁12。英國1989年修改的《公司法》第711條A(1)也規定:“僅僅因為某事項已在公司注冊處的存檔文件中被披露(因而能夠調查)或可以到公司調查,一個人不應被視為知道任何事項。”[注]虞政平編:《英國公司法規匯編——從早期的特許狀到當代的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頁1716。類似地,《日本公司法》第11、14、15條規定,對公司經理等人的代理權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注]王保樹主編:《最新日本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頁30-31。
基于此,一些公司法學者主張公司章程關于擔保權限的規定,不得對抗第三人。[注]2010年11月由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舉辦的“公司法適用高端論壇”上,包括施天濤教授在內的一些學者持此種見解。此種見解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然而,它存在的邏輯缺陷在于:其一,通觀各國實在法及基本法理,雖然并不假定公布章程即推定公知,因而無法推定第三人均知悉章程的內容,但均未規定要保護非善意第三人。如果作為第三人的擔保人有義務查閱公司章程而未查閱,或者雖查閱卻未發現或理解章程關于公司擔保的規定,則非屬善意第三人。其二,根據我國的合同法理,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如果合同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對方超越權限,則該合同應歸于無效。[注]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0條的規定。因而,非屬善意的第三方不受保護,乃我國制定法的現實規定。其三,根據公司章程或公司決議乃公司內部行為之機理,固然可以推知第三人并非當然地具有查閱公司章程之義務,但一旦公司擔保程序由公司內部要求提升為公司法規定時,其效力層級及范圍就發生了變化。眾所周知的是,法律具有普遍適用的效力,因而具有推定公知的屬性。
就我國而言,一方面,2005年《公司法》第16條明確規定由公司章程來設定擔保權;另一方面,該法第6條第3款明確規定,公眾可以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查詢公司登記事項,公司登記機關應當提供查詢服務。因而,由于公司章程是公司設立申請登記時必須報送的文件之一,具有公開性。第三人得經由登記機關得知章程之內容,而決定是否與之發生交易關系。[注]王文宇:《公司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80。如果公司章程已經登記在冊,但第三人并未前往公司登記機關查詢,也未要求公司出具公司章程,則第三人非為善意,公司章程記載的事項可以對其發生對抗效力。
(三)擔保權人審查的限度:合理的形式審查
認為章程的規定不得拘束擔保權人的觀點,其理由還在于,公眾查閱公司章程、辨識可能存在的虛假簽章存在困難。的確,雖然《公司法》第6條授權公眾查詢公司的登記事項,但該條并沒有對登記事項的內容進行細致的界定。在實踐中,為了平衡公眾的知情權和公司的隱私權,公司登記機關將公司登記資料分為內部登記資料和外部登記資料,外部登記資料對公眾公開,而公司章程則屬于公司的內部登記資料,不對公眾公開。在一些工商部門,普通民眾往往只能查詢到非常簡單的基本信息,如果要查詢詳細的信息必須由律師出面。由此,有學者認為,第三人并非能夠輕而易舉地查詢公司章程的有關內容,此時仍然想當然地認為,章程屬于第三人可隨時知曉的范圍,無疑是對第三人的法律歧視。[注]劉玲伶,見前注〔29〕。
更有學者擔憂,在極端的情況下,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為達到提供非法擔保的目的,無所不用其極,偽造股東或董事簽章,形成有利于其的擔保決議,對此,擔保權人是否有義務審查簽章的真實性?如有義務而未審查出簽章虛假,是否可以因此而認定擔保無效?[注]2010年11月由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舉辦的“公司法適用高端論壇”上,一些學者和法官提出了此種見解。
筆者認為,這些技術層面的問題固然重要,但如果因此認定公司章程和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對于第三人沒有拘束力,則在法理和邏輯上均難圓暢,其理由如下:
其一,確如所述,實踐中查閱章程確實存在困難,但這種困難完全可以在技術層面解決。舉例而言,銀行在發放貸款并要求借款人提供擔保時,如果銀行不易獲得擔保人的公司章程和有關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完全可以要求借款人商請擔保人提供,否則不予發放貸款。借款人為了獲得貸款,勢必會辦妥相關事宜,擔保權人固無須親自調閱。
當然,從便利查閱考慮,我國的工商登記制度可作相應配套修改:一方面,明確公司章程關于擔保的規定為公司的外部登記資料,應對外公開; 另一方面,規定公司對外提供的擔保,除根據擔保法在相關登記機構登記外,還應在公司登記機構統一進行備案登記,以供潛在的債權人查閱,并可就此提示交易風險。
其二,在實踐中,公司章程和相關的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甚至簽名,都存在造假的可能,但如果因此而認定這些公司內部行為對外不生任何效力,則實在是“倒洗腳水時把嬰兒也一起倒掉了”。類似地,這種技術上的困難可以在技術層面解決。舉例而言,如果擔憂擔保人提供的資料造假,擔保權人完全可以商請借款人,要求擔保人提供經過公證的相關資料,費用由借款人承擔。由于偽造公證文書涉嫌犯罪,高昂的違法成本足以遏制擔保人與公證人共謀造假的激勵。
其三,雖然在技術層面可以解決因公司內部文件造假而給擔保權人帶來的困難,但在法理層面,擔保權人是否有義務辨識公司章程和相關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甚至簽名的真假,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一般認為,擔保權人對公司章程具有合理審查義務,這種合理審查義務是指擔保權人對公司章程的真實性與合法性、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的真實性和有效性進行必要而合理的形式審查,但不宜超過一定的限度。有學者指出,“形式審查既不是實質審查,也不是不審查,而是審慎的形式審查”。[注]劉俊海:《現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頁491。這種表述不無道理,但仍嫌過于抽象。筆者認為,在這方面可以借鑒美國公司法上的“注意義務”標準。換言之,擔保權人只須承擔“一般的理性人在類似情況下應當具有的注意義務”即可。[注]2010年11月由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舉辦的“公司法適用高端論壇”上,顧功耘教授認為,應區分擔保權人的身份,從而施加程度不同的注意義務。如果擔保權人是專業擔保公司,則須承擔更高的審查義務;而如果擔保權人是一般的公司或個人,則其承擔的審查義務較低。此種見解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對法官的理論學養和專業裁判水平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具體說來,擔保權人只須查驗擔保人的章程中關于擔保權的規定、查驗股東會(或董事會)的決議是否符合章程規定的多數比例等形式方面的內容,而無須查驗股東或董事的簽名是否虛假,因為擔保權人并無渠道獲得這些人員的簽名樣本,而且即便能夠獲得,要鑒別真假亦需專業水平。在“通常不會發生簽章造假”的合理假定下,要求擔保權人審查簽章真偽,已經超越了合理的注意義務。
值得關注的是,2008年4月21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公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四部分“關于公司擔保”第6條規定,“公司提供擔保未履行《公司法》第16條規定的內部決議程序,或者違反公司章程規定的,應認定擔保合同未生效,由公司承擔締約過失責任。擔保權人不能證明其盡到充分注意義務的,應承擔相應的締約過失責任”。該規定明確了擔保權人對公司內部決議程序的審查義務。
(四)司法裁判的導向功能:以保守立場促成誠信醇厚的商業文化
近年來,我國法院累積了大量的商事案件審理經驗,進入了一個追求裁判質量的時期。這固是有利之事,然而,對于法律行為效力架構精細化的過分追逐,卻容易遮蔽司法在商事領域的最基礎價值,即通過定分止爭,促成誠信醇厚的商業文明的形成。具體到公司擔保而言,如果擔保權人可以通過審查擔保人的章程和相關決議而避免爭議,法院仍區分種種情事,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認定違背章程規定的擔保有效(而且似乎有進一步強化的態勢),[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負責商事審判的民二庭庭長宋曉明稱,公司為股東或實際控制人進行擔保,即使未經股東會決議,也不宜籠統認定該擔保無效,應當根據不同情形分別判斷。對于封閉性公司,比如有限公司或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由于股東人數少,股東通常兼任公司董事或高管,管理層與股東并未實質性地分離,股東對公司重大事項仍有一定的影響力,該類事項即使未經股東會決議,但通常也不違背股東的意志。況且封閉性公司不涉及眾多股民利益保證、證券市場秩序維護等公共利益問題。但如果是公眾公司,比如上市公司為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則應當審查該擔保是否經過股東大會決議同意,未經股東大會決議同意的擔保,屬于重大違規行為,侵害了眾多投資者利益,應當認定無效。這種分類方法最大的危險在于為封閉公司控股股東或內部人濫用擔保權損害中小股東、雇員以及其它無擔保債權人利益,提供了裁判法理的支撐。參見宋曉明:“關于商事審判若干疑難問題的思考”,《人民法院報》2010年9月1日。或者雖認定擔保無效但仍判定擔保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則實不利于促成誠信重諾的商業文化。反之,如果能夠像北京高院所作出的指導意見那樣,公司擔保違背章程規定或未履行內部決議程序的,一概認定無效,則可倒逼擔保權人細為審查擔保人的章程和相關決議,從而減少爭端,降低訟累。久而久之,市場主體的機會主義心理將漸為消弭,誠信醇厚的商業文化將漸次形成。從長遠看,它將降低社會整體交易成本,增進社會福祉。
就目前來看,法院之所以傾向于認定公司違反章程規定的擔保有效,或者不論擔保是否有效均要求擔保人承擔連帶責任,其深層原因在于法院秉持的裁判價值觀偏重一隅,認為這有利于提升交易效率,保障債權安全。
在實在法的層面上,就法益保護而言,《擔保法》與《公司法》存在潛在的沖突。《擔保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資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債權的實現,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制定本法。”由此可見,其立法目的在于促進交易效率并保障債權。《公司法》第1條則規定:“為了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定本法。”因此,公司法的首要目標是保護公司利益,因為公司財產承載著股東、債權人、雇員、管理層等多元主體的利益訴求。這兩部法律所保護的法益,在公司擔保違反章程規定時,呈現出了劇烈的沖突。析言之,如果法院重在保護擔保權人而認定擔保有效,看似促進了交易效率,但傳遞出的信息卻是擔保權人無須細為查驗公司章程而可隨意接受擔保,則勢必會造成控股股東、董事會或公司內部人濫用擔保權而侵害中小股東、雇員以及公司無擔保債權人的利益。故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對于本質上屬于處分公司財產的擔保行為,法院實不應偏重交易效率,而應本著穩健保守的立場,本著在多元法益中求取妥當平衡的原則來作出裁判。
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化是,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釋二》最初將該“強制性規定”解釋為“效力性強制性規范”,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范的合同才無效。而2009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中又要求“人民法院應當注意區分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具體情形認定其效力。”因而,筆者認為,公司擔保違背章程規定或內部決議程序的,即便只屬于違背管理性強制規定,從倡揚誠實守信的商業文化、審慎處分公司資財、保護多元法益角度,亦因認定擔保無效。
四、 結 語
的確,從歷史上看,在商業世界里,驅動著法律發展演變的是實踐人士而不是立法機構,法院在市場的創新性結構面臨不確定性時來判定其法律效力。在這一意義上,司法裁判發揮著重要的資源再分配功能。在這方面,英國法院的做法發人深省。一方面,法院固不可因循守舊而扼殺市場人士的靈活性和創造力,另一方面,在存有疑義的領域,法院也不能對市場人士天才般的思維所創造的種種方案,提供一份橡皮圖章般的認可。合同自由要受到公平價值觀的制約。[注]F Oditah, “Fixed Charges and Recycling of Proceeds of Receivables” (2004) 120 LQR 533, 537-8.當法院所信守的價值觀被違背時,法院并不僅僅因為會使實踐人士失望而羞于作出決定。[注]Re Spectrum Plus Ltd [2005] 2 AC 680, HL (上議院拒絕推翻早期不連貫的判例,以免破壞既存的擔保安排); Smith(Administrator of Cossleit (Contractors) Ltd) v Bridgend County Borough Council [2002] 1 AC 336, HL. (標準格式的文本已被使用多年,而從未有人認為它創造了浮動抵押,這一事實并不構成法院認為其并不構成浮動抵押的理由;Hoffmann法官稱:“因而,不能假定合同主體試圖創建此類抵押。但固化形式的合同所表達出來的合同主體的意圖,只關乎他們相互權利和義務的確立。而此類權利和義務是否被界定為浮動抵押,則是個法律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的解答,可能在合同主體的意料之外,但沒有理由做出不同的界定”)。
就公司擔保而言,如果偏重擔保的創新與交易效率,則勢必會帶來關于公平的擔憂:[注]V Finch, “Security, Insolvency and Risk: Who Pays the Price” (199) 62 MLR 633, 660—7.法律輕易接受債權人的擔保偏好,從而允許發生以下情形:擔保權人可以介入并卷走一切,而給無擔保債權人什么都沒有留下,特別是那些未獲薪酬支付的員工。[注]Re Spectrum Plus Ltd [2005] 2 AC 680, HL, para 97 per Lord Scott. In Salomon v A Salomon and Co Ltd [1897] 2 AC 22, HL, 53(Macnaghten法官將浮動抵押卷走財產的后果,描述為“大的丑聞”)。在英國,此類擔憂已經引起了立法機關的關注,從而在公司立法中引入強制性披露要求來予以干預,據此,絕大多數的擔保形態必須進行登記才能獲得法律效力。[注]參見英國《2006年公司法》第25部分。向來尊崇市場機制的英國,對于公司擔保的保守立場,當值我國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