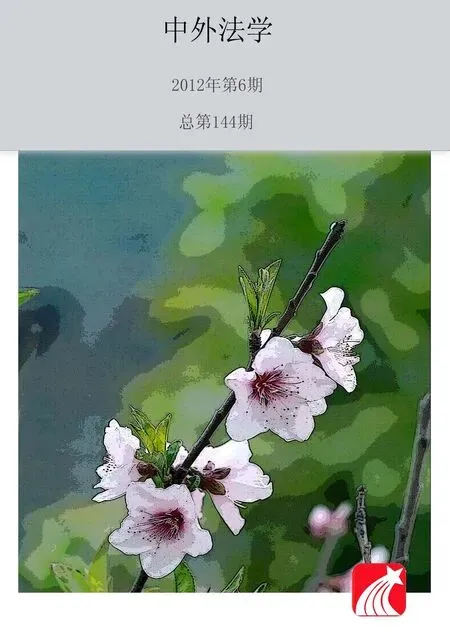公債和民主
沈朝暉
是誰掌握世界的樞紐?誰左右
議會,不管它傾向自由或保皇?
是誰把西班牙赤背的愛國者
逼得作亂?使舊歐洲的雜志報章
一致怪叫起來?是誰使新舊世界
或喜或悲的?誰使政客打著油腔?
是拿破侖的英靈嗎?不,這該問
猶太人羅斯察爾德,基督徒巴林!
(第十二章第五節)
這些人和那真正慷慨的拉菲特[注]拉菲特是當時作為巴黎金融業中心的的法蘭西銀行的行長。1800年,拿破侖簽發命令,成立法蘭西銀行,形式為私有企業,資本金為3000萬法郎,由15名董事管理及3名監察員監管。拿破侖不久就加強對法蘭西銀行的控制,1806年簽發命令指派一名管理者和兩名副官,并不可被解職。尤瑟夫·凱西斯:《資本之都——國際金融中心變遷史》,陳晗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頁23。
才是歐洲真正的主人。每筆貸款
不僅是一宗投機生意,而且足能
安邦定國,或者把王位踢翻。
(第十二章第六節,節選)
——拜倫:《唐璜》,查良錚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頁748。
本文從民主的視角切入中國債券市場的研究,探討金融市場影響政府治理的一般原理,以及中國金融市場政治功能的完善和前景展望。
隨著2011年“7·23”甬溫線高鐵特別重大事故[注]在2011年7月23日晚上20時30分左右,北京南站開往福州站的D301次(南昌局)列車高速撞擊正在鐵軌上等待信號的由杭州站開往福州南站的D3115動車(上海局)。官方認定,此次高鐵特大事故造成約40人死亡、172人受傷。國務院“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調查組:《“7·23”甬溫線特大鐵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2011年12月25日。相關報道參見鄭道等:“信號奔命”,《新世紀》2011年第34期。一同爆發的還有鐵道部的債務危機,中國債券市場由于基礎設施跨越式發展而累積的不可承受的危機爆發了。“7·23”事故發生前后,金融市場對鐵道部債券的反應頗為意味深長。這里講的金融市場對“7·23”悲劇的反應不是指那些與鐵道部有業務往來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的波動——這不是新鮮現象;而是指在一個相對不為公眾所熟悉的中國政府債券市場,以鐵道部名義發行的鐵路建設債券的市場成交情況和價格波動,它反映了市場參與者,尤其是債權人,對鐵道部和鐵路建設債券的信心和觀點。事故兩日之后,即7月25日周一債券市場開盤,鐵道部債券成交很冷清;7月26日,無一筆鐵道部債券成交。[注]付濤:《“7·23”追尾與鐵道債遇冷》,2011年08月01日,網絡來源“財新網”:http://finance.caixin.com/2011-08-01/100285877.html#comment_top;張宇哲:《鐵道部短融零成交 債市左右為難》,2011年07月26日,網絡來源“財新網”:http://finance.caixin.com/2011-07-26/100284204.html(本文資料的網絡來源最后驗證日期均為2012年8月18日,下同)。“7·23”事故后的半個月,即8月8日鐵道部在債券市場發行90天的超短期融資券(SCP)——這說明鐵道部資金緊張才選擇發行SCP,而且期限越短,風險越小,則相應的利率也應越低。根據以往的情況,以3-4%的利率成本,鐵道部就能將債券成功發行出去,可是實際發行的招投標利率攀升至5.55%,相比歷史情況上升了兩個百分點左右,鐵道部為此要多向債權人支付8000萬的利息。債務危機具有長期性,鐵道部的資金緊張至少持續了三個多月,并引發一系列的反應,包括鐵路建設停工、相關企業的業務和股價下跌、農民工工資拖欠等問題。國務院在10月份以稅收減免和將鐵道部債券拔高定性為政府支持債券的措施,緩解了鐵道部的資金問題,但直到2012年春節之前,鐵道部在債務市場籌資仍不順利。
吊詭的是,在“7·23”事故的前兩天,金融市場仿佛有了預感。7月21日(周四),鐵道部準備在債券市場招投標2011年第三期短期融資券(代號:11鐵道CP03),募集資金的用途是用于鐵路建設、機車車輛購置及運營中的資金周轉。這些往常被認為高信用等級的債券竟意外地招標未滿,計劃募資200億元,實際中標量187多(187.3)億元,中標利率5.18%落在鐵道部給定的投標利率區間的上限。流標的13.7億元只能由承銷商包銷。盡管七月債券市場行情不好,但作為信用等級為超AAA的鐵道部債券卻流標,這在中國債券市場歷史上還是頭一回。[注]張宇哲,見前注〔3〕。承銷商銀行兜底后,“11鐵道CP03”仍然進入債券市場流通。當然,7月21日的金融市場和債權人并沒有能力預見“7·23”高鐵特大事故的發生。鐵道部債券流標的原因是7月14日鐵道部公布了2010年年報。年報中反映,隨著高鐵四縱四橫的跨越式發展,鐵道部的負債和虧損也在大幅增加,負債率增加到將近60%(從53.06%增加到57.44%),每年要還本付息1501億元(本金1250億元,利息251億元),而鐵道部的經營現金流僅1567億元,還需借新債還舊債。[注]于寧:“鐵道部進入虧損周期”,《新世紀》2011年第29期(“鐵道部今年經營現金流約2000億元,而還本付息的壓力則有2500億元。由于今年債券到期明顯增加,在貝樂斯看來,“2500億元債務是保守估算,這包括債券還本1210億元,債券利息238億元;貸款本金1000億元,貸款利息100億元。相比之下,去年只有300億元的債券到期”)。
同一個重大事件的發生,對不同知識結構的受眾會產生不同的外來刺激和思維反應。筆者的研究領域是公司金融法。鐵道部債券在債券市場中先是投標不足,后是融資利率上升,形成對鐵道部的制約。這些隨著“7·23”事故而跳躍出來的現象對金融法學者很有啟發。“融資、約束和治理”是金融法的基本邏輯和范式。它立足于公司,公司接受投資者的資本,投資者約束并促進公司的治理。公司金融法實際上是在處理不同投資者的保護問題,不同類型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和投資者與公司管理層之間的代理問題等。它強調管理層要對投資者承擔信義義務。總之,“融資、約束、治理”這六個字概括了公司金融法的基本內容。[注]Lawrence E. Mitchell, et 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Governance, 3rd ed.,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6, pp. 3-5; Erik Berglof, “A Note on the Typology of Financial Systems”, in Klaus J. Hopt, Eddy Wymeersch, ed., Compara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Essays and Materials,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1997, pp. 159-164;維夫斯(編),《公司治理:理論與經驗研究》,鄭江淮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頁100-111。
而作為政府部門,鐵道部在金融市場的大量融資及實踐表明,不僅僅是公司,國家也存在旺盛的金融需求與活躍的金融活動。順著“融資、約束、治理”的思路,將公式中的公司替換為國家或政府,由此推導出下文將用全篇幅的文字加以論證的一個大膽結論:債券市場對政府具有約束、治理的民主功能。當國家或政府進入金融市場融資,要遵守金融市場及法制中已經形成的一整套保護投資者的制度和慣例(比如信息披露的質量與政府融資的利率掛鉤),接受投資者的約束與監督。投資者通過金融市場參與那些影響債券收益的重大事項的政府決策,促進政府的治理。比如,“7·23”高鐵事故后,鐵道部在債券市場融資的短期利率上升兩個百分點,這就是中國債券市場對政治事件和政府狀況有所反應與約束的初步表現,但它的民主機制和政治功能遠遠發揮的不夠,還有很大的潛力。
本文是從私法視角看待一個公法問題,下面將從兩個方面打通公債和民主機制之間的聯系:歷史和理論。本文相當一部分取材于歷史,考察歐美的債權人在資產階級民主誕生和鞏固中發揮的作用。在理論方面,本文將論述債券市場和私人債權人影響政府,使政府敬畏市場意志進而順從民眾意志的具體機制。最后一部分討論中國公債市場的性質、結構及其政治局限。
在展開論述之前,首先界定公債和民主的涵義。一般認為,“公債”即公共債務或公共部門債務的簡稱,包括一個國家的公共部門憑借公共信用舉借的各類債務。這里的公共部門是指不同層級的政府及其部門,[注]張雷寶(主編):《公債經濟學——理論·政策·實踐》,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13。包括政府設立的殼公司。相對于公債定義的普遍共識,學術界對民主的定義則有多種觀點,并形成了脈絡清晰的學術史。民主不等同于選舉,而是經歷從代議制民主到“選舉民主”、“自由民主”、“法治民主”的認識過程,[注]蔡定劍:“重論民主或為民主辯護”,《中外法學》2007年第3期。流派包括密爾的代議制民主理論、熊彼特的選舉民主理論、達爾的多元民主理論、科恩的公眾參與的民主理論、薩托利的自由民主理論、協商民主理論。[注]同上注,頁260-262;(美)佩特曼:《參與和民主理論》,陳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頁1-21。開篇明義,本文對民主的定義是指通過約束、直接監督和公共參與等方式,民意影響政府的決策和行為,使之與民眾的利益一致,切實對民眾負責。公共參與是民主的顯著標志。[注]王錫鋅:《公眾參與和行政過程——一個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頁2-3;關于參與民主理論的學術述評,參見佩特曼,同上注,頁22-41。民主還意味著某種程度的代議制:債權人通過債券市場,轉化為民眾的代議人,具體行使約束、監督和公共參與的功能。
一、 歷 史
政法制度的變遷和金融市場的發達之間存在卡爾·波蘭尼所謂的“雙向運動”。[注](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剛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頁66。一方面,在North和Weingast的歷史制度主義中,政府的可信承諾是金融市場發展的關鍵因素。他們指出,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促使英國憲政轉型,政府不得不在獲得議會同意后才能改變其決定,而議會代表著財富持有者,議會角色的增強減少君主/政府對債務違約的可能,英國政府由此建立起對金融市場的可信承諾。相比18世紀仍實行君主專制主義的法國,英國在發行政府債券籌集戰爭軍費中更有制度優勢。[注]Douglass C. North,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4 (Dec., 1989), pp. 803-832.基于通過金融市場動員國內財政資源的能力,英國迅速在光榮革命后崛起為世界強國。
另一方面,金融史學家的研究指出,金融市場不是被動地接受現存的政法制度,它具有能動性,會促進上層建筑轉型。[注]James Macdonald, 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 2nd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Fausto Piola Caselli, ed., Government Debts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Europe, Pickering & Chatto, 2008; Larry Neal,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 Rea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英)弗格遜:《金錢關系:現代世界中的金錢與權利(1700-2000)》,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蒂利指出,從1480年到1800年,歐洲的戰爭不斷,[注](美)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992年)》,魏洪鐘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頁74。戰爭等持續的外部威脅是歐洲資產階級民主建立并鞏固的重要因素。因為君主依靠征稅,能應付日常的開支,但是一旦發生戰爭,特別是長期持續性的戰爭,君主和王室的負擔激增,在增稅、賣官爵、出賣王室土地、向國際金融家借外債等融資渠道均窮盡的同時,歐洲的君主們往往不得不求助于國內的借款。[注]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第三版),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頁308-312。而金融市場是國家在面臨持續外部威脅的環境中,動員國內民眾資源的最佳手段之一。[注]Svetlana Andrianova, Panicos Demetriades and Chenggang Xu, “Political Economy Origins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Europe and Asi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9, No. 5, 2011, p. 695-696.飆升的金融需求使得政府或君主越來越依賴通過議會的融資。只有當君主需要議會控制的金錢資源時,議會才能控制君主。[注]Edgar Kiser, “The Formation of State Policy in Western European Absolutisms: A Comparison of England and France”,Politics & Society, Vol.15, No.3, 1986-1987, p.282.長期處于休眠狀態的議會和民眾的力量開始崛起,打破已經形成的稅收契約,對國內政府財政改革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進而逼迫國內的專制政權進行政治改革,突出議會的代議作用。
回望歐洲的歷史,政府的債權人通過既存的議會機構鞏固民主,例如荷蘭;政府的債權人結成黨派力量,通過在議會中結盟,維護自己的債權利益,使得代議機構具有長期穩定性,例如英國;金融市場和國債,特別是國家的長期借款及還債聲譽,對君主的生存非常重要,例如,法國君主屢次不還債,債權人/資產階級通過大革命推翻舊制度,不過在大革命后,法國的政治社會結構使得法國的債權人在制憲會議得不到保護,債權人退出制憲會議,繼續革命,破壞了法國代議機構的穩定性。
首先從國債的源頭地說起。相比私人借款,[注]關于史前、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和羅馬等的私人借款情況和利率史的匯總考證,參見(美)霍默、西勒:《利率史》,肖新明等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頁3-43。君主借款的歷史要短一些,特別是發展出長期借款制度的歷史更短。一般認為,在13世紀中期之前,意大利的城邦國家創造了先進的國債發行和流通機制,并在意大利城邦(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復雜的公債體系下產生了類似食利者的團體。[注](美)戈茲曼、羅文霍斯特(編著):《價值起源》(修訂版),王宇等譯,萬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頁152-153。在熱那亞共和國,為了應對戰爭所造成的臨時性支出的增加,議會以稅收作抵押,向由投資者組成的的辛迪加借款。在1432年,為籌集12艘“加蓬”船的建造費用,議會又將對海事保險合同的課稅權作為借款的擔保,由辛迪加向民眾發行了7%收益率的證券,為國王籌集資金。在15世紀早期,熱那亞共和國在金融災難的邊緣搖搖欲墜。熱那亞共和國的債權人意識到這種情形難以為繼,于是著手保護其債權免受迫在眉睫的國家破產的威脅。1407年,他們建立了在政府債務史上有名的Casa di San Giorgio (House St. George, 圣·喬治銀行)。它是由債權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債權發展起來的一個組織。該機構名義上是一個私人聯盟,但其功能卻在于恢復國家金融秩序,降低債務違約的風險。圣·喬治銀行的運作始于債轉股:將債權人對熱那亞的巨額國債轉化為對圣·喬治銀行的持股。圣·喬治銀行向共和國的政府行為提供“捐款”。作為回報,圣·喬治銀行獲得了征稅權、利潤豐厚的鹽與薄荷的壟斷專營權,以及若干海外領地的管理權。[注]戈茲曼、羅文霍斯特(編著),見前注〔19〕,頁158。圣·喬治銀行擁有相對完善的公司治理,設有若干委員會以及一個被稱為“圣·喬治銀行保護者”的八個具有財務專長的人組成的董事會,圣·喬治銀行的11000名股東同時也是城邦的民眾。[注]Michele Fratianni, “Government Debt, Reputation and Creditors’ Protection: the Tale of San Giorgio”, Review of Finance, Vol. 10, 2006, pp. 493-494.圣·喬治銀行逐步成為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金融機構。[注]戈茲曼、羅文霍斯特(編著),見前注〔19〕,頁158。圣·喬治銀行持續了從1407年到1805年四百年的歷史。它有力地束縛住了熱那亞政府的手腳。“熱那亞的儲蓄者都知道,圣·喬治銀行的基礎是不可動搖的,否則就有可能引發社會動亂。”[注]戈茲曼、羅文霍斯特(編著),見前注〔19〕,頁162。它是一個以債權人對于國家信貸的控制權來限制那些謀求熱那亞統治權力的人通過濫用民眾授權而攫取權力的案例。它削弱少數幾個曾經統治熱那亞的獨裁家族的權威、通過控制金融事務來限制政治權力的專斷實施。以致馬基雅維利(Machiaveli)把這個金融組織描述為熱那亞的國家核心:“在市民的心中,管理良好的、公平的圣·喬治銀行終于替代了獨裁的公社成為熱那亞的國家核心。”[注]轉引自戈茲曼、羅文霍斯特(編著),見前注〔19〕,頁158-159。有法律學者也認為,由于股東絕大部分也是熱那亞的居民,圣·喬治銀行的政策大大促進了民主價值的生長,促成官員與民眾利益的一致。[注]Clayton P. Gillette, “Can Public Debt Enhance Democracy?” 50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p. 941(2008-2009)(中譯文請參見:克萊頓 P. 吉列:《公債能增進民主嗎》,沈朝暉、林凱譯,載張守文主編:《經濟法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如果圣·喬治銀行還只是債權人約束專制者的一個特殊案例,那么荷蘭的債權人在議會的作用則是債權人促進民主的常態。17世紀之前,因為兩次戰爭(荷蘭與西班牙戰爭、荷蘭與英國之間的戰爭),荷蘭在債券市場上籌集了大量資金,建立了可靠的公共財政和公共債務市場。[注]戈茲曼、羅文霍斯特(編著),見前注〔19〕,頁315。17世紀早期荷蘭的金融革命使得荷蘭迅速崛起。原因是債權人通過議會——有產者會議制衡獨裁的王權。荷蘭有產者會議相當大的權力掌握在城市的利益群體中,代表每一個城市的地方官員通常是商人或銀行家,議會成員就是政府債的重要購買者。[注](英)斯塔薩維奇:《公債與民主國家的誕生》,畢競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57。因此,私人債權人在議會中得到了很好的代表。[注]同上注,頁50。在政府債務執行方面具有直接利益的個人支配了荷蘭的代議機構。[注]同上注,頁57。進而,政府的債權人控制荷蘭的財政政策,這是尼德蘭公共借款體制在哈普斯堡統治開始時期以及輝煌的17世紀的天才之舉。[注]同上注,頁57。
荷蘭的金融體制對英國影響頗深。雖然1215年英國貴族和教士通過“大會議”(Grand Council)制定大憲章后,議會有權接受或拒絕國王征收新稅的要求,但是,英國王室在1603至1688年間仍然在財政支出和借款決策上享有實質裁量權。[注]同上注,頁61。(“在與議會的關系上,國王也有優勢,他可以決定議會何時召開、何時平民院進行新的選舉。非常支持查理二世的騎士國會坐鎮長達18年(1661-1679年)。1641年通過的一項法案要求每三年召開一屆新的國會,但是這項法案在查理二世統治的1664年被廢止。”)1603-1688年,議會與國王的沖突不斷加劇,[注]同上注,頁61。英國國王屢次不償還貸款。例如,復辟的斯圖亞特王朝查理二世為了戰爭需要和獲得免費收入,在1671年宣布止付政策。[注]同上注,頁61。1688年光榮革命后,君主的債權人通過組成輝格黨,鞏固了光榮革命后議會的實權和對君主專制的限制。[注]同上注,頁97。輝格黨(代表債權人的利益,貨幣權益者)和托利黨(代表土地主的利益,土地權益者)通過妥協和結盟,維護了議會在英國政治生活中的權威。而且,當輝格黨在議會占據優勢時,英國政府的借款利率會顯著降低。[注]同上注,頁77-80。輝格黨的力量和政治謀略使得議會和政府必須充分地尊重債權人的利益。
不同于“光榮革命”,法國現代自由的建立是通過激烈的大革命,而引爆1787年法國大革命的是法國君主的財政危機。[注]J. F. Bosher, French Finances, 1770-1795, From Business to Bureau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83-196;Kathryn Norberg:“1789年法國財政危機與1789年革命的財政起源”,載(美)霍夫曼 等編:《財政危機、自由和代議制政府(1450-1789)》,儲建國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頁280。大革命前,法國的公共借款有三個特征:全國性代議機構的薄弱;嚴重地依賴中介進行借款(法國年金);為籌集戰爭資金而賣官賣爵。[注]斯塔薩維奇,見前注〔27〕,頁83。其中,搞垮法國國家財政的是一個蘇格蘭人——約翰·勞。路易十四的窮奢極欲為攝政王時期留下一團糟糕的財政。攝政王召集法庭,調查債權人的非法行為,對債權人施以嚴厲的罰金或監禁,同時將貨幣貶值。[注]斯塔薩維奇,見前注〔27〕,頁89。他聘請約翰·勞進行國家金融改革。約翰·勞是個爭議很大的歷史人物,具有傳奇的經歷,曾是一個賭徒,擅長概率的數學運算,[注]約翰·勞1705年完成的著作在我國有譯本,參見 (英)約翰·勞:《論貨幣與貿易——兼向國家供應貨幣的建議》,朱泱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該著作是勞對經濟問題的思考結晶。后流落到法國,被攝政王重用,雄心勃勃施展自己的金融才華。從1715—1720年,勞主要做了三件事情:模仿英國的英格蘭銀行,創辦法國的國家銀行,替政府或國王管理政府債務;成立西印度公司,債轉股(將國債全部轉為對西印度公司的股權)解決了君主的欠款;發行紙幣。由于西印度公司股價的抬升依賴密西西比河和法屬路易斯安娜的經濟,而事實上法屬路易斯安娜還是蠻荒之地,沒有勞宣傳的繁榮。1720年的密西西比股災,徹底摧毀民眾對皇家銀行和銀行體系的信心,法幣體系的崩潰造成民眾對銀行、信貸和金融革新的敵意。[注]Antoin Murphy:“法國公司所有權——歷史的重要性”,(加)莫克主編:《公司治理的歷史——從家族企業集團到職業經理人》,徐俊哲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頁136。勞逃離法國,留下法國財政和經濟的殘局。在債權人力量和資產階級階層逐漸生長的同時,法國君主的不斷違約激發了反抗。16世紀早期新的軍事沖突,特別是哈普斯堡戰爭,促使法國國王尋求新的財源,催生了很多政府的債權人。而法國工商業的發展,逐漸創造出不同于土地的新的財富形式——流動財富或商業財富,以及一個新的階級——資產階級,它自14世紀以來作為第三等級在王國的三級會議中占有一席之地。[注](法)勒費弗爾:《法國大革命的降臨》,洪慶明譯,格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頁1。皇室的債權人范圍比較廣泛,包括“貴族和資產階級、主教和傳教、官員和公務員、商人和手工業者、男傭女傭”。其中大部分人沒有在體制上確立政治“發言權”(包括資產階級)。
另一方面,法國的專制君主不斷對債務違約,債權人階層集聚了不滿和怨言。法國的外部戰爭不斷爆發,特別是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戰爭,使得法國的公共財政難以為繼。法國的專制君主經常采用簽令等手段勾銷自己的債務或干脆無賴地不承認自己的債務,公共信用崩潰,玩弄債權人,[注]Kathryn Norberg,見前注〔36〕,頁309。甚至作為君主附庸的某位法官也出來指責國王擱置皇家債券的利息支付。[注]Kathryn Norberg,見前注〔36〕,頁311。盡管約翰·勞導致的金融崩潰之后,法國君主在金融操縱方面有所收斂,但王室仍然大規模地抵賴和勾銷債務,[注]Kathryn Norberg,見前注〔36〕,頁337。直到“信用的死亡”。而18世紀的法國人民信奉以下道理,即君主必須遵守他自己訂立的契約,特別是君主不應將同樣的稅收用于償還其他的貸款,[注]Kathryn Norberg,見前注〔36〕,頁311。而法國君主常常否認債務,中止償還,以及威脅金融業主。國王再也得不到債權人的資金,公共信用枯竭。[注]Kathryn Norberg,見前注〔36〕,頁313。法國的三級會議在13世紀中葉到1789年長期衰落,對君主的財政問題沒有發言權。而在爆發財政危機瀕臨破產之際,君主及大臣試圖利用三級會議,增加新的君主財源。但是,1788年,第三等級利用召開三級會議的機會宣布獨立,建立制憲會議。

表一 法國君主的債權人所屬的社會群體類型(%)
資料來源:David Stasavage,PublicDebtandTheBirthoftheDemocraticState,FranceandGreatBritain, 1688-17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5.

表二 法國君主的債權人的地域分布
資料來源:David Stasavage,PublicDebtandTheBirthoftheDemocraticState,FranceandGreatBritain, 1688-17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5.
不過,法國議會的結構不同于英國。1789年6月召開的制憲會議中,604名代表是舊制度下的第三等級,295名代表來自于僧侶,278名來自于貴族。[注]斯塔薩維奇,見前注〔27〕,頁144。制憲會議分裂為左、右兩派,其中左派如雅各賓派的領袖馬拉,不支持履行之前的國王債務。債權人在制憲會議中占不了主導作用,如表一和表二所示,一半以上的債權人是貴族和官員,而且大部分是巴黎省內的,它們得不到省外代表的支持。1789-1791年的制憲會議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陣營:貴族和僧侶的多數是右派,大部分第三等級代表是左派。[注]David Stasavage, Public Debt and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1688-17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68.債權人訴諸制憲會議以外的革命手段聲張政治主張,越來越多的右翼人員退出制憲會議,甚至公開要求外國干涉,法國政局持續動蕩,[注]David Stasavage,見前注〔48〕, p. 168。這影響了法國代議機構的穩定性。
美國獨立之初,聯邦黨人巧妙利用債權人的力量,為聯邦政府爭取到了債權人的穩定支持。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各地發行了大量國債,漢密爾頓意識到,債權人是一股政治穩定的重要力量,誰爭取到了債權人的支持,誰就能獲得民心。漢密爾頓將各地方在獨立戰爭時期所欠的債務,全部轉由聯邦政府承擔。表面看起來,聯邦政府要承擔巨額的債務,但實際上聯邦政府獲得了債權人的支持。因為沒有債權人希望自己的債務人垮臺。[注](美)徹諾:《漢密爾頓:美國金融之父》,應韶荃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年版,頁249。另外一重效果是,美國開國之初,通過承擔債務的政府舉措樹立了國際資本對美國的信心,資本從世界各地迅速流向美國證券市場,美國經濟由此開始長達212年的增長周期。[注]戈茲曼、羅文霍斯特(編著),見前注〔19〕,頁311。19世紀40年代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當時持有美國州債券的債權人分布在歐洲(主要是倫敦)、紐約和費城。[注]William B. English, “Understanding the Costs of Sovereign Default: American State Debts in the 1840’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1 (1996), p. 261.美國爆發了嚴重的債務危機,民眾的憤怒促成了各州出臺財政憲法,例如平衡預算原則、債務總額限制等,[注](美)理查德·施拉格爾:《民主與債務》,沈朝暉譯,載《比較》第60輯,吳敬璉主編,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頁151。約束政府,鞏固了美國的憲政民主。
總之,在歐美資產階級民主誕生和鞏固過程中,債權人構成了市民社會的一部分,它的力量并不取決于資本的大小,而是取決于人數的多寡和債權人的組織能力。市民購買公債,關心政府的一舉一動,并形成公民社會,一旦君主或政府違約,就可能導致政治的變革或民主新制度的建立。當國王依賴少數幾個銀行家獲得貸款的時候,他往往通過國家權力將債權人進行“清洗”,猶太銀行家的悲慘命運就是典型的例子。奧本海默從擔當符騰堡公爵的宮廷官員起家,后來成為樞密院官員。1733年,他又成為駐法蘭克福特使。然而,幾年后他被判濫用政治職權,有損符騰堡家族地位而被處死。[注](英)弗格森:《金錢關系:現代世界中的金錢與權利(1700-2000)》,唐穎華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頁181-182。但是,當公共債權人階層變得人數眾多時,在政治上則正好相反,債權人會難以對付。[注]同上注,頁181。
二、 理 論
金融市場對政府的治理機理在于:既然進入金融市場直接融資,政府就要遵守金融市場的紀律和規律,否則將受到金融市場的懲罰,影響該國通過金融市場動員國民資金和儲蓄的能力,進而影響該國的制度競爭力。政府債券和金融市場是通向民主、增進民主和鞏固民主的重要渠道之一。
(一)約束
市場紀律是指債權人、所有者和客戶等利益相關者為維護自身的切身利益,隨時關注其利益所在的債務人的經營情況,在其認為必要時采取一定的措施,由此影響與債務人相關的利率和資產價格,從而通過金融市場對債務人的治理和運作產生約束作用。[注]田光偉:《金融監管中的市場約束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頁50。它有兩個層面的涵義:第一層是金融市場通過利率的變動,對政府的財務治理狀況作出反應;第二層是政府對金融市場發出的信號作出反應,從而調整政策。
第一,金融市場強調政府信息披露,進入金融市場的政府必須詳細披露相關的信息。這有利于陽光治理,避免政府“黑洞”。
金融市場不僅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更是政府治理狀況好壞的晴雨表。投資者和債務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使得任何金融市場的發展必須解決信息問題。信息披露是債務人融資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基礎,強制信息披露是金融市場的根基法則。任何債務人包括政府,必須詳細披露與債權人投資決策相關的各種信息,并擔保其真實、及時和全面。[注]Robert S. Amdursky, Clayton P. Gillette, Municipal Debt Financ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p. 316-330.而金融市場和投資者有能力對債務人(政府)披露的信息進行集成和加工,并反映在政府債券利率的變化上。這就是為什么在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中,當公債價格穩定,則預示著政權的穩定。[注](英)弗格森:《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一部):金錢的先知》,顧錦生譯,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頁270。
當政府的信息披露質量有問題的時候,債券市場的利率會有所反應。Kerstin Bernoth等對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的實證研究表明,政府采用一些創造性的財務手段愚弄市場的時候,金融市場能通過利率反映出來。[注]Kerstin Bernoth, Guntram B. Wolff, “Fool the Markets? Creative Accounting, Fiscal Transparency and Sovereign Risk Premia”,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5, No. 4, 2008, pp.465-467.當金融市場不確定政府的創造性財務手段的程度,那么,政府的風險會顯著增加。反之,政府財務透明度能降低風險溢價,使政府獲得更低成本的融資。[注]同上注, pp. 465-467。中國也有類似的例子。中國鐵道部一直以來遮遮掩掩的糟糕財務狀況,已成痼疾沉疴。如果按照發達和理想金融市場的公開披露要求,陽光披露可以倒逼鐵道部的財務改善與自我約束。“7·23”高鐵事故前后,鐵道部得不到社會的好感,不是在于它的巨額虧損和高負債,因為鐵道部擁有穩定的現金流,中國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普遍達到60-70%,超過擁有公共信用的鐵道部,問題的關鍵在于鐵道部財務不透明,造成公共監督渠道出了問題。外界難以判斷它的負債和虧損是切實地補貼了票價,還是鐵道部大量浪費、經營不善、權力尋租、利益騰挪?[注]徐小涵:《高鐵=“高價鐵路”?》,載高柏編:《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頁96。在這個意義上,如果鐵道部充分、及時和準確地披露信息,在理論上,它是可以獲得債權人的認可和好的融資價格的。
第二,金融市場的利率能靈敏地反映政府治理的狀況,而利率直接構成政府融資的成本。主權債券市場的基本規律是在政府財政收入一定的情況下,隨著政府債務量的增加,政府違約風險增大,市場會對增加的政府違約風險出價,要求政府負擔更高的利率(也叫違約風險溢價),政府將支付更大的融資成本,從而降低主權政府的借貸能力。[注]如果用數學坐標軸來表示的話,橫軸代表政府的債務量,縱軸代表該政府債券的利率,隨著政府債務量的增加,政府債券的利率先是緩慢上升,當增加到某個點時,利率陡然隨著債務量的增加而上升。Timothy D. Lane, “Market Discipline”, IMF Staff Papers, Vol. 40, No. 1, Mar., 1993, at 54.這構成了某種對政府融資的壓力,政府被迫對市場的利率信號有所反應,包括政府緊縮其財務狀況或優化其財政政策,以獲得市場的認可并降低政府融資的利率。在實證研究方面,Bayoumi等利用美國政府債券市場的數據,驗證了政府債券非線性供給曲線的金融規律。[注]Tamim Bayoumi, Morris Goldstein, Geoffrey Woglom, “Do Credit Markets Discipline Sovereign Borrowers? Evidence from U.S. Stat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27, No. 4, (Nov., 1995), pp. 1046-1059. 后續關于政府債券市場對政府的市場紀律作用的支持性實證研究還有很多,比如Erik R. Fasten, “Market Mechanisms to Restrict Irresponsible Politicians, Lessons from Switzerland”, EPCS 2006; Bernardin Akitoby and Thomas Stratmann, “The Value of Institutions for Financial Markets: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of World Economy, Vol. 146, 2010, pp. 781-797; Friedrich Heinemann and Viktor Winschel, “Public Deficits and Borrowing Costs: The Missing Half of Market Discipline”,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31083; Kristin Stowe and M. T. Maloney, “The Response of the Debt Market to Municipal Financial Distress”, http://myweb.clemson.edu/~maloney/papers/muni-financial-distress.pdf; Mark D. Robbins and Bill Simonsen, “Do Debts Levels Influence State Borrowing Cos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72, Issue 4, 2012, pp. 498-505; Levent Bulut, “Market Disciplining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overeign Government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465-7287.2011.00253.x/full; Fabrizio Balassone, et al., “Market-Induced Fiscal Discipline: Is There A Fall-Back Solution for Rule Failure?”, http://www.bancaditalia.it/studiricerche/convegni/atti/publ_debt/session2/389-426_balassone_franco_and_giordano.pdf.Kiewiet等更是認為,債券市場的紀律才是政府的真正限制,而不是美國州的財政憲法。[注]D. Roderick Kiewiet and Kristin Szakaly,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 on Borrowing: An Analysis of State Bonded Indebtedness”,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12, No.1, pp. 62-97.
第三,債權人退出或“用腳投票”也是金融市場約束發揮作用的一種重要形式。除了利率之外,市場紀律還強調資本的自由流動,對于有不誠信記錄的政府或不透明的政府,債權人通過不購買政府的債券,使其難以再次進入金融市場融資。[注]Ugo Panizza, et al., “The Economics and Law of Sovereign Debt and Defaul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7, No. 3, 2009, pp. 651-698; Clayton P. Gillette, “Political Will and Fiscal Federalism in Municipal Bankruptcy”, NYU law school, Law &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No. 11-13, March 2011, at 11, footnote 26 (認為拒絕還債的地方政府將難以再進入資本市場融資)。
(二)監督
在公司金融法中,盡管制度設計對債權人沒有特別的保護,董事高管只對公司的股東承擔信義義務,不對債權人承擔信義義務,[注]赫蒂格、神田秀樹:“債權人保護”,載《公司法剖析:比較與功能的視角》,劉俊海、徐海燕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91。然而在實踐中,股東對公司是軟約束,債權人對公司才是硬約束。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由于得不到公司法的特別保護,因此債權人通過合同保護自身,對公司管理層的監督和治理享有特別的權利,例如指定公司償付本金和利息,要求公司滿足最低的財務標準,定期向債權人報告,在債權人約定的范圍內運作等。債權人對公司管理層的監督和治理作用,甚至超過公司股東的作用。[注]Frederick Tung, “Leverage in the Board Room: The Unsung Influence of Private Lende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UCLA Law Review, Vol. 57, Issue 1, 2009, pp. 115-181; Charles K. Whitehead, “The Evolution of Debt: Covenants, The Credit Marke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Vol. 34, No. 3, 2009, pp. 101-137; Douglas G. Baird and Robert K. Rasmussen, “Private Debt and the Missing Lever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54, 2006, pp. 1209-1251; Charles K. Whitehead, “Creditors and Debt Governance”, Cornell Law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 011-04; George G. Triantis, Ronald J. Daniels, “The Role of Debt in Interac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83, 1995, pp. 1073-1113.
在債券融資中,政府和債權人之間是直接的合同關系,債券合同定義了債權人的基本權利。債權人享有的合同權利構成了債權人監督政府和獲取政府信息的私法依據。債權人私權的構建是直接針對政府的,因此具有政治功能的潛力。債權人根據私權合同對政府行使的知情權和監督權,起到了民眾的利益代言者的角色,而代議民主制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保證政府的政策和決策能夠反映民眾的利益或偏好,[注]Mathew D. McCubbins, Roger G. Noll, and Barry R. Weingas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s Instruments of Political Control”,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3, No. 2, 1987(fall), p. 243.因此,債權人私權的行使促進了民主價值的生長。一方面,當債權人和民眾在歷史上或其它國家高度重合的情境中(如圣·喬治銀行的情況),債權人對政府的監督和行使權利相當于維護民眾利益,[注]Clayton P. Gillette,見前注〔25〕, p. 969.增進民主;但是,另一方面,當民眾群體和債權人群體的重合度不高的情境中,債權人的私權行使又如何與民眾利益一致呢?
私人債權人和民眾利益之間既有沖突,更有一致性,二者構成利益重疊的關系,這種利益重疊的關系使得民眾與私人債權人之間能建立一種非自覺的合作關系,維護他們指向威權政府的共同利益。債權人監督政府財務治理狀況的動機是自私的,是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債權利益,在出發點上不是為了民眾的利益而行事。因此,它們并不是代理人(債權人)和被代理(民眾)的關系,不構成直接的代議民主特征。但是,二者的利益重疊關系使得債權人出于自私目的的監督,卻客觀上維護和代言了民眾的利益。所謂利益重疊關系——不同于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間的另外一種合作關系——是指雙方盡管出發點不同,但基于共同的利益目標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二者實際利益存在重合或交叉而形成的合同模式。[注]John Duggan, “Contracting Theory with Coincidence of Interest”, at http://www.hss.caltech.edu/SSPapers/sswp805.pdf.在這種不自覺的合作模式中,行動者(債權人)為了自身利益的行事客觀上維護了重疊利益,有利于民眾利益的代言和維護。債權人和民眾的關系為利益重疊模式,具體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債權人和民眾都關心政府的治理狀況,二者在政府財務治理方面的利益是重疊的。債權人希望政府治理良好,既要防止政府違約或拖延,也為了手中持有的政府債券保值增值,因為政府治理好,政府債券在基本價值層面才有升值的空間。[注]政府的公信力、行政效率、監管的質量、法治和對腐敗的控制等因素對于債券市場的資本流動和該國的國家債券的評級有很大的影響。Suk-Joong Kim and Eliza Wu, “Sovereign Credit Ratings,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Markets”,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Vol. 9, Issue 1, 2008, pp. 17-39.這一點也切合民眾對政府的要求和利益。債權人為了自身利益對政府的監督,其范圍是非常寬的,確保了債權人對政府財務治理的全面監督。表面上,債權人只需要監督政府還本付息即可,但事實上,債權人并不僅僅盯著政府財務報告上那些空洞的數字;作為精明的投資者,債權人擅長從政府行為和表象的蛛絲馬跡中探察到政府財政狀況的好壞和自己投資前景的明暗。影響政府財務狀況的因素是很多的,有直接的因素,比如政府的財政政策、財政管理、政府開支、財政透明度和對貪污腐敗的治理等;還有間接的因素,比如官員的調動、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會影響政府稅收和財政收入)等。這些情報都會被金融市場和債權人敏銳地捕捉到并反映到債券的風險評級和債券收益率等市場數據中,進而影響整體債權人的資金流動和投資決定。[注]例如克林頓的競選顧問卡維爾曾經說過,如果人真的可以投胎轉世,那么他來生既不想當總統領導國家,也不想當教皇領導宗教,而是想成為債券市場的操縱者,因為誰控制了債券市場,誰就統治了全世界。克林頓當選總統的形勢趨于明朗時,美國債券市場把長期債券收益率推高了35個基點。因為克林頓在醫保和同性戀士兵方面的早期政策無法消除政府債券持有人的憂慮,債權人擔心這些政策如果實行可能會大規模增大政府的開支,影響政府的償還能力。弗格森,見前注〔54〕,頁255-256。總之,債權人的監督活動極大地促進了政府的透明度和治理狀況,包括政府的公信力、誠信度、辦事效率、法治程度以及對于腐敗的控制等,這客觀上符合一般民眾的期許和利益。
第二,債權人和民眾都希望控制政府的財政支出。當然,如同公司的債權人和股東存在利益沖突,[注]Richard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8th ed., Aspen, 2011, pp. 539-544.對于國家而言,雖然政府的債權人和民眾的利益存在很大的利益重疊部分,但二者發生沖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政府收入和資產一定的前提下,債權人和民眾之間如何分配政府的財產,是一個矛盾。民眾希望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多支出,甚至可以為了公共福利廢黜債務;而債權人希望政府的收入優先用于償還債務,償還債務之后的剩余資金再用于對民眾的公共服務支出。必須承認,利益沖突是難以調和的。在西方民主國家,那些生活主要依靠社會福利的民眾會傾向于加大政府的社會福利的支出,民眾還會把這種財政傾向反映到他們手中的選票。[注]P. Coughlin and S. Nitzan, “Electoral Outcomes with Probabilistic Voting and Nash Social Welfare Maxim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5, 1981, pp. 113-122.為了迎合民眾的需求,政客們在每次大選前都會許諾擴大福利開支,而這帶來的后果是財政赤字的增大,形成“選舉財政周期”。[注]Robert Franzese, Jr., “Electoral and Partisan Manipulation of Public Debt in Developed Democracies”, in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Fiscal Policy, Rolf Strauch and Jurgen von Hagen, ed., Kluwer Academic Pulishers, 2000, pp. 61-76.政府廢黜債務,迎合民眾和公共福利,更符合民主的精神。[注]施拉格爾,見前注〔53〕,頁162。
然而,政府的債權人和民眾在社會福利支出方面的沖突不是根本性的,這種沖突的深層次是民眾和公債債券持有人利益的契合點:厭惡通貨膨脹,防止財政過度支出而帶來的財政性的通貨膨脹。如前面所述,債權人厭惡政府財政支出過度或財政管理不當,導致政府陷入資不抵債的境地,而民眾同樣厭惡政府過度的財政支出,因為這會帶來通貨膨脹。[注]Michael Woodford,“Control of the Public Debt: A Requirement for Prices Stability? ”, at http://faculty.wcas.northwestern.edu/~lchrist/papers/w5684.pdf.當政府財政赤字擴大到一定程度時,這種赤字將通過政府向中央銀行的透支來彌補,貨幣數量超過經濟所需將導致通貨膨脹,民眾將是受害者。
對于地方政府的過度支出而言,民眾同樣不愿意其陷入因財政支出過度或管理不當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地方政府不具有貨幣發行權,不能通過印刷貨幣來彌補赤字。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三種解決辦法都會傷害民眾的實際利益。一是中央政府介入和救助,通過中央的財政撥款來解決地方的債務危機。問題是,這是舉國承擔某個地方政府的過度揮霍帶來的外部性。二是地方政府增稅或開征新稅,這會增加民眾的負擔。三是地方政府通過法院的債務重組來緩解債務。債務重組的方案一般是雙方各退一步,達成和解,政府提出削減開支甚至是裁員和增加稅收的計劃以增加償還能力,而債權人則可能適當減少債務或債務延期。債務重組方案中的增稅、削減福利開支、降低養老金等“開源節流”的辦法會損害民眾的利益。[注]例如,根據美國的市政破產法,法官可以酌情減少甚至免除市政支付養老金的債務。Steven Greenhut, “Vallejo’s Painful Lessons in Municipal Bankruptcy”, WALL ST. J., Mar. 27, 2010, at A13 (破產“可能是抽屜中降低養老金義務的最有效的工具”).其次,市政破產可能會給市政轄區內的經濟造成沖擊,增加失業率。
相比民眾的監督,債權人通過金融市場監督和管治政府對于民主的改善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優勢。第一,相比一般的民眾,債權人能夠作出更好的財務決策。債權人群體可以進一步分為投機者和長期投資者。盡管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者是一群只盯著市場變動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從價格漲跌中獲利,不太關心政府作為債務人的信息和財務治理,但投機者也是金融市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于活躍市場交易的氣氛和流動性具有重要的意義。政府債務往往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是長期的,例如我國的中期票據是3至5年,發改委審批的企業債是10至15年,政府的債權人大多數是長期投資者,關注債務人的基本面,而且必須關注政府未來的長期支付的風險,考慮10年以上的問題,平衡政府的財政決策對當前一代和下一代施加的收益和負擔,兼顧民眾之間的代際公平問題,[注]Clayton P. Gillette,見前注〔25〕, p. 971.更好地增進民主,而不會如同民眾只關心下一屆選舉官員等短視的行為。[注]Clayton Gillette,見前注〔25〕, p. 971。第二,在債權人的風險偏好方面,債權人追求的是固定的預先約定的回報,不喜歡政府從事風險大的項目,時刻防止政府將資金挪用到風險大的項目。因此,債權人適合履行風險監督的職能,并在政府的長期運營方面具有更為保守和理性的策略。[注]Clayton Gillette,見前注〔25〕, p. 972。第三,民眾的監督存在集體行動困境和理性冷漠,而債權人群體更容易克服集體行動困境。相比民眾的人數來說,債權人的人數相對少一些,人數多少和搭便車之間多少有些關系。[注]Clayton Gillette,見前注〔25〕, p. 966。雖然債券持有人可能很多,但是,債券交易中會委托他人。受托人往往是市場中介組織,如債券的承銷商,其存在部分解決了集體行動問題,[注]Clayton Gillette,見前注〔25〕, p.967。他們的工作就是密切關注作為債務人的政府的財務指標、政策和財務狀況。實踐中,債權人和受托人往往通過設置一些方便觀測的警戒線指標作為觀測政府財務狀況的指數。[注]Clayton Gillette,見前注〔25〕, p. 967。
此外,在監督渠道方面,民眾對政府的監督依賴媒體、投訴,其監督效果取決于政治渠道的完善程度;而債權人對政府的監督是通過金融市場,法律依據是私法和債券合同。在監督方式方面,民眾促進政治改革往往是暴力,如暴力抗稅;[注]弗格森,見前注〔54〕,第2章“令人痛恨的稅收”。而債權人是依據私權和私法法院,和平地促進政治轉型。在請求權基礎方面,民眾的監督往往是依據財稅法,屬于公法的請求權;而債權人的監督是依據債券合同,屬于私法的請求權。
(三)公共參與
債權人對政府事項還具有公共參與和決策的能力。筆者還是從與公司的潛在類比開始。當公司財務指標出現問題,或者某一期分期付款沒能償還,特別是資不抵債的時候,債權人潛伏的權利就會大增,介入公司的內部事項,[注]Stuart C. Gilson and Michael Vetsuypens, “Creditor Control in Financially Distressed Firms: Empirical Evidenc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 Vol. 72, 1994, pp. 1005-1026.包括替換公司管理層、任命新的管理人員、申請公司破產。總之,在一定條件出現時,債權人會介入、參與和決策公司的內部事務。在政府債的情境中,當債務人資不抵債時,債權人對政府的權利會大增。根據美國的市政債務融資法律,當政府債務人違約或出現違約跡象的時候,債權人可以向法院申請接管(receivership)負責該債券的準公共公司。
債權人通過組織有序的債權人會議,對政府涉及債權人利益的重大事項有權進行表決,未達到法定表決通過數,地方政府不得擅自主張,以維護債權人對政府的利益。中國的政府債市場也建立了債權人會議的制度,但是地方政府轉移融資平臺的優質資產而未經債權人會議同意的債市丑聞依然出現了。地方政府惡意侵犯債權人利益的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10廣州建投債”(廣州市政府劃轉優質資產)、“10華靖債”、“08云投債”、“10云投債”均是發改委主管下的企業債丑聞,“10川高速MTN1和MTN2”則是交易商主管下的債券丑聞。因此,發改委在2011年7月21日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企業債券存續期監管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
二、規范企業資產重組程序。在債券存續期內進行資產重組,事關企業盈利前景和償債能力,屬于對債券持有人權益具有影響的重大事項,政府部門或主要股東在做出重組決策前應充分考慮債券募集說明書規定的相關義務,并履行必要的程序。一是重組方案必須經企業債券持有人會議同意。二是應就重組對企業償債能力的影響進行專項評級,評級結果應不低于原來評級。三是應及時進行信息披露。四是重組方案應報送國家發展改革委備案。三、完善信息披露。……在企業債券存續期內,發行人經營方針和經營范圍發生重大變化,生產經營外部條件發生重大變化,未能清償到期債務,凈資產損失超過10%以上,作出減資、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請破產決定,涉及重大訴訟、仲裁事項或受到重大行政處罰,申請發行新的債券等重大事項,均應及時披露相關信息。如發行人擬變更債券募集說明書約定條款,擬變更債券受托管理人,擔保人或擔保物發生重大變化,作出減資、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請破產決定等對債券持有人權益有重大影響的事項,應當召開債券持有人會議并取得債券持有人法定多數同意方可生效,并及時公告。
(四)信用評級機構對政府財政治理狀況的專業評估與監督
政府債的私人投資者可能懶惰或欠缺專業能力,以致不能有效地監督政府或參與政府的內部事項,但是,債券市場中的信用評級機構等金融中介,在聲譽機制的驅使下,履行市場看門人和監督債務人的角色。它的優勢是不僅擁有獨家信息,通過評級向市場提供信息,而且通過專業的分析,為投資者創造價值,行使私人監管的功能;[注](美)科菲:《看門人機制:市場中介與公司治理》,黃輝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頁2-5。通過資信評級的上調或下調,還對政府債務人實施激勵或懲罰;私人債權人的記憶可能是短暫的,而信用評級機構是市場的記憶者;最重要的是,信用評級機構對政府債的評級,具有治理的功能,因為評級的過程是在行使有約束力的紀律,影響政策的選擇和政府的問責性。[注]Timothy J. Sinclair, The New Masters of Capital, American Bond Rating Agencies and the Politics of Creditworthines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13.
三、 中 國
中國政府債券市場的基本特征是幾乎沒有私人債權人。
(一)國家控制
部門政治和分割的權威[注]“分割的權威”來自海外中國學對我國政法秩序的觀察,能解釋當代中國的很多現象。參見Andrew Mertha,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 Political Plu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0, December 2009, pp. 995-1012; (美)李侃如:《治理中國》,胡國成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188-190。塑造了中國金融市場的碎片化格局。根據主管政府部門的不同,中國債券市場及融資工具分為如下幾類:
第一,財政部以及由財政部審批的國債與地方政府債。中央和地方政府以自己的名義發行政府債券,這也是狹義的政府債券市場。2009年3月,財政部首次代理地方政府發行地方債;2011年10月,上海、浙江、廣東、深圳試點“自行發債”,額度分別為71億、67億、69億和22億元。
第二,國家發改委審批的企業債。我國的企業債雖然名義上叫企業債,但實質上是西方的市政債和地方政府債券。[注]王國剛:“論‘公司債券’與‘企業債券’的分立”,《中國工業經濟》2007年第2期。發債主體是各級地方政府設立的城投公司。
第三,中國人民銀行主管的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簡稱“交易商協會”)。它是銀行間債券市場的自律組織,除了管理銀行間債券市場,還管理同業拆借市場、外匯市場、票據市場和黃金市場等其它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為各級政府的融資平臺、鐵道部和中央企業等提供的融資工具有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定向工具”,PPN)、中期票據(MTN)、短期融資券(CP)、超短期融資券(SCP)、中小企業集合票據(SMECN)等。各種融資工具的差別主要在于債務期限不同。
第四,中國證監會主管的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兩大證券交易所可以向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提供公司債券的融資工具。
在碎片化的市場格局中,中國政府債券市場的基本性質是作為相對一個封閉的國家融資體制而存在,國家對資本的供給(債權人)和融資進入門檻(債務人)均進行控制。在這個金融市場,一般只有政府(含政府的融資平臺殼公司、中央企業)是債務人,債權人則是國有機構,資金的循環控制在國家體制內循環,幾乎沒有私人債權人的參與,市民社會的力量在政府債券市場中不存在。
1. 國家對資本需求方的控制
債務人是資本的需求方,能進入中國政府債券市場舉債的基本上是政府、政府的融資平臺、鐵道部、中央企業等。
第一,有資格發行國債和地方政府債的是中央政府、由財政部代理的地方政府以及經過國務院批準試點的地方政府。
第二,發改委主管的企業債服務于中央企業、鐵道部、各級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大型國企等。它的特征是融資主體必須提前向發改委報批投資項目,企業債服務于經發改委審批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盡管在發改委申請企業債的排隊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但是企業債的債務期限可以長達10至15年,這是交易商協會提供的融資工具不具備的優勢。因此,企業債成為政府和國有機構青睞的融資工具。中國金融法的特色之一是成文的法律很粗疏,真正在實踐發揮作用的是不成文法,通過觀察執法部門的行為或搜集紅頭文件來探知一二。發改委對企業債的發行主體實行“211”名額制——是中國不成文的金融法之一,它是指每個省會城市可以有兩家融資平臺申請發債,國家級開發區、保稅區和地級市允許一家平臺發債,縣級主體必須是百強縣才能有一家平臺發債;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四個直轄市申報城投項目沒有限制,但直轄市所屬的區僅可同時申報一家。[注]張宇哲等:“債市新政”,載財信《新世紀》2012年第30期。
第三,中國人民銀行主管的交易商協會主要服務于中央企業、鐵道部、各級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等。國家對該市場的融資進入門檻同樣控制。比如,交易商協會有一份企業的名單,在名單之上的企業,哪些城投公司能發中票,則根據銀監會的名單;后來交易商協會擴展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房、全民所有制企業。[注]同上注,頁42。這是隱形的金融配額制。因此,雖然法規上沒有設置所有制的門檻,但是,2011年共有257家民營企業共發行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1754億元,占全部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總發行規模的比例僅為7.4%。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是中國問題專家,他曾經問道:“收入這么低的國家的政府從哪里得到錢來支持如此浩大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注]黃亞生:“中國的另一條道路”,王哲編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4期。除了中國農村向城市輸入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國家通過商業銀行將資金從農村抽移到城市,還有一個封閉的債券市場作為國家融資體制在隱蔽的運作。以鐵道部為例,它需要資金,可以有哪些融資渠道?這些渠道包括:財政撥款、鐵路票價收入、銀行直接貸款、鐵道部通過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鐵龍物流、廣深鐵路和大秦鐵路)在證監會主管的股票市場融資,以及以鐵道部自己的名義發行債券,如向發改委申請發行企業債,因鐵道部是政企合一,它能以部委的名義向發改委申請發行鐵路建設債券,還可以向交易商協會申請發行金融工具,除了中小企業集合票據(SMECN),交易商協會主管的其它四種金融工具(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券),鐵道部都可以使用。
地方政府的融資來源有稅收、財政轉移支付、養老金、地方政府的企業通過證監會在股票市場首次公開發行并上市、銀行貸款、地方政府的金融創新——融資平臺。《預算法》第28條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因此,地方政府的直接發債,需要經過國務院同意,由財政部代理。但是,實踐中地方政府進行金融創新,設立融資平臺公司,它的名稱叫公司,但在市場看來它的實質是地方政府的殼。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向商業銀行舉債或在債券市場發債,用于本地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房和城市化運動。政府融資平臺被國外稱為中國最新鮮的創造。據國家審計署2010年的調查,政府融資平臺至少有6576個。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中,融資平臺公司、政府部門和機構舉借的分別為49710.68億元和24975.59億元,占政府性債務中的比例為69.69%。[注]國家審計署:《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國家審計署審計結果公告2011年第35號。
政府使用金融市場,導致中國債券市場非常龐大,因為政府的融資需求遠遠大于私人公司,它的融資規模大約是民眾熟悉的股票市場的十幾倍。
2. 國家對資本供給方的控制
國債、地方政府債、企業債、交易商協會提供的各種金融工具,均使用同一套發行系統:銀行間債券市場。表三顯示,能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投資者包括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信用社、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信托公司、投資基金、財務公司、信用評級公司、大中型工商企業等各類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
其中,商業銀行等國有機構投資者主導中國政府債券市場。由于具有吸收公眾存款的資金優勢,商業銀行具有天然的資金優勢,資金實力最雄厚的是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包括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各個地方的城市商業銀行等。到了2009年,71%由商業銀行持有,9%由保險公司持有,4%由基金持有,合作社持有3%,交易所持有2%,特別結算會員持有10%,其中,1%是零售給公眾投資者。總之,92%的債券由國有機構持有。[注]Carl E. Walter, Fraser J. T. Howie, 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 Singapore: John Wiley & Sons (Asia) Pre. Ltd., 2011, p. 103.

表三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者數量變化 單位:家
注:各數據為各年末值。資料來源: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

表四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主要機構投資者持券比例,2009年12月 單位:%
資料來源: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
比較法的功能之一是讓我們透過對方更看清楚自身的面貌。美國的市政債券持有人結構與中國政府債券的持有人結構正好相反。它是個人投資者主導的政府債券市場,居民(包括基金)持有美國國內公債的比例將近70%(69.2%)。美國國內的市政債券持有人主要是三類:第一類是居民,包括個人直接持有或通過投資咨詢機構持有;第二類是居民的代理人,即各類基金,如債券基金例如開放式互助基金、閉鎖式基金、貨幣市場基金;第三類才是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財產與災難保險公司。[注]Neil O’Hara, The Fundamentals of Municipal Bonds, sixth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2012, pp.17-18.民眾可以直接購買政府債券。[注]Robert Zipf, How Municipal Bonds Work, New York Institute of Finance, 1995, p. 139, 170.

表五 美國國內公債的持有人結構(1955-2010)
資料來源:美聯儲,轉引自Neil O’Hara,TheFundamentalsofMunicipalBonds, sixth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2012, p. 164.
(二)市場失靈
作為約束、監督和公共參與的民主機制,金融市場對政府發揮作用需具備一些前提條件,否則會產生市場失靈。一般認為,市場紀律發揮作用的條件有:資本自由流動;利率自由變動;政府債務人的信息充分披露;市場認為不存在外部的擔保和預期政府不會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以償債,即中央銀行是獨立的。[注]Timothy D. Lane, “Market Discipline”, IMF Staff Papers, Vol. 40, No. 1, Mar., 1993; Teresa Ter-Minassian, “Fiscal Rules for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Can They Promote Fiscal Discipline?” OECD Journal on Budgeting, Vol. 6, No. 3, 2006, p. 114.在私人債權人的監督和參與方面,一是取決于資本方和債務人之間的談判力量對比,二是司法體系能否有效地執行和保障政府與私人債權人之間的融資合同。信用評級機構的看門人功能則取決于評級機構的獨立性和專業性。
從債權人監督、參與和約束政府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政府債券市場基本失靈,因為它的債券持有人結構存在根本的缺陷。國有金融機構作為政府債券的絕對持有者,沒有激勵去限制政府。國有金融機構的大股東是政府;國有金融機構的領導的升遷不完全是在金融系統內部升遷,而是很可能根據組織安排,升遷到政府系統工作。
具體來看,第一,在利率方面,我國是一個利率管制的經濟體,比如,企業債的利率不能超過同期銀行存款利息的40%。[注]《企業債券管理條例》(1993年國務院令第121號)第18條:“企業債券的利率不得高于銀行相同期限居民儲蓄定期存款利率的百分之四十。”目前國家規定居民在商業銀行的一年定期的儲蓄利率大約是3%,不能超過40%則意味著企業債的利率不會超過4.2%,而其實商業銀行向一般的公司貸款的利率已經是7%了;而且,國有金融機構對利率不敏感,使得利率這個重要的市場風向標不能很好地對政府的治理情況和風險進行定價。第二,在債權人的投資自由度方面,政府債的承銷和購買,尤其是國債,是商業銀行的政治任務,而企業債服務于在國家發改委立項的國家項目,必須確保企業債的發行成功,在這個意義上,國有金融機構不能不購買政府債券。第三,在信息披露方面,交易商協會的監管仍然比較軟弱。第四,債權人普遍預期對于有違約跡象的市政公司或鐵道部債券,相關的政府部門會出手救助,而政府在最終時刻的屢次救助行為也強化了債權人的預期。[注]鄭菲等:“山東海龍短融:坐等兜底”,載財信《新世紀》2012年第8期(“‘海龍短融發行的時候,大家都看到了它的業績情況,但很多投資者認為,山東海龍是國有企業,無論如何,政府不會讓國有企業出現實質違約’,某資深債券交易員表示。”“伴隨著情況的不斷惡化,更多的機構相信地方政府最終還是會出面解決。‘以前市場上出了事都會“包住”,而且規模越大,風險越高越能夠獲得更高層級政府的支持’,一位交易員表示。”)國有金融機構作為債市的投資者也不太在意公共債務人的財務治理情況。第五,由于國有金融機構主導的債權人結構,債權人會議由大的商業銀行控制,一些基金無法發揮對政府等債務人的影響。第六,信用評級機構的市場功能缺失。國際三大評級機構的影響力、獨立性和聲譽是在一百多年的市場競爭與檢驗中形成的,而中國目前五家全國性的信用評級機構[注]中誠信、聯合資信、上海遠東、上海新世紀、大公國際。基本上是半官方機構。
(三)國家控制的形成
中國債券市場的持有人結構經歷了劇烈的嬗變。1988年,62%的公共債券由個人投資者直接持有,另外38%的債券由機構持有。[注]Carl E. Walter and Fraser J. T. Howie, 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 Singapore: John Wiley & Sons (Asia) Pre. Ltd., 2011, p. 103.1998年,國務院下令所有的銀行撤出上海、深圳的證券交易所,銀行等大的金融機構之間建立起一個封閉的債券市場,服務于國家體制內的資金循環。究其根源在于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和動力來源。建立封閉的國家融資體制的原因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開始形成并不斷強化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時期,依靠政府主導的“鐵公基”等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已經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慣性了。與之相配套的金融體系則是國家控制的債券市場。前總理朱镕基先生在2001年說:
老百姓看到這種形勢,不敢消費,把錢都存到銀行里,銀行一年的存款增加8000億元到1萬億元。如果這個錢我們不用的話,銀行也得給老百姓付利息。要用的話,用到哪里去呢?再搞加工工業是不行的,那都是生產能力過剩,供過于求了。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這個錢用國家財政的名義從銀行借出來,付給利息,然后國家拿這個錢搞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建設一搞,需要的鋼材、水泥、玻璃、建筑材料、機械設備,馬上都有市場,一下子把整個生產都搞活了。同時,這些項目都是我們多年來想辦而沒錢來辦的事情。這個情況跟1993年是不一樣的。1993年不是靠存款,而是靠發票子來搞建設、搞房地產,又沒有物資,鋼材從每噸1000元漲到4000元,物價飛漲。這三年干了這么多事情,整個的經濟搞活了。[注]朱镕基:《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湖南省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01年3月6日)卷四,載《朱镕基講話實錄》卷四,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頁121。
三年發了3600億元的國債,一年平均1000億元多一點,干了多少事情呀!3000多億元的國債,帶動了1萬多億元的銀行貸款,加上其他的資金,干了1.5萬億元的工程。出現的結果是經濟搞活了。鐵路的新建、改建、電氣化,差不多1萬公里。……現在國債的余額,到去年年底是1.2萬億元,按國際慣例的水平來看并不高;而且從去年的財政收入來看,回收得很快,國債一投進去,工程一干,它馬上帶動原材料工業、加工工業發展起來,它的稅收就交給了國家,還你這個錢還有剩余。去年我們增加了1950億元的財政收入,我們預算增收只有1200億元,超收了700多億元,超收的錢我們一個也沒有亂花。……拿200億元減少了赤字,這就等于去年的國債又少發了200億元;拿300億元放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注]同上注,頁123-124。
在資本的需求面,國家對債務人的市場準入實施控制,防止私人項目和國有項目在債券市場競爭有限的金融資源。從經濟效率上講,私人項目更能盈利和富有活力,因為國有項目往往受到嚴格的管制,承擔公共功能。如果放開競爭的話,則逐利的資本更青睞于資本回報率高的私人項目。
在資本的供給面,國家對資本的市場準入實施控制,防止民間資本進入債券市場,炒高政府融資的利率,增加國家融資的成本。馬克思經典著作中洞察到的私人資本的逐利性被國人反復引用。朱镕基先生在1998年曾強調:
我到現在也認為,他還是錯的,他那種發國債的辦法是不行的,去年不是已經證明按我的辦法做是正確的嗎?不能搞市場招標,把利息抬得那么高,國家怎么負擔呀?……你搞國債市場招標,只能把高利息給那些投機倒把的人。[注]朱镕基:《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98年3月24日),載《朱镕基講話實錄》卷三,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頁5。
四、 結 語
公債的存在是民主的催化劑。政府在金融市場大量融資引發的債務危機及通脹風險是2008年以來突出的全球現象,中國也不例外。政府債給金融法學者帶來了一系列的研究課題,本文不拘泥于債券市場的法律教條研究路數,而是選取公債的民主機制進行研究,試圖論證金融市場是國家民主的一個可能的入口:政府進入金融市場融資,將受制于金融市場的紀律和規律,對投資者負責;投資者可以對政府債券“用腳投票”或通過利率的變化影響政府;債權人依據融資合同和私法權利對政府的監督,具有風險偏好的優勢和長期的戰略眼光;在一定條件下,債權人有私法上參與政府決策的權利;政府事關債權人重大利益的決策需要經過債權人會議的同意;此外,信用評級機構能發揮市場守門人的角色。
展望中國債券市場的政治功能,前景是不樂觀的,但是金融市場的政治功能是客觀存在和潛伏的,等待人們的挖掘。本文的研究對歐美等發達民主國家意義不大,因為當民眾有完善的政治代議渠道去表達意見和偏好時,金融市場的政治功能將逐漸退化,而變遷為高度金融技術化的金融家的投機名利場。但對于中國等新興轉軌國家,金融市場的政治維度才剛剛開發出來。
這是一個變化的世界。不樂觀的前景并不意味著一成不變。國家控制的債券市場的運作是有成本和風險的:扭曲市場。商業銀行的競爭優勢在于債券市場之外的商業貸款,通過一對一的客戶談判,調查客戶的信息,對風險給出恰當的定價,而不是債券市場的投資。而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持有大約70%的債券,這使得國民經濟中的金融風險并沒有透過金融市場很好地分散開來,金融風險仍集中在商業銀行,而商業銀行的資金終端來自于民眾,這勾勒出我國國家融資體制的擊鼓傳花游戲。一旦碰到經濟下滑周期,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到一定程度,公共債務人只能對債券違約,導致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增多,威脅到普通民眾的儲蓄安全,進而造成時局動蕩或通貨膨脹。
我們不應像19世紀中葉基礎設施跨越式發展時期的自由資本主義美國那樣,等到債券市場危機爆發再被動地采取變革措施,我們應未雨綢繆。銀行間債券市場應向民間資本與外國資本開放,改變國有機構壟斷的債券市場投資者結構,吸收與聚集市民社會的資本力量,形成“國家-市民社會”的格局。民間資本無疑會對政府融資的利率與風險更為敏感。建立私人資本主導的債券評級機構,它們從聲譽出發,應能更客觀地評估政府債券的風險。完善債權人監督政府的金融法渠道。基礎設施的跨越式發展基本完成之后,經濟發展將隨之由政府投資轉到內需與出口,國家不需要為了拿到便宜的資金而扭曲債券市場的利率,利率市場化的條件將成熟。截至2010年底,我國中央政府(含鐵道部)之下有31個省級政府、283個地級市、2856個縣級市、33981個鄉鎮,[注]《中國統計年鑒》2011年版。還有大約100家中央企業。讓我們發揮一下想象力吧:如果幾萬個公共債務人都有公共債券在市場競爭發行和交易,由民眾或民眾的資金集合基金去競爭認購和出售,每一級政府在債券市場充分地披露信息,由市場給定利率,當市場的信號和政府行動的互動得到最大的發揮,既有利于金融風險的分散化,也有利于政府的問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