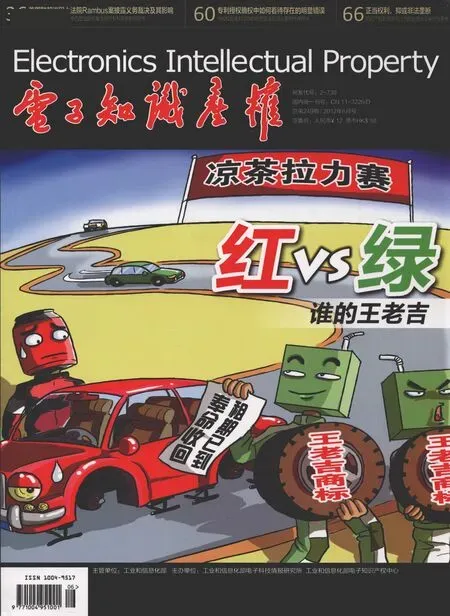由人觀己:從印度的科技創新看中國
文 / 盧寶鋒
最近Facebook成功上市,印度人Sanjay Anandaram寫了一篇文章,感嘆“何時印度能創造出一個Facebook這樣全球化的產品”。文中Sanjay除了指出印度和美國在研發之間的差距,也以中國為參考,反思了印度在研發投入上的不足。中國與印度同處于亞洲大陸,又同為經濟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難怪印度國家科學院院長馬舍爾卡無奈且認真地說:“相鄰的地理位置無可奈何地賦予了中印兩國時時刻刻被比較的命運。”
2005年,印度的科技研發投資占GDP比重為0.9%,到2020年預計也不過2%,相比而言,同期中國的科技研發投資占GDP比重將由1.34%增加到3%。當百分比換算成絕對值時,差距將更加明顯,印度2011年科技研發上的花費是165億美元,而中國則達到了1740億美元。截止2010年,印度在全球最大的科技文獻出版平臺“Elsevier”上出版的論文為233,027篇,而中國的數字則達到了印度的三倍。2011年印度專利申請量增長了11.2%,中國的增長幅度為33.4%。專利的年絕對申請數量,中國也是印度的5倍以上。另外,經濟學人創新指數排名,中國也領先于印度,預計2013年中國的排名將是第46位,而印度是54位。以上差距有著經濟、政治以及文化上的多方面原因。
一些在中國工作的印度外交官非常羨慕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效率。也許一些人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造成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有人認為,究其根本,中國與印度的差距并不在于1979年以后的改革開放,而是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所進行的土地改革。中國的土地國有為中央政府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提供了基礎性的經濟和制度保證。相比而言,印度的土地依然為類似封建社會的地主所有,政府所倡導的民主與這種最根本的經濟基礎出現了錯位,政府許多重大決策也受到了這種民主的拖累。美國前駐印度大使莫尼漢把印度的民主稱為“功能性無政府狀態”。科技研發是一項針對將來的長期投資,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可以有效地彌補人們過度關注短期利益回報的缺陷。
從具體措施上來看,印度政府更多地是以企業為主導進行研發投入,研發的初衷來源于市場,而中國很多情況下是以政府為主導,由政府給予企業實質的研發支持,研發的目的雖然也與市場需求相關,但很多時候是單純為解決某個技術難題。印度的學術研究機構,相比而言接受了更多來自于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的研究資助。而在中國,政府對于研究機構的投入占據了主導地位。與政府相比,企業雖然對市場的微觀把握更加敏銳,但其實力有限,相對而言更注重短期回報。對于一些長期的、基礎性的、可使整個行業受益的科研投入,政府的財政支持不可或缺。在專利申請意識方面,中國政府對于企業的專利申請提供了更多的財政支持,還給予優惠的稅收政策,同時營造輿論氛圍,培養企業的專利申請意識,鼓勵企業更多地申請專利。

雖然從一些數據上看,中國在與印度的科研競技上處于領先地位,但我們也應看到,中國現行的科技創新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
首先,政府主導對于那些長期性和基礎性的科研項目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但企業生存在日益變化的市場需求中,那些定期的(通常以年為周期的)政府支持不可避免具有滯后性。
其次,政府提供的財政和稅收支持存在被企業濫用的情形。一些企業申請專利或科研立項的目的更多地是從“政府圈錢”, 申請的專利更多地是為了獲得政府的補貼或稅收減免,而非真正要轉化為具體的產品技術。
最后,中國眾多的私人中小企業雖然在專利申請費用上享有一定的政府優惠和資助,但總體而言其創新活動所能獲得的來自政府的資金支持有限。面對殘酷的生存壓力,他們不得不停止或者暫緩科研活動。
當我們回到文首Sanjay Anandaram的自問時,我們會突然發現,中國目前似乎也需要回答一個類似的問題。也許這個問題的最終答案還有賴于創新的多元性在中國的廣泛實現。除了政府的不斷“灌溉”之外,一個生機勃勃的創新土壤也許才能培養出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