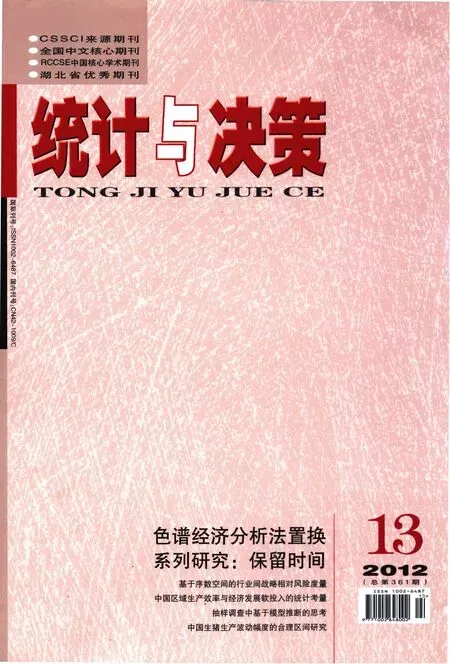中國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與收入不平等的動態(tài)實(shí)證
王延軍,溫嬌秀
(1.上海立信會計(jì)學(xué)院 經(jīng)貿(mào)學(xué)院,上海 200434;2.上海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0 引言
國內(nèi)現(xiàn)有研究(賴得勝,1997;白雪梅,2004;楊俊、黃瀟、李曉羽,2008等)對教育與收入分配的關(guān)系作了一定的計(jì)量分析與探討,但他們基本上只考察了教育不平等的靜態(tài)收入分配效應(yīng),而沒有深入分析教育不平等對收入分配的動態(tài)影響。此外,關(guān)于我國農(nóng)村區(qū)域間收入不平等的文獻(xiàn)大多是從東、中、西三大地帶進(jìn)行研究的,以省、市、自治區(qū)為單位進(jìn)行研究的文獻(xiàn)很少。鑒于此,本文以省級單位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構(gòu)造內(nèi)生收入函數(shù)模型,對我國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與收入不平等的動態(tài)關(guān)系進(jìn)行專門研究,以期更深入地了解我國農(nóng)村教育不平等影響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機(jī)制,從而提出降低我國農(nóng)村教育不平等進(jìn)而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建議。
1 中國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與收入不平等的狀況
(1)我國農(nóng)村省際間收入不平等的變化趨勢
受地區(qū)間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平衡的影響,我國農(nóng)村省際間的收入差距非常懸殊,且呈逐步擴(kuò)大趨勢。以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排在前5位和后5位的省份相比,1985年,排在前5位的省份的收入為:上海市806元、北京市775.08元、天津市564元、浙江省549元、廣東省495.31元,收入最高的5個(gè)省市的平均收入是637.9元;排在后5位的省市的收入分別是:四川315.07元、廣西302.96元、貴州302.14元、陜西295元、甘肅257元,收入最低的5個(gè)省市的平均收入為294.4元。收入最高的5個(gè)省市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5個(gè)省市的平均收入的2.17倍,兩者絕對額相差343.5元。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甘肅省的3.14倍,兩者相差549元。到2008年,收入最高的5個(gè)省份的收入為:上海11440.26元、北京10661.92元、浙江9257.93元、天津7910.78元、江蘇7356.47元,5個(gè)省市的平均收入為9325.47元;收入最低的5個(gè)省份的收入分別是:陜西3136.46元、云南3102.6元、青海3061.24元、貴州2796.93元、甘肅2723.79元,平均收入為2964.2元。收入最高的5個(gè)省市的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5個(gè)省市的平均收入的差距擴(kuò)大到3.15倍,絕對差距擴(kuò)大到6361.27元。另外,最高的上海市的收入與最低的甘肅省的收入的差距擴(kuò)大到4.20倍,兩者絕對差距擴(kuò)大到8716.47元。
(2)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狀況分析
自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我國農(nóng)村的教育事業(yè)取得了長足的進(jìn)步。但是,在農(nóng)村教育事業(yè)快速發(fā)展過程中,仍然存在著省際間發(fā)展不平衡的問題。
我國農(nóng)村教育經(jīng)費(fèi)的省際差距很大。2008年,農(nóng)村初中生均教育經(jīng)費(fèi)支出排在前兩位的是北京市與上海市,分別為21756.06元、16695.88元,均超過15000元;而后兩位分別是河南省與貴州省,分別是2786.42元與2455.23元。最高的北京市是最低的貴州省的8.86倍,兩者相差19300.83元。農(nóng)村小學(xué)生均教育經(jīng)費(fèi)排在前兩位的仍然是北京與上海,分別為14724.81元和13322.81元;而貴州省和河南省的農(nóng)村小學(xué)生均教育經(jīng)費(fèi)僅為1901.22元與1836.21元,最高的北京市是最低的河南省的8.02倍,兩者相差12888.6元。
農(nóng)村師資水平的省際差距也非常明顯。2008年,農(nóng)村普通初中教師文化程度在大學(xué)及以上的比例,北京、上海分別達(dá)到89.60%和81.68%,而貴州、河南的這一比例僅為31.8%與30.57%。農(nóng)村普通小學(xué)教師文化程度在大專及以上的比例,北京、上海分別達(dá)到87.58%和77.21%,但安徽、江西的這一比例只有54.8%與47.25%。
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衡發(fā)展的一個(gè)直接后果是導(dǎo)致農(nóng)村省際間勞動力素質(zhì)的差異。2008年,全國教育水平發(fā)達(dá)的三個(gè)直轄市北京、上海和天津農(nóng)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超過8年(依次為8.69年、8.06年及8.06年),而教育水平相對落后的云南、青海省以及西藏自治區(qū)的農(nóng)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僅為6.36年、6.16年及4.94年,特別是西藏自治區(qū),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2 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與收入不平等的實(shí)證研究
2.1 計(jì)量模型設(shè)定
明瑟爾收入方程在一系列嚴(yán)格的假定下推導(dǎo)了個(gè)人收入與其教育、工作經(jīng)驗(yàn)及其平方間的線性關(guān)系,許多研究教育與收入分配的經(jīng)驗(yàn)文獻(xiàn)也都是基于對該模型的線性回歸。由于該模型不適合采用面板數(shù)據(jù)來分析,這限制了它的應(yīng)用范圍。為此,本文構(gòu)造了一個(gè)類似于內(nèi)生增長生產(chǎn)函數(shù)形式的收入函數(shù)模型來研究我國農(nóng)村教育不平等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
據(jù)測算,我國農(nóng)村居民收入來源于財(cái)產(chǎn)性收入的比重為3.11%,而工資性收入和經(jīng)營收入則占90.1%。基于此,我們認(rèn)為: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主要是通過勞動掙得的,即收入(Y)是勞動投入(P)的函數(shù):

式中,A表示其它因素對農(nóng)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研究表明,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存量對勞動生產(chǎn)率具有積極的影響,并具有正的外部效應(yīng)。因此我們假定:勞動投入(P)是勞動數(shù)量(L)和質(zhì)量(人力資本,用H表示)的函數(shù),并把P設(shè)定為:

其中,H為人力資本變量(實(shí)證分析中我們用農(nóng)村平均受教育年限來代替),L是勞動數(shù)量(實(shí)證分析中我們用農(nóng)村就業(yè)人員數(shù)表示)。一般認(rèn)為,簡單勞動的邊際生產(chǎn)率是遞減的,因此式(1)的具體函數(shù)形式可表示為:

式中,α,γ為參數(shù),且0<α<1;Hγ表示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yīng)。
上式兩邊都除以勞動數(shù)量L,得到:

(4)式左邊為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于是我們可得到:

其中,下標(biāo)i和w分別代表各省市與全國。
令yr=yi/yw,Lr=Li/Lw,α0=Ln(Ai/Aw),Hr=Hi/Hw,對(5)式兩邊取對數(shù)得:

根據(jù)(6)式我們得到基本的計(jì)量方程:

式(7)中ε為擾動項(xiàng)。被解釋變量Lnyr是衡量農(nóng)村省際間收入不平等的指標(biāo),以地區(qū)相對收入水平即各省市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全國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來度量。LnHr和LnLr分別是各省市農(nóng)村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全國農(nóng)村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的對數(shù)值和就業(yè)人員比對數(shù)值。我們關(guān)注農(nóng)村教育不平等指標(biāo)LnHr的系數(shù)β1,其含義是教育不平等的彈性,即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每上升1%,收入不平等將上升β1%。為考察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對收入不平等影響的動態(tài)變化,我們在式(7)的基礎(chǔ)上增加了年虛擬變量與教育不平等的乘積項(xiàng)(DtLnHr),其系數(shù)的含義是,相對于基期,教育不平等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程度在t期的變化;若系數(shù)顯著為正,則說明相對于基期,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越來越重要。
由于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原因來自多個(gè)方面,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城市化水平、私營經(jīng)濟(jì)活躍程度等都有可能影響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但限于數(shù)據(jù)的可獲得性,我們只控制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城市化及私營經(jīng)濟(jì)活躍程度因素對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此外,賴得勝(1997)、白雪梅(2004)等的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教育擴(kuò)展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倒U關(guān)系,為驗(yàn)證我國農(nóng)村教育擴(kuò)展與收入不平等是否存在倒U關(guān)系,我們在回歸方程中還加入了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其平方項(xiàng)。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建立如下回歸方程:

E與E2分別代表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其平方項(xiàng),其系數(shù)β4、β5若互為正負(fù),則農(nóng)村教育擴(kuò)展與收入不平等的倒U假設(shè)能夠成立,反之則不成立。indus2,indus3是表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指標(biāo),分別以第二產(chǎn)業(yè)、第三產(chǎn)業(yè)的產(chǎn)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urb是代表城市化的指標(biāo),以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人口占總?cè)丝诘谋戎貋砗饬浚籹ou是代表私營經(jīng)濟(jì)活躍程度的指標(biāo),以國有經(jīng)濟(jì)單位職工人數(shù)占總職工人數(shù)的比重來表示,這一比值越高,說明私營經(jīng)濟(jì)活躍程度越低;ω是隨機(jī)擾動項(xiàng)。
2.2 樣本數(shù)據(jù)說明
以上指標(biāo)的原始數(shù)據(jù)均來源于《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相應(yīng)各年,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統(tǒng)計(jì)年鑒相應(yīng)各年,《中國人口與就業(yè)統(tǒng)計(jì)年鑒》相應(yīng)各年以及《新中國五十年統(tǒng)計(jì)資料匯編》。為考察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同時(shí)也考慮到全部數(shù)據(jù)的可獲得性,筆者選取了1997~2008年的省級面板數(shù)據(jù)。另外,我們的面板數(shù)據(jù)不包括港澳臺地區(qū),西藏和新疆由于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不全也不包括在內(nèi),這樣一共有29個(gè)省、市、自治區(qū)的數(shù)據(jù)。
需要說明的是,平均受教育年限系根據(jù)各地區(qū)農(nóng)村各種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乘以相應(yīng)的教育年限而得。具體地,將不識字或識字很少、小學(xué)、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定義為1、6、9、12、16年。

2.3 回歸結(jié)果分析
利用Eviews軟件,采用固定效應(yīng)變截距模型,對式(8)進(jìn)行回歸,回歸結(jié)果見表1:
從上述回歸結(jié)果中我們可以看出,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指標(biāo)LnHr的系數(shù)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說明,農(nóng)村教育不平等是影響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每上升1個(gè)百分點(diǎn),將使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上升15.7346個(gè)百分點(diǎn)。這是因?yàn)椋?dāng)前我國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狀況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的直接后果導(dǎo)致不同勞動力素質(zhì)的差異(見表2),根據(jù)人力資本理論,教育作為最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其差異影響到勞動力生產(chǎn)率,并最終反映為收入的差異。年虛擬變量與農(nóng)村教育不平等的乘積項(xiàng)DtLnHr的系數(shù)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意味著相對于基期1997年,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越來越重要,教育正在成為一種凝固和擴(kuò)大農(nóng)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機(jī)制。這是由于,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要素報(bào)酬逐漸得到還原,勞動作為一種要素投入,其報(bào)酬越來越接近于邊際收益產(chǎn)品;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造成了農(nóng)村省際間勞動力素質(zhì)的差異,并最終導(dǎo)致了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的持續(xù)上升。

表1 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與收入不平等
教育擴(kuò)展指標(biāo)E及其平方項(xiàng)E2的系數(shù)互為正負(fù),這說明我國農(nóng)村教育擴(kuò)展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倒U型關(guān)系成立,這與Ram(1984)、賴德勝(1997)及白雪梅(2004)等的研究結(jié)論是一致的。在教育不平等程度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當(dāng)平均受教育年限達(dá)到8.21年左右的時(shí)候,收入不平等程度達(dá)到最大。根據(jù)2008年中國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計(jì)算,我國農(nóng)村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38年,顯然,位于倒U型曲線頂點(diǎn)的左側(cè),即目前我國農(nóng)村教育擴(kuò)展不利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這主要是由于我國教育利益在農(nóng)村省際間分布不平等所致。
就業(yè)人比率LnLr反映了農(nóng)村省際間就業(yè)狀況的差異,它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表明縮小農(nóng)村就業(yè)差距有助于降低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這一結(jié)論是符合理論邏輯的。第二產(chǎn)業(yè)比重indus2的系數(shù)為負(fù),但在統(tǒng)計(jì)上不顯著。第三產(chǎn)業(yè)比重indus3的系數(shù)顯著為負(fù),這表明第三產(chǎn)業(yè)比重上升有助于縮小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這一結(jié)果也符合大多數(shù)的研究結(jié)論。變量urb系數(shù)為負(fù)且在統(tǒng)計(jì)上顯著是符合我們的理論預(yù)期的,這意味著城市化水平提高有助于降低農(nóng)村省際間收入不平等。我國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上升主要來自于工資性收入不平等的擴(kuò)大(薛宇峰,2005;鄒薇、張芬,2006),而工資性收入不平等的狀況又與各省農(nóng)村之間獲得非農(nóng)就業(yè)的機(jī)會有關(guān)。城市化水平提高特別是落后省區(qū)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農(nóng)村居民特別是落后地區(qū)農(nóng)村居民的非農(nóng)就業(yè),從而有助于降低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sou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這說明發(fā)展私營經(jīng)濟(jì)有利于縮小農(nóng)村收入差距。
3 結(jié)論與政策建議
上述分析結(jié)果表明,我國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不僅是當(dāng)前我國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上升的重要原因,并且它在相當(dāng)程度上是影響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今后動態(tài)變化的因素。此外,我國目前農(nóng)村教育擴(kuò)展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擴(kuò)大了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這主要是由于教育利益在農(nóng)村省際間分布不平等所致。基于此,我們有理由認(rèn)為,我國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狀況若得不到根本改善,那么,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趨勢可能在所難免。因此,為縮小農(nóng)村省際間教育不平等,進(jìn)而降低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我國政府應(yīng)該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大對農(nóng)村教育的投入,調(diào)整公共教育投入流向,把公共教育投入更多地用于農(nóng)村地區(qū)特別是中西部落后省區(qū)農(nóng)村的教育。盡快建立由中央財(cái)政統(tǒng)一撥付的義務(wù)教育資金保證體系,確保減輕農(nóng)民義務(wù)教育負(fù)擔(dān)。
第二,必須對農(nóng)村居民尤其是貧困農(nóng)民采取適當(dāng)?shù)膬A斜政策,增加他們的受教育機(jī)會和改善教育質(zhì)量。保障農(nóng)村貧困居民都能夠完成義務(wù)教育,同時(shí)建立支持助學(xué)制度,幫助農(nóng)民特別是落后省區(qū)農(nóng)民子女完成高等教育。通過大眾化教育提高他們對生存和發(fā)展機(jī)會的選擇能力,進(jìn)而改變命運(yùn),擺脫貧困,從而提高收入,降低收入不平等。
第三,加大對落后省區(qū)農(nóng)村的財(cái)政投入和農(nóng)業(yè)扶植;推進(jìn)城市化進(jìn)程特別是落后省區(qū)的城市化進(jìn)程,大力發(fā)展第三產(chǎn)業(yè),鼓勵(lì)農(nóng)村勞動力向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轉(zhuǎn)移,積極開拓農(nóng)村居民尤其是落后省區(qū)農(nóng)村居民的非農(nóng)就業(yè)機(jī)會。
[1]Rozelle,Scott.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Emerging Patterns in China’s Reforming Economy[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44,(19).
[2]賴德勝.教育擴(kuò)展與收入不平等[J].經(jīng)濟(jì)研究,1997,(10).
[3]張平.中國農(nóng)村居民區(qū)域間收入不平等與非農(nóng)就業(yè)[J].經(jīng)濟(jì)研究,1998,(8).
[5]董曉媛.中國農(nóng)村工業(yè)的私有化與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來自山東和江蘇的證據(jù)[J].經(jīng)濟(jì)學(xué)季刊,2003,(2).
[6]白雪梅.教育與收入不平等:中國的經(jīng)驗(yàn)研究[J].管理世界,2004,(6).
[7]萬廣華等.中國農(nóng)村收入不平等:運(yùn)用農(nóng)戶數(shù)據(jù)的回歸分解[J].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05,(5).
[8]楊俊等.教育不平等與收入分配差距:中國的實(shí)證分析[J].管理世界,2008,(1).
[9]萬廣華,張藕香,伏潤民.1985~2002年中國農(nóng)村地區(qū)收入不平等:趨勢、起因和政策含義[J].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