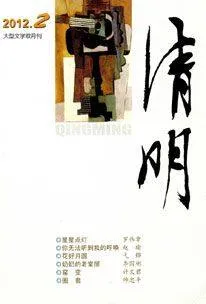我在北大的修煉
2008年6月下旬,我從北大暢春新園學生公寓搬出來,北大七年讀書生活結(jié)束了。說是讀書,實際上是讀書、聽課、辦刊、打工,四分天下。
我是拖家?guī)Э谏媳贝蟮摹?001年到2008年,我在北京換過十幾個住處。每當問起我的女兒,她總會說,暢春新園她最留戀,北大校園最好。
在200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讀碩士之前,每次出差到北京,總會抽空到北大來一趟。我有個同事在生物系讀研,住在靠小南門的40號樓,宿舍雖小,天地卻寬。我不止一次跟他說,你的現(xiàn)實就是我的夢想。我想死北大了。
考上北大之前,我曾狂妄地想,我比北大學生更像北大學生。發(fā)表過詩歌、散文,單位還資助我出過一個小集子。除了孔慶東、余杰,也沒有聽說中文系哪個學生寫過什么東西,天下也就那么三兩個人物。
然而,等進了中文系,開始上課后才發(fā)現(xiàn),自己是多么淺薄,多么狹隘。第一次受打擊,是在洪子誠先生的詩歌選讀課上。上課的學生濟濟一堂,很多人站著聽課,場面火爆,像是搶購。按說自己也是搞詩歌的,在這個課堂上卻像個門外漢。第一節(jié)課的發(fā)言就遭到了先我一步經(jīng)過嚴格北大訓練的高材生們的批駁。洪先生的一名弟子有一句話刺激性非常大,大意是某某同學所秉持的仍是八十年代的知識儲備,言外之意是早已經(jīng)落伍了。當時,我還不太理解這句話的分量,還不明白是指一個人真正理解文學,特別是做當代文學研究,要經(jīng)過相當?shù)膶W術(shù)訓練。因此,討論發(fā)言,寫論文,都是原來那一套隨感式,敢說敢寫。入北大第一個學期選修了九門課,除了英語和政治,一共寫了七篇作業(yè)。聽起來是作業(yè),實際上都應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shù)論文。可謂題材廣泛,沒有不敢寫不敢研究的。現(xiàn)在看這些作業(yè),真是狗屁不通。我的北大本科出身的同學,他們一般都只選兩到三門專業(yè)課!
我是帶著強烈的文學夢想來的,然而,到中文系遭遇的當頭一棒便是,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導師張頤武先生在第一學期給我只開了兩本書,一本是伊格爾頓的《當代西方文學理論》,最好是伍曉明的譯本,而我只弄到了王逢振的版本。另一本是杰姆遜的《后現(xiàn)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張先生說,要把杰姆遜的書當成紅寶書來讀。這句話我以為是我在北大得到的重要教導之一。
然而,我根本讀不懂。我不明白,一個文學專業(yè)的學生,為什么非要讀一本文化的理論書,而且是外國的理論。在北大的痛苦就是從讀杰姆遜開始的。由此,我才知道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是一個什么概念。再到后來,就是硬著頭皮閱讀各種各樣西方文學理論書籍。由杰姆遜摸到伊格爾頓、馬爾庫塞、阿多諾,到霍爾、雷蒙·維廉斯,再到羅蘭·巴特、福柯、德里達,這份書單是個超級鏈接,套用劉震云小說《一句頂一萬句》的話說,一個事扯出十個事,一個問題扯出十個問題,一部著作涉及到十部著作。最后就淹沒到西方理論的汪洋大海中去了。有一句經(jīng)典臺詞就是,中文系學生不讀小說。可以想見,這對于一個懷揣文學夢想的人來說有多么荒誕,多么殘酷。
直到2004年碩士畢業(yè),我才真正明白為什么要讀這些理論,為什么文學離不開政治,為什么不叫作品而叫文本,為什么中文系的師生要研究大眾文化,而不是純粹的文學。在中文系受訓之前,寫論文是野狐禪,受訓之后又成了小腳女人,引經(jīng)據(jù)典,處處小心,然而內(nèi)心創(chuàng)新的野馬又狂奔不止,這種痛苦不堪忍受。每寫一個觀點都會想,曹文軒先生會怎么看,李楊先生會怎么看,陳曉明先生會不會挑毛病。從此,我真正理解了北大的嚴謹,理解了學術(shù)是需要傳承的,也理解了什么是學術(shù)之苦。
摸到了門道,也就沒有了之前的狂妄。在課堂上,我總能遇到那些理論讀得如數(shù)家珍、用得像土特產(chǎn)一樣的牛人。人家不跟你比讀賈平凹、王安憶,人家跟你比英語原著,跟你比海德格爾,跟你比行文能夠氣死人的德里達。在課堂上如魚得水的總是那些滿口德里達的學生,而這恰恰是我的痛苦。我于是崇尚獨自看書,很少聽什么大師的講座,特別害怕教室里擠得水泄不通,末了還要湊上去簽名的場面。
但我發(fā)現(xiàn),有一種講座不該錯過,那就是當代文學教研室的論文答辯。論文答辯是五院的精品菜。五院是最經(jīng)典的課堂。中文系當代教研室活躍著各種不同立場和觀點的老師,每次學生答辯都會變成老師答辯。陳曉明偏右,韓毓海偏左,張頤武不左不右,曹文軒固執(zhí)文學本體論于胸中,那個激烈討論的場面,真是比看戲還熱鬧。
碩士三年是躡手躡腳的三年。北大牛人太多,我的自卑感無時不在。當時,我和心理系的學生住在一個宿舍。我聽他們說北大自殺的學生不少。我一入學就立誓,不自殺,不離婚。
上北大時,年齡已過三十,是中文系最老的學生之一。在食堂打飯,師傅會問,老師,你打幾兩?很受刺激。我在五食堂旁的攤子邊修自行車,兩名女生過來說,師傅,你看我的車子能不能修?大學本科時,我在班里年齡最小,到讀研時,我最老。這就是人生的戲劇性。但這種痛苦只屬于表層,它遠遠不及讀書的痛苦。通過碩士三年的修煉,我從一個一窮二白的門外漢變成一個滿腦子理論概念卻又自知淺陋的老書生。我這樣總結(jié)前半生:做人比較成功,做男人很失敗。前者,因為自己能按內(nèi)心生活,選擇了真正熱愛的文學;后者,出于上不能報國家,下不能孝父母,中不能養(yǎng)妻女。而立之年,無房無車,飯碗都沒有。小平同志二十來歲就當大官了。博士答辯時,不禁感慨個人經(jīng)歷,讀本科時是動亂,讀碩士時是“非典”,人生不易呵。
2003年是我在北大最難熬的一年。為了防止5歲的女兒被感染,我在封校前兩天,在鏡春園租了一間平房,據(jù)說,是季羨林先生的鄰居,屋前有池,季先生親種的荷花。我每天要陪女兒在校園里逛,中午就在未名湖邊或民主樓東北角的小山坡下的一塊石頭上吃飯,飯后和她到圖書館北面的草地上找蒲公英,靠天倫的力量來打發(fā)時光。也就是在那時,我喜愛上了這種又黃又白、可飛可駐、既腳踏大地又向往天空、雖然弱小卻能將子孫遍撒五湖四海的植物。陶淵明獨愛菊,余光中獨愛蓮,我雖非牛人,也終于找到了自己心愛的花兒,蒲公英。這可能就是所謂的人生啟悟吧。
也正是“非典”,五院前邊的靜園草坪成為我每天光顧的地方。我在松樹下看書,復習英語準備考博,女兒在那個革命烈士紀念石碑上玩滑梯,是陳云題寫的碑名。青青校園,上有白云,在草坪上踱步的喜鵲像系著領(lǐng)結(jié)的胖紳士。自然界的優(yōu)雅怎能比擬?曹文軒先生將他的課搬在鳴鶴園的涼亭里上,而我的導師張頤武先生,則戴了手套在四教門前的草坪上堅持上課。恐懼和煎熬,制造了別樣的樂趣。有一陣曾傳言,軍方會用飛機從天上往下撒消毒劑,而事實上,那一段時光或許是北大歷史上最清凈的時光,未名湖有時候一個人都沒有。我就繞著湖轉(zhuǎn)圈,獨享殊遇。“非典”最嚴重的時期,正是我寫碩士論文的時期。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導師張頤武先生打來的電話,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是我入學以后他第一次主動打電話到宿舍。感動涌上我的心頭。
五院是個風水寶地,是一片廣闊天地,是各路神仙聚集的地方。小小的房子,院子,但有多少大師來過?每次走進那個紫藤花的大門,看到院內(nèi)毛茸茸的草坪,就心生幾分敬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只不過是一個過客。每每此時,我便產(chǎn)生強烈的過客的心情。北大太大,不是因為未名湖,也不是因為五院,更不是因為漂亮的燕園,而是因為這里的牛人,太多的牛人。不到這里,不知什么是牛人。每開一次答辯會,都會看到各位老師相互贈送新書。記得陳曉明先生將他的《表意的焦慮》帶來時,孟繁華等先生不約而同瞪大眼睛:曉明又出專著了?遑論什么胡適、魯迅之類的五四英雄,就是眼前的這些大師,自己不吃不喝,一天讀書寫作十八小時也攆不上呵。這真的是一種絕望感。每每這時,都會強烈地感覺北大不是你的,你只是一個北大的過客,一個前來朝圣的香客而已。五院的小廟屬于大師,屬于學術(shù)狂人。我甚至聽說這樣的典故,賀桂梅老師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她與我?guī)缀跬瑲q。那時節(jié),我特別焦慮,尤其怕看到年輕的學術(shù)狂人們又出了新著。大名鼎鼎的張旭東教授,杰姆遜的高徒,看上去比我還年輕,而他翻譯的杰姆遜大師的文集夠我啃一輩子。在五院,我完成了碩士、博士論文答辯,聽了六年大部分當代文學先我進行的論文答辯,有緣遇見了諸多大師、名人、美女、帥哥,參加了邵燕君老師的當代文學期刊論壇。在五院,我的狂妄和井底之見徹底消失了。所剩的,只有對這座古典風格小院子的尊敬與眷戀。
北大以學術(shù)為盛。不介入學術(shù)活動,只能算半個北大人。我真正融入北大生活是從靜園的一次小型學術(shù)聚會開始的。就在五院門口那一片草地上,我參加了由柳春蕊組織的《北大研究生學志》的主題研討,話題是“詩歌的聲音現(xiàn)象學”。參加的人還有北大的辛曉娟(即后來走紅的武俠寫手步飛煙)、王璞,北師大的譚旭東,人民大學的楊慶祥。不知道春蕊兄是如何知道我的聯(lián)系方式的,但我非常喜歡他五湖四海的學術(shù)交友風格。就是這次不經(jīng)意的交往,吸引我走進了《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的天地。2004年10月,經(jīng)過研究生學志的招新面試,我加入了這個學術(shù)社團。按說自己老大不小的人了,跟一幫年輕娃娃混在一起不是個事,但一個人埋頭讀書的感覺實在不妙,非常想嘗試“學術(shù)是聊出來的”滋味,想通過學術(shù)結(jié)識牛人,首先是沖著柳春蕊的個人魅力。之后,就開始了長達三年繁忙的學生編輯生活。這是我在北大最充實、最忙碌的日子。為了籌備底層寫作的討論,和現(xiàn)代文學的張春田有過一次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聊天,投機之至,如坐春風,是我在北大最快樂的一次學術(shù)閑聊。2006年下半年,約請北大、清華、南開三校12位學友,做了一個《讀書》雜志的學術(shù)史研究,結(jié)識了諸多學科的牛人,有許多討論、許多美好回憶。法學院蘇力教授的研究生劉晗是典型的學術(shù)牛人,因?qū)W術(shù)“債務”太多,沒有給這個研究寫稿,但和他的討論使我受益匪淺。此君2008年同時考取耶魯、哈佛、哥倫比亞的博士,最后去了耶魯。年紀輕輕,道行不淺。此外,還有兩件事記憶猶新。2005年正逢刊慶二十周年。5月,在五院中文系一樓會議室,協(xié)助春蕊兄組織舉辦了研究生學志新老編輯座談會,聚集了近一百號人,場面很大。春蕊兄是個執(zhí)著而堅定的人,他把會議一直開到下午一點多,會上發(fā)言動了真情,眼淚差點下來。我非常清楚,在一個無權(quán)力制約、無金錢潤滑、組織極其松散、完全靠學術(shù)的吸引和個人能力來運轉(zhuǎn)的學生群體中,又是在北大這樣學生都比較高傲的地方,要組織指揮30來號人辦一件事,需要付出多少心血!他為籌辦此次活動忍受了諸多委屈,有不少苦衷。會開到下午一點,大家都餓了,但都被編輯部的投入和熱情所打動,每個人都堅持到會議結(jié)束。這次會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學術(shù)不是簡單地上課和發(fā)言,有時需要投入、信念、堅持,甚至犧牲。
2007年我主持研究生學志時有了切身的體會,但其中的充實感不足為外人道。也是在同樣的地點,和廣西師大出版社合作舉辦了一次題為“青年與治學”的講座,湯一介先生主講。老先生八十歲了,但思路清晰,娓娓道來,他的治學與人生道路很使我受啟發(fā)。散會后,我陪湯先生走回暢春園他的公寓。在路上,我問他關(guān)于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他說,當代中國其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如果有,李澤厚算一家,我本人頂多算一個哲學史家。類似這樣的學術(shù)判斷,書本上鮮見。湯先生當然是謙虛。但他推崇李澤厚是非常合我心的。來北大之后,哲學方面我看書很少,像流行的海德格爾、施密特、胡塞爾等基本不敢問津,太高深了。但李澤厚的中國思想史論,我認真地讀了,特別是現(xiàn)代和近代兩本深有認同感。他是當代學者中少有的打通古代、近代和現(xiàn)代,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都下過工夫的一個人,更為重要的是,他有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對當代中國的社會實踐有切身體會。后來,我看到一篇他與杰姆遜的對話,他所站的高度和眼光非杰姆遜可比。這也算是課堂之外的心得吧。
不怕人笑話,北大最讓我記憶深刻的是我的打工生涯。在這里,我既當學生,也當過先生。2006年到2007年,為糊口,先后給外國留學生教過三次漢語寫作課。這要感謝蔣朗朗先生,他非常體察我這個老學生的生活疾苦,給了我這個機會。在象牙塔里,像蔣先生的低調(diào)、務實和平易并不多見,讓我時時心生感激。但是,給老外上課對學術(shù)助益不大,主要為稻粱謀。賺生活費是真,練外語口語是我的心理安慰。舉目四顧,四處找兼職的學生何其多。我又何曾想到,中國大學校園里,涌動著如此巨大的打工潮?我始終無法克服對學生打工抱有的恥辱感,像在賣身。勤工儉學或社會鍛煉之類的說法不過是遮羞布。老師更名為老板,校園轉(zhuǎn)換為勞動力工場,教育變身為職業(yè)培訓,我無論如何都有一種深深的厭惡。但毫無辦法,殘酷的生活總以它的不可回避逼著人從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甚至變態(tài)的樂趣。
我給美國班的課是在五院二樓北側(cè)的小教室里上的。每次上課走上樓梯,都會有恍如夢中的感覺。自己的中文系生活竟然是這樣子的。這不是我?guī)啄昵跋胂笾械谋贝笊睿冶绕鹉切┟刻焖奶幷一畹耐瑢W來,已經(jīng)很幸運了。我還在北大網(wǎng)絡教育學院兼職助教,工作十分繁忙,要備課,布置和批改作業(yè),尤其痛苦的是,要在網(wǎng)上和那些并不懂和并不喜愛文學、完全是混文憑的“學生”講文學。對牛彈琴就是我的掙錢之道,真是滑稽之極。教了兩年多,只發(fā)現(xiàn)一個好學生,她后來成了一家報紙的編輯,經(jīng)常和我約稿,算是我北大打工的小小安慰。
我還是想方設法把精力花在學習上,把別人看電影、談戀愛的時間用來看書。在研究生學志的日子里,每天都會看許多來自各個學科的稿子,法學的、歷史的、哲學的、社會學的,但萬變不離其宗,學術(shù)的擔當和問題意識都是我最看重的。我自知不是一個學術(shù)苗子,沒有哪一樣是自己的專長,但經(jīng)過研究生學志的三年修煉,眼界漸寬,終于能從學術(shù)和理論的拘囿中脫身出來了。當最后兩年做博士論文選題的時候,在導師的指導下,我非常熱情地投身到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這樣一個與文學八竿子打不著的研究對象中來。前五年的學習給了我進入這個研究的勇氣和基本訓練,我試圖從中解釋當下中國,認識我身處的這個世界。
開題和論文預答辯都進行得很順利,我非常慶幸,覺得總算要煎熬出來了,二十年寒窗總算要結(jié)束了。然而,就在論文答辯的前一天,導師打電話給我,說研究生院有關(guān)老師看了我的材料,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學的選題,而目前的答辯委員會組成人員當中,沒有社會學的老師,必須加入一位社會學的教授。言外之意就是中文系當代文學教研室目前的師資和研究力量,無法或者沒有足夠資格就這個選題進行答辯。這真是一個嚴肅而可笑的判斷。然而,這也是一個現(xiàn)實的判斷。我做夢也想不到,在我行將結(jié)束北大七年行程的時刻,遇上了“交警”。
離答辯只有二十四小時了,而我的論文25萬字,就是能夠請到一位社會學系的評委,就是他或她一小時能看一萬字的論文,一天一夜不睡覺也看不完我的論文呵,何況能否請到這樣一位大救星還未知可否!2008年的夏天是我最難熬的時光。一面要找工作,為將來的生路操心,一面還要著手畢業(yè)論文的答辯。更令人著急的是,我患了嚴重的眼疾,在電腦前停留不能超過一個小時。
最后依然是導師幫我解決了這個難題。他請到了社會學系的一位教授。這位教授完全是菩薩作風,在她下課之后,前來參加了答辯會,并在論文上簽了字。
這位菩薩放了我一馬。我的師妹將一把鮮花及時塞在她的懷中。
我的論文評委由八位教授組成,而且有社會學系的教授,不知道在中文系百年歷史上有無先例。
我?guī)缀跏强目慕O絆走出了北大校門,告別了五院。現(xiàn)在,我常坐在辦公室里想,我的北大之行是一部小說,一個人很狂傲地走進北大,很落魄地走了出來,脫胎換骨。那七年是我修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