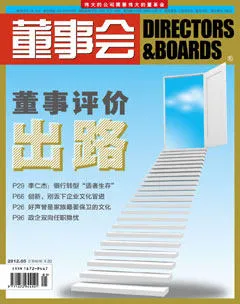比政策本身更重要的是時機與順序
“兩會”期間,與會代表的提案是各大媒體報道的熱點,從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到醫療體系,從股票發行改革到產業轉型升級,從中小企業融資到碳排放,豐富多彩、不一而足。這些提案輪番出現在報紙、電視的重要版面上,似乎個個都迫在眉睫,大有不破則萬事不立的架勢。
經濟發展本身就是一個涉及范圍極廣的過程,各項活動之間往往相互關聯、互為影響,難以單獨考量一種活動的投入產出關系。例如,企業創新升級和研發投入,需要有大量科技人才的支持,而創新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則要仰仗政府加大教育投入,而教育投入的提高又要有經濟發展水平的支撐,從而對企業的創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有很多事項之間有時是相互沖突的,比如通過出口退稅等方式鼓勵企業出口,擴大了產品的海外銷售市場,但與此同時也給予了企業偏重規模擴張、忽視質量的負面激勵。經濟發展具有的復雜性、動態性和整體性,對制定治國方略的決策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對新時期的中國經濟而言,在經歷了三十余年的高速發展之后,各種矛盾累積下來,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問題錯綜復雜,難以厘清。在現有的資源約束和環境條件下,要處理好這些彼此沖突、相互聯系、依時而變的關系,實屬不易。
縱觀世界,可以發現日本、韓25759f7e13035ab27dafd62af365bd1b國和我國臺灣地區有著相似的發展過程和成長規律,比如通過出口帶動外向型經濟的發展;由于重視教育投入,擁有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勞動者,從而成為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臺灣的經濟發展,也是從計劃色彩很濃的經濟體系開始,到建立完整而有效率的工業體系,最后發展形成全面自由化的市場經濟體系,這個過程也是充滿了各種矛盾和沖突,圍繞多種發展模式的爭論一直持續不斷。其成功的關鍵之處在于因地、因時制宜的政策及其實施,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所評價的那樣,臺灣的成功在于政策的順序而不是政策本身,即在適當的時機提出并實踐了適當的政策,比如在資本積累不足的時候出臺政策,鼓勵優先發展輕工業而不是重工業;在鼓勵企業進行產業升級的時候,出臺了大量培育和吸引人才的計劃。日本和韓國也在不同的時期完成了從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跨越,靠的也是這種“抽絲剝繭”的智慧和政策的適時推動。
遺憾的是,我國眾多的經濟學家熱衷于提出問題,很少有立足中國實際又具有國際視野的解決方案,批評者多、建設者少。討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專業學術論文可謂汗牛充棟,學者們用大量數據和回歸模型來證明影響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進步的諸多因素,但對適應性的政策及其實施的輕重緩急、優先順序卻鮮有研究,因此,這些論文大多最終也只能束之高閣,對經濟決策的影響作用極為有限。
與宏觀層面的問題類似,企業的微觀治理改革方面也存在著時機不當、順序不明的問題。目前中國還處于一個國有經濟成分較高、行政干預較多的時期,在評價公司治理績效、董事會運作效率和董事履職表現的時候,也要考慮到約束條件下各種關系的復雜性、動態性和整體性,否則會造成評價結果的不公平或扭曲,反過來會阻礙一個有效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