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新聞出版戰(zhàn)線老戰(zhàn)士金沙同志
2011-12-31 00:00:00楊牧之
百年潮 2011年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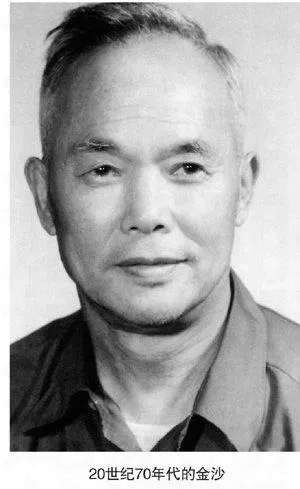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的光輝歷史中,有許多難忘的人和事。許多人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業(yè)績永存。黨的優(yōu)秀新聞出版工作者,原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聯(lián)合黨委書記金沙同志,就是這樣一位令人景仰和懷念的人。
為黨的新聞出版事業(yè)奮斗一生
今年早些時候,我收到金沙同志夫人萬慧芬同志給我的一封信,并附上她親自撰寫的金沙的傳記《金沙的革命生涯》手稿復印件,囑我一定為這部文集寫點什么。
這段時間以來,我一直為各種事務困擾,但我還是抽時間翻閱了這部書稿,并盡我可能對書中記載的關于金沙同志當年在中華、商務工作期間一些事情的時間、地點做些核實和訂正。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翻閱中,金沙同志30年前領導中華、商務的往事在我頭腦中逐漸清晰了;特別是我對金沙同志將畢生心血都傾注給黨的新聞出版事業(yè)的經歷,有了一個大體的了解。
這個輪廓實際是金沙同志奮斗一生的“線索”。
1916年,金沙出生于江蘇太倉一個城市貧民家庭;
1933年,在上海參加“左聯(lián)”、“反帝大同盟”,參與創(chuàng)辦進步刊物《鐵流》、《跳躍》等,參與主辦和編著進步書刊《兒童文藝》、《少年世界》、《新兒童故事》等;
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
1938年,奔赴延安,任抗大總校文工團文學組組長;
1941年,在抗日戰(zhàn)爭最殘酷的年代,到達太行、太岳革命根據(jù)地,先后擔任新華社太岳分社社長,新華日報(太岳版)特派員、副總編輯、總編輯,并以前線記者團團長身份,跟隨陳賡將軍轉戰(zhàn)晉南,先后發(fā)表過100多篇文章、戰(zhàn)地通訊和評論文章等,被譽為“太岳三杰”之一;
1949年進京,到剛剛形成建制的人民日報社任職,先后主持報社黨的生活組、國內政治部和農村工作部工作;
1960年赴藏,任西藏日報總編輯,并主持黨的西藏工委宣傳部工作;
1966年,成為西藏第一個被揪出來的所謂“走資派”、鄧拓“三家村”在西藏的代言人;
1973年調中華、商務,不久,任聯(lián)合黨委書記和總編輯;
1978年調五機部任教育局局長;
1982年離休;
1998年逝世,享年82歲。
我詳盡地列出金沙同志的生平線索,是因為我從中看出來,在我們追蹤金沙同志的生平足跡時,實際上差不多就是在追蹤黨的新聞出版工作的經歷。幾十年來,他是黨的新聞出版工作的見證者、親歷者,他在黨的這條戰(zhàn)線上,在白色恐怖中、在槍林彈雨中、在饑寒交迫中、在委屈和誤解中,進行了奮斗不息的追求和探索;與這個事業(yè)一起,備嘗了艱辛、苦難和波折……
今天,我國新聞出版事業(yè)已經具有上萬種雜志、幾千種報紙、六七百家出版社的蓬勃大軍,已然成為文化產業(yè)中的支柱產業(yè),在推動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在全世界樹立中華民族偉大形象的事業(yè)中,發(fā)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飲水思源,我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離不開金沙同志這樣的老一輩的革命者一步一步艱辛的跋涉,一年一年頑強的奮斗。
在我們舉國慶祝我們的偉大勝利的時候,理應在金沙同志的墓碑前,獻上一束鮮艷的花,表達我們永遠的追思和敬仰。
主政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
金沙同志1973年5月,在西藏徹底平反、官復原職一年以后,奉命調回北京,到在“文化大革命”廢墟中剛剛恢復組建的中華、商務聯(lián)合黨委主持工作,任黨委書記、總編輯。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都是我國歷史上最為悠久的出版基地,哪一個單位都是聲名顯赫,將兩個單位合在一起,將這副重擔交給金沙,而且黨務、業(yè)務一肩挑,這足見黨組織對金沙同志的高度信任。1974年,金沙和當時的國家出版局領導一起,在中南海接受周總理垂詢。這也是中央對他信任的一個明證。但是,對金沙來說,當時他的面前擺著四個不利條件,因此經受著全新的考驗。
此前,從“左聯(lián)”開始,在前后40多年的革命經歷中,他有著30多年的宣傳、文藝、新聞工作經驗,獨獨沒有在出版部門工作過。顯然,他缺少這方面的領導經驗。
中華、商務是專家、名人薈萃的地方,像白壽彝、翁獨健、宋云彬、王鐘翰、周振甫等這些舉世聞名的大學者,都曾在這里工作過。做他們的領導,金沙雖不能說是“外行領導內行”,但如何調動這些人的積極性,干好專業(yè)工作,需要特殊的領導藝術。
1973年還處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各單位的派性還沒有完全消除,中華、商務兩個單位合在一起,其復雜可想而知。
一般領導人調動,往往都帶上幾個骨干力量前往“助陣”,以擺脫“孤家寡人”的困難局面,而金沙同志不帶一兵一卒,只身一人前往一個陌生單位、陌生的領域赴任。
上述種種困難,像沉重的擔子壓在金沙同志肩上,他能夠承擔起來嗎?
從1973年到1978年,早已經結束的這段歷史證明,金沙同志勝任在中華、商務的領導工作,基本完成了上級領導交給的任務。他靠什么?他不是靠狹隘的“行業(yè)經驗”、不是靠強加于人的“專政”力量,也不是靠拉攏收買的“組織手段”,更不是靠圈圈伙伙的無原則交易。金沙同志靠的是忘我無私的工作精神、真誠坦率的人格力量、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記得在當時的形勢下,為了“給知識分子摻砂子”,很多地方專門派去工農兵代表做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領導者,就是所謂“外行領導內行”的做法,結果往往是天怒人怨,很少有好結果的。
但是,從1973年到1978年這段時間,在以金沙同志為主的黨委一班人領導下,中華、商務卻做到了人心逐漸平和,隊伍趨于穩(wěn)定,領導班子基本團結。做到這一點已屬不易,在業(yè)務上這兩個出版單位又都有所作為。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關心過問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點校本的整理工作就是在這段時間集中進行的;還出版了像《陸游集》、《李太白全集》這樣一些重量級的古典文學整理著作;翻譯出版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新譯本、米涅的《法國革命史》等世界歷史名著10余部,英國、意大利等國別史40余部,中俄關系史料30余部。在那樣一個背景下,金沙同志作為中華、商務的一把手,功不可沒。
當時金沙同志面對的形勢之復雜、困難之嚴重,只要我們每個人能客觀地回憶一下這段歷史的經過都會了然于心。然而,這位久經考驗的黨的新聞宣傳工作者沒有被困難嚇倒。至今,中華、商務的老人們回憶起那段歷史,對金沙同志的贊許之情,仍然溢于言表。確實,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當時主政中華、商務的不是這位資歷深、有政策經驗、公平正直、溫文爾雅的金沙同志,1973年到1978年中華、商務的歷史可能將會成為怎樣一種寫法呢?
正因為這樣,中華、商務的人們是懷念金沙同志的。
當然,在當時的形勢下,作為中央重點關注的古籍出版單位,中華、商務也奉命編輯出版過一些“法家著作”,也“緊跟”、“配合”過“上面”的指示,為此,金沙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曾做過十幾場檢查,并接受群眾的批判和質詢。這是金沙同志無法選擇的“歷史”,也是所有中華、商務人無法選擇的“歷史”。
把握大局,抓住主流,有所作為
歷史是復雜的。有時歷史是過程,有時歷史是結果。但不論是過程還是結果,我們則必須從今天的結果中反推當初過程的得失。
1973年,金沙同志到中華、商務主持工作時,我只是一個剛剛從干校走上工作崗位的青年編輯。那時,我不是黨員,也不是干部,我不會有多少機會與中華、商務“一把手”接觸。許多事情我是從別人的回憶中聯(lián)想起來的。
1973年到1974年,金沙同志按照當時中央的要求,鼓勵年輕的編輯到工農兵中去,和工農兵“三結合”評法批儒寫文章,這才命定地使我與金沙同志有了一定的接觸和向他學習的機會。無論是金沙同志還是我自己,在這段歷史結束后,我們都有過沉重的反思。我們無法改變當時必經的過程,但可以從這個過程中、從自己的作為里,引發(fā)終生受益的經驗和教訓。人生的道路是漫長的,有時又十分短暫。實踐、思考、學習,再實踐、再思考、再學習,庶幾可以有所進步,可以更好地從事我們?yōu)橹畩^斗的事業(yè)。
金沙同志在中華、商務工作已經過去近30年,往事大多淡漠。但是,今天閱讀《金沙的革命生涯》手稿,使這段記憶與金沙同志的往事一起在我們腦海中復活。我重新檢點金沙同志當初在中華、商務工作的那段“過程”,反推金沙同志的“必然性”,使我看到,金沙同志長期辦報紙,從事新聞工作,這就培養(yǎng)了他敏銳的政治嗅覺,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觀念,“緊跟”、“配合”的大局意識,對一個新聞工作者這是必備的素養(yǎng),但拿這些來辦出版社,尤其像中華、商務這樣的老成持重、強調學術的百年老店,其結果當可想而知。尤其是在社會那樣劇烈變革的形勢下,在“上面”都出現(xiàn)了嚴重問題的時候,“獨善”和“兼濟”都很難做到了。金沙同志的內心苦惱,以及后來的許多矛盾,恐怕都與此有關。但金沙畢竟是一位老革命,久經風雨,有革命者的職業(yè)素養(yǎng),他能夠把握大局,抓住主流,而有所作為。他在那種復雜的形勢之中,能夠盡最大力量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努力去完成毛主席、周總理交辦的整理古籍的任務就是明證。
關心同志、平易近人,
處處為他人著想
金沙同志的另一突出之點就是他關心人,平易近人,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他和人談話時語調平和,總是笑瞇瞇的。
當時的中華書局二編室主任方南生說:有一次我患病請假,發(fā)病時天旋地轉。金沙同志得知后,立即騎上自行車,到我家里探望。
當時的商務印書館第五編輯室副主任張?zhí)煊诱f:后來我調離北京到西安工作,他還關心地向他工作的下屬單位介紹我的情況,希望幫我安排更合適的工作。
當時的商務印書館編輯胡企林說:金沙與人交談總是面帶笑容,認真聽取大家意見,博采眾議,即使胸有成竹,也總是與大家商量辦事,不以己見強加于人,顯示出平等、開明的民主作風。因此,我和同事們都很愿意接近他……
在我,對金沙永遠不能忘記的,不是表揚我、不是批評我,而是關于衣服的一件小事。1974年9月30日下午,我突然得到通知去參加當晚的國慶招待會。對于一個公民,一個勞動者,這是國家給予的最高榮譽,高興、激動,不能自己,急忙回家找衣服。我那時每月掙46元錢,只有一件八成新的衣服,算好一點,趕快洗,到晚上5點鐘還沒干,來不及了,只好穿上另一件舊衣服前往。金沙同志看到,說,“這件不行。我給你找一件。”急忙回宿舍從箱子里找出一件他的稍好的衣服。金沙同志看我穿上,笑瞇瞇地說:“總比你那件強。”那笑瞇瞇的眼神,讓我感到父兄般的溫暖。
而金沙對自己卻十分嚴格。他到了中華、商務基本不坐小車,出版局通知開會,他騎上自行車就出發(fā);國慶游園,家里人都希望坐小車,可以多走幾處,他想了想,還是和家里人一起乘公交車去。他說:司機師傅休個假不容易,我們乘公交車去,他就可以回家休息了。他從到中華、商務上任后,一直住在辦公室。他老伴說:“我們住在機關樓內時,原來有兩間住房,但金沙把大辦公室隔成兩間:一間辦公,一間住宿,從而騰出一間住房讓給別人居住。當我發(fā)牢騷時,他寬慰我說:‘你就知足吧,單位住房這么緊張,我們能有兩間住房已經很不錯了。’”
這些僅僅是從我所認識的人寫的回憶文章中摘出的片斷。我常想,在那樣錯綜復雜的環(huán)境中,金沙能夠在中華、商務立足、能夠團結大家,做好工作,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嚴格律己、以身作則,是一個重要原因吧?
金沙同志對青年人更加愛護,他總是發(fā)現(xiàn)青年人的長處,鼓勵他們的每一點進步,不拘一格地扶持和重用年輕人。這在《金沙紀念文集》中到處都有印證。包括著名詩人汪承棟、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瑪,后來成為新華總社社長的郭超人、河北省政協(xié)主席李文珊、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這些人年輕的時候,作為金沙的下屬,或者因為金沙力排眾議、破格提拔,或者因為金沙飽含熱情,大力舉薦,最后終于成就了他們的事業(yè)和功名。金沙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有時被誤解,甚至蒙受冤屈,遭受迫害,但他的態(tài)度是無怨無悔。閱讀《金沙紀念文集》中他的同事或部下寫的文章,你會被這些事跡感動得熱淚盈眶。
金沙信任年輕人,培養(yǎng)年輕人,愿意給年輕人創(chuàng)造條件,勇于替年輕人承擔責任。這是我30年前對他的印象;30年后的今天,我在《金沙紀念文集》中發(fā)現(xiàn),在他一生中,在他所到之處,對年輕人是永遠地情有獨鐘。這在今天,當我們已經工作了幾十年并不年輕的時候,感慨尤其強烈。
金沙同志去世已有8年了,感謝萬慧芬同志的辛勞使我們得以了解金沙同志從17歲開始六十幾年的奮斗歷程。愿金沙同志的這種追求精神,鼓勵我們在新的征途中前進。
2006年9月?第一稿
2010年6月?再修改
(責任編輯?劉榮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