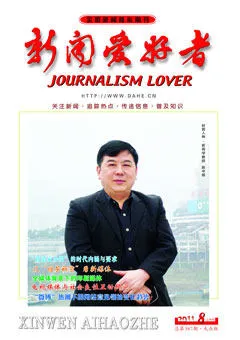藝術設計中的整體意識
藝術設計是一項復雜而又有著差異的思維活動,思維活動的差異源于創作者思維方式的差異,而思維方式的形成又源于傳統文化的熏陶。中國的傳統文化綿延數千年,使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和鮮明的獨特性。因此觀照中國的藝術設計活動,不能不觀照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
中國傳統文化思維方式的突出表現是思維的整體意識,對藝術設計來說,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意識。所謂整體意識,就是指在認識事物時要從多視角、多方面、多因素做整體把握。這種整體把握具有立體性、動態性、綜合性以及混沌性等特征。
立體性。藝術設計往往是通過平面來展現的,然而平面性的展現并非來自平面思維,而是立體思維的產物。就一個物體的觀察而言,需做多角度、全方位的觀察,反映出橫縱、上下、左右、內外等多種關系才有可能獲得物體的立體性體貌。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取象就十分強調立體性。它不是囿于一個固定的視角,而是采取多視角;它不是反映一個側面,而是全方位。因此,西方繪畫強調透視,而中國繪畫則迥然。但北朝時期的文藝理論家劉勰首創“物游”一語,宋代畫家郭熙將之概括為“飽游飫看”。所謂“飽游飫看”,就是盡量更多更全面地觀察。“游”和“看”是兩種不同的行為狀態,“游”是不固定一個點觀察,是邊走邊看,而“看”則有相對穩定性,是停下腳步細看。為什么要“飽游飫看”?郭熙說:“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遠十數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不悉乎!”同樣的感受,清代文學家戴名世將之概括為“移步換形”,他在《雁蕩記》中說:“大抵雁蕩諸峰,巧通造化,移步換形。”是說由于邊走邊看,不斷變換立足點和觀察點,雁蕩山的形象也因此發生變化。宋代的大文豪、大畫家蘇軾在《題西林壁》的詩中說到他觀察廬山的體會:“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從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視角看山,得到的印象也各不相同。然而,即使這樣做,也還無法獲得廬山的整體印象:“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就是說,要認識廬山的真面目,不僅要深入山中做面面觀,還要跳出廬山,做鳥瞰式觀察。在山水畫中常見長軸畫卷,對表現對象作全景式展現。如王希孟的長卷《千里江山圖》,畫面千山萬壑爭雄競秀,江河交錯,煙波浩渺,氣勢雄偉壯麗,令人目不暇接。與這種全景式展現相映成趣的是邊角式特寫,畫面上主體景物很少,往往留有大面積空白。這種“計白當黑”的手法,充分拓展了想象空間。可謂以少勝多,以偏賅全,象外有象,余味無窮。如人稱“馬一角”的馬遠,在《寒江獨釣圖》中,只有一葉扁舟及獨坐船頭垂釣的漁翁。船頭低傾,船尾微翹,不穩定的構圖,表現了波濤的洶涌起伏,極具動態感;而大片空白則表現出了煙波的浩渺,又極具空間感,從而強化了“寒江獨釣”的意蘊,可謂“無畫處皆成妙境”。邊角式特寫雖只寫山水一角,卻同樣有氣象萬千的藝術效果。這是因為畫家在構思的時候已然全局在胸,只不過在畫面上沒有表現全局罷了。
動態性。中國傳統繪畫,具有一種動態之美,無論是山水、花鳥還是人物,靜止是相對的,而動態則是絕對的。我們在欣賞的時候,強烈地感受到了那種延續而不間斷的運動過程。這種動態思維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對客觀世界的動態認識。就“宇宙”一詞,中國古代文獻《尸子》說“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來曰宙”,認為宇宙不僅是一個空間概念,還是一個時間概念,是一個運動著的客觀世界。因此,對宇宙的反映不僅要反映它靜止的狀態,還要反映它運動的狀態。動態是個過程,是個時間概念,只有時間的推移才能表現事物的動態變化。就在郭熙強調對山水自然進行空間觀察的時候,他還強調做時間上的動態觀察。他說:“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陰晴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可得不究乎!”
綜合性。藝術設計是一項綜合性的思維創作活動。這種綜合性不僅包括時間、空間、方位、運動方向等方面的綜合,力求完美、準確地反映客觀物體的體貌特征,還要包括創作主體的主觀因素。藝術與科學不同,它不僅求真、求美,還要求善。真善美的綜合才是完美的藝術,才是藝術追求的最高境界。基于此,藝術創作絕非如同“鏡子”那樣純客觀、純理性地反映客觀世界,還要使自己的主觀世界與之融為一體。還是引用郭熙的闡述,他主張山水畫不但要“可行可望”,而且還要“可居可游”。為什么?對欣賞者來說,郭熙認為:“君子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見也。”而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山水畫恰恰可以成為這種精神尋求的代替物。這種精神需要,對創作者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在“飽游飫看”的過程中,苦苦尋求的不正是他的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精神家園嗎?
綜合性并非面面俱到的整合,其中也有選擇取舍,綜合的目的是把事物的最佳處整合表現出來。清代畫家石濤說“搜盡奇峰打草稿”,為什么要搜盡?他又說:“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豐致,有縹緲,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薦靈于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茍非其然,焉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蹲有跳,有潛伏,有沖霄,有崱屴(zè lì山高聳),有磅礴,有嵯峨,有巑岏(cuán wán山高峻),有奇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可見,無論是山川的外部形態,還是本質特征,都不是單一的,而是綜合的,不僅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只有將它們完美地綜合交融,才能“盡其靈而足其神”。
混沌性。混沌是古人想象中天地未開辟以前宇宙模糊一團的狀態,后用以形容模糊隱約的樣子。在中國文化中,“混沌”作為積極的正面意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可以宏觀整體地把握事物,辯證統一地認識事物。在中國神話把時空浩渺、充滿未知的宇宙理解為:“渾天之說:天地如雞卵,卵中之黃白未分,是混沌也。卵中之黃白既分,是開辟也。”這樣,就把難以說清楚的宇宙形象完整地表述出來了。不能不說,在科學意識非常缺乏的遠古,我們的先人對宇宙世界的具體分析和認識也是不準確的,但從整體宏觀把握上無疑是正確的。更可貴的是,這種原始的混沌思維最終形成了中國文化的辯證思維方式,造就了獨特的創造思維和審美體系。
“混沌”與“模糊”詞義相近,就是不那么透徹和清楚。《道德經》里面說:“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窈兮冥兮”都是指混沌和模糊的狀態。對這種混沌和模糊的語言描述,著名學者季羨林很是贊賞,他說:“模糊能給人以整體概念和整體印象。這樣一來,每個讀者都有發揮自己想象能力和審美能力完全的自由。”混沌思維常常被用作追求和創造以虛見實、以空見形、以無見有、以靜見動的審美意境上。在中國傳統藝術中所推崇的朦朧之美、含蓄之美、雄渾之美、空靈之美等正是混沌之美。
中國傳統藝術創作的整體意識與古代哲學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是一脈相承的。認為天地是一個整體,萬物是一個整體,人是一個整體,而天地人又是一個整體。無論大小,都是一個整體。因為“物類相同,本標相應”。這種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不僅是認識世界的總鑰匙,而且是反映表現世界的總鑰匙。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意識不僅是一種思維方式,還寄托著中國文化的理想追求和審美情趣。美術中的以大為美、以充實為美,戲劇中的“大團圓”結局,“全聚德”的店名,無不彰顯著這種理想追求和審美情趣。作為當代藝術的組成部分,藝術設計應當充分認知“整體意識”的重要意義。(本文為吉林省教育廳“十一五”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09JYT46)
參考文獻:
1.趙則誠等:《中國歷代文論譯講》,吉林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2.姜耕玉:《藝術辯證法——中國藝術智慧形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均為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講師)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