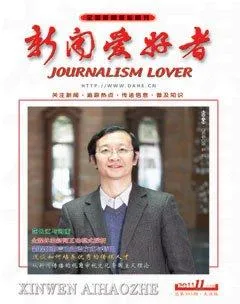《非誠勿擾》中的性別敘事探析
摘要:電視相親節目《非誠勿擾》里蘊涵著一個主角單一、層次明晰、戲劇沖突不斷的故事,一個男人和24個女人的故事,主角是男生,配角是女生。在故事的演繹中,男生擁有最后的選擇權與拒絕權,而女生則只擁有相對有限的拒絕權。看的主體永遠是男性,而被看的客體永遠是女性。
關鍵詞:《非誠勿擾》性別敘事
江蘇衛視的相親節目《非誠勿擾》自2010年1月15日開播以來,影響日甚,長期雄踞周末收視冠軍。據央視索福瑞71城市的收視率統計,《非誠勿擾》的收視率一度達到4.53%,其他電視臺的跟風效顰之作也層出不窮。分析其近兩年以來風行不衰的原因,筆者認為這離不開制作團隊所營造的音效、舞美氛圍等,離不開主持人孟非的睿智博學、口才氣場與現場調度能力以及樂嘉和黃菡的協助,也離不開男女生或業余或半專業的現場表現。筆者擬從性別意識形態的角度分主角與配角、選擇與拒絕、看與被看等三方面來探析該節目中的性別敘事。
主角與配角
所謂敘事就是講故事,人是唯一會講故事的動物,敘事是人類一種獲取生存意義甚至安身立命的本體性需要,故事因此也就成了人類“意義世界的基本成分之一”。①而所謂性別敘事就是從敘事中探究其中的性別意識形態,看其內里到底是男權思想還是女權思想。《非誠勿擾》表面上看是一檔時髦的現代相親節目,其實里邊蘊涵著一個主角單一、層次明晰、戲劇沖突不斷的故事,一個男人和24個女人的故事。與十年前的《玫瑰之約》《非常男女》等節目多對多的復雜混戰風格迥然而異,男生是貫穿整個故事的核心人物和單一主角,而24位女生毫無懸念地淪為配角,在鏡頭時間的優勢分配上再奪目的女生也無法望男生之項背。
《非誠勿擾》中故事演繹的幾個階段是:序曲是主持人和女生的亮相。敘事發生階段是男生的上場,敘述契機就是男生上臺自我介紹完后的心動女生選擇。敘事發展階段是隨后人為設置各種矛盾與沖突的“愛之初體驗”、“愛之再判斷”和“愛之終決選”等敘述環節。敘事高潮階段是一個男生與三位(或兩位)女生面對面地溝通、交流并最后抉擇,男生可能一往情深地“一根筋到底”,也可能審時度勢地“移情別戀”。敘事結束是男性主角(或牽手或空手)離開時與眾人的告別。尾聲則是男性主角或一人或與牽手成功的女生兩人一起(失敗或幸福)的感言。
結局不管是喜劇還是悲劇、是神奇還是平淡,都是圍繞男嘉賓展開的。如果男生被女生中途全部熄燈而獨自一人黯然退場,那就是一個中斷了的故事,原因自然是男生實力不夠或表現不佳。而最瀟灑的結局是男生最后把三位(兩位)女生請上場,經過交流對話后說全部不滿意,鞠一個躬然后獨自離開,把女生們尷尬地留在臺上,如第114期的3號男生安田博士和第131期的3號男生郎波。觀眾則在或驚奇或扼腕的情緒狀態中觀看這么一個男性主角一上場就有多種發展可能性,然后不斷現實化、具體化的故事。
在節目現場的空間布局上也可見出男女生的主次和中心邊緣的區別來。現場的空間布局其實是一個扇形,24位女生均勻分布在扇沿上,而男生和主持人則站在扇軸軸心上,被24位女生和觀眾層層環繞,從而自然成為全場的聚焦點,他們在視線上也就能輕而易舉控制全場。這種女生處在邊緣(扇沿)男生站在中心(扇軸軸心)的布局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男主女次的角色分配與性別差異色彩來。
如果說心動女生環節與愛之初體驗環節主要還是以貌取人的話,那隨后的三段VCR其實是對男生社會地位、人際關系、受教育程度、薪水財產和感情經歷等社會實力的展示。最后有個環節是男生就女生的十項基本資料任選一項提問,這十項基本資料幾乎全是男權社會對女性依附角色如賢妻良母、賢內助等的要求與規范,如三圍、婚戀史、消費觀、是否愿意和父母同住、是否愿意生孩子等。對男生的要求主要還是社會屬性的物質保障為主,權責對等,這也符合幾千年來男權社會的性別角色分配。
選擇與拒絕
其實從故事一開始的男生出場及最后男生牽手一位女生離開就已經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男生應該主動選擇、爭取,女生應該被動等待、拒絕等傳統的性別意識形態理念。比較一下男女嘉賓出場的背景音樂,《Can You Feel It》明顯比《Girlfriend》要更具有雄性沖鋒陷陣的征服色彩與陽剛意味。而在其后的故事演繹中,男生也是主動來表現與征服,而女生基本上就是安靜地站在那里等待被審視與被挑選。
有人會說這其實是一個雙向選擇的互動過程,再說女生還有特權呢!雙向互動與選擇當然沒有錯,但是在節目中選擇的主動權始終在男生手中,女生只有被動拒絕的權利。如果一個女生對男生中意并留燈到最后,她有可能還沒有上臺就被男生滅燈,毫無主動爭取之可能。而即使僥幸上臺了,她還是只有1/3(或1/2)的機會。也就是說,女生要想與自己所中意的上場男生配對成功,自己只有“從一而終”,堅持留燈到最后才有1/24的可能性,如果自己開始不小心把燈滅了就不能再后悔了。而男生可以不“從一而終”,他可以在心動女生和其他亮燈的女生間隨意選擇,或者最后獨自離開,當初的心動女生選擇并不對他的最終牽手結果產生決定性影響。
而就拒絕的權利來說,男女生也是不對等的,特別表現在男生與心動女生的選擇上。男生在權利反轉后對女生拒絕的有效性是絕對的、一次性的,女生再不情愿也沒有辦法。但是,心動女生拒絕的有效性是成問題的,因為只要男生能夠堅持闖過三關進入權利反轉階段,心動女生就會被再次請上臺去,接受一個已經通過滅燈對其釋放了拒絕信號的男生的最后糾纏,即回答男生問題與傾聽最后表白。就已有節目的大致結果來說,90%以上的心動女生一般都是再次拒絕,但還是有百分之幾的男生可能咸魚翻生。也就是說,心動女生的拒絕要兩次才生效,相比之下男生的拒絕權則是斬釘截鐵的。總之,男生擁有最后的拒絕權、選擇權與拍板權,而相對來說女生則沒有主動選擇權,而只擁有相對有限的拒絕權,這種選擇權與拒絕權方面的性別不平等與不平衡是非常明顯的。
再說概率。24個女生之間其實是一種鉤心斗角、爭奇斗艷的競爭關系,而一個男生一上臺就有24位女生在等他。就成功的概率而言,男女之間相差太懸殊,男生有24種可能,也就是24次機會,而女生呢,事實上一個女生一場就牽手成功的概率只有1/24。
1個男人和24個女人,表面上看是女生多,人多勢眾的樣子。其實從文化符號學來看,文明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女性取代男性而標出”,男生是正項,是強勢方、本色方,女生是異項,是弱勢方、是妝飾方、標出方,女生的濃妝艷抹和伶牙俐齒都是一種“標出性”表現。正如拉康所言:“女性通過化妝,成為把‘無’的真實裝飾在身上的存在。”②女生的刁鉆古怪、尖酸刻薄甚至群起而攻之一般也不會破壞男強女弱的文化心理平衡。
看與被看
從精神分析學看來,影視文化正是利用了人類與生俱來的窺淫癖本能才在當代大眾傳媒中大行其道的。而電視因其是在更加私人化的空間中近距離地觀看在特寫比例上最接近真人的表演以及各種私密情感的暴露,故被譽為“所有大眾傳媒中最有窺淫癖的一種”。③但在一個由性別不平等和不平衡所安排的社會里,看的主體永遠是男性,而被看的客體永遠是女性,一如穆爾維所言:“看的快感分裂為主動的/男性和被動的/女性。”④男性把自己的欲望和幻想投射到女性身體上,女性則被迫客體化,不斷指稱男性的欲望,竭力迎合男人的視線。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性別是指文化性別和社會性別(gender),而非僅指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性別和生理性別(sex),那些沒有性別意識和主體性的女性之看,其實是在已經內化與自然化了的男性思維主導下之男性觀看。
這在《非誠勿擾》中也不可能例外。隨著主持人孟非說:“有請今晚24位美麗的單身女生”,女生的“被看”就正式開始了。如果主辦方讓姐妹同臺或讓“高矮胖瘦”站一塊兒還可以說是為環肥燕瘦的視覺效果而采取的差異化策略,那有段時間讓母女齊上陣則純粹是一個噱頭了。反過來如果臺上站著24位男士,那應該是一個女權色彩濃厚的節目,但其可看性就要大打折扣。因為在男權社會里女性生來是被看的,不管是從性別意識形態還是從其背后的理論支撐——精神結構來看,“男性人物不能承擔性對象化的負荷”⑤,若要男性來替代女性成為被看的角色的話,我們只能說這種探索精神難能可貴,形式也新穎別致,但結局會以觀眾的逐漸流失和收視率的大幅滑坡而收場。
表面上看是24位女生同時觀看與審視一位男生,其實她們在看的同時更是在被看。面向她們而站的男生、面向她們而坐的現場觀眾以及面向她們而設的替代電視觀眾觀看的鏡頭等都是凝視她們的“眼睛”,而這些決定了整個節目的性質、形態與接受程度。同時24位女生的相對穩定也給了觀眾相對持久而愉悅地觀看與窺視的機會。當初的敘述契機即男生“心動女生”的選擇,其結果只有主持人、男生和電視觀眾知曉,24位女生則毫不知情,這種信息的不對稱很大程度上已經無聲無息地把電視觀眾置于一個雙重窺視者的位置上了,這不但增強了觀眾與男性主角的角色認同感,而且無形中又增加了電視觀眾的心理優越感和窺視快感。
節目的獎勵規定是男嘉賓在第一輪亮相獲得22盞及以上的燈亮著,牽手女嘉賓離開之后都將獲得一次夏威夷的浪漫之旅。這是節目對符合社會規范與期待的優秀男生的一種獎勵,之所以不說是女生,是因為所獎勵的女生對象具有非特指性,即不確定性甚至隨意性。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使女生處于一種無名的客體地位和被看狀態。而從性別比例來說,臺上孟非、樂嘉和男生共3男與24女,這也基本取得了性別比例的象征性平衡。一個男人對七、八個女人就是封建社會的性別比例平衡之要求,所以古代衡量成功男人的一項標準就是看他是否擁有“三妻四妾”。而在中國數文化中,七往往是和女性聯系在一起的命運之數,是“女性王國里的陽數”。⑥
至此,我們主要從主角與配角、選擇與拒絕、看與被看等三方面就《非誠勿擾》的性別意識形態進行了具體而微的分析與探討。該節目雖然表面上有著某種似是而非的女權色彩與女性話語權,但內里卻有著相當濃厚且根深蒂固的男權思想。其實只要我們運用相關的理論工具深入剖析,就能發現大眾文化在娛樂化外衣下必然隱藏的意識形態內容,進而挑戰和顛覆大眾的常識,幫助人們弄清楚那些習以為常和天經地義的文化現象背后之權力真相與利益關聯,使其明白“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⑦,最終為理性商談意義上的公共文化空間之培育和建構提供某種理論上的方向性說明。
注 釋:
①高小康:《人與故事》,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頁。
②趙毅衡:《文化符號學中的“標出性”》,《文藝理論研究》,2008(3)。
③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頁。
④⑤勞拉·穆爾維:《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載吳瓊編《凝視的快感——電影文本的精神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頁,第9頁。
⑥吳慧穎:《中國數文化》,岳麓書社,1995年版,第76頁。
⑦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頁。
(作者為嘉應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