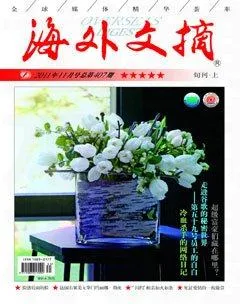傾聽大自然的聲音
最近,我的世界異常喧囂。這是因為,我2歲的兒子伊斯拉發現了噪聲。
“飛機,飛機,飛機……”他用手指著天空不停地叫,直到我重復一句“飛機”他才停。“汽車!”我給他講故事時,他打斷我,轉身跑向窗戶,一輛沃爾沃旅行車隨即疾馳而過。“電話,電話,電話……”當我們在超市購物時,聽到手機鈴聲大作他就一直喊。
通常情況下,我都會自動回避或關掉那些聲音,這是幫助我在充滿令人不快的刺耳噪聲中生活的一種生存機制,但現在,因為伊斯拉把它們特別指出來,令我十分渴望安靜。
我不是惟一有這種感受的人。戈登·漢普頓是一位聲音生態學家,為了記錄自然界的聲音他走遍了世界,他向我們發出警告說:自然界的寂靜正在滅絕。“在過去30年里,我發現美國境內幾乎沒有超過15分鐘的無噪聲干擾的背景音。”近日,漢普頓先生在接受電臺采訪時說。
又過了幾周,伊斯拉開始識別聲音。我妹妹說她要過來看望我們,并想和我們一起去遠足。“只要找個安靜的地方就行!”我告訴她。我們決定去麥克道爾溪瀑布,它離我們位于俄勒岡州尤金市的家只有一小時的車程。我們離開5號州際公路,轉入一條鄉村小路。農舍漸小,道路漸窄,道格拉斯樅樹、西部鐵杉和苔蘚覆蓋的大葉楓樹遍布四周。一條小溪在我們的右側潺潺流動,我幾乎體驗到了寂靜。
漢普頓所講的自然的寂靜,不是指沒有一點聲音的死寂,而是說沒有人類制造的聲響。自然的寂靜可以有很大的響聲,當人們去俄勒岡州海岸的雨林探險時,或許能聽到一聲高亢的麋鹿嘶鳴把整個清晨驚醒,便是一個好例證。
妹妹停好車,我背上兒子,我們走過一座橋,攀爬一座小山。妹妹不時停下腳步,給大樹莓、蝸牛拍照,我則閉上眼睛,聆聽瀑布的喧響、鳥兒的啁啾、小動物在灌木叢中蹦蹦跳跳地奔跑。
“大卡車!”伊斯拉尖叫,一輛采伐木材的大卡車正轟隆隆地駛過小路。
回到尤金市家里,我打開故鄉科羅拉多州的網頁。在讀大學之前,我一直住在科羅拉多的一個小山村,那里非常安靜,尤其是晚上,大部分的人家一到9點就熄燈睡覺。小村離最近的公路有1英里遠,夜晚幾乎沒有車輛經過。
我開始計劃回家鄉:晚上我要坐在屋子外看星星——只有我、蟋蟀和偶爾吠叫的狗。我打電話給父母,說我們馬上要回老家,如果我們繼續留在城市里就得考慮帶上耳塞生活了。
“我原以為你離開家鄉是不喜歡它太安靜。”媽媽說。我回想起在上丹佛大學前,我在家鄉度過的最后一個夏天。當時,我是多么渴望喧囂繁華的生活,隨人流擠上電車,一直開往最熱鬧的第16大街,穿梭在擁擠的城市人行道上,在紅石公園的搖滾音樂會上一起吶喊。“還記得嗎,你以前常抱怨這里是多么無聊,所有人一到9點就上床睡覺了,怎么……”我打斷媽媽,告訴她現在我的夢想就是每晚9點睡覺。
戈登·漢普頓在奧林匹克國家公園的荒地給人們上傾聽大自然聲音的課程,他說,在開始時很困難,許多學生都聽不見多少自然的聲音,直到兩三天之后情況才會好轉。有一位年長的女士甚至以為自己失聰了。后來她意識到,不是她失去了聽力,而是她喪失了傾聽的能力。我想,伊斯拉正在教我相同的事情。“樹葉!”當我們在家附近散步時,他用手指著樹說。在我們的頭上,樺樹葉正在枝條上輕歌曼舞,可它們輕柔的“沙沙”聲卻被經過的汽車聲音給淹沒了。我把臉轉回來,用心傾聽大自然的聲音。
[譯自國外英文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