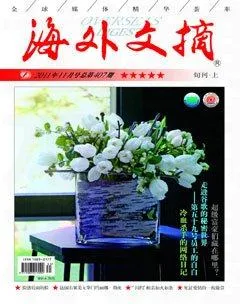情系藍天
帕特·皮爾斯用無比冰冷的眼神狠狠瞪了我一下,身體前傾,用食指沖我一點,輕聲說:“你再敢那么做,小心我給你點顏色看看。”老實說,我的確被嚇住了,即使真在3萬英尺高空的波音747上,我恐怕也會沖向緊急出口落荒而逃。好在我們是在陸地上,這位67歲、風采依舊的空乘元老只是在向我演示她的招牌“眼神”,如果哪個好色的男乘客膽敢把手貼近帕特的臀部,她蛇發女妖般的瞪眼毫無疑問將立即起到震懾作用。
“這種事不會經常發生,但總會有些個醉漢認為那么做很好玩兒”,帕特說,“那種‘眼神’就能阻止其再犯。面對這種待遇,有時他們會罵人,但更多的時候,他們會道歉。當我們履行職責時,我們不能容忍任何胡來。”
空中乘務員、空服人員、機艙乘務員、空姐——不管你怎么叫她們,過去70多年以來,她們為蔚藍晴空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
近日,在倫敦南岸區舉行的“懷舊節”上演了一場空姐制服秀,展示了英國航空公司女性機組人員在過去幾十年穿過的400多套制服,從上世紀40年代軍服風格灰色精紡毛料的制服到70年代撩人的短裙,讓在場所有男觀眾脈搏加速。此次演出更讓人洞察空姐生活發生的巨變。保羅·賈維斯是英航文物收藏博物館館長,他說,“二戰以前,空服行業是一個男性主導的行業。直到二戰男人都去參軍打仗,擁有護理資格的女性才于1943年被允許在飛機上工作。”
整個20世紀50年代,機艙乘務員多以男性為主。直到60年代早期,在女權主義第一波浪潮中,年輕女性才批量走入機艙、飛上藍天。帕特·皮爾斯加入英航的前身英國海外航空公司時才24歲,她說:“當我在1966年加入時,女性在職場的選擇不是很多,除了從事護士或秘書。我的家在希思羅機場附近,我常常看到飛機起降,我從9歲起就想成為一名空姐。我第一筆工資是每月43英鎊,那在當時是很多錢了,但男空服依然比我們掙得多得多。男空服可以結婚生子,但女空服不能結婚,也不能有孩子。我們只被允許工作10年,或工作到36歲,哪個先到以哪個為準。公司認為,女性過了36歲,年齡就太大了,然而只要男性愿意,他們可以一直干下去。在今天看來,這項規定一定令人震驚,但當時我們沒人敢挑戰。”
上世紀60年代,為期6周的培訓課程向空姐傳授多項技能,包括急救、機上安全、調制雞尾酒,以及如何化妝。“那時,坐飛機可是很光鮮的事,它只屬于富人和名人”,帕特說,“不像今天,坐頭等艙的乘客可以穿著帶洞的牛仔褲。那時,男性穿西服,女性穿套裝并戴珠寶。飛機上沒有盛在塑料托盤中做好的食物。我們過去可是在飛機上切肉,從水晶瓶中倒酒。我們至少要記住10種雞尾酒的配方,我討厭乘客要我做一杯‘曼哈頓’或‘馬爹利’,因為我總記不住該怎么做。謝天謝地,大多數人只點雪利酒或威士忌。”
對于儀表,過去有嚴格的規定,現在仍有。“我們的身高必須超過5英尺4英寸(現在的標準是5英尺2英寸),身材苗條,頭發不能長過衣領。我們只被允許穿幾種顏色的服裝,主要是紅色、粉色和中性色。我們還要上禮儀課,老師教我們如何穿著緊身套裙在機艙過道里端莊地走路。每次上機之前,乘務長都要確保我們的發型得體,確保我們化了足夠的妝。她甚至檢查我們長襪后的線是否是直的。空姐現在的表現放在過去肯定不達標。”
如果不是因為上世紀70年代有關平等工作機會的立法,帕特的職業生涯將劃上句號。該立法不僅給予女性同工同酬,而且允許女性得到提升。帕特是首批女性乘務長中的一員,該職位是某些航線上級別最高的機艙乘務員。“我記得只遇到過一次性別歧視。當一名男性機組成員發現由我負責時,他冒了一句‘我的老天’”,帕特回憶說,“我對他說,‘如果你對此不爽,那就請你現在下去。’”
“作為負責整個機組的首批女性,我們不得不更加努力,因為我們不想讓追隨我們的姑娘們失望。如果我們不適合做這份職業,管理層不會讓其他女性繼續做的。現在,許多女性不僅管理機組人員,而且五六十歲還在工作,我就是在2005年63歲時退休的。”
雖然空姐的職責正發生變化,但公眾對她們的看法需要時間來改變。當55歲的喬·玲于1978年加入英航時,她只有22歲。“那時,女權主義還沒有興起,我們經常忍受歧視性的行為,這些行為要是放到現在絕不被允許。男性乘客永遠叫我們‘親愛的’,我們只能當沒聽見,繼續完成份內的工作。現在回看當初那些制服時,我對裙邊如此之高感到詫異,但在那時我們都覺得很正常。我記得穿過一身淺藍色制服,拉鏈從下一直拉到前胸,拉鏈頭上還帶了一個環兒,乘客們總想去抓那個環兒,解我們的衣服。”
49歲的莫拉格·奧西1988年加入英航時只有26歲。除了常規禮儀和安全培訓,以及一本如何對付“危險乘客”的行為準則以外,她回憶說,文化差異在她接受的培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飛沙特的航線時,我們不能露肩或穿超短裙,因為那樣是不敬。加入英航之前,我效力于英國金獅航空公司,如果是飛穆斯林的國家,我們要取下制服上劍型的別針,因為它被認為像一個十字架。”
《平等機會法案》被通過后,空姐被允許結婚生子。然而,一邊當母親,一邊做空姐依然很難,由于職業的需要,空姐通常一次要離家數天。莫拉格說:“當我女兒1993年出生時,我請了6個月的產假。但那時還不允許兼職做空姐,所以產假一結束我不得不全職工作。”
到1997年喬·玲生兒子杰克時,這一情況發生了改變。需要帶孩子的空姐可以選擇利用30%、50%或75%的時間兼職繼續做。“這給予我們更多的自由,但即便如此,我還是無法忍受離開我寶貝的想法。如果他病了,而我又在千里之外,我實在難以招架,所以我辭了職,到另一家航空公司做地勤。一旦你做過空姐,它就融入了你的血液,沒有其他職業能像這個行業那樣吸引人。”
如今,英航雇傭的機艙乘務員達到1.4萬人(其中2/3是女性),服務于英航240架飛機上。他們的平均年薪是3萬英鎊;母親被允許兼職工作,或申請在照顧孩子以外的時間飛航線;男女雇員的退休年齡都是65歲。
“這是一個很棒的職業,當我第一次穿上制服時,我驕傲地幾乎哭起來。”41歲的特雷西·博爾頓說道,她于2010年加入英航。39歲的麗貝卡·沃茲沃思1994年加入英航。兩人均已結婚,但都沒有孩子。盡管她們都被要求化妝,但她們都未曾經歷過性別歧視。當我問麗貝卡有沒有遇到過“色狼”時,這位5英尺10英寸、身材修長的金發女郎笑了起來。“我干這行17年,臀部從未被別人碰過!”
這確實是不小的進步。
[譯自英國《每日郵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