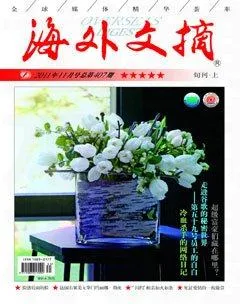我成了“坐牢”專業戶
2011-12-29 00:00:00法布里奇奧.梅西亞欣哲
海外文摘
2011年11期
我本是一個安分的作家,如今,我落入了監牢。
在我痛訴我的入獄經歷前,我想先做一個客觀的說明:墨西哥的司法就好比至高無上的信仰、就像宣揚教義的禮堂、末日審判的再現,但能證明你清白的不是證據和證詞,而是鈔票。
我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這個家庭就只信奉因果報應,不相信壞人的存在。大家都認為如果你做好事的話,什么壞事也不會發生在你身上,我的家人從不與人為敵,把一切惡事都歸咎于經濟、無知、年少、卑鄙或是厄運。
1998年,一件糟糕的事情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一個憂郁的作家,他準備以實地調查的方式寫一本揭穿恰帕斯游擊隊員真面目的書。這支把爭取“土地與自由”作為行動口號的農民武裝隊伍,自1994年1月發動武裝暴動以來,與政府軍沖突不斷。這個憂郁作家的行為明顯是為了迎合當時政府。我很氣憤。
6個月后,憂郁作家寫成了這本書并且出版。慶祝聚餐時,一些采訪游擊隊員的專家團——他們是墨西哥政治謎案的英勇衛士,其中3人把這本虛假的關于薩帕塔主義的“歷史書”撕個粉碎。 但那位憂郁的作家卻認定這是我的主張,因為我說這是一本專為政治量身訂做的書,而告我誹謗罪。
我的罪行得遵照墨西哥司法部門的處理:在進入法庭前,我必須赤身裸體地面對一位醫生,警察在我身上拳打腳踢的印記也已經消失,醫生還不懷好意地上下打量著我。
法庭上,我遞給法官一本我自己的小說,希望他能理解、幫助我,可他把書扔掉,就像丟手榴彈一樣,生怕我會與他同歸于盡。……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