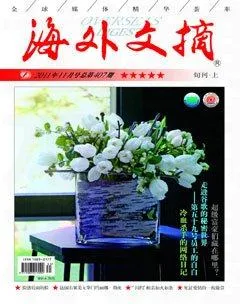人生如戲
幾天前我去一家咖啡館喝咖啡,在一旁收拾桌子的女招待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大概十幾歲,一雙美麗的眼睛帶著笑意,周身散發著青春活力。她告訴我打工是為了積攢大學學費。
就在我們聊天的工夫,她偶爾望了一下窗外,先是變得目瞪口呆,繼而臉色迅速陰沉下來。難道是看見了外星人?我好奇地也扭頭朝外望去,原來發生了比外星人光臨地球更能讓一個女招待驚恐的事情——咖啡店外的停車場上剛到達了一輛旅游大巴。
一整車客人涌進店里對女招待是個巨大挑戰,哪怕經驗豐富的女招待也很難面對,更何況我面前的這個小丫頭。我想提醒她,接下來的一小時對她來說將是場嚴酷的考驗。你必須跟廚師協調好,讓他也有心理準備。當整個巴士的游客魚貫而入以后,就像用漁網撈到了一網的魚雷,觸碰哪一個結果都會比較慘痛。
看窗外那些正依次下車的游客我都能想象得到,他們將會如何地難伺候:很有可能你要半盤沙拉,他要半包薯條。有的人會點一個草莓圣代卻要求添加發泡鮮奶而不要普通冰激凌球,只有等有人點了奶昔才能幫她解決這個問題。總而言之,場面會是一團糟。
我的推斷依據是什么呢?因為我也曾是個女招待,還是一個干了13年的女招待。
我16歲時,家附近的一間餐館要招女招待,我被聘用了。作為家里6個孩子中的老大,我早就習慣了給大家端盤子遞水,一想到這樣做還能有薪水拿,我高興得直想叫出來,而且還能拿到小費呢。說到小費,我祖母一直認為收小費的女人只有妓女。我可不這樣想,我覺得自己跟她們惟一的相同點就是都在夜晚工作——我每天要從下午5點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點。
客人們總是恨不得你能飛起來,老板也見不得你插著手在一旁悠哉的樣子。回首往事,我很感謝自己那段當女招待的經歷,那段經歷不僅造就了我樂觀的性格,更重要的是鍛煉了我的“演技”。
我當女招待的時候,人們給小費遠沒有今天這樣自覺,我必須非常努力才能得到小費。我工作的時段剛好是酒吧關門,酒鬼上門的時間。坦白說我太討厭他們了,這些人不是打翻調料瓶,就是把糖粒什么的灑得到處都是,而且永遠沒有歉疚還不給小費。喜歡表演的我常苦中作樂地把自己想象成外國來的移民,我逐漸變得潑辣起來,還嚼上了口香糖。
離開那家餐館以后,我去了加拿大西部,在一家湖邊酒店里當女招待。我突發奇想開始模仿英國口音,我發現只要你操著一口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區的口音,說什么別人都能相信。我就曾告訴許多日本游客:“是的,這里的山重50萬噸,湖中有1300萬加侖的水。”他們高興地與我合影,把日元放在我的圍裙里。正是這些小費幫助我還清了助學貸款。
當我搬到多倫多去尋找當演員的機會時,當然我的正式工作還是女招待。因為女招待的工作能讓我有時間去試鏡,那期間我工作過的餐館遠多于接到的演出。
我曾在一間酒吧工作,那里有顧客問過我:“這只蟑螂在湯里做什么?”作為一個喜劇演員加資深女招待,還有比這種問題更好面對的嗎?我微笑地回答:“它在仰泳。”后來我又在一間素食餐館里工作,我發現哭是顧客比較喜歡的。為了討好客人、表達自己對動物之死的深切痛苦,我練就了說哭就能哭的本領。接著我去了一家藍調音樂咖啡館,我要伴隨著這種令我肅然起敬的音樂工作到凌晨4點。我開始抽法國香煙,跟玩各種樂器的音樂人約會。后來我在一家英國連鎖酒店練就了一口倫敦東區口音。當遇到客人把我高高舉起,試圖猜我有多重的情形時,我就用這種正宗的倫敦音平靜地說:“好吧,伙計,再不把我放下來,你的腰子餡餅就要涼了。”
在家里,我要服侍家人,在社會,我的身份是女招待。就這樣直到29歲那一年,我終于不用依靠當女招待的錢來過活,解下圍裙成為了一名全職演員。可我接到的第一個角色就是女招待!
對于如何當好一個女招待,如何從自己的每份工作中受益,有很多心得我本來可以跟面前這個小女孩分享。但是女招待的成長史就像女人分娩的過程,只得自己細細體味。于是我坐在一旁,看她如何應對挑戰。
當客人三次改變餐單,她仍微笑著面對他們,并問他們旅途中有哪些見聞;當他們抱怨天冷胃痛的時候,她把清湯加熱到恰到好處的溫度;她傾聽他們的笑話并大笑,雖然那些笑話其實很無聊;她不厭其煩地幫他們分餐和找零錢。女孩全程對這些游客都顯得彬彬有禮,面對任何要求都不曾面帶不悅。
女孩的表現出乎我的意料,我欣賞地看著她的一舉一動,為她的演技所折服。我放下一張20美元的鈔票,用最擅長的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區口音說:“干得好,親愛的,干得好!”人生如戲,需要我們全身心地去演繹每一個細節,世上不應該有擺著撲克臉的女招待,只有不肯努力鉆研、吝于付出的蹩腳演員,你說不是嗎?
[譯自國外英文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