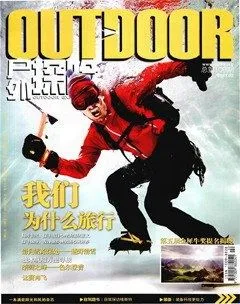療傷的起點
2011-12-29 00:00:00語冰
戶外探險 2011年2期

語冰 曾旅居加拿大。
不是我想否認我的過去。療傷曾經對我那么重要,幾乎就是我出行戶外和四處游走的全部理由。但是就像登山的人費盡力氣歷經周折終于到達山頂,展現在他面前的是他沒有預想到的開闊和空曠,是將世間萬物盡收眼底的大氣,是渾然一體的天和地,是無邊無際的純粹和豪情萬丈的俊美。他本來以為在爬山的時候流了那么多汗,跨越了一次又一次極限,他已經磨礪和洗滌了自己日趨沉重的身體他沒有想到最終真正得到洗滌和提升的是他的整個生命和整個靈魂;
對我來說就是這樣,戶外和旅行已經成為我生命的終極意義,成為我比所謂的日常生活百倍重要的生活方式,成為我的愛情,成為我之所以成為我。“療傷”是我的起點。但我已經超越了這起點。再讀到自己過去曾經對“療傷”反復回味的文字,就像看到過于自戀的人反復對人訴說自己遭受過的痛苦不使人同情,卻令人避而遠之。我必須刪除那個章節,因為那以后我已經找回真正的自我,脫胎換骨,煥然一新。再保留那樣的呻吟文字,就對不起我和戶外之間無需要言語不會有傷害永遠新鮮永不變心的愛情。
我不想否認我的過去。我忘不了我的戶外經歷的起點。我忘不了那時候我處于怎樣的絕望的深淵里。是偶然的一次登山活動拯救了我。
現在看來,深淵可以并非深淵,一切全取決于自己的心。但那時置身其中,痛苦卻是實實在在的。這痛苦的來源和大多數人沒有兩樣。便是我以為世界上最愛我的那個人,那個會愛我一輩子的人愛上了別人,不再愛我了。而我卻不肯相信那是事實。我不肯相信我曾經那樣全心全意把自己生命的所有都投入其中連自我都忘卻了的感情真的走到了盡頭。自從進人那段我以為可以托付終生的感情。我忘了那個青春期時在詩歌里流連忘返的我,我忘了那個廢寢忘食閱讀的我,我忘了那個少年時就曾經被森林之靜美震撼的我。俗世的歲月一日和一日沒有分別。我也就陶醉和沉浸在瑣碎和庸碌的光陰里因為覺得自己已經找到港灣一就并不覺得被丟失的自我有什么可惜,可是港灣原來并非港灣,而只是一座被風一吹就消失無形的沙丘,這時的我驚慌失措全然不知該如何應對。感情已經成為我的一切,我忘了這感情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樣子,我更不記得付出這感情的自我本來是什么樣子。我徹底失去了安全感,以為沒有了這感情我就沒有了一切。
這種狀況持續了多久?我不能準確記得。或許一年,兩年,或許長得就像八年抗戰那么艱苦。時間的長度畢竟是由心靈的感受來決定的。總之在遙遙無期的谷底的跋涉中我偶然認識了一個新朋友,他鼓勵我和他,還有別的一些新朋友去爬溫哥華郊外的一座名叫“shannon fall”的小山。
我至今忘不了我爬到半山腰時看到的陽光下一粒一粒飛舞的潔白的雪子。我更忘不了當我爬到山頂時撲入我眼底的景象。就像人們忘不了他們的初戀。
我幾乎不能呼吸。是震撼,是喜悅,是突如其來的沖擊,是君臨天下的豪邁,是久違的親切,是融化的快感。是河流山巒,公路,船只。是每一片粼粼的波光里我的倒影,是視線盡頭的冰山頂上陽光撞擊冰柱時清脆一響。我原來竟是這樣無與倫比的富有和博大。
這是那時候我站在山頂低頭四顧時的感受,也是這么多年以后依然歷歷在目對我來說如此清晰從未褪色的感受。后來我一次又一次登頂,一次又一次被相似的情懷充盈心胸。但我從來沒有覺得厭倦。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那樣給我帶來發自心底的感動和歡喜。
我想那一刻我已預感到今后的歲月里戶外將怎樣深刻契入我的內心,有形的并非時時在眼前的風景將怎樣化作無形卻無所不在的精神融進我的血脈里。那一次其實郊游般輕松的登山活動在我面前打開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世界和我從前沉浸其中的那個昏暗,閉塞狹隘,頹廢的世界截然不同。這個世界同時又讓我感到莫名的親切,好像它本來就屬于我,只是我離開它太久幾乎忘了它的存在。我想那一刻我骨子里一種一直在冬眠的情結蘇醒了過來。
那發登山以后我迅速變成了一個如癡如醉的戶外迷。整整一年的時間里我沒有錯過任何一個周末。走出我自己那個狹小暗淡的天地我才知道溫哥華的山山水水有多美。那是天地間的大美——世上最自然最質樸最豐富最單純的美,那是人類的易于被分離,猜疑,嫉妒爭執所傷害的感情所不能比擬的心心相印無怨無悔的大愛和真情。
如今我和那片山水遠隔萬里,卻從來不曾覺得自己離開過,那片山水是我的家園,就像此時此刻我腳下這片同樣美麗的山水也是我的家園。我不會忘記sunset trall上穿過森林那片飄著潔白枯木的靜謐小湖。我不會忘記pitts lake上萬飄蕩的仙境般的淡淡霧靄。我不會忘記garibardi的皚皚白雪。我當然更不會忘記west coast trall。在那條在大海邊和森林里交替穿行的小徑上我和同伴一起跋涉了七天。那是我永遠無法忘懷的七天。大海始終在我的身邊,就像我是在浪尖上起舞。潮起潮落始終在我身邊 就像深情涌動在我胸口。我心中還有雜念,但是雜念怎么敵得過眼前的無限遼闊。在天地之間,在參天古木的懷里入睡,我睡得前所未有的踏實和深沉。
那時候我已明白,戶外和旅行于我將是只有起點沒有終點的旅程。
必須承認,回國后那一兩年里,戶外和旅行對我而言變成了不折不扣的“療傷”。我一次次去云南那個永遠擁有藍天白云的地方。我去拉薩,在納木錯和羊卓雍錯的岸邊久坐,在清晨的甘丹寺接受金子般的晨光的洗禮。我去奧太娜雪山的山頂,讓體力透支,讓心靈在一望無際的茫茫雪原上沐浴翻滾。我去大西北,在巨龍般盤踞的山脊上被一片蒼黃中幾抹春天的新綠打動。我去跑馬溜溜的康定,再一次證明高原之美是世界上最令我動容的美。一旦我出去,我就不再是世俗生活中那個瞻前顧后藕斷絲連的我,我就把一切現實的顧慮和瑣碎的糾結全部拋在腦后。那個我是干凈的。然而回到家中我的記行文字中卻常常不日自主地出現傷感和無奈的調子。這讓我漸漸覺得羞愧。明明在戶外的時候我的心靈那么純凈而爽朗。明明在戶外的時候我完全不記得我有什么傷口。為什么我還念念不忘舔傷?我后來才明白,那時候所謂的“療傷”其實是一場曠日持久的爭奪。是天性和惰性的爭奪,是熱愛和習慣的爭奪,是開拓和守舊的爭奪是勇氣和懦弱的爭奪。所謂的爭奪也只是時間問題。異己的,外來的,該從我生命中退場的必然會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