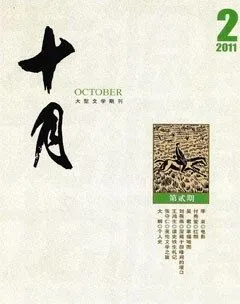讀史鐵生札記
2011-12-29 00:00:00鴻生
十月
2011年2期
“性命攸關的一躍”
那一年,《務虛筆記》問世已兩年了,除了三四篇專業性評論和幾處捎帶提及的文字,它幾乎沒有引起任何社會性激動。就像黑暗中有人投湖,那沉沉的一響,于投湖者是性命攸關的一躍,而在湖水的知覺里,卻和擲入一塊石頭沒什么兩樣。也許,這不值得驚訝。在商業化時代,有多少珍貴可愛的事物、語言和情感正在離我們遠去,我們不是照樣沒有一點兒揪心的感覺嗎?
但事情還是有些蹊蹺。按當年《收獲》的發行量再加上出版社的印數,國內至少有10萬人擁有這部長篇。這些人大多知道史鐵生,大多喜歡和傳誦過短短的《我與地壇》,該是最懂得文學的一類。然而,是什么原因使他們對同一作者嘔心瀝血的40萬言,卻保持了長時間的緘默呢?
“緘默的理由”
曾有仁慈的友人告訴我,鐵生的這部長篇是失敗的,實在讀不下去,真不忍心去說它。也有年輕作家真誠地以為,在一個崇尚行動的年代,這種優雅的形而上冥想已經過時了。而更值得關注的批評似乎可以這樣概括,《務虛筆記》中的“我”只是各種可能世界的發現者,而不是創造者,“我”還沒有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具體存在,一個能動的主體。
我不能否認他人閱讀感受的真實性,也無意與各種私下的或公開的看法進行討論。當伴著料峭春寒,再度沉入《務虛筆記》,又一次呼吸它命若琴弦般的純粹的語言氣息,我只是在想,作為一個文學藝術的探詢者,尤其是作為與史鐵生和他的一系列精神化身(Z、I、F、C等)有著相似經歷的“老三屆”,為什么我也曾是緘默的大多數中的一個?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