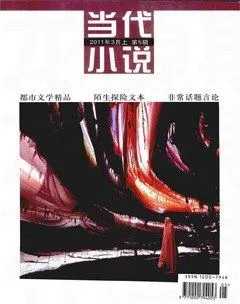到處都是春天的氣息
每當夕陽把堤上的柳樹影子拉得老長時,四叔蹬著三輪車,車上有幾個大水桶,來到村南的豐收河河邊上,把車停下來。四叔提水來了。四叔做豆腐都是來豐收河里提水。
豐收河是黃河的支流,流程長,水活。經過長距離的流淌,沉淀,流到大劉村時,黃河水渾濁的影子不見了,河水一律是澄清的,碧綠的。豐收河的水這么清,四叔卻不用。四叔是在河岸的草層里挖了個坑,用坑里的泉水。四叔做的這個水坑,位置選得好,離河水有三米多,鑿得也深,洞一樣,整個兒都在淤泥上,泉出的水,露水一樣,晶瑩剔透,比現在的純凈水還純凈,還甜著呢。四叔打了個大木蓋子,平時將洞口蓋上,用時揭開,自家的水缸一樣。四叔就用這坑里泉出的水,做豆腐。這樣的水做成的豆腐,細膩,白嫩,筋道,無異味,十六七歲的女孩兒的臉蛋一樣,見了叫人拉不動腿兒。
四叔姓劉,祖祖輩輩住的這個村子又叫大劉村。“劉”“柳”諧音。四叔就給自己做的豆腐起了個好聽的名字,叫“水嫩柳豆腐”。
四叔是個瘸子,左腿少了一截,出門得拄拐。每次來河堤上提水,三輪車停在堤下面,抽出拐,穩穩地拄好了,然后右手提上一只水桶,左手拄著拐,一歪一歪地就上了大堤。
那天下午,娘和我在找我爹的路上。走得很艱辛。走上這條河堤,我就一點也不想走了。我已經咳嗽好幾天了,咳嗽得都快哈不出聲來了,走到這兒,就想死死地在娘的懷里睡上一大覺。我就和娘說:“娘,妮累……”娘就說:“咱就歇歇,娘也累了。”娘說著,看著不遠處的村莊,手捂口打了個哈欠。眼前有一棵粗大的柳樹,粗大的樹根露出地面,板凳樣橫著,娘把我們帶的那個大包袱,順手往地上一丟,倚著這棵柳樹,坐下來,我往娘的懷里一歪,娘緊緊地抱著了我,我立時就像死過去了似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霜降已經到了,可還沒下霜。地里的莊稼收得差不多了;豆子,棒子,谷子人了倉,早茬麥露出了油油的綠。雖然是晴天,陽光在這個季節里沒了威力,娘和我都穿著兩個夾襖。渾身還是冷颼颼的像什么也沒穿。娘朝堤下面的田里望。春紅薯刨了,夏紅薯也長成了,正對著我們的堤下面就有一塊。有幾個人在堤下拾掇著什么,還有一群羊,在這塊紅薯地里啃秧子吃。一陣風吹來,娘把我抱得更緊了。那片紅薯葉子,隨風微微擺動,墨綠墨綠的,很誘人。那么旺盛的秧子,下面的紅薯肯定小不了,娘抱著我想等天擦黑,地里沒人了,路上也沒人了,挖幾塊放著,沒飯時吃。正是因了娘的想法,娘坐在那棵柳樹根上,緊緊地抱著我,等了很久;娘等得可耐心了,盡管娘冷得渾身不住地打顫。太陽終于落下去了,遠處的、近處的一些人,扛著家什,背著糞筐,趕著羊群往家走了,娘來了精神,要站起來去挖紅薯。娘一動,我卻一陣劇烈地咳嗽。娘伸手往我的脖子里一摸,燙熱燙熱的。娘一驚,又摸了摸我的手,也火炭一樣燙。娘馬上把我放松點,摸了摸我的額頭,熱,低下頭,用她的眉頭抵抵我的眉頭,試試溫度,燙,渾身上下都燙人。人也像沒了骨頭,發軟。一陣風吹來,我咳嗽得更厲害了,迷迷糊糊聽到娘在喊我,我想睜開眼睛看看娘,卻怎么也睜不開來。娘慌了,端起我的臉,小聲叫了我幾聲,我仍舊睜不開眼睛看娘,娘怕了,接著一聲高過一聲地叫著我,說:“妮!妮妮!你這是咋啦?!你可別嚇娘……”
天一下子暗了下來。樹葉子從空中飄落,蝴蝶樣飛舞著。堤上沒有人,堤下也沒有人。娘左右看了又看,沒人,還是沒人。娘急了,一股急勁站起來。大包袱扛到肩上,抱起我,尋找著下堤的路,大跑下堤來,往村子的方向跑。當時我已經八歲了,雖然很瘦,也得有幾十斤,娘抱上我,又背著大包袱,跑得趔趔趄趄的。娘跑著,恍恍惚惚看到前面有人。娘像落水的人抓住了稻草一樣,拼命地攆。娘終于攆上了,是輛三輪車,是個大男人騎著,娘就在后面喊:
“大哥,大哥,你別走,俺打聽個事兒。”
三輪車停下了,娘又在后面說:“你是前面村里的嗎?”
“是。”
“村里有衛生室嗎?”
“有。”
“俺妮妮病了……”
其實,四叔早就聽見娘焦急的叫喊聲了,只是四叔是個殘疾人,弄這么一車水走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已經很艱難了;逆風,又聽不清楚娘喊了些什么,只有放慢了腳步。
娘抱著我攆上來,四叔抽動車上的拐,想下來,水桶壓著沒抽動。四叔仍舊坐在三輪車上,不過,四叔把手伸得老長,夠過來摸摸我的額頭,說:“孩子燒得夠狠的!”
四叔說著扶著車把從車上下來,單腿一跳一跳地把車上的水桶都弄下來,說:“走,我帶你娘倆去衛生室!”讓娘和我趕快上車。娘抱著我坐好之后,四叔死力地用那條僅有的右腿蹬三輪。蹬得很瘋。
這輛三輪車,就這樣,第一次載著我們一家,進了大劉村。
后來,雖然我們一家多次坐這輛三輪車,但是,娘說起最多的,還是這第一次。
當時,我年齡小,發著燒,記不得多少,連四叔當時的模樣也記不得,只隱約記得三輪車在大隊衛生室門前停下后,四叔拄著拐,把我從娘的手里接過來抱在懷里的一瞬間:溫暖,厚實,像座山。
我成人以后,也曾經問過娘,上了四叔的三輪車,有啥感覺。娘聽了,臉上的皺紋更多了,更深了,笑了,說:“傻丫頭,能有啥感覺?啥感覺也沒有。你病著,我能有啥感覺?”
我不信。難道娘對未來沒有一點預感么?這輛三輪車,把娘推進大劉村,一住就是一輩子。
我還問過娘:“你剛到四叔家時,害怕不?”
“害怕?”
娘好像愣了一下,把思緒放得很遠,很長,然后,回過一半神來,滿不在意地說:“沒有,好像沒有,誰知道呢,你病那樣,我忘了。”
娘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喜歡心里藏事。不過,娘后來和我說,四叔帶我們娘倆在村衛生室看了病之后,四叔走到哪兒娘就跟到了哪兒。娘說,娘那時候腿上不當家。娘跟著四叔回家的路上,娘低著頭,小聲對四叔說:“我從河南來,帶孩子來山東找她爹。沒想到這孩子咋就……咋就病了……”
四叔說:“別急,給孩子看好了再去找她爹也不遲。孩子的爹在啥地方?”
娘看了看南方,又低頭看了看懷里的我,說:“在zao莊。”
“早上?咋叫早上?沒聽說過這個地兒呀!”四叔問。四叔聽不懂我娘有點蠻的口音。
“我也說不上來,就知道在山東。我包袱里有個字條,上面寫著呢。人家給我說,向東走,一直向東走,看見山,看見煤礦,再看見幾個湖就快到了,得走半月一二十天呢。”
娘說完就攤開包袱,從一堆舊衣裳里挑出一件新衣裳,水紅色的,水麻布料,雖然不舊,卻也折得皺皺巴巴的了。娘從那件新衣裳的內口袋里,掏出一個小小的丫丫葫蘆,上面刻畫著什么。丫丫葫蘆兩個鼓鼓的肚子,像娃娃的兩個臉蛋一樣。丫丫葫蘆的腰里有條紅線,系著個折疊成長方形的舊信封。娘解開紅線,拿出那個舊信封,把丫丫葫蘆放好了,才把舊信封遞給四叔。
四叔接過信封,煞有介事地打開看了看,又倒過來看了看,說:“嗯,嗯,我也不知道這地方。”
其實,是四叔不認識上面的字。后來,四叔在街上找了個識字的人看這信封,才知道是棗莊。
“棗莊啊!你娘倆,路走偏了!”
“大哥,到棗莊還有多遠?”
“棗莊和這兒掉著向呢。少說也得有三百里路吧?”
“大哥,這路咋著走啊?”
“走河堤,往東走。走到一架公路橋,順橋下正南,遇上第一個十字路口再往東走……據說,往東直走就能到棗莊了。”
“大哥沒去過?”
“沒去過。聽人說的。”
四叔看著娘,臉紅了,撓撓頭皮,靦腆地笑了。
四叔接著說:“這樣吧,你娘倆先在我家住著,等孩子的病好了再去棗莊。”
路走偏了,我又病著,三百里路不是個小數,四叔這么一說,娘心里熱騰騰的,忙說:“給大哥添麻煩了。孩子病好了,我們就走。”娘說著掏出些錢來給四叔,四叔說啥也不要,說:“別,別!別說你娘倆在這兒住幾天,就是住上一年兩載的,我也不能要你娘倆的錢呀!”四叔說著撓著頭,躲著娘的目光,靦腆地笑了。我和娘就這樣在四叔家住下了。
我得的是肺炎。時常燒得迷迷糊糊,娘和我在四叔家里住著,好好歹歹,將近一個月才好。我的病好了,天卻說冷就冷了。北風呼呼的,老刮。娘卻要走,執意要走,偷偷給四叔放了點錢。收拾好東西,和在泡豆子的四叔打了聲招呼,抱起我就往外走。四叔的手水啦啦的,在圍裙上擦了擦,看著娘的后背不好說留,也不好說你走吧,就拄著拐跟在我們后面。娘和我出門一股狂風刮來,險些把娘和我刮倒,四叔就上去一把把我從娘的懷里抱了過來,說:“這么大的風,上路。還不得給刮走人么?”
四叔抱著我往家里走,又說:“孩子的病剛有點好,要走,沒風了再走,一樣。”連續說了好幾遍。
后來,風沒停,又下起了雪,娘再也等不得了,收拾好東西,抱起我來又要走,四叔就拄著拐,在門口把娘和我攔住了,有幾分生氣地說:“這么大的雪上路,還不得把孩子凍成冰塊?我又沒攆你!”
我娘扛著包袱,抱著我,在四叔的面前急出了淚水。
四叔就轉著圈圈。心平氣和地說:“不用急。不用急,啥時候能走,你就啥時候走,我不擋你……”
娘終于猶豫了。我大病初愈,天不好,娘心疼我,真不想走;不走,又不知道怎么辦,娘想了想,對四叔說:“大哥,這樣吧,你找人替俺寫封信,讓俺孩她爹來接俺,這樣也就少麻煩你些。”
四叔沒吱聲,拄著拐,耷拉著腦袋開始卷煙,卷好了,點上。吸一口才說:“也好。”
娘就回到屋里,把我放下來,把包袱放在床上,從懷里摸出那個舊信封來遞給四叔,四叔接過去,深吸了一口煙,裹裹身上的棉衣,拄著拐就去找人給爹寫信。
信寫好了,四叔把信拿回家,讓娘看。娘不識字,還是把信攤開看。信很簡短,也就半張信紙的字,字還很大,娘卻看得一笑一顰的。娘看上一陣,說:“大哥,就這樣吧。”把信給四叔,又給了四叔一毛錢,四叔把信仔細地放進上衣兜里,使勁摁了摁,悄悄地把一毛錢塞進我的兜里,然后和娘說:“我去寄信。”推起三輪,一跳一跳地出門,走了。
就這樣,娘和我就在四叔家開始了等待。
那天,四叔從村衛生室把我們娘倆領到他家里,夜已經很深了。風仍舊在刮。四叔從娘的懷里把睡熟的我接過去,安頓在自己的床上,又給娘搬來一個馬扎,娘沒坐四叔搬來的馬扎,借助微弱的煤油燈光。環顧了一下四叔凌亂的屋子,怯生生的。四叔又給娘倒了碗熱水。晃悠了一會兒,吹了一陣子,遞給娘,娘接過來,咕咕咚咚喝下去,不好意思地抬頭看看四叔。一整天了,才咽上水,真好喝。四叔呢,一手拄著拐,一手伸長胳膊,昂著頭,從梁頭上垂下來的木鉤上,摘下一個柳條編的饃饃籃子,湊近燈光看看,喲,只有一個雜面卷子了,三個人,不夠吃的。四叔看著雜面卷子,看看娘,笑了一下。他為自己蒸得歪歪扭扭的,不好意思呢。
“喲,卷子不夠吃的了,咱搟面條喝吧。”
“哎,好吧。”娘跟上四叔,進了廚屋。
廚屋里的燈亮了,娘挽好袖子。找來洗臉盆,洗了洗手,端起面盆,刷了刷,在盆里加了點水,又加了面。開始和面。那時候,白面稀罕,娘搟了白包黑的那種面條。娘先和了一塊白面,放在一邊,醒著,又和了一塊高粱豆子面,娘和著面,一綹頭發從發卡上滑出來,滑到臉上,遮住了光,娘用手背朝一邊撥了撥,接著和面。從娘和那塊白面團時,四叔就看出了娘是個和面的高手。要知道,搟面條,和面講究著呢,人說,七分和三分搟。白面黏,粘手,娘先在盆里放少量的水,加上面后,均勻地攪拌,然后邊加水邊攪拌。和面條面。不能一下子加水太多,那樣和出來的面瓤,搟出來的面條不好喝。要一點點慢慢加水,和出來的面硬,搟出來的面條才好喝。俗話說,瓤面餃子硬面湯(面湯,就是面條),就是這個意思。和面又講究三凈,即手凈,面凈,盆凈,也就是說,面和好了,手是干凈的,不能沾面,和好的面團是干凈的,光滑的,不能坑坑洼洼的,和完面面盆也是干凈的,不能留面。既要用水少,又要做到三凈,這可不容易。娘做到了。娘用她白凈的手拍了拍白凈的面團,又讓面團在盆底里轉了一圈,粘粘落下的面,才拿出來放在一邊。
四叔看看白凈的面團和娘白凈的手,目光爬上了娘的臉。那目光里,包含的是肯定,是贊揚。
接下來,娘要搟面條了。一般的面條也好搟,就是把面團放在面板上,撒上面粉,先來回地揉,一直揉得玻璃球一樣,滑溜溜的,然后用搟面杖,均勻地用勁搟就行了。娘那天搟的可是白包黑的這種。這種面條。先把白面揉好,搟成面餅,估計能包上黑面團的大小,然后再把黑面團放在上面,用白面餅把黑面團包上,再搟。這樣,既要把面餅搟得很薄,又不能露出黑面,如果不是心靈手巧,誰能做到呢?
娘做到了。
那天,四叔也許是餓了,一連喝了三碗面條,又舀上一碗,在灶臺上涼著。四叔打了個嗝。肚子明明飽了。可還是想喝。而且,喝著喝著,就哧哧溜溜地響了,四叔忘了,他可是第一次和娘在一起吃飯呢。四叔有一句話想說,但沒說出來,那就是,他還從來沒喝過那么好喝的面條呢。四叔看著碗里的面條,嘿嘿地笑了。
吃完飯,拐完豆漿,四叔在磨道里攤開了剛軋的碎豆秸,鋪上席,抱來被子。娘從床上抱起我,要去磨道里四叔鋪好的鋪上睡,四叔擋在堂屋門口,不讓娘去。
四叔說:“可不行!孩子這么小,還病著,咋能睡磨道呢?你娘倆就在這堂屋里睡。我一個男人家,睡哪里不一樣?再說,我還要早起做豆腐,睡磨道正好。”
一提起我的病,娘就軟了下來,沒再堅持。
四叔的堂屋是三間呢,娘和我睡東間。是張大床,是四叔正睡著的。西頭的那間雖然沒隔開,卻是空著的,還有一張小床。床上雖然擺滿了雜物,收拾一下也就一小會兒的工夫。四叔沒說睡西間小床,娘也沒讓。就這樣,四叔在磨道里睡了大半個冬天,直到四叔找人壘了間西屋搬了進去,才不睡磨道了。
第二天,天亮了,四叔再去堂屋里時,好像到了別人家一樣,站在當門不敢動腳了。地面掃得干干凈凈,桌子擦得一塵不染,東西擺放得整整齊齊。他的那些該洗沒洗的衣裳,爛了該補的衣裳,也被娘歸類放在一起,等得閑了,娘就要動手洗洗補補。看見這些,四叔驚得嘴巴張成圓形,眼睛瞪得大大的。四叔的表情不僅是驚訝,一定也在感嘆,這家,有了女人咋就這么不一樣呢?
從那以后,四叔不再用笨拙的手,捏著細小的針,在暗淡的煤油燈下穿針引線,縫補衣裳了。像所有有家室的男人那樣,自己不動手,也穿得干干凈凈整整齊齊的了。
娘在家里是有名的勤快人,來到四叔家更勤快了。當天夜里,娘把我安頓好就幫著四叔看毛驢。拐豆漿。第二天。娘還沒聽到四叔的動靜就早早起來了。四叔開始燒地鍋煮豆漿做豆腐了,娘就過去了。下午,四叔要去豐收河提水,娘什么也沒說就跟了去。上堤和下堤的路是四叔鑿的。一個臺階一個臺階的。娘跟在四叔的后面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上堤,然后再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走下岸來,來到四叔鑿的坑邊,揭開了蓋子,舀水。
坑里的水真清啊,鏡子一樣,天上的云,映得真真切切。就像天就在眼前。藍藍的天幕上,兒朵稀薄的白云,霧一樣,夢一樣。人映在水里,鼻子,眉毛,嘴巴,都那么清晰,水汪汪的黑眼珠一轉,黑是黑,白是白,都能分得清。水里的四叔,寬臉盤,大眼睛,高鼻梁,闊嘴,眉毛、胡子、頭發都又濃又黑。娘第一次看清楚了四叔。四叔的眼睛真亮啊!娘慌了,一扭臉,險些和四叔碰在一塊兒,臉一熱,忙把水桶放進洞里,舀水。水桶碰到水面,漾起圈圈波紋,娘和四叔的影子就不見了。
之后,四叔再去河里提水,就不是四叔一個人了。四叔騎著三輪車,娘擔著水桶,兩人有說有笑地去提水。到了堤邊。四叔停下三輪車,拄好拐,兩人就肩并肩上堤下河岸。來到水坑前,四叔守著水坑負責舀水,娘就來來回回地把三輪車上的水桶裝滿了,然后擔上滿滿的兩桶水,和四叔一塊兒有說有笑地回家來。
四叔每天就做兩個豆腐。也就在村里賣,本村的人,外村的人,多到家里來買,不出門就賣完了。
娘就說:“我不是這兒的人,生產隊里不會派我活給你掙工分,你就多做兩個吧,你在家里賣,我推著車子到外村里去賣,逢集我就到集上去賣,省下閑得慌。”四叔想了想,點頭答應了。
四叔家一下子添了兩張嘴,多賣點豆腐,倒換成糧食,就不愁吃的了。就這樣,每天吃過早飯,娘推上三輪車,走街串巷幫四叔賣豆腐。
娘天生的好嗓子,沒唱戲說書,也派上了用場。一聲“賣豆腐咯,水嫩柳豆腐!誰買豆腐?水嫩柳豆腐——賣水嫩柳豆腐咯!”半個村子都能聽見。那些想吃豆腐的人,早早準備好盛豆腐的碗盆,等著娘走近。那些沒想吃豆腐的人,聽見娘的叫賣聲,清脆,悅耳,也想吃豆腐了。莊稼人,不吃豆腐吃啥?白菜炒豆腐,既家常又好吃。不炒白菜,也可以用小蔥拌。也可以用油煎。煎得金黃金黃。冒著肉味,花椒鹽水一煮,香著呢。
也就幾天的工夫,大劉村,大劉村附近的村子,包括柳子鎮上的人,誰不知道那個推著三輪車賣豆腐的女人呢?娘從此就和“水嫩柳豆腐”聯系在了一起。
在這期間,娘經常賣完豆腐心就空了。四叔說了,過了橋再往南走,遇十字路口再往東走,就能走到棗莊。娘時常不自覺地蹬著空三輪往橋上趕。有一次娘竟然趕了三十多里路,不是路邊上一個和我一樣大的小女孩子給了娘一個驚醒,娘怕是一下子真就去了棗莊。娘從有了這次,經常會一個人,不說話也不做事。呆立著。有時會光做事不說話。別人一個不大的動靜,都會嚇娘一跳。有一天夜里,娘哄我睡了,娘就從包里翻出那件水紅色的褂子,水麻布料的,從褂子兜里掏出那個刻畫著什么的小丫丫葫蘆,躺在床上,抱在胸前,目不轉睛地盯著房梁。來回摩挲著。淚水把我打醒了。我坐起來要玩娘的小丫丫葫蘆,娘堅決不讓,又寶貝似的放了起來。
娘在飯桌上,在和四叔一起做豆腐的過程中。不止一次地念叨,“咋還沒回信呢?也該收到了呀?”
娘念叨完,有一次突然加上一句,說:“大哥,你沒忘記寄信吧?”
四叔聽了,一驚,說:“沒有,沒有,我昨能忘記寄信呢?這么大的事,我咋能忘呢?”
四叔沉默一會兒,極力把臉上弄得明亮一些說:“是不是地址弄錯了?或者是人換了地方,沒收著?”
娘一聽,心里一緊,臉上馬上換出笑容,說:“嗯,嗯。”
娘想,吃著人家的喝著人家的,人家對咱,對孩子都這么好,不能多說什么。
四叔又說:“你娘倆就安心在這里住著,不用慌。也許是孩她爹正忙,不得閑過來呢。”
娘卻在想:也許我爹在棗莊真真有了別的女人,有了孩子,不要娘和我了,這可咋辦呀咋辦呀!娘怕四叔笑話,不敢表現出來,更不敢說出來,就“嗯嗯”了兩聲。然而娘卻時常在夢里哭醒。
這年的冬天好冷啊,時常刮風下雪,出奇的冷,娘整天皺著眉頭。
豆腐渣原本是喂豬的,娘又吃起了豆腐渣。四叔不讓娘吃豆腐渣,娘就說這豆腐渣養人著呢。娘自己吃豆腐渣。炒豆腐渣,做豆腐渣窩窩。換著花樣吃豆腐渣。娘吃豆腐渣常噎著,有幾次像要噎過去,還是吃。可四叔心里明白,這是娘給他省啊。
剛入臘月,娘病倒了。娘是要去賣豆腐,剛上去三輪車就一頭栽下來了。
四叔推著娘在大隊衛生室里打了三天針,也不見怎么管用,頭照暈。四叔就推著娘去西劉村老中醫喬醫生那兒,讓喬醫生給娘看看。喬醫生給娘搭了把脈,睜開微閉的眼睛,說:“沒大礙。是身子虛。抓兩付藥吃吃,再多吃點好的就行了。”
回來的路上,四叔騎著三輪車一直在想,吃啥好的呢?
那年頭,肉可稀罕哩,只有逢年過節,才吃上一點,還沒品出肉味來呢,就吃完了。平時啊,別說吃了,賣的也少,只有集日才有賣肉的。自家養幾只雞鴨,下了蛋,也不舍得吃,得拿到集上換幾個吃鹽點火的錢。四叔沒養雞鴨,雞蛋鴨蛋當然就沒有了。到哪里弄點好吃的呢?四叔想了一路子,想好了。四叔要到豐收河里給娘逮魚吃。熬上幾碗魚湯,白花花的,奶一樣,喝到肚里,可有營養哩。大劉村往東,在大劉村和吳村之間,河上建了排灌站,控制水況。河床在那里有一段凸起,船塢樣,水流緩慢,水草也豐美,那里常有魚出現。四叔把娘安頓好了,翻騰出逮魚的家什,就出發了。
娘吃了四叔熬的中藥在家睡了一覺,天就恍黑了。娘醒來感到好多了,起來拾掇了拾掇院子,就要去廚屋里做飯。這時,娘到西屋門口走了一趟,想叫四叔一聲。又一想,四叔也許累了,每天起早磨豆腐,又剛蓋好了屋子,就讓他多睡一會兒吧。娘坐在灶窩里,突然又想起,平時四叔不這樣,今天這是怎么了?
娘就在西屋門口叫四叔了:“大哥,大哥。”
娘叫了一遍,屋里沒動靜,又叫一遍,還是沒動靜。
娘開開西屋門,一看,床上空蕩蕩的,又看看院子里。三輪車也不在。
娘心里犯嘀咕了,都這個時辰了,到哪里去了?
娘兩步跑出大門,問在大門口玩沙包的我:“妮妮,妮妮,你四叔呢?”
“不知道。”我玩得正起勁,沒多看娘一眼。
天已經黑了下來,小伙伴都回家去了,我也回家了。回家后,娘和四叔都不在。后來,我才知道,四叔到豐收河里給娘逮魚,魚逮著了,他也摔傷了。四叔是砸開冰面,逮了一條不小的魚。在從河里向堤上爬時。路面結了冰,滑,摔下去了,那條好腿腳崴了。頭也磕破了,躺在河沿上,抱著條魚,不能動了。冬天,過路的人少,天又那么黑,誰會想到四叔到那里去呢?幸虧吳村的吳立,晚飯去羊圈里飲羊,發現白天放羊時,把羊韁繩丟了,打著手電筒回去找羊韁繩時,才發現了躺著的四叔。等娘見到四叔時,四叔已經說不出話來了。四叔逮的那條魚,也早已硬邦邦的木棍一樣了。
聽說,那天晚上,在醫院里,娘把四叔抱了整整一夜,用自己的體溫,溫暖著四叔。四叔好了后,娘一個勁兒說:“你看你,受罪了吧。聽說,你這腿能安假肢,等咱有錢了,一定給你安個。”
我考上高中那年,這愿望也實現了。
那年,棉花大豐收,娘和四叔(那時,四叔已經是我父親了1賣了一車又一車。
春天,娘又賣了節余的糧食,家里的羊羔,加上多年的積蓄,給四叔安了假肢。四叔又能正常走路了。那時,娘和我到大劉村已經九個年頭了。不知道娘是不是感覺到了,當時,她說的那句話,下意識地用了一個“咱”。那個“咱”字,把娘和四叔緊緊綁在一起了,一綁就是一輩子。
來到四叔家第二年我九歲了。九歲的我好像突然長大了,能記住很多事了,而且,我覺得,那年,有好多好多值得我記住的事。
經過這么久的休養,我壯了,也胖了,不再是個賴苗苗了。
我有了很多要好的朋友,平時,不是我去找他們玩。就是他們來找我玩。我們玩跳房,踢毽子,投沙包,拾石子等,日子過得非常溫暖、充實。
正月初七那天下雪了,娘去鄰居家套鞋樣子,我趁娘不在家,把娘藏在水紅色褂子里的丫丫葫蘆拿出來玩,不小心把葫蘆攔腰弄斷了。娘發現后臉色都紫了,二話不說舉手就打我;打得我嗷嗷大哭,好像娘不是娘了,是狼,是狠毒的豺狼!娘還在打我,下死把打,四叔來了,一把把我抱到了懷里。訓斥娘,說:“你這是瘋了還是咋啦?”
娘下手真狠啊,打得我在四叔的懷里好哭,四叔抱著我到小賣鋪里給我買了一大把糖,我都沒止住哭。
娘那個小丫丫葫蘆上面刻著兩頭小豬,嘴對著嘴,
后來我再見到那個小丫丫葫蘆時,被死死裹了一層鮮紅的布,壓在娘的箱子底下。
過罷正月十五,四叔給我弄了個舊帆布包,買了幾個小本子,要我去村里學校上學。娘說啥也不干。四叔再三和娘說:“這花不了幾個錢。先讓孩子上著,省下耽誤了孩子。”娘才罷休了。
娘和街上的嬸子大娘也混熟了。東家西家的借個家什,前院后院的說說話,晚飯后,怕做著活困得磕頭打盹,也為了省點煤油,在一起做針線活了。
女人們在一起,旁邊沒有需要避諱的人,也要頭抵頭說悄悄話。有時候,正安靜著,突然,她們就哄笑起來,會嚇人一跳。有一次,胖嬸和娘頭抵頭說話,說著說著,娘就紅著臉,繼而捶打胖嬸,還爭辯說:“你瞎說,沒有,沒有呢。”鬧一陣,這胖嬸就一本正經了,說:“就一起過了唄。老四心眼好,模樣也不錯,人又能干。雖然腿不好,但啥活也不耽誤,以后的日子還能難過了?你一個女人,帶著個孩子,人家可是沒結過婚的童男子呢。”娘沉默一陣,拿眼看了看四叔,沒吱聲。
過了二月二,眼看就要到寒食,天漸漸暖和了。雖然棉衣還在身上,但風已不入骨了。天暖和了,萬物都蘇醒了,連人的心思也活泛起來。娘睡得不踏實了。
這樣下去總不是辦法,別人不說,自己心里也過意不去。在人家白吃白喝的幾個月,孤男寡女地住著,算啥呢,算啥呢?如果離開這里,又會落到哪種地步?
有些事,娘不說,別人也不知道,可娘心里明白。奶奶得了噎食落下了一屁股兩肋巴賬走了,爹為了還賬,跟老鄉到山東棗莊煤礦上掙錢。離家三年多了。三年多來,爹打來錢,娘把賬還完了,爹人卻沒影了。大半年了,爹沒再往家里打錢,也沒寄一封信。有人傳言,說爹在外面有了別的女人,還有了孩子。還說是個男孩;還有人說爹得了癆傷,掙不了錢了,不好意思寫信,更不好意思回家。到底是怎么了,誰也不知道。姥爺去世早,娘又沒有兄弟姐妹幫襯,姥姥又堅信爹是有了別的女人,也不顧自己年邁需要娘照顧,說啥也要娘帶著我去找爹。說找到爹,就不要娘回來了。家里窮,爺爺幫娘賣了豬羊。姥姥又給娘一些錢,娘就告別了家人,裝上個舊信封,包上幾件衣裳,領著我,去了車站。在車站,娘拿著一沓零錢,卻不舍得買車票了。娘就想,我年紀輕輕的,有腿有腳的,還能有走不到的地方?不就幾百里路嘛,走小路。用不了多久就到了呢。娘找人詢問了棗莊的大致方向和位置,領起我來就上路了。路上,娘舍不得花錢。風餐露宿。要著飯,走了十多天。可沒想到我病了娘又把路走偏了,落到了大劉村。我病好了之后,不去找爹吧,娘不甘心;去找吧,爹在哪兒?爹那么能掙錢,是不是真養了別的女人?娘心里沒底。
娘讓四叔給爹寄了信,這么久過去了,爹不來接我和娘,也不回信,娘就堅信爹是在棗莊有了別的女人,生了孩子,不要娘和我了。可娘實在不能和四叔說這些,就緊緊地憋在心里。
“大哥,她爹人不來,信也不來,又天寒地凍的,這可咋辦啊!”
我娘失聲哭了。哭著哭著又嚎啕大哭了起來。
四叔也沒有什么好辦法,就在娘的眼前轉圈圈。
娘的情緒跌落到了谷底,死的滋味都有。
一個星期天,是柳子鎮集。天陰著。娘和四叔早早起來,做好了三個豆腐,擺放在三輪車上。
四叔說:“我也去集上吧?”
娘說:“今天天不好,說不定就下雨,你別去了。”
四叔說:“我去吧,下了雨也好有個照應啊。”
娘說:“春天下不了大雨,你就在家賣吧。昨天,我碰上西街那個送信的了。我讓人給孩她爹又寫了封信,放在當門的桌子上了,他說今天來咱家拿,你在家也好給他。”
娘頓了頓,又說:“我這是最后一次給他寄信了。我問了,從這兒到棗莊最慢也就七八天就能收到信。等上個十天半月的,他再不來信,不來人,我娘倆就不走了,咱……咱就把事辦了。”
娘說著最后一句話,聲音低了,眼皮也耷拉下來。
我猜測,那時,娘也許早就預料到了事情的結果。娘那么聰明,怎能預料不到呢?只是,只是娘在用這最后一封信,畫個句號。這句號不是結束,而是個開始,是娘和四叔我們一家的開始。這句號也是個臺階,娘順著這個臺階,自然而然地滑到了四叔的懷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頭天夜里,娘在煤油燈下。把那個被我弄斷了的小丫丫葫蘆,拿出來,看了好久很久,看得兩眼淚蒙蒙的,之后藏了起來。
四叔正想幫娘捆車子,拿著根繩子,解疙瘩,聽見娘的最后一句話,手不動了。四叔看著娘。用他多次想用,但沒敢用的目光,大膽地看著娘,火辣辣地,熱烈地。四叔覺得,他好久沒見娘了。
“嗯。”四叔只說出一個字,歡快地,又低頭解繩了。
空氣很粘稠,熱烈。街上,柳葉長了,柳葚子出來了。榆樹枝上,榆錢圓圓的,擠在一起。楊樹吐出淡黃的綠意。到處都是春天的氣息。春天,春天真的來了。四叔說過,過段時間,在東墻邊栽棵葡萄樹,到秋天,我就能吃上紅得發紫的葡萄了。
“娘,今天不上學,我也去趕集。”
我從屋里出來,蹲下提上鞋,揉搓著眼屎。
“今天有雨,妮妮不去。等哪天好天了,四叔帶你去,四叔給你買包子。”
四叔給我扣上沒扣全的扣子說。
四叔沒去集上和娘一起賣豆腐。我也沒去。四叔給娘帶了塊塑料紙,又到屋里給娘拿了件衣裳,讓她帶上,說:“預備著吧,如果下了,就穿上。”
四叔不是天生的瘸,是他二十歲那年摔傷的。
那年冬天,四叔和村里人一起到外地挖河。那條河挖得很寬,很深。從對岸看人,人都矮了一截;從河底看岸,土堆得山一樣高。河底滲出了水,結了冰,砸碎了,再挖。差不多是從水里撈泥了。布鞋不能穿,穿膠鞋,穿雨靴。那時候,沒有機器,畜力也用不上,全靠人力一車一車拉。
那天傍晚,干了一天了,人都累了,都說不干了,明天再干。可隊長說,再加把油吧,沒多少了,拉完了咱就能回家了,不然。還得在這里多待一天。大家一想也是這個理兒,就咬著牙硬撐。
最后一車土,本來是另外兩個人拉的,一個人駕轅子,一個人用繩子拉。四叔尋思大家都累了,幫把手吧。四叔就上去推車幫。走到半路,怎么使勁,車子就是不動。前面的兩個人實在沒勁了,干脆松開了手。四叔沒松手,四叔的一只腳壓在車轱轆下面,車子載著土,死沉死沉,帶著四叔,滾了下去。一瞬間,四叔還沒弄明白發生了什么事,腿就斷了。大家連夜把四叔拉到城里,四叔的腿也沒接上,準備來年結婚的親事也散了。
這些年,給四叔介紹的對象也不少,可介紹的女人,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歪瓜裂棗。四叔見也不見就辭掉了。父母去世后,四叔就一個人過了。四叔雖然少了一條腿,可年輕、壯實,到生產隊里干活卻給不了高工分,四叔就學上了做豆腐這門手藝……
我和小伙伴正玩得歡,突然有人說:“電驢子,電驢子。”
那時候,還沒有摩托車,人們就用自行車安了機器,燒油當動力,走起路來嗚嗚響,就這,也很少。我們停下來,一起朝響聲看去。很快,一團綠色停在我家門口。那個一身郵電綠的人,對著我家的方向喊:“老四,老四,你家那個女的說要郵信,讓我給她捎著。”
“啥?讓你捎?你看看。我不知道是你來,我讓別人捎走了。”
三月初六,家里請了客人,擺了酒席。小娘一歲的四叔結婚了,和娘。我也改稱四叔為爹。在這里,我更愿意稱他為父親。
父親疼我。小時候,父親常常牽著我的手,走街串巷,給我買好吃的,好穿的。有了弟弟后,每每我和弟弟起了爭執,父親總會偏袒我。為此,父親沒少挨弟弟的白眼。弟弟沒怎么上學,父親卻堅持供我上學。我考上大學后,離開了大劉村,到城里上班,才有了今天用文字記錄他的故事的機會。
父親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戴著帽子。冬天戴棉帽子,春秋天戴夾帽子。天都熱了,像那些禿頂的人一樣,還戴著帽子遲遲不肯摘下來。就是平時,不經過他的允許,帽子絕對不能隨便讓娘洗,讓我和弟弟摸。無論父親的棉帽子還是夾帽子,總比他的頭還貴重。父親戴帽子總愛在帽子里墊上厚厚的一沓紙。這沓紙腦油臟了。再換沓紙。幾十年如一日。每次別人問起,父親就靦腆地笑笑,說:“嘿嘿,習慣了,習慣了。”
父親年老后,常帶侄子到豐收河的那個大堤上玩,仍舊戴著頂帽子。父親早已不賣豆腐了。有時候,不用看孩子了,父親就牽上娘,倆人到那里走走。村里修了公路,大堤早就不是交通要道了,堤上的土被拉到村里蓋屋子,蓋樓房了,一個缺口一個缺口的,換牙年齡的孩子的牙床似的。可是,那草還綠,那樹還旺,楊樹,柳樹,梧桐樹,都有。父親牽著娘的手,就在樹下散步。
父親安上假肢后,那輛三輪車就不用了。那輛三輪車,歷經風雨,幾經修理,也傷痕累累了。可是,父親不舍得扔掉。父親把那不用的三輪車。擦得干干凈凈,從這屋挪那屋,從那屋挪這屋。弟弟結婚后,扒了老屋蓋新屋,屋里實在沒地方放三輪車了,父親就把三輪車高高地掛在了弟弟的車庫里。
父親六十九歲那年初秋,突然病倒了。腦血栓。拉到縣醫院,已無治療價值,只好拉回來準備后事。
父親臨終時用手比劃著,把弟弟攆出去,讓娘和我守在他身邊。
父親艱難地抬起手,去拿床頭上那頂帽子。帽子沒拿到,卻碰掉了。我彎腰拾起來,打打帽子上的土,想給父親戴上,父親搖著手,不讓;看著娘,緩緩地指著帽子,指著帽子里面。
帽子里墊的都是紙。
娘從我手里接過帽子,疑惑地看著里面,一張一張地往外揭紙。紙,是侄子寫滿字的作業紙。
娘拿著這些紙讓父親看。
父親端起的手臂仍然指向帽子,娘就摸摸帽子,突然感覺到了什么,“哧啦”把帽子撕開,從里面掉出了一個薄薄的塑料袋。娘打開塑料袋,是一支扎著口的避孕套。避孕套里面裝著東西。娘就用牙咬開避孕套,從里面掏出了兩個發黃了的紙塊。娘哆嗦著兩手慢慢揭開,是兩封信。
父親看了我一眼,就死死地盯看了娘,指著娘手里的東西,磕磕絆絆地說:“妮她娘,我……我壓根就沒……沒……沒給妮她爹、她爹寄這……這信,我對不起他,對不起妮,更……更對不……”
父親沒把話說完,頭一歪,咽氣了。
娘一驚,手里的信散落在地上,抱起父親的頭,死死地抱著,抱在胸前,說:“他爹,你傻子啊你……”
娘說著,嚎啕大哭。我呆了。一瞬間,我竟然弄不明白娘在哭誰。
去年我做了一小官,今年春天組織派我到南方考察,回來的路上我順便去了姥姥的鎮上,到姥姥的墓地祭奠了一下姥姥姥爺。陪我去的是我遠房堂舅來民,比娘大一歲,身體很結實,一路上和我說個不停,告訴了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才知道,娘不是一般的善良和有忍耐性。
來民舅舅告訴我,他曾接到過娘打給姥姥的一封信。娘在信上和姥姥說,娘沒找到爹。爹也許真的有了別的女人,娘不找了,娘在山東找了個婆家。對象叫小福,小一歲,做豆腐的,是個少一條腿的瘸子,姥姥要是沒什么意見的話,娘就和小福帶著我一塊兒去看姥姥,然后把姥姥接來山東,養老送終。可是,姥姥在娘和我出來找爹的第二天,為了斷了娘的掛念和后路,跳井了。來民舅舅把我娘的來信,在姥姥的墳頭上念了一遍燒之后,如實給娘回了信,要娘不要再掛念啥了,好好在山東過日子。祭奠完姥姥回來的路上,正在猶豫是不是去爺爺奶奶的莊上看看,一陣細風吹來,濕漉漉的,很暖,心里一緊,我想到了我爹,想到了我那記憶全無了的爹,我就問來民舅舅,說:“舅舅,我爹真的有別的女人了?”
來民舅舅猛一吃驚,說:“妮,你娘沒告訴你?”
“沒有!我爹的事。我娘極少提起……”
來民舅舅嘆了一口氣說:“你爹沒有別的女人。你爹在煤礦上得了癆傷;拖著病身子下煤窯,不小心死在了事故里。你爺爺和你叔把你爹的骨灰從山東背回來,四處找你們娘倆,找不到,你爺爺就把你爹下葬了,不久也撒手歸西了。我在給你娘的那封回信上,一五一十,都和你娘說了。說得很仔細。要你娘別再想家了,家里啥也沒了……”
我淚如泉涌。我也終于明白了我多次要改姓,娘為啥不讓改,
我還記起了,娘和四叔結婚后的一天晚上,別人都去看電影,娘卻帶我跑到豐收河的大堤上,要我面向南方好好跪下;然后娘“撲通”一下,也雙膝跪下了,跪在我一邊,狠狠地磕了三個響頭。之后娘趴在地上嚎啕大哭。那次娘在大堤上哭得揪心,很揪心,是放開嗓子撕心裂肺般的嚎啕大哭。驚天動地。哭得我哭著不讓娘哭:不讓娘這樣哭,娘這樣哭我就拽著娘的胳膊說:“妮怕,妮好怕啊,娘——”娘就不哭了,可也止不住悲痛,抽泣著,跪著給我擦淚水。娘和我說:“妮,我的妮啊,娘哭,娘是想咱家了啊。想咱的老家了啊,想咱老家的妮那些親人了啊,可娘和妮再也回不去了啊,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我嗚咽著和來民舅舅說:“舅舅,我去看爺爺,看奶奶,看我爹……”
我背著來民舅舅擦了一下眼睛,深吸了一口氣,濕漉漉的,暖暖的,到處都是春天的氣息。
作者簡介:張悅紅,女,上個世紀70年代出生。2008年開始利用業余時間從事文學創作,已在《當代小說》、《天池》、《山東文學》等文學刊物發表小說十余篇。現供職于山東省鄆城縣職教中心。
責任編輯: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