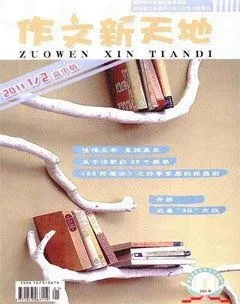夜行者
我還在盯著那道該死的物理題。窗外吱吱的蟲鳴擾亂著我的心。我面對著它,已經足足有三十分鐘。現在的我已經筋疲力盡,我的大腦在這漫長的三十分鐘里已經熬成了一團根本無法思考的糨糊。
……怎么辦呢,我們的物理老師,那只微微謝頂的老綿羊,說這張講義極為簡單一這意味著做不出來的人不是傻瓜就是笨蛋。
同桌早就寫好了。她的講義就放在離我的手臂很近的地方。
我偷偷瞄了眼講臺上的老師,恰巧她也在看我。我慌里慌張地低下了頭。
墻上的時鐘滴答滴答地走著。我聽見課代表站起來的窸窸窣窣聲。他已經在催促前排的同學了。
我迫切地需要這道題的解題過程。他已經收好了兩組,而我必須寫出來。
我已經沒有心思再去顧及老師。我的目光一寸一寸地移到同桌的講義上。她寫得潦草。我看得不是很分明,不得不把頭再湊過去點,卻撞上了她怪異的目光。
我的臉上有點燒。我動了動嘴唇,企圖說些什么。只見她若無其事,拿起講義遞給了課代表。
然后——
“你的呢?”
“沒……我還沒好。待會兒我自己交給老師。”對,我僅僅是沒有寫好而已。
課代表走了。我不得不又重新面對那道惱人的題目。
一陣涼爽的夜風透過窗子的縫隙吹在我燥熱的臉頰上,我突然覺得,我的生命不應該為一道乏味的物理題而白白耗費。
不如就這樣交上去吧。我這樣想著,竟如釋重負般走出教室。
可當我一眼瞥見老師桌上成堆的滿分講義時,我又悄悄地攥緊了手中的講義,慢慢地把它放回了口袋里。
察覺到了什么,老師詫異地轉過頭來:“什么事?”
“沒,沒什么……”一時間如有針芒在背,我尷尬地笑著,生硬地擠出幾個字,“……那個,路過這里,團委里有人找我……”說著,一步步退進通往行政樓的側門里。
我背過身去,站在行政樓昏暗的甬道里,沉默下來。
長長的走廊兩側有無數扇緊閉的門,沒有一扇因為我的到來而打開。我扶著墻壁默默地走下逼仄的樓梯,每一步都是一聲悠長而清晰的孤寂。
突然一陣清風拂面。我抬頭看見轉角處一扇不大不小的氣窗。
婆娑搖曳的樹影,深邃幽藍的天穹,碩大又明亮的星星,以及站在那里一動不動、靜靜放著清光的路燈。
仿佛就在一瞬間看見了幾個世紀前凡·高眼中動人心魄的那個星夜。
我站在那里半晌沒有動。
夜涼如水。時間像是在流經這里時靜止了一般。
這里沒有監視器,或許我可以逗留一會兒。
站得久了,累了我就在樓梯上坐下來,托著腮。我驚奇地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多么奇妙的位置:我的頭頂上是寬敞明亮的教師辦公室,腳下踩著的卻是緊鎖門窗的行政office——我的右手邊是一個一個碼得整整齊齊的班房,而我的左手邊連通的卻是燈紅酒綠、車水馬龍的市井。
現在是一個萬籟俱寂的夜晚,我的同學統統都在教室里自習,而我卻莫名其妙地成為了一個夜行者,逃離了這一切。
在這樣的時間,以這樣的身份出現在這樣一個地點,是不是一種宿命的相遇?我眷戀地摩挲著墻上的瓷磚,什么也不想,在這個僅僅屬于我一個人的時空。
打破這片靜謐的,是頭頂陡然響起的,咔咔的皮鞋聲。神回的我倉促地站起來,腦海里只有一個念頭,快點離開。
我提起腳尖快步走著,努力使腳下惱人的聲響放到最輕。我逃也似地沖進迷蒙的夜色之中,慌亂中與那些檢查紀律的學生擦肩而過。我聽見背后有人在喊:“喂,哪個班的?!”
我顧不了那么多,逃命般地一頭扎進了教學樓里,一連跑上了好幾層才停下來。
我的身后一片寂靜。不絕于耳的只有夏蟲的吱吱聲。
他們沒有追上來。我拍拍劇烈起伏的胸口,抬起頭來對上了頭頂正赫然看著我的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