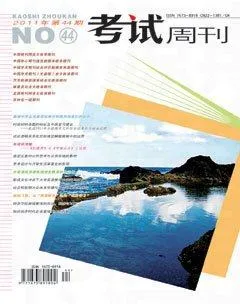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幸福》中的同性戀身份焦慮
摘 要: 《幸福》是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中一部不可多得的珍品。本文力圖從小說女主人公貝莎幸福感驟然幻滅的遭遇來探求其同性戀身份焦慮的根源和困惑。而貝莎的強烈身份焦慮導致了她在不斷尋覓自身身份的過程中流露出游離于邊緣地位的無奈。
關鍵詞: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 小說《幸福》 女主人公貝莎 同性戀身份焦慮
出生于新西蘭的英國女作家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短篇小說一直是世界文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她的每一篇作品都可謂匠心獨具的精品。曼斯菲爾德以其在短篇小說領域里的優秀創作在英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并且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和爭論。曼斯菲爾德對現代小說的貢獻,亦如新西蘭文學評論家C.K.斯特德指出的那樣:她的小說是一座“寶庫”。[1](44)發表于1918年8月《英國評論》(English Review)上的《幸福》(Bliss)是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小說《幸福》以貝莎宴請賓客這一事件為中心,敘述了貝莎由開始感到莫名的無比的幸福到幸福感驟然幻滅的心路歷程。紐約時代周刊書評一欄這樣評價道:“精心策劃,自圓其說,寫得極好。”[2](230)國內外已經有很多學者對曼斯菲爾德的短篇小說作了深入研究。國內學者蔣虹以作家復雜而矛盾的文化身份為出發點,對曼斯菲爾德的作品中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新西蘭作家安東尼·阿爾伯斯(Antony Alpers)在傳記《一次輕率的旅行: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一生》中呈現了曼斯菲爾德由漂泊生活引起的民族身份焦慮。然而從1980年至2010年國內權威數據庫中國知網和國外權威數據庫Academic OneFile數據庫對她的研究看來,對曼斯菲爾德作品中同性戀身份焦慮這個問題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幾乎沒有。鑒于上述國內外對她的研究現狀,我選取了身份焦慮這個切入點,力圖從《幸福》女主人公貝莎(Bertha Young)的遭遇來探求其同性戀身份焦慮的根源和困惑。
1.同性戀身份的根源
女主人公貝莎表現出了強烈的同性戀心態,其同性戀傾向有著深刻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小說一開始就向讀者揭示了貝莎矛盾的性心態。貝莎的幸福之情在胸膛里熊熊燃燒,“每個毛孔,每個手指和腳趾里都迸發一陣陣火花”,此時她很困惑:“既然一定得把這份心情當一把稀世珍寶般的提琴那樣珍藏在琴盒里,那么老天給你肉體干嗎呀?”[3](172)由此我們仿佛感到貝莎在性上有多么的狂熱,生理上她極度地渴望釋放自己內心壓抑的欲望,她在不斷地尋找著欲望的發泄口。
貝莎是一個三十歲的已婚婦女,走路都是連奔帶跑,“踏著舞步在走道上蹦上跳下,再不就干脆愣著不走,兀自發笑——平白無故的——就那么沒來由地笑一通”。[3](172)表面上她的心中似乎充滿了一種難以遏制的幸福感,然而她的家庭生活并不理想,丈夫對她不以為然。因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英國,男性仍然處于絕對的霸主地位,女性的天空低矮狹小,社會留給她們的機會少得可憐。而且男性壟斷了政治與經濟的主要資源,女性“被排除出嚴肅的事情、公共事物空間,她們長期以來扎根于家庭空間和與子嗣的生物和社會再生產相關的活動中”。[4](135)在家里,女性只是丈夫的私有財產,丈夫也只是把妻子當作擺設和活玩具,幾乎不過問妻子的感情生活。貝莎的丈夫哈里(Harry)也是如此。他打電話告訴妻子說要晚一點回家時,總是待在家里的貝莎很想和她的丈夫親密一會兒,可是哈里不給她這個機會,不耐煩地結束了通話。對于哈里來說,貝莎是家庭主婦,主要負責管理家里的大小事務。他并不在意貝莎的情感需要,他在她的面前總是一副冷靜和泰然自若的樣子。每次聚會哈里總是遲到,“他還決意在走進客廳時,要擺出一副格外鎮定自若的神態”,以便客人歡迎他的到來。[3](180)作為父親他沒有責任感。他甚至說:“好奈特太太,別問我孩子的事吧。我從不去看她。不到她有了愛人那一天,我對她是一點兒興趣也沒有的。”[3](184)同時哈里還是一個地道的裝腔作勢的小人。他和富爾頓(Fulton)小姐之間早有曖昧,卻裝作對她很冷淡。在與富爾頓小姐勾搭之后,反過身能鎮定沉著地面對妻子,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貝莎和他之間并無共同語言,他們的愛好興趣迥然不同。在性那方面貝莎對他無動于衷,兩人之間也沒有真愛存在,幸福更無從談起了。丈夫對自己的冷漠和不重視使貝莎從心理上對異性的愛也不再抱有幻想。
富爾頓小姐的出現是貝莎苦悶生活的調劑。貝莎和富爾頓小姐在一家俱樂部萍水相逢,貝莎對她有一種不可言傳的好感,她認為富爾頓小姐新奇又神秘,因為她對古怪的漂亮女人一向是懷有好感的。當富爾頓小姐到她家赴晚宴時,貝莎臉上流露出占有者所特有的一種得意神色。當貝莎挨到富爾頓小姐冰涼的胳臂時,她“心頭那股幸福的火焰又給什么東西扇旺了——扇旺了——還在熊熊燃燒”。[3](181)貝莎對富爾頓小姐的感情無疑超越了一般友誼。貝莎感到很不可思議,她能一下子就準確而迅速地猜中富爾頓小姐的心思。她與富爾頓小姐心靈相通,面對富爾頓小姐,貝莎身上有股強大無比的感情潛流在激蕩。一個能給自己帶來幸福的同性朋友的出現,促使貝莎壓抑的同性戀傾向悄悄浮出水面。
“女性在人的發展領域的從屬關系,表現為女性發展的邊緣化,即女性發展被壓制、被忽視、被歧視、被排斥等”。[5](26)每位女性多多少少都經歷著相同的命運:逼仄的空間、禁錮的欲望、壓迫的沉默、窒息的心靈。女性的本質生存狀態使貝莎的精神和心理都受到嚴重的壓迫和抑制,讓貝莎感覺仿佛掉進萬丈冰窟,美好的現實成了人間地獄。貝莎表面沉靜的外表下惴惴不安的驚恐使她感覺自己總在社會的邊緣徘徊。家庭幸福感的缺失導致貝莎感情天平的傾斜,把目光轉移到能懂得欣賞自己的同性身上,同性戀傾向的萌芽促使同性戀身份的焦慮漸漸襲上她的心頭。
2.同性戀身份的困惑
20世紀初中上層社會的男男女女生活富足,行為高尚,追求高檔次的文化生活,互相宴請作樂。然而這只是他們生活的表象,實際上他們都壓抑著自己的欲望,而過著一種虛偽的生活。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完美婚姻往往藏污納垢。無論是誰,一旦破壞了這種規則,便會受人排斥。婚外情會遭人唾棄,同性戀更意味著奇恥大辱和道德淪喪。小說中的梨樹是雌雄同體的植物,貝莎覺得繁花盛開的梨樹“就是她自己的生命的象征”。[3](177)在宴會歡樂的氣氛中,“她心坎里,仍舊念念不忘那棵梨樹”。[3](183)貝莎表現出了強烈的同性戀心態。對于貝莎這樣有著同性戀傾向的人來說,壓抑在身體深處是唯一的方式,她不想因為“常為與某個女生關系密切而被懷疑是某種道德上的墮落”。[6](199)“同性戀者永遠只能把自己的行為默默地局限在‘櫥柜’內而不能擺到‘庭院’里。‘櫥柜’指同性戀關系被壓抑的狀態,而‘庭院’則是其被公開接受的狀態”。[7](86)性的背叛在道德風尚嚴厲的維多利亞時代,卻如同彈簧原理——壓力愈大,暗中的反抗就愈大。在傳統的異性戀婚姻之外發展“時髦的”同性戀似乎是貝莎苦苦尋覓的一劑良藥,她很渴望在異性戀霸權和父權制的社會里尋找自己的一片天空并確認自身身份。“身份狹義上指個人在團體中法定或職業的地位,而廣義上指個人在他人眼中的價值和重要性。身份是某個體區別于他人特別是區別于群體的獨特特征和品質”。[8](6)身份只有在自我和他者、社會的對比中才能實現,而認同是對自我身份的確認。然而在當時同性戀身份是不被大家認可的,被大家懷疑是道德上的墮落。身份的焦慮是我們對自己地位的一種擔憂。“擔憂我們無法處在與社會設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險中,從而被奪去尊嚴和尊重,這種擔憂的破壞力足以摧毀我們生活的松緊度,以及擔憂我們當下所處的社會等級過于平庸,或者會墮落至更低的等級”。[8](6)感受不到人情冷暖,貝莎便不能獲得對自己的良好感覺,以致在心理上產生了深深的擔憂,擔憂他人看不到她的價值和重要性。由于同性戀本身并不能給予發展和社會道德壓抑的雙重壓力,貝莎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感到很焦慮,擔憂被奪去尊嚴和尊重。
貝莎期望自己被重視,自己的價值會有慧眼發現,渴望與他人心靈相通。富爾頓小姐的出現給貝莎的生活帶來了曙光,她在同性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了心靈的慰藉。然而這所有的一切只是她的一廂情愿。晚宴結束時,貝莎看見哈里雙手搭在富爾頓小姐肩膀上,“猛地把她轉過來面對著他,他嘴里說:‘我喜歡你。’”[3](188)當知道自己傾慕的富爾頓小姐和她親愛的丈夫哈里相互勾搭時,貝莎在同性戀上經受了嚴重的創傷。感情的背叛使這種尋找自我身份的成功變得尤其凄慘和無奈,進而進一步加劇了她的同性戀身份焦慮。深深的幻滅感刺痛了貝莎的心,她壓根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在何處。貝莎的幸福只不過是一層薄薄的遮蓋這個中產階級家庭女性空洞生活的覆蓋物。一個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女同性戀者,只要沒有離開所處的社會,便不能解決惶惶不安的同性戀身份的困惑,缺乏歸屬的同性戀身份焦慮感永遠使她總處于社會邊緣人的地位。
3.結語
貝莎,一個在異性戀霸權和父權制社會中的家庭主婦,其美好的期待與殘酷的現實發生沖突,當經年的幸福被不經意的一瞥便土崩瓦解,瞬間的頓悟便淹沒了自以為永恒的暖意。貝莎在生活中無所適從,只能在荒謬而陌生的世界中尋尋覓覓,執著地希望找到心靈的慰藉,然而卻無情地遭遇感情的背叛。這種傷害使得貝莎陷入同性戀身份焦慮的困境,產生極端壓抑和痛苦的心理體驗。對人生的頓悟,對婚姻的洞悉,使貝莎深刻地感受到了同性戀身份缺乏歸屬的焦慮感。對自身同性戀身份強烈的焦慮感使貝莎始終擺脫不了成為游離于社會邊緣的靈魂的命運。
參考文獻:
[1]付燦邦.“新的聲音”——曼斯菲爾德的《幸福》[J].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2):41-44.
[2]Boddy,Gillian.Katherine Mansfield:The Woman and the Writer[M].New York:Penguin Books,1988.
[3]凱瑟琳·曼斯菲爾德著.陳良廷等譯.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4]皮埃爾·布爾迪厄著.劉暉譯.男性統治[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5]楊鳳,田阡.性別政治下的女性發展邊緣化[J].思想戰線,2006,(1):26-30.
[6]蔣虹.凱瑟琳·曼斯菲爾德作品中的矛盾身份[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7]姜禮福.游離于“美麗世界”的邊緣人——論《美麗曲線》中尼克的身份焦慮和認同危機[J].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82-93.
[8]阿蘭·德波頓著.陳廣興,南治國譯.身份的焦慮[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