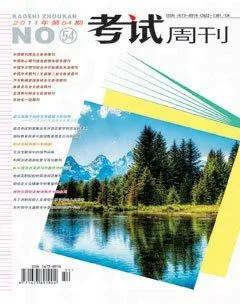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的回歸\\拓展和欠缺
摘 要: 19世紀30年代西方出現的“現實主義”與中國傳統文論中對真實、寫實手法的推崇和對現實社會、人生的關注存在著內在的一致性,因而,西方現實主義的影響其實是我們自身現實主義潛意識的解放。但是“現實主義”在進入我國的本土化的過程中被過濾和再創造,經歷了背離、回歸、拓展的過程。本文意從“現實主義”在我國本土化過程中的一系列變化來探求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的回歸、拓展和欠缺。
關鍵詞: 現實主義 新時期小說 回歸 拓展 欠缺
作為現實主義小說精髓的“冷靜、客觀、忠實于現實生活,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的典型人物”在進入我國本土化的過程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存在到偏離、從偏離到回歸、從回歸到拓展的一系列變化,形成了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多樣性的直面現實、直面人生的新時期小說,但同時,它也存在著一些缺少對社會現實和制度的縱深思索,對人類靈魂和人性的本質探求,對生死和愛恨的終極關懷,以及作家自身的“鐵肩擔重任”的歷史使命。
一、現實主義小說的起源、濫觴和回歸
當我們研究一個事物的發展和變化的時候,首先要考察的就是它的根源,因為只有明白了它的根源,才能有利于預測和把握它的發展和變化。同樣的,如果我們要研究“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的回歸、拓展和欠缺”,首先就要明白“現實主義”的背景、來源和內涵。
“現實主義”最早是作為一個與“唯名論”相對的哲學概念在19世紀30年代出現的。人們通常認為現實主義就是“忠實地反映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以及人的內心世界”。但是,將“現實主義”這樣一個名詞作為一種文學方法,則始于德國“狂飆突進”運動的代表作家席勒的《論樸素的詩與傷感的詩》一文,他首次在文學領域使用了“現實主義”這一名詞,確立了它作為“理想主義”的對立面的含義。同時“現實主義”還是一個藝術流派,也稱為“寫實主義”。它堅決如是地表現出了畫家所處時代的風格、思想和面貌,其中至關重要的就是“真誠”。[2]
在了解了“現實主義”的出處和流變的基礎上,我們便很容易掌握它的內涵和特征了,其中“現實主義”的內涵具體包括:(一)它是19世紀中期產生于歐洲的文學思潮流派和文學理論體系。(二)它是對19世紀前期浪漫主義的反駁。(三)它融合了“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不同流派的思潮。它的特征與現實是密不可分的:(一)“現實主義”作為一種精神表現在對真實事物的追求、對社會的批判。(二)作為手法的寫實性,它忠于現實、忠實地反映現實生活;注重細節的描寫,具有宏大的敘事,全景式、全面、系統、整體、本質地關照和把握社會歷史。(三)強調典型原則。(四)它的審美觀是對真實和生活的遵從。
然而,在上世紀由日語翻譯過來的“現實主義”在我國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實主義”最初是以“寫實主義”的名稱引入的,它是在進化論的角度上對西方現實主義的認同。在理論的探索和深化方面,周樹人和周作人兄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當時也出現了很多優秀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比如《吶喊》《阿Q正傳》等。但是,由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移植及其與戰爭文化規范的合流,“現實主義”已經失去了它原先的特色,而這個被蘇聯用來作為“從思想上以黨派目的來教育人們”的工具,在周揚的引介和毛澤東的運用之后,尤其是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標志著“紅色古典主義”主流文學的興起之后,產生了正反兩個方面的影響,既出現了如《子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宏大的作品,又開了文學政治化、概念化的先河,從而使文學意識形態化,并最終淪為政治的傳聲筒。這種對現實主義的改寫和置換在建國后尤為明顯,在我們全盤接收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后,在“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兩結合”手法之下,作品中再也找不到“現實”的蹤跡,所剩下的只有浮夸和虛飾了。而“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結合創作原則更是對“現實主義”精神的全面否定和徹底背棄。[3]
但是,一時的謬誤擋不住永恒的真理,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就像在盤山公路上的前行,雖然迂回,但最終還是上升前行的。隨著“文革”的結束,“社會主義的批判現實主義”等新觀點的提出,人們開始對“現實主義”重新進行了審視和探索:一是對政治原貌的恢復,在撥亂反正的大背景下出現了“傷痕小說”和“反思小說”。二是對歷史真相的還原,在新歷史小說中客觀重述了“國共斗爭”、“抗日戰爭”、“階級與人性”的主題。三是對現實的審視和批判,不管是對國民的文化心理還是政治體制,都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揭露和批判,繼而使之走向在內容上“關注下層民眾生態、心態”,在敘事策略上“將重點由抒情寫意轉向客觀敘事”的“新寫實主義”。它吸收了先鋒小說的精神內涵而展現個體生命的生存本相,為人們開啟了深層內涵的心靈世界。它向人們展現了國民的生存狀態,對人生處境進行還原和重構;為人們撩開了婚戀的神秘面紗,消解了虛幻的理想;它展示了生存負重中人的無奈、沉淪和喪失;揭示了人性之惡和環境之陋的雙向同構。
二、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的拓展
此時的“現實主義”不僅已經回歸了它“反映現實、揭露、批判社會”的本質,而且有了新的拓展,即“新現實主義沖擊波”的出現。“新現實主義沖擊波”在思想上依然是現實主義的,但是比以往的現實主義更為開放,更具包容性,更為多樣化,也使現實主義登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現實主義大師的優秀作品大概都具有難以言語形容的對人們的‘天真的關懷’、再現他們日常生活時的清新和自然的氣息”。以劉醒龍,“三駕馬車”的談歌、和申、關仁山等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們的“新現實主義沖擊波”,用“現實主義”的手法表現當前現實生活、社會矛盾,將關注的目標由原先的生活瑣事轉向與國際民生相關的重大事件,敘事視點也由平民而轉向干部。能夠正視尖銳的社會矛盾,反映復雜的人際關系,塑造了一些抗爭邪惡、造福民眾、充滿人間關懷、擁有民間操守和智慧的干部形象。比如談歌在《大廠》、《大廠續編》中塑造的廠長呂建國等一批在困苦中堅韌奮斗的企業干部。和申通過《村民組長》、《年前年后》、《窮鄉》、《窮縣》塑造的村民組長黃祿、鄉長李德林、鄉長兼黨委書記陳明、常務副縣長鄭德海,他們都是有著“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責任感,都是百姓心中的好干部,讓我們看到了在那個經濟改革的特定時期里,人們的心靈、道德、人性的搏斗。[4]
現實主義的另一個拓展則表現為“新寫實小說”,新寫實小說吸收了現實主義面對人生的寫作態度,同時摒棄了居高臨下的敘述視角;吸收了先鋒小說的平面化、零散化的運作手段,同時摒棄了它由無序敘述所帶來的遠離普通讀者的文藝貴族作派。從文學精神來看,它仍然是屬于現實主義的,但是,它更具有一種新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注重現實生活原生態的還原,真誠直面現實,直面人生。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很多,主要有劉震云、方方、池莉等。在劉震云的最初的兩部小說《塔鋪》、《新兵連》中就流露出了作者作為新寫實小說的代表的創作宗旨:對底層、平民、小人物的生活境遇的關注。他將一切實在的真實轉化為寫在文本中的真實,更關心“返回平民”、“返回真實”。他在《一地雞毛》中描述了權力網絡向家庭的延伸,指出了生活本身就是一大堆瑣碎的實際問題。方方于1978年發表的《風景》被評論界稱為“拉開‘新寫實主義’的序幕”,她關注底層人物的生存狀況,善于刻畫卑瑣丑陋的病態人生,以冷峻的眼光剖析人性的弱點,探索生命的本真意義,她的《祖父在父親心中》、《行云流水》、《桃花燦爛》、《烏泥河年譜》、《春天來到曇花林》等,都是以敏銳、深邃的洞察力,舒暢、淋漓的語言揭示著她所理解的人生的真意。還有池莉的表現平民生活的“人生三部曲”:《不談愛情》、《太陽出世》、《煩惱人生》,被譽為新寫實小說代表。她自己也強調說:“我追求的就是要把中國人的生活非常逼真地表現出來,我的追求就是中國人的生命本質、日常生活的本質,而不是宏大話語,不是任何其他的東西。”
三、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的欠缺
至此,我們對“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的回歸和拓展有了基本的理解和認識,那么在此基礎上,我們不禁要進一步思索:“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還有什么欠缺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要首先回到“現實主義”的本質上來,從總體來看,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的確是體現了現實主義“真實反映社會、揭露現實”的精髓的,但是,它也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
(一)在反映和揭露社會現實和社會制度方面,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缺少了深度的真。作家應該深入思考或者說敢于揭示社會現實和社會制度的種種不合理,應該看到雖然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都在進行著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多年以來的陳規陋習卻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徹底清除的,它也許需要幾代人的艱辛付出和痛苦洗禮,比如富國窮民、貧富不均的分配體制,城鄉差異、城市差別的戶籍制度,政企不分、醫藥不分的醫療體制,覆蓋狹窄、缺乏共濟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升學率評優劣、以學生分數評獎教師的教育體制,等等。作家應該從這些更深的層次里揭示人們在這些不和諧社會環境之中,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得不異化自身、扭曲心態、背叛靈魂的本質原因,從而使小說更具有廣度、深度和張力,更能體現出現實主義的真正本意。
(二)在對靈魂的拷問方面,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缺少了本質的真。在這一點上,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列夫·托爾斯泰在《復活》中不僅剖析了高高坐在審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貴族代表的靈魂,更注重對主人公聶赫留道夫的靈魂的拷問:“他靈魂的深處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為的殘酷、懦怯、卑鄙,還感到他閑散的、墮落的、殘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樣。”“直到現在,他才了解自己的全部罪孽……發覺自己罪孽的深重……感覺到他害她害到什么地步……以前聶赫留道夫一直孤芳自賞,連自己的懺悔都感到很得意,如今他覺得這一切簡直可怕。”通過對靈魂的拷問,聶赫留道夫的精神覺醒了,他醒悟了:“人吃人并不是從森林里開始的,而是從各部、各委員會、各政府衙門里開始的。”從而使聶赫留道夫由“獸性的人”到“精神的人”的轉變自然合理、水到渠成,而不像新時期的一些現實主義小說中的人物那樣,因為缺乏對人物心靈的拷問,因為缺乏人物心靈的震動和感悟而顯得那么生澀、牽強,從而影響了整個作品的可信度和說服力,淡化了現實主義的色彩,失去了現實主義小說的特色。
(三)在對人的生死、愛恨的終極關懷方面被“打工文學”、“底層文學”等反映生存的外在和局限所代替,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缺少了犀利的真。以鄭小瓊、浪淘沙、王十月等為代表的“打工文學”,以曹征路、王祥夫、劉繼明等為代表的“底層文學”其實是一個階層的文學,它反映的農民和其他底層人們的辛酸、痛苦、掙扎和夢想,它確是起到了喚醒國民、引起療救的作用,但是它的狹隘性和個人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另外,很多作者也只是基于簡單的人道主義的同情,又由于思想資源的匱乏,往往從一個高高在上的視角來觀察和審視,根本無法充分理解這個階層除了“愚昧、落后”之外的本質問題,而使這些停留在肉體的、表面的、物欲的“愚昧和落后”缺乏了真正能打動人心、能拯救靈魂的內涵,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外在性,而缺少普遍性、深刻性,甚至于在“娛樂至死”的當下成為人們的一種獵奇。
(四)在作家觀照世事人生和塑造人物方面,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失去了和諧的真。作品中出現兩極了分化的偏頗:要么虛構人生的美麗、粉飾虛幻的詩意、制造矯情的悲壯,要么直呈人性的自私、懶惰、冷漠、貪婪,揭露社會的不公、殘酷、困窘和瑣屑。陷入了虛幻、矯情或絕望、叛逆的兩個極端。事實上這兩種傾向都沒有真實、完整、客觀地反映現實,在某種意義上背離了現實主義小說的真諦,都沒有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的一條恰如其分的通道,從而對人們的現實生活有所引導和啟迪。在這方面英國,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具有濃厚浪漫主義色彩的現實主義小說《簡·愛》,被稱為“詩意的生平寫照”,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在小說中她真實地揭露了社會的陰暗面,如:處于社會底層的孤兒院殘酷的生活境遇;奢侈糜爛的封建上流社會;但是同時,作者也給人們編織了新的希望和夢想:簡和羅切斯特先生終成眷屬,他們有了自己的孩子,羅切斯特的一只眼睛也重見了光明。她將揭露、批判現實,與感悟、啟迪人生完美地結合了起來,實現了真摯、和諧的美,給人們指出了前進的方向。[1]
(五)現實主義在新時期小說中的缺失還有一點,就是作家們自身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責任感的缺失。“因為對任何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現實,全盤肯定之,盲目為隨之都是違背了文學藝術應有的超越現實的自由品格”。當今社會的快節奏、高效率使人們日益浮躁、機械,失去了內心的平靜和祥和,人們正在用一種異化了的心靈和充血了的眼睛來審視、評價身邊的一切。而同樣處于這種大環境中的作家們或多或少地也會被這些身外之物所異化,眼睛里的世界自然也會有失偏頗,從而在作品中表現出虛幻、矯情或絕望、叛逆的兩個不客觀、不忠實的極端,忘記了自己的道義和使命。那些被這個喧囂、浮躁的大環境制造出來的同樣是喧囂、浮躁的“快餐式”的作家,為了眼前的目的,常常會使用各種各樣打破、顛覆已經存在的舊事物的“求異”方式以吸引讀者的眼球。但是,打破一個舊框架不是一件太難的事,而再筑建一個新的理想卻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沒有沉靜的心靈來思索,沒有寂寞時間的來沉淀,沒有深厚學識的來積累,沒有苦難的人生的來頓悟,是不可能寫出好的作品的。就像心中沒有陽光的人不能給別人帶來光明,心中沒有夢想的人不能給別人帶來希望一樣,震撼的作品常常出于高尚的靈魂,傳世的經典往往來自完美的人格。[5]
真正的現實主義是對社會、人生的客觀、全面、冷靜、忠實地觀察、思索、探求和感悟;是對社會、人生的縱深解剖;是發自內心和靈魂深處的一聲吶喊,是指引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一盞明燈。就像我國古代長篇小說中現實主義最高峰的傳世巨作《紅樓夢》,還有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文學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司湯達的《紅與黑》,果戈理的《死靈魂》,它們的傳世影響不僅在于深刻地揭露、批判現實,而且在于它們無與倫比的藝術價值和醍醐灌頂的感悟和啟迪。它們擁有現實主義最核心的人類進步的信念、理想和希望,它們擁有鼓舞和激勵社會與人類發展進步的動力和斗志。它們給予我們的穿越時空的頓悟,使我們的一切經歷、經驗、喜怒哀樂都能從中找到參照、解釋和依托,都能找到心心相印的共鳴,它們所描述的永恒不變的人性,它們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都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自從它們問世以來,便如黑夜中的一顆顆朗星,光芒四射、熠熠生輝,在黑夜中照亮著人們前行的道路。
參考文獻:
[1]李永建.新時期小說的人學研究[M].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12.
[2]文學理論基礎編寫組.文學理論基礎[M].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5.
[3]殷囯明.20世紀中西文藝理論交流史論[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2.
[4]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現代文學理論譯叢[M].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5.
[5]張利群,張榮翼,張小元.文藝學概論.天地出版社,2001.11.
(作者系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2010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