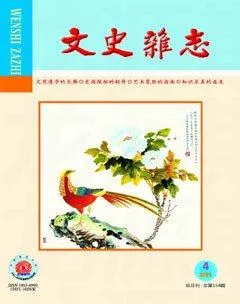評聯務實 治史求真(上)
清人梁章鉅的《楹聯叢話》(以及其后編輯的“續話、三話和四話”)如今已經成為楹聯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參考書,甚至可以稱為指導書籍。其中許多楹聯文本和楹聯史料以及楹聯評論都給楹聯家們提供了比較可靠的資料,不可或缺,理應細讀。但它畢竟是清代的個人著述,難免有局限性。如果不加識別地照抄,勢必不能充分發揮其參考指導書的作用,而且會以訛傳訛,形成誤導。筆者近年來幾度翻閱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白化文、李如鸞點校本(簡稱《叢話》,下同),發現一些可取之處,也發現與其他書籍抵牾之處;經過比較分析,有點滴心得體會。這里分條敘述,雖屬獻芹,或可供楹聯界諸位同人參考。
鄭板橋原聯如何?
《廢都》的作者賈平凹轉引清人鄭板橋(燮)寫的對聯,說是:
春風放膽去梳柳,夜雨瞞人在潤花
《中國對聯譚概》載鄭板橋的對聯根據余德泉先生《對聯縱橫談》所載墨跡影印件,說是:
春風放膽來梳柳,夜雨瞞人去潤花
于是乎,既讀小說,又讀聯書的人就發現了“兩賢相厄”的場面。賈平凹先生的引文,與一般傳聞大不相同,又沒有交代自己考證所得的此聯出處。孰是孰非,亟待明辨。
難嗎?不難,讀書可知!《楹聯四話》卷五略云:
仁和馬慶孫……為盜劫,呈失單曰:有鄭板橋楹聯,先人性命寶也,務乞追償。”未三日果于貨擔間得之。其聯曰:“飄風作態來梳柳,細雨瞞人去潤花”。
白化文、李如鸞二先生在《楹聯叢話·前言》中介紹過,《楹聯四話》是梁章鉅死(1849年)后,由其第三子梁恭辰編成。既然目前尚無別的反駁證據,那么此說較為可信。
鄭板橋此聯可能不止一次書寫,且有所改動,但是他沒有寫過不合格的對聯。
看來,賈平凹先生是既蔑視一般傳聞,又未嘗翻過楹聯必讀教材,“信手開河”,抓沙抵水,連“來、去”這種簡單對仗都任意竄改,給對聯界造成不必要的混亂。賈先生曾經把《牡丹亭》的唱詞“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改作“良辰美景天,賞心樂事家”,當成對聯伙同其他一些不合格“春聯”發表,曾經遭到楹聯界的嚴厲批評;不過他似乎從未檢討過,仍然我行我素……
謹防“硬傷”
《中國對聯大詞典》第410頁“名勝類·寺觀”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凌云寺(上海)
萬戶侯何足道哉,顧鳥帽春鞋,難得津梁摩大佛
三神山如或見之,問黃鶴赤壁,何如鄉郡挾飛仙
──郭蘭石
[簡注]在上海嘉定,為蘇東坡讀書處。
讀后深深不解:中國楹聯學會這個國家一級的學術組織主編的大型楹聯工具書,照理該算是“樣板書刊”了,怎么僅此一段文字就會出現如此多而重的“硬傷”呢?
請看聯人必讀的楹聯專著《楹聯叢話》卷之七有文字如次:
四川嘉定府城外有凌云山,山下有凌云寺,為坡公少年讀書處,有樓,塑坡公少時像。……樓中有郭蘭石學使尚先題聯云:
萬戶侯何足道哉,顧烏帽青鞋,難得津梁逢大佛
三神山如或見之,問黃樓赤壁,何如鄉郡挾飛仙
(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誤植“問”作“間”。“鞋”用“從革,奚聲”的“鞵”。)
兩相對比,我們發現《中國對聯大詞典》所載,至少有三處“硬傷”:即誤植“烏帽”為“鳥帽”,“逢大佛”為“摩大佛”,“黃樓”為“黃鶴”;至今未見校訂更正。仔細分析,那后兩字不一定是“誤植”,可能是“誤編”,因為根據文意只有用“逢”才合情合理;再說如果原稿是“逢”,排字者也不至于看成形體相差甚遠的或者字音相差甚遠的“摩”字。上聯“帽”是仄聲,懂得對聯格律的人,誰都知道下聯這里該用平聲字,不至于用仄聲的“鶴”去代替平聲的“樓”。
至于把“樂山凌云寺”硬劃給“上海”,這顯然是編者本身歷史地理知識缺欠造致。一個負責任的編者,只要查查辭書,就知道我國古代有兩個地名叫“嘉定”,一是縣名,原在江蘇,后劃歸今上海市;一是府名,在四川,治今樂山市。《楹聯叢話》已經講得十分清楚了。
鑒于楹聯書刊(突出的有梁石販賣的《中國對聯寶典》)中錯誤屢出,而且極少有更正之舉,故再度建議中國楹聯學會認真把好對聯書刊的質量關,責成負責編輯出版工作的同志注意學術組織的行為影響。即使是編輯一本小冊子,也要認真細致,在校對訂正方面多花點精力,哪怕事后發個更正勘誤也好。
“臣心如水”的化用
《楹聯叢話》卷十二云:“彭文勤公自書京邸春聯云:‘門心皆水,物我同春。’日下士大夫頗以出句為話柄:‘不過以“門心”二字強捏耳。’然古人此等句法甚多,唐賈島《題長江廳》詩有‘言心俱好靜’之句,意境正與相似,則用之楹帖,有何不可?況對句甚渾成乎。后汪銳齋儀曹德鉞仿其意云:‘臣心如水,王道猶龍。’則青出于藍,而不能青于藍矣。”
彭元瑞實際上運用“兩個詞性相同的詞,可以組合成為聯合結構”的辦法,從“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這兩組詞語中各選一個名詞,組成聯合詞組,表達并列的兩個概念。這種創新理當肯定。梁章鉅也是使用了“結構分析”的方法(盡管他當時并未也不能使用這類名詞術語),舉出實例分析評定,同樣是創新。
梁大師批評一般拘泥字面,以為“門心”二字不文的說法,引賈島詩句的“言心”為例,雖未明確點破,其實已經暗示這里當視為并列結構,意境相似,且渾然天成;既已有先例,當然可以推廣。其實我們今天學過漢語知識的中青年都可以理解:“言心俱好靜”中“言心”是聯合結構作主語。“門”與“心”各取自“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以兩個名詞構成聯合結構作主語,再與“齊物我”的“物我”相應對仗,自是典型的“結構相應”。
梁氏批評道,后汪銳齋仿其意云:“‘臣心如水,王道猶龍。’則青出于藍而不能青于藍矣。”蓋汪聯用偏正結構“臣心、王道”,雖然脫胎前者,對仗工穩,從意境分析,卻是墨守成規,并無創新。
朱應鎬《楹聯新話》引顧公燮《丹午雜記》(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本作“顧丹午《雜記》”,疑有誤。──筆者)云:“商邱宋牧仲犖撫吳,修滄浪亭,作聯云:‘共知心似水,安見我非魚。’一夕,或改‘水’為‘火’,‘魚’為‘牛’,以暗合公名。公聞之大笑,亟命撤去。”
清代江蘇巡撫宋犖在任上,培修了名勝古跡的建筑物。他喜愛楹帖,自撰一聯懸掛于滄浪亭。上聯引用典故“臣心如水”(“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見《漢書·鄭崇傳》),其意在表示自己心地純正,廉潔奉公。下聯化用莊子之言(莊子曰:“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強調我行我素,自得其樂。當然此聯與《滄浪歌》(見《孟子·離婁》:“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的主題還是切合的。
那不知名的忒有幽默感的“好事者”所作改竄,非常出色。“共知心似火,安見我非牛。”尾字橫嵌“火牛”,無異讓宋犖以自己的話給本人“定性”。(戰國時期,齊將田單集千余頭牛,披五彩龍文,角束兵刃,尾束灌脂薪芻。夜半驅牛出城,而焚其尾,牛被燒痛,直沖燕軍;齊軍遂大敗之。)讀者不妨想想火牛被焚時的具體感受。這般點竄十分巧妙,倍增詼諧,無怪宋犖也被逗樂了。
再說“葭莩”的結構
梁章鉅大師在《浪跡三談》卷三有《葭莩》篇,剖析實例,從結構角度(非惟“字”、“詞”)討論對仗之特點。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古人不可能使用后人創立的名詞術語,也不可能系統地作語法分析,但是從一些具體實例的闡釋中,我們完全可以體會到,他們已經開始自發地使用語法分析去解釋語言結構的問題。余多年來主張“以‘結構相應’代替‘詞性相同’”的對仗分析法,其實暗合前賢的意思。現申梁氏之說如次。
那位代梁作應酬筆啟者以“葭莩”對“桑梓”,自夸其工,不滿意梁氏“此不過常用語料,工則未也”的評價。于是大師有如下一番告誡他的議論。
首先說“葭莩”出自《漢書·中山靖王傳》:“今群臣非葭莩之親,鴻毛之重。”注:“葭,蘆也。莩者,其筒中白皮至薄者也。”梁氏指出“以鴻毛為對,則二字非平列可知”。按,“非平列”值得重視,那是就詞語結構而言的,即大師已經肯定“桑梓”二字是平列結構,而“葭莩”非平列結構。論據如前引文,“鴻(之)毛”與“葭(之)莩”都是偏正結構,故曰“非平列”。“平列”即現代漢語所謂“并列”結構、“聯合”結構也。既然結構不相應,所以批評道:“此對并未妥,何工之有?”
接著大師引前人文字經用者:蔡邕《讓高陽侯表》:“事輕葭莩,功薄蟬翼。”魏徴《為李密檄郇王慶》:“預占磐石,名在葭莩。”溫庭筠《書懷》詩:“浪言輝棣萼,何意托葭莩。”引用對文,指出“葭莩”與分別用在相應位置上的“蟬翼”、“磐石”、“棣萼”對仗,都“非平列”,也不言而喻。按,梁氏利用對文分析音義、結構,雖未使用現代語言學術語,業已說明問題。
最后又舉東坡詩“人生百年寄鬢須,富貴何啻葭中莩。”指出“著一中字,極為明白。”按,此例證明“葭莩”二字中間可以嵌入字詞,可知其“非平列”結構。讀者自可舉一反三,斷定“桑梓”中間不可“著一中字”,明白兩者結構不可等同,故以“葭莩”對“桑梓”,“此不過常用語料,工則未也”。多方求證,反復解釋,不以孤證論斷,更令人信服,是為不失學者身分。
反顧今之論者,口口聲聲奢言“放寬聲律,不講平仄”,“驅使形式,服從內容”,惟“破格”獨尊,卻不舉實例,不加闡述,不作討論,可乎?何不效法前賢,就一個具體問題,舉出實例,針鋒相對、條分縷析地討論討論呢!
“(仄仄)平平仄平仄”句式
王力先生分析五言句為“頭節—腹節—腳節”,指出七言句只是在此基礎上加個“頂節”而已。準此,我們用“(仄仄)平平仄平仄”兼表這兩種有關聯的句式。本文一題二論,既說“平平仄平仄”(年方服官政)句式,又說“仄仄平平仄平仄”(燈火萬家祝生佛)句式。(文中例句見《楹聯叢話》)
這種句式特點是:“頭節”落在平聲,“腹節”又仄(必須是仄)平相連,出句與對句腹節偶位字“兩平相對”,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句式的變體。如“高文有風雅,新渥照乾坤”、“文章自娛戲,忠義老研磨”出句均為“平平仄平仄”;“千種相思向誰說,一生愛好是天然”、“(燭問燈云:)靠汝遮光作門面,(鼓對鑼曰:)虧儂空腹受拳頭”,出句均為“仄仄平平仄平仄”。它經常被詩人聯家使用,所以張中行先生認為可以視同律句正格。不過一般都把它用于詩歌的出句(上聯)或下聯首句,而不用作對句(下聯)或上聯首句。
以下三類句型不能與“(仄仄)平平仄平仄”句式劃等號:
1.五言的“1-4(2-2)”句式(頌-無量壽佛,作-中興名臣)和七言的“3-4(2-2)”句式(年少已-豪情蓋世,功成則-高揖歸田),這是正格,但屬于“非律句”。
2.按規矩在非偶位字位置使用“可平可仄”的手段處理文字,將“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變為“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如:“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合乎“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既講究當句內音節交替,又保持上下句平仄相對,(出句與對句腹節偶位字并未“兩平相對”)仍屬于正格佳構。
3.聲律失調的句子,如:“酒香文明閣”(仄平平平仄)和“虎嘯驚百獸”、(仄仄平仄仄)“何須別處尋福地”(平平仄仄平仄仄)和“同舉金樽邀明月”(平仄平平平平仄),“二四六不分明”,顯然不合音節交替,未經錘煉加工,不是正品。
筆者曾經摘抄《楹聯新話》卷五《慶賀》類的37副五七言對聯和55例五七言分句(二者聲律沒有差別),總計92例作分析(節省篇幅,不錄具體聯文)。分析結果:五言句式中正格24例,“平平仄平仄”3例,聲律失調1例。七言句式中正格57例,“仄仄平平仄平仄”4例,聲律失調3例。從統計數字看,正格始終是多數,占總數的88%強。“平平仄平仄”和“仄仄平平仄平仄”句式占7.6%強。聲律失調占4.3%強。這說明懂得聲律的聯家選擇句式確實有所側重,不是信手拈來。
類似的律聯還有:“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雙飛兩虹影,萬古一牛心”、“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早見詩篇滿吳郡,行看草制出東坡”。至于《叢話》未對此類句式作具體分析,極大可能是因為,這些常識理應在發蒙階段學習掌握,值不得“小題大做”;但今人未必盡知,所以專題分析,以增見識,實有必要。例如:
碧血|丹心|彪青|史
仄仄平平平平仄
紅顏|白發|展宏|圖
平平仄仄仄平平
此聯出句不合“仄仄平平平仄仄”要求,第六字青對鴻失對,青與心失替。
其實可以用“仄仄平平仄平仄”句式,“碧血丹心照(耀、寫、續)青史”則可。
不該信口開河
梁章鉅的信口開河表現在《楹聯叢話》卷之十二:
……(鄭)板橋曰:“此難對。昔契丹使者以‘三才天地人’屬語,東坡對以‘四詩風雅頌’,稱為絕對。……”
此說未曾注明出處,不知是否鄭燮原語。但是“三才天地人”(平平平仄平)與“四詩風雅頌”(仄平平仄仄),僅僅尾字相對而已,其余則平對平,仄對仄,的確不協聲律。
馮夢龍《古今譚概》引岳珂《桯史》云:
……元祐初,東坡復除翰林學士,充館伴北使。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無能屬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曷先以此復之?”使如言。使方嘆愕,坡徐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閟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為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其不意,大駭服。
這段文字是宋人筆記,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但是讀過此書者甚少,而傳說東坡故事者往往只談其初選的對句。(不但如今一些對聯書刊和對聯詞典,甚至中華書局出版的《蘇軾詩集》所附錄“聯句”抄錄的對句也只是“四詩風雅頌”,同樣以訛傳訛。)鄭板橋和梁大師都沒有讀過岳珂《桯史》,所以無法正確敘述東坡自己難倒遼(契丹)使的對句。再說,梁氏之錯誤還在于不辨正文與附記,胡亂編造東坡屬對故事。其68歲所輯的另一對聯專著《巧對錄》(據岳麓書社1991年點校本)云:
宋與遼交歡,文禁甚寬。……(以上文字大體與《古今譚概》相同,從略)旋復令醫官對曰:“六脈寸關尺”。遼使愈悚然,既而請曰:“學士前對究欠一字,仍請另構有語。”適雷雨大作,公云:“‘一陣風雷雨’,即景可乎?”遂大敬服。
故事固然精彩,可惜杜撰畢竟經不起檢驗!《古今譚概》原本有兩筆馮夢龍的附記:
近張幼于以“六脈寸關尺”對,亦佳。(馮夢龍所謂“近”,當是明人。)
震澤吳聞之翰林善作對,每言“日月星”為天文門,“風雅頌”殊為假借,更對云:“一陣風雷雨”。見者謂有神助。(各自研究與東坡毫無干系!)
只要實事求是,我們就會發現梁大師借以生編硬造的“原材料”,或許就可以不再盲從附和了。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中國楹聯學會顧問、
中南大學楹聯研究所研究員